
“(北青艺术)办公室”创作于艺术家王友身对北京中间美术馆“自我批评”展(2017.5.27-9.17)的一次回应,他以“艺术的名义”自上而下地启动了此次北青系统的“自我批评”,并召集了身边的同事以业余的“北青艺术家”身份,以艺术为媒介记录和展现了自1992年至2017年的日常工作和艺术工作的文献、档案、作品和现场,共同完成了这次过程性的展示项目。这一项目源于艺术家1992年的一份年度工作总结《自我批判与进入规则》,它是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界市场化初期的“北京青年报现象”,以及当时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状态的反思和自省。在2017年这一时间节点,北京青年报/北青传媒与其他国际传媒集团一样面临着关乎生存的数字化与多媒体变革的市场迭代,王友身试图以艺术事件的方式,完成一场冷静的、共同的“自我批评”。
王友身通过将北京青年报社的办公室现场搬迁至中间美术馆展场,将原本的办公室重置为“美术馆”空间,通过组织媒体和当代艺术两个平台的对话和身份置换,艺术家王友身在媒体所象征的日常和日常话语系统与当代艺术所象征的野生和开放状态之间建立起一条通道,从而实现对该命题的反思。
1.而今天,我们继续进行一种“自我批评”式的思考,对于这样一场变革里的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或许会有一种精神的启迪。
2.《(北青艺术)办公室》既是具体的、私人的,也有社会属性在里面。
3.我要全力以赴打通美术馆、报社这两个系统,置换两个有着不同系统属性的空间。
4.在美术馆和办公室之间,事情如何通过记录、编辑、制作、介入而不断演变着,并“自我更新”为一种开放的艺术和工作平台?
在2017年中间美术馆的“自我批评”展中,一道虚线将展厅化为了两个空间:一侧是展厅;另一侧则是46平方米的“(北青艺术)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中,办公桌上摆放着《北京青年报》和《北青社区报》;会议桌上放置着版样;办公室前方的电视机中播放着“北青报”的新闻美编;挂钟上的时针写着“自我”,分针写着“批评”。艺术家王友身的“办公室”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真实的工作场景打造,与此同时,所有的物件都经过了艺术家巧妙的安排、设计和布局,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这样,“当办公室出现在展厅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件艺术品。”


王友身,(北青艺术)办公室,“自我批评”展览现场,北京中间美术馆,2017

王友身,(北青艺术)办公室,北京青年报大厦,2017
展览期间,艺术家王友身突然收到一个报社文件,内容是他的办公室空间使用面积超标,需要缩减到12平米。在接到这个通知以后,艺术家把美术馆的办公室空间也缩成12平米,富裕出来的空间变成了公教区域。

王友身,(北青艺术)办公室(改前46平米),表、照片、录像、挂历、文档尺寸可变,1992-2017

王友身,(北青艺术)办公室(改后12平米),表、照片、录像、挂历、文档尺寸可变,1992-2017



王友身,(北青艺术)办公室,“文化符码——王友身的旅程”展览现场,北京中间美术馆,2022
(北青艺术)办公室
延展项目
“自我批评”展览期间“(北青艺术)办公室”相继推出了“北青艺术商店”、“北青课堂”和“北青美术馆”三个延展性的项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艺术与现实之间连接的可能性。
在北京青年报大厦的“北青美术馆”空间内,4位“北青艺术家”在此举办了个展。王友身在设问美术馆与办公室之间,事情如何通过记录、编辑、制作、介入而不断演变着,并“自我更新”为一种开放的艺术和工作平台?同时,参与其中的“北青艺术家”既是从事媒体业内美编与设计的媒体人,也具备专业美术背景和创作经历,这种双重属性也对应了王友身试图探索的关于边界和系统的问题。
司徒晓春个展【梦境计划︱家庭旅游】2017.6.27-7.26
在中间美术馆的“北青办公室”则开展了两场“北青课堂”。在这个项目中,《北京青年报》的资深编辑与高管们来到中间美术馆“(北青艺术)办公室”面向普通观众授课,分享职业的媒体经验与和案例。在短暂的几个小时之内,职业媒体的内部培训课程向有限的公众开放,中间美术馆的一隅转换成了一间开放的北青艺术办公室。
北青课堂(升级版):做一天媒体人


“北青课堂:媒体是什么?”,北京中间美术馆,2017
“北青艺术商店”是“(北青艺术)办公室”的衍生空间,呈现的是北青艺术家们的日常工作,是北青集团企业文化的外化物。每件限量版作品都会有一份书面的“北青艺术—作品证明”,内含作品编号、图文信息、艺术家亲笔签名和“北青艺术”钢印印章等。它是证明该作品真实有效的唯一“身份证”。

王友身,北青艺术商店,“自我批评”展览现场,北京中间美术馆,2017


王友身,北青艺术商店,“文化符码——王友身的旅程”展览现场,北京中间美术馆,2022
编辑:蒋永真、易若扬
正在展出 What's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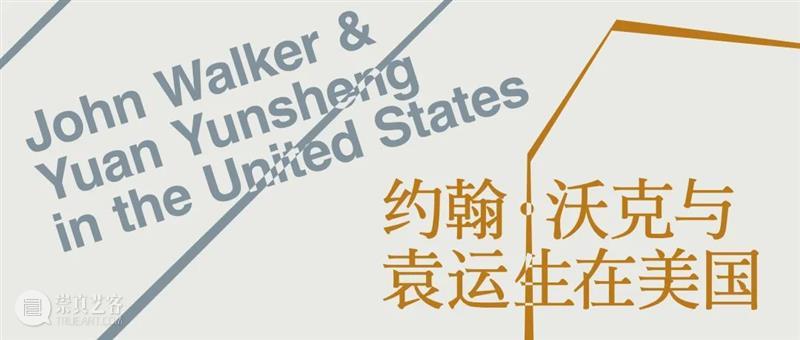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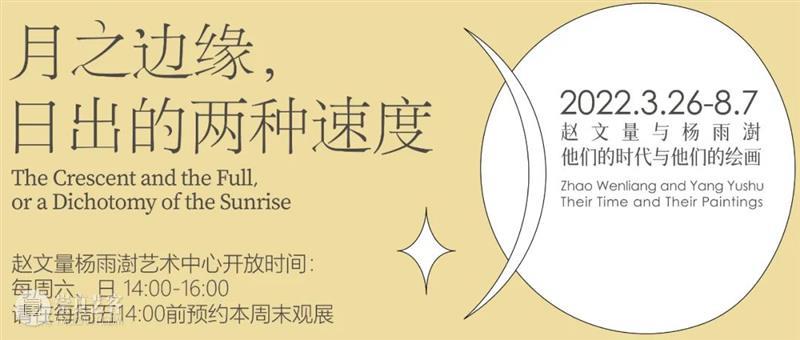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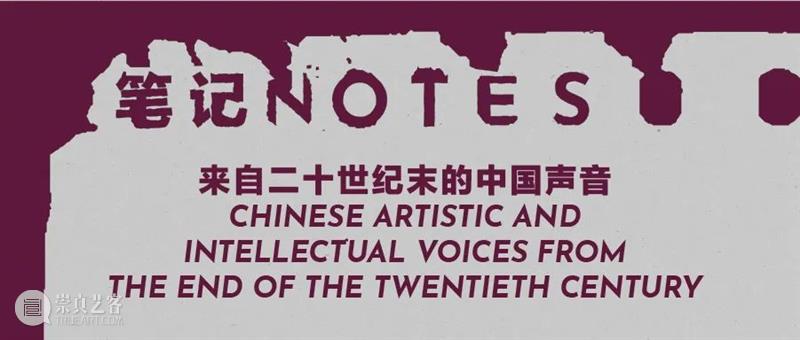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