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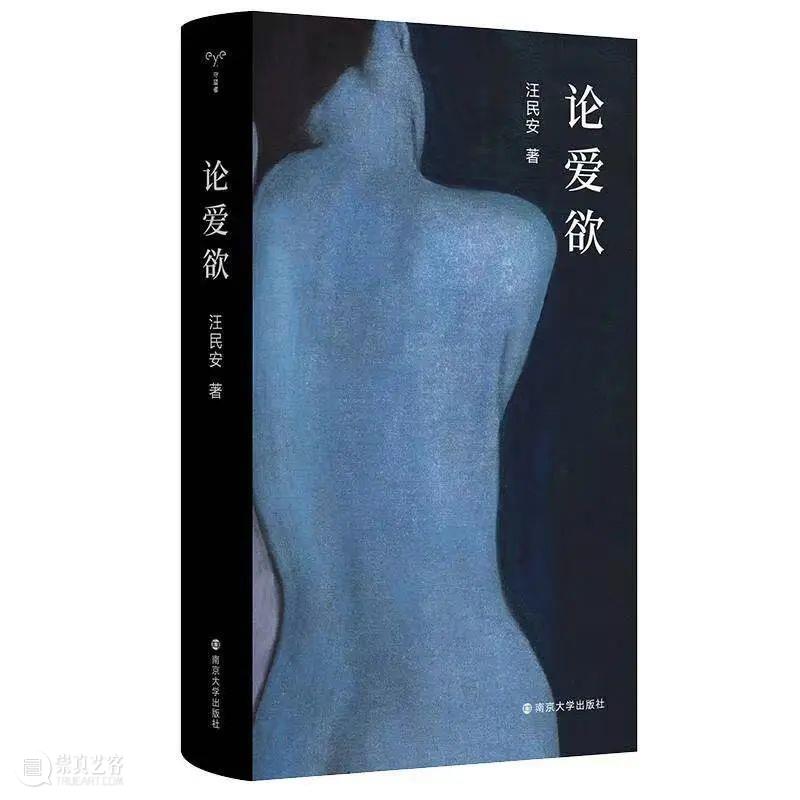
论爱欲
汪民安著
ISBN: 9787305254109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
按:汪民安老师的新著《论爱欲》以“转向”为界,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爱欲的谱系为主线,讨论了古希腊时期的真理之爱、基督教时期的神圣(上帝)之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尘世(身体)之爱。下篇围绕爱欲的政治,从承认、事件和奇遇三个角度讨论了现代的爱欲思想:爱意味着彼此的承认,意味着导致生命发生断裂的事件,意味着针对普通文化和习俗的冒险。
目录
上篇 爱欲的谱系
第一章:真理之爱
第二章:神圣之爱
第三章:尘世之爱
转向
第四章:爱的几何学和地理学
下篇 爱欲的政治
第五章:承认
第六章:事件
第七章:奇遇
附录:论友谊
尘世之爱
本文摘选自该书第三章
《十日谈》中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以小说人物之口来讲述的。这是一个故事的套叠叙述。薄伽丘叙述了一个讲故事的场景:故事中的十个人物围坐在一起,他们在轮番讲故事,也因此在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的听众之间不断地转换自己身份。当一个人讲述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听众,都沉浸在故事中,都在故事讲完后有自己的特殊反应,或者沉重或者放松或者唏嘘或者大笑。《十日谈》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讲述这些性的故事组织了一个共同体的生活。人们过的是一种讲故事的生活,人们生活在文学之中。正是这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生活将现实生活挡在外面。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遭受着瘟疫的侵袭,布满着死亡的巨大阴影。死神盘旋在所有人的头上,随时都可能伸手扼住你。死,是此刻此地的爱和性的深厚布景。我们可以说,爱,或者说,讲述爱欲的故事,沉迷于爱欲的故事之中,生活在爱的文学中,就可以推开这个死亡幕布,就可以遗忘死亡,回避死亡,将死亡阻挡在外。这再一次是对尼采的提前呼应,尼采曾经说过,古代人只有生活在狄奥尼索斯的悲剧中,只有生活在虚假的文学生活中,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和野蛮,只有沉浸在希腊悲剧中的生活才是值得一过的生活,也才是能过得下去的生活。狄奥尼索斯的悲剧生活,就是痛苦和性相互强化的生活。狄奥尼索斯是痛苦之神,也是性的狂欢之神。痛苦需要性来抚慰,性需要痛苦和绝望来加以反向强化。希腊悲剧造就了一个虚构的狂欢世界来克服死亡的狰狞。薄伽丘的爱,或者说,他在《十日谈》中津津乐道的性爱,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对死亡的抚慰和克服。只不过这不是狄奥尼索斯那样带有生育意味的性,也不是需要痛苦从反面来强化的性,不是受到虐待的处在一种巨大折磨中的性,这是单纯的直接的欢乐的令人捧腹的性,这样的性并没有道德上的挣扎,只有将它置放在谈论它的背景的情况下,只有将它和瘟疫的爆发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它才会注入悲凉和虚空的要素,围绕它的笑声是度过瘟疫和死亡威胁的无奈之笑声。但,越是悲凉和虚空,越是无助和绝望,越是需要性。
如果说,苏格拉底和基督教都是通过爱来达成不朽从而来抵制死亡的话,那么在薄伽丘这里,似乎是通过沉浸于性爱的游戏追逐来忘却死亡。这是爱和死亡的一种新的关系:沉浸在爱欲的故事中,沉浸在爱的情景中在爱的感同身受中在爱的经验中,就可以遗忘死亡,忽视死亡、抚慰死亡和逃避死亡。也就是说,哪怕死亡迫在眉睫包围了我弥漫了我即将席卷我,但我只要现在爱了,我就不会想到死亡;只要我被爱所主宰,被性爱的目标以及它带来的欢乐所主宰,我在性爱的幻象中或者性爱的巅峰中,我就远离了死亡;或者说,如果我要死了,如果我知道我马上要死了,我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体验性爱,就是不顾一切地体验性爱,享受性爱。性爱可以吞没、掩饰、忘却和对抗死亡。性如此地自主和封闭,以至于它会忘却一切,它不仅让自己忘却自己的死亡,也会让自己忘却他人的死亡。无论是忘却他人将临的死亡还是忘却他人已经发生的死亡。当他人的死亡发生过了,当他人的死亡让幸存者陷入痛苦的失去状态时,性也是解除幸存者的痛苦的方法。在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电影《反基督者》中,正是因为父母沉浸于自己的性爱而导致了对儿子的忽视致使儿子坠落而亡,为了冲淡这样的失子之痛,母亲试图通过沉浸于性来疗愈这样的痛苦。性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试图导致死亡之痛的康复。性试图从各个方面驱逐死亡。性爱的快乐是死亡的解毒剂。反之亦然:“只要心中还记着死亡,我们在现世的诸事中便永远品尝不到欢乐。”《十日谈》中的人们绝对地沉浸在爱的故事中,他们听这些故事,享用这些故事,他们是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共在,而不是和现实生活共在,不是和城中的瘟疫和病人共在,他们这么做就是遗忘现实遗忘死亡从而抵抗死亡。如果现在的这一天是人的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故事就是人能经历和听说的最后一个故事的话,那么,这最后一个故事就应该是性的故事,最后一个经验就应该是性的经验,最后一天就应该是性的迷狂的一天。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最后的经验最后的故事最后的一天,是真理的经验,是获取真理的故事,是学习真理获取真理的一天。获取了真理就可以死去。这是希腊版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最后的死亡真理是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对薄伽丘来说,获取了性就可以死去。如果有什么好的死亡方法的话,如果有什么死亡真理的话,也许就是通过性来交换死亡,性可以补偿死亡,性是死前最后的人类礼物——这也是薄伽丘的最后真理。
这也是巴塔耶的真理。不过,对薄伽丘来说,在性中死去是要忘却死的苦痛和恐惧,是避免死亡的折磨和残酷。但是,在巴塔耶这里,在性中死去是要肯定死的苦痛。性和死不是抵消的关系,而是相互强化和交织的关系。死的苦痛强化了性的快感。死的折磨将性推到了享乐的极限。性和死是以张力的关系结成一体。对巴塔耶来说,这同时是对死和性的最高强化,死的狂暴激发了性的狂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性和死的双重圣化。至高的性就是至高的死;它们是仇视的亲密伴侣。这是巴塔耶的一切矛盾情感的核心之所在。矛盾经验,这也是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寓言。如果说,在狄奥尼索斯那里,濒死的苦痛和情欲的欢乐的至高结合是生育的那一瞬间,而在巴塔耶这里,则是死亡的那一瞬间。像希腊人一样,尼采赋予诞生的时刻以最高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诞生,痛苦地诞生,轮回式地诞生;而巴塔耶从来不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一个萨德主义者,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地接近死亡,趋向死亡,趋向残暴和快乐交织在一起的死亡,这同时是亢奋和阴沉的死亡,是热烈和倦怠的死亡,是正午时刻的黑夜死亡。尼采的苦痛情欲能感受到生的快乐;萨德的苦痛情欲能感受到死的快乐,通向死亡之途也就是通向极乐之途。如果说,薄伽丘那种愉快而单纯的情欲通过16世纪提香的偶然传递而到达了18世纪的布歇(Francois Boucher)那里,而布歇则将这种情欲变得更漂浮更颓靡更迷幻。稍后一点的萨德开始了新的反向的沉重、尖锐和生硬的情欲哲学:一种容纳死亡而不是排斥死亡的情欲,一种和死亡拥抱也因此和痛苦拥抱的情欲,一种拥抱痛苦也因此迷恋暴力迷恋血腥迷恋恐怖的情欲。正是这样邪恶的情欲禁闭了他也解放了他,无论是空间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这种恶的情欲催生了一种痛苦和快乐纠缠不休的泪水,也催生了被禁闭的萨德这样的生命经验:“他特别地用不计其数的幻想来充实他的孤独:他幻想可怕的尖叫和流血的尸体。只有想象那不可容忍的事情,萨德自己才忍受了这样的生命。在萨德的狂躁中,有一场爆炸的对等物:既把他撕碎,又无论如何令他窒息。”这种矛盾、尖锐、流血和撕裂的情欲,通过尼采的隐含过渡最终传递到巴塔耶这里:“一种无限维持着的尖锐而永恒的张力,从对我们进行限制的关注中诞生。……在一场无尽且不安的旋风中,欲望的诸多客体被持续地推向折磨和死亡。那唯一可以想得到的结局,就是刽子手这样的可能欲望:他自己想成为酷刑之牺牲品。在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萨德之意志里,这样的本能在萨德要求连他的坟墓都没必要保留的时候,达到了其顶点:它引向一种愿望,即他的名字应该‘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巴塔耶没有让萨德消失。正是他重新发现了萨德。他不仅摧毁了死和爱的界线,他还摧毁了神圣之爱和肉体之爱的界线。如果说,奥古斯丁和薄伽丘分头占据这两端并且让这两端势不两立的话,那么,巴塔耶则神奇地在这两种爱中发现了重叠。神圣之爱和身体之爱可以互换,肉体的即是神圣的,神圣的即是肉体的。兽性的就是宗教的,宗教的就是兽性的。对他来说,神圣的兽性,兽性的神性,是爱的共同特质。在它们的高潮时段,它们都自我迷失,它们都遗忘现实,它们都失去理性,它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哭泣,它们都充满颤栗:身体的颤栗交织着灵魂的颤栗。颤栗是爱欲高潮的极限运动。在爱欲的高潮时刻,爱的对象就是一个神圣者,他(她)的身体发出了神圣之光,他(她)让面前的对象获得一种宗教般的迷狂体验,身体成为一个无限的感恩客体。对身体的爱欲体验就是神圣体验。反过来,神圣的宗教体验难道不是爱欲的身体体验吗?但丁在看到上帝的刹那不是有一种迷狂的不能自已的高潮吗?它不是抵达了一种绝对的爱欲峰巅吗?如果说,奥古斯丁神圣之爱绝对地贬低身体之爱,但丁则重新召回了身体之爱,并将它纳入到神圣之爱的卑微的根基上,就像柏拉图将身体之爱植于知识之爱的卑微根基一样。而薄伽丘则将身体之爱取代了上帝之爱,这是爱的秩序和等级的翻转,虽然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摧毁神圣之爱,但这是尼采式的翻转的前身。而巴塔耶与其说是像尼采那样对这两种爱进行翻转和颠倒,不如说,他将它们融为一体。在他这里,没有爱的等级,只有爱的混淆;没有爱的区分,只有爱的共同经验;没有爱的价值尊卑,只有爱的共同的情不自禁的身体颤栗。爱,穿透了野兽和上帝的界线。
萨德的名字只是被19世纪的欧洲文化短暂地抹去,他现在因为有了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福柯和罗兰·巴特这样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重新浮现。尽管横亘着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沟壑,但他们都是邪恶的“萨德的邻居”。除了拉斯·冯·提尔外,萨德也在大岛渚(Nagisa Oshima)、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金基德(Ki-duk Kim)、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电影中赫然显现。大岛渚的情欲高潮终结于暴力的屠戮,在欲望的客体死亡之际,这种情欲还无法停下来,只能以刀割阴茎的方式,以二次死亡的方式,以一种永久占有性器官的方式,保持着它的轮回冲动;金基德让人的舌头静止从而让电影沉默,在沉默的银幕上面,只有阴茎在进行无休止的切割、重生和毁灭的莫比乌斯循环;柯南伯格的情欲巅峰依赖于汽车一次次地毁灭性的呼啸撞击,依赖于钢铁机器对柔软身体的一遍遍撕毁,情欲只有在舔自己的身体伤疤的时候才分外激动;而帕索里尼则用萨德改写了薄伽丘,薄伽丘轻浮和甜腻的情欲故事场景一旦被萨德化,就变成了一个暴戾、怪异和恐怖的情欲空间。在这个充满颠倒、叫喊和喧哗的空间中,爱若斯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这融合了喜悦和苦痛,纯洁和肮脏,感激和悔恨的情欲,已经超越了萨德的痛苦宣告而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忍不住倾泻出来。这是萨德在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的遥远回声:
“我根据爷爷的恋爱历史、根据我父亲的爱情狂澜、根据我自己的苍白的爱情沙漠,总结出一条只适合我们一家三代爱情的钢铁纪律:构成狂热的爱情的第一要素是锥心的痛苦,被刺穿的心脏淅淅沥沥地滴答着松胶般的液体,因爱情痛苦而付出的鲜血从胃里流出来,流经小肠、大肠,变成柏油般的大便排出体外;构成残酷的爱情的第二要素是无情地批判,互爱着的双方都恨不得活剥掉对方的皮,生理的皮和心理的皮,精神的皮和物质的皮,剥出血管、肌肉、蠢蠢欲动的内脏,黑色的或者红色的心,然后双方都把心向对方掷去,两颗心在空中碰撞粉碎;构成冰凉的爱情的第三要素是持久的沉默,寒冷的感情把恋爱者冻成了冰棍,先在寒风中冻,又在雪地里冻,又扔进冰河里冻,最后放在现代文明的冰柜里冻,挂在冷藏猪肉黄花鱼的冷藏室里冻。所以真正的恋爱者都面如白霜,体温二十五度,只会打牙巴鼓,根本不会说话,他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已经不会说话,别人以为他们装哑巴。
所以,狂热的、残酷的、冰凉的爱情=胃出血+活剥皮+装哑巴。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不息。”
这是萨德主义在今天尚不确切的委婉胜利。如果说,苏格拉底为了真理之爱而不惜一死,彼特拉克为了灵魂之爱而不惜一死,薄伽丘则是为了身体之爱而不惜一死。而在萨德那里,身体之爱就是身体之死。为了获得爱,不必像前人那样浮夸和做作地以死作代价,而是在死中去爱,在爱中去死。性爱,在萨德这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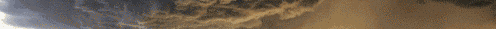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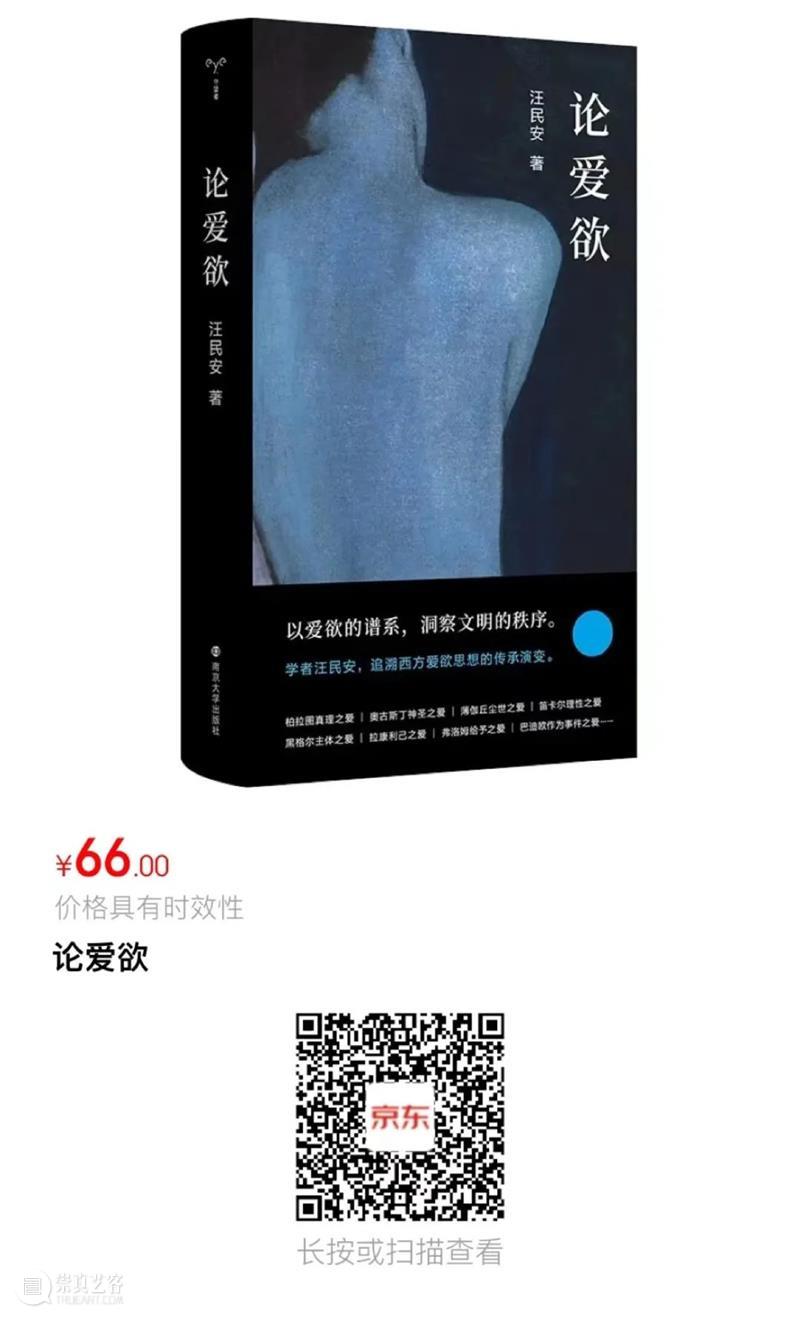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