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艺术和新如画主义
西德尼·提利姆丨文 王丹华丨译
选自《白立方内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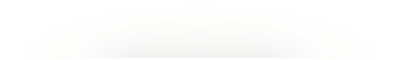
1964年,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写道,普通媒体和绘画已经不足以作为艺术当代性表达的媒介了,他呼吁产生一种“具体性、具有实际材料、实际颜色和实际空间力量”的艺术。近期,在纽约杜文画廊(Dwan Gallery)的大地艺术展将随后运用“实际”媒介创作的艺术推向了高潮。大地艺术是这样的作品,或用土壤完成,或在地表某处画线、打洞,以环线进行切割(展览展出了在各种地方进行的大地艺术的图片)。在这种艺术中,世间万物均可成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只要人们原原本本地对它进行使用(而非象征性使用)。同时,从所有这一切来看,很难有现代主义的未来似乎更成问题。
大地艺术代表了一种对真实大自然独特的、具有观念性的介入,并非一种偶然,几乎展览中的每位艺术家在前不久都展出了“极简”艺术作品。无论是将一片风景变成艺术或将物体艺术(object-art)变成一种风景,还是将物体和风景以一种美学和原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丹尼斯·奥本海姆(Dennis Oppenheim)计划在明年七月在尼瓜多尔的一座活火山附近的麦地里,开辟十里宽的环状地带,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则在一间画廊里,放了一堆黑土、管子、毛毡,一大堆胶状的工业油脂。其他以风景体验进行的创作,无论是图文说明还是在展览现场出现的作品,包括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穿过西部的一片荒地画下的巨大平行线,慕尼黑一家画廊满墙的土,也是玛利亚的作品。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于树林中的匆匆砍伐在灌木丛中蔓延开来;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在森林和太阳灼烤的泥地中挖坑。克里斯·奥登堡(Claes Oldenburg)在一个塑料容器里放了一些污泥,据说是要和虫子一起种下去。另外有影片表现了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后面挖洞填坑的行为。
我认为与具体的大地艺术和通常所说的实际媒介艺术有关的是20世纪的“如画”(picturesque)一说。如画主义本是一种风景理论,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英格兰为甚。就如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如画是指以看画的方式去看风景。人们从如画般的美丽角度去品味风景,同样的效果产生在绘画中就受到高度推崇。换言之,这是观看自然的一种方式,场景极为重要。大量表现如画般旅行的文学作品由此产生。
极简主义艺术同样也依赖于环境。无论是工艺的、轮廓鲜明的,还是地质学、更柔软一些的,极简主义是一种人工自然的形式,或者说,是人类打造的自然。它并不呈现具有艺术性的物品,而是一些能够创造某种场景而非一个空间的无用艺术品。极简主义观察者或极简主义物景(object-scape)之间的关系,类似一个有品位的人和他所欣赏的如画风景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特征激发了迈克尔·弗雷德,他轻蔑地用“夸张的戏剧性”这个词来形容极简主义者,如他所言,实在主义者(literalist)雕塑。在面对戏剧性作品时,观众不再是置身于作品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场景中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作品就为观众进行了“表演”。一些极简主义的场所只能从空中欣赏。另一方面,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参观帕塞伊克的“纪念碑”时,对现代的如画之境进行了嘲讽,他携带着柯达傻瓜相机就如老行家带着素描本一样。史密森写下了自己的旅行见闻并且用图片记录下来,里面有工厂沙坑、排水管、工业废气等。
就如在早期的和原始的如画中,判断和选择“场所”或“非场所”(史密森这样称他在画廊展示的物品)的价值或风格完全源于艺术。对现代主义艺术透彻的了解因此成为提纯的前提,其实际与直白的(literistic)如画是分不开的。例如,形状和构图或非构图的特征来自抽象的先例。一些是平面的,一些是直线的(海泽早期的环形,德·玛利亚的线条),一些是波普的(史密森的石头储藏箱和照片,他去帕塞伊克的旅行,奥登堡在中央公园的洞),其他的是以观念化的方式呈现的抽象表现主义(莫里斯的土堆)。大地艺术局限于与大地有关的作品,但是由于媒介美学的要求,所以并不限于地质范围,其他的艺术家也用其他的媒介创作,间或插入相应的与风景有关的创作策略。自对如画的狂热迷恋伊始,很多大地艺术都将软硬元素结合在一起,对处于艺术根本的形式上的一分为二(边缘VS大众)进行了重新归纳。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推论,极简主义产生了很多理论性写作,堪比早期如画的信徒和理论家们的写作。
但是如画不仅仅是自然和艺术中的风景理论。它是历史品味发展中不可小觑的插曲。虽然并未达到神圣境界,但却是理想化的替代品,它以其所萌发的伤感象征着高级艺术(high art)理想的终结。它以高贵的情感代替了多愁善感,发展成对自然的狂热迷恋,成为过于复杂的文明社会的一剂解药。同时,它也是对最高雅的品味的热爱。它初期的病态最终以19世纪早期规模上的全盘失败而臻于成熟(甚至浪漫主义也无济于事;现实主义对它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崛起是抵触的)。
作为如画之境在20世纪的表现形式,大地艺术意味着这一现代主义语汇过度熏陶所达到的一个程度。在探索重新恢复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它以直接运用“实际”媒介而达到过度提炼的程度,其运用的媒介涉及木头、金属、塑料、整个工业生产过程和普通的泥土。这样,作为一种可贵的原始主义,通过有意为之的乏味寻求新生,它就与波普艺术联系起来。就如波普艺术一样,只有当它确定了自身所欲扭转的风格化消磨后,方才发生效力。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者将品质的可能性限制到日益狭窄的艺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艺术脱离于形式主义这门被人们所认为的严厉的历史自我批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代替了他们自己的现代主义艺术史的历史——理论定义。应对当代风格问题的形式主义解决之道越来越少。于是,形式主义立场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的品质观与艺术文化是疏离的,已经变成了其他的手段,其中包括大地艺术中的夸张手法。现代重要的形式主义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深知现代主义愈演愈烈的动荡不安,他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里总结了一些可以维护抽象艺术的方法,文章名为《抽象艺术的危机》。他拒绝“危机”的定义,要求彩色绘画能够成为绘画抽象的继承者。文章结尾他这样说:
造画(picture-making)的一个未知的领域正逐渐散开(年轻的模仿者们尚无法追随),其将会足够宽阔博大而能容纳至少又一代的重要画家。
“至少又一代”:这是一个谦逊而几近简朴的宣言,就如格林伯格所言,现代主义结构日益式微。如今,即使是最好的现代主义抽象都不能从掠夺现代主义力量的脆弱中幸免。大地艺术在现代主义处于最低潮的时刻到来,这也预示了整个现代主义的虚弱。
通过定义,极端的事物变得太过强烈。只有通过非传统的过度简化和对被选择方的绝对依赖,极端之物才成为可能。这在革新中是有必要的,但当革命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被同化后,极端主义就变成了伤感的形式。在极简主义雕塑中,这导致了对艺术某一面(媒介)的过度信赖,而且进一步认为每种媒介都有其固有的、决定整件作品形状的属性。不利用媒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通过形状来控制它,我们依然会说出形状将如何产生。于是,极简主义造成了发明物的缺乏,当在创作中都是发明物时,却兼具粗粝生猛和精致考究的特征。
另一方面,伤感是一种解决方法并有其愉悦性。其是唯一可以解决某种问题的方式。极简主义寻求一种缺乏复杂性的复合体、一座没有局部的壮观纪念碑和一种对形式的“自然的”选择。从极简主义具有教化性的一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后色彩艺术里关于形状、色彩、规模的问题。从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与建筑的联系上,极简主义者中的风景主义者是新哥特类型的预言家,我们了解到一种对艺术和建筑、建筑和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的特殊渴望,它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欲望。在所有活动中,它都是非常神秘的,与对整个社会曾经共同体验的那种仪式般冲动的渴望多少是分不开的。但复兴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产生什么先例去提醒人们究竟什么丢失了。因为极简主义拒绝过去,它只能通过一种成为表现的替代品媒介去诠释这种冲动。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