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麻烦共存: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
[美]唐娜·哈拉维 著,仿物机游 Chthulu 译
译自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转载自公众号“仿物机游 Chthulu ”
序言
麻烦(trouble)是一个有趣的单词。它起源于十三世纪的一个法语动词意思为“搅拌”,“弄浑浊”,“干扰”。我们——在泰拉(Terra大地之母)上的我们所有人——生活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混乱的时代、麻烦和浑浊的时代。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同我们所有的傲慢物种相互回应。混乱的时代同时充满痛苦和欢乐—一个极其不公平的模式,充斥着对进程性(ongoingness)的毫无必要的杀戮,但也存在必要的复苏。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创造性的联系中制造亲缘,作为我们在拥挤的当下学会生死与共的实践。我们的任务是制造麻烦,去激发对毁灭性事件的有力回应。处置浑水,重建宁静的地方。在紧急时刻,为了创造下一代的未来,很多人试图让想象的未来变得安全,阻止未来的隐患发生,清除现在和过去来解决麻烦。与麻烦共存并不需要与未来时代建立这种关系,事实上,与麻烦共存要学会真正活在当下,而非在可怕或伊甸园般的过去同世界末日或救赎的未来之间摇摆不定,而是作为平凡的生物,缠绕于无数未竟的地点、时间、事件和意义的结构中。
克苏鲁世(Chthulucene)是一个简单的单词。它由2个希腊词根(khthôn and kainos)构成,共同命名了一种在受伤的地球上学会与生死麻烦共存,能够进行回应的“时间场所”。khthôn意思是现在,一个为了求新而开始的时刻,一个进行的时段。kainos指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指涉传统的过去、当下或者未来。在这一开端时期,没有任何事物坚持要抹除过去,或者,抹除未来。kainos完全可以继承、记忆、迎接和培育可能的存在之物。我听说kainos用来代表厚实、持久的存在,同菌丝一起引入了各种时间性(temporalities)和物质性(materialities)。
克托尼俄斯(Chthonic)[1]是地球上的生物,既古老又现代。我想象克托尼俄斯充满了触手、触角、指头、绳索、鞭尾(whiptail无需雄性动物繁殖后代的物种)、蜘蛛腿和极不规则的头发。克托尼俄斯在多种生物腐殖质中嬉戏,但不与凝视天空的人类往来。克托尼俄斯是最好的怪物;它们说明了地球的过程和生物的物质意义。它们还呈现了后果。克托尼俄斯是不安全的;他们拒绝和意识形态拥护者往来;他们不属于任何人;他们在地球上所有的空气、水域和地方以多种形式和多种名称扭动和繁荣生长;它们创造和毁灭;它们被创造和被毁灭。它们是其所是。难怪世界上伟大的一神论在宗教和世俗的幌子下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消灭克托尼俄斯。被称作人类世(Anthropocene)和资本世(Capitalocen)的时代丑闻是这些灭绝力量中最新近和最危险的。在克苏鲁世(Chthulucene)中彼此有力地共生共存,这可能是对人类和资本指令的激进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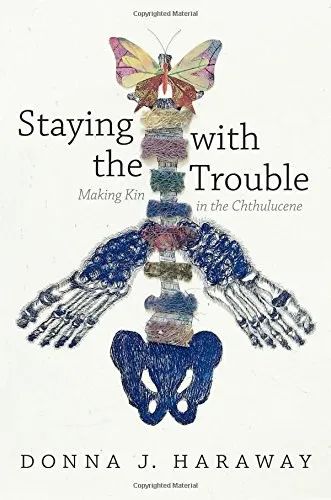
亲缘(kin)是一个野蛮的范畴,各种人都竭尽全力驯化它。制造亲缘,作为古怪的亲属,而不是与神(godkin)、与宗族和生物遗传的家庭结亲,或者说至少不是它们,这令许多重要问题变得麻烦,比如一个人究竟是由谁来负责养育。谁生,谁死,如何处于这一亲属关系而非另一亲属关系中?是什么塑造了亲属关系?其线路在哪里?连接了谁?又分离了谁?那又如何?假如在地球上繁盛的多物种,包括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和非人,它们能够有机会的话,必须要切断什么?又必须连接什么?本书一个无处不在的形象(configuration)是sf:即科幻小说、展望式虚构(speculative fabulation)、花绳图形(String figure)、展望式女权主义(speculative feminism)、科学事实等[ 注:这5个sf都以sf英文字母开头,故称sf。]。这一清单在接下来的页面中反复浮现,以文字和视觉图像,将我和我的读者编织进危险的状态和模式里。科学事实和展望式虚构彼此都需要展望式女权主义。我认为科幻小说和花绳图形具有三种虚构(figuring)意义。第一,在凝结和密集的事件和实践中杂乱地采摘纤维,我试图沿着它们所引导的线索,以追踪它们并找到它们的缠结和模式,这对于在现实和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中与麻烦共存中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小说是一种追踪的方法,在黑暗中沿着一条线索的方法,谁生谁死?为培育多物种的公正,该线索可能会如何发展?在一个危险的真实冒险故事中,这些问题变得更清晰了。第二,花绳图形并不是无形的痕迹,而是实际的事物,是恳求回应的模式和集合(assembly),它并非是它自己,而是与必须前进的人一起。第三,花绳图形正在传递和接收、制造和分解、捡拾线索并丢弃它们。科幻小说是实践和过程;它是在奇异的接力中彼此的“共同-生成”;它是在克苏鲁世中追求进程性(ongoingness)的一个形象。
关于人类世和资本世的恐怖,有两种反应,本书及“与麻烦共存”的想法尤其对这两种反应十分不耐烦。第一条很容易描述,我认为可以忽略,也就是说,对技术修复的滑稽信念,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技术将会莫名其妙地拯救它那顽皮但非常聪明的孩子,或同样的,上帝将拯救它那违逆但永远充满希望的孩子。面对关于技术修复(或技术-世界末日)的感人至极的愚蠢,有时很难想起,拥抱情境技术计划及其成员是很重要的。她们不是敌人;为了与麻烦共存,为了制造下一代的古怪亲缘,她们可以做很多重要的事。
第二种反应,较难以忽视,可能更具有破坏性:即游戏已经结束了,太迟了,尝试让一切变得更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复兴的世界一起工作和游戏,彼此相互积极地信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知道有些科学家,表达了这种苦涩的犬儒主义,即使他们实际上努力去为所有人和生物制造积极的差异。有些人自称为批判性文化理论家或者政治进步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实际上为多物种繁荣而工作和游戏的古怪联盟需要有充沛的精力和技巧,表现出一种明显“游戏结束”的态度会打击她人,包括学生,她们被许多种未来主义观念所影响。有种人似乎想象只有事情可以解决,这些事情才是重要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只有我和我的专家同事能够弥补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更普遍的情况是,有些科学家和其她阅读学习,并焦虑操心的人知道得太多了,这太沉重了。或者,至少我们认为,我们足以明确得出结论,在地球上以任何忍受方式进行的生活,真的已经结束了,而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临了。

《内共生:向 Lynn Margulis 致敬》(Endosymbiosis:Homage to Lynn Margulis)
图源:www.cybermuse.com.
这种态度在地球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事件,以及数十亿人和其它生物为某些所谓“利益”或“权力”—或者所谓重要的“上帝”陷入了战争、开采和贫穷的情况下产生巨大意义。“游戏结束”的态度已经使它们自己陷入了感知的强烈风暴,并不仅仅是认知,到2100年人类数量几乎能确定达到110亿人以上。这个数字表明从1950年到2100年的150年内人类数量增长了90亿,这导致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极度不平等——更别提富人相比于穷人施加于地球更严重的负担——甚至更糟糕的后果是,几乎每个地方的非人类都要承受这一后果。这里有许多可怕的现实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s)时代在地球上的岩石、水、空气和生物上留下了痕迹。承认麻烦的程度和严重性,与屈服于抽象未来主义及它崇高的绝望效果和冷漠政治,存在微妙的差别。
本书论证并试图表明,远离未来主义,与麻烦共存是更严肃也更富有生机的。与麻烦共存要求制造古怪的亲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彼此在一个意外的合作和组合中,在热堆肥中。我们彼此“共同-生成”(become-with)或者根本不联系。这种物质符号学经常定位于某些地方世俗地纠缠,而非无地方。我们独自一人,我们的专业和经验各自分隔,我们都知道太多,也太无知了,所以我们屈从于绝望,或者去希望,这些都不是明智的态度。绝望或希望对于应关注的事情,对于物质符号学,对于密集共处的平凡的地球人来说,都没有意义。既非希望也非绝望则知道怎样教育我们“同伴侣物种玩花绳图形”,这是本书第一章节的标题。

花绳图形:纳西尔穆夫提 (Nassir Mufti)《多物种猫的摇篮》(2011 年)
图源: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Multispecies-Cats-Cradle-by-Nassir-Mufti-2011_fig1_338115550
本书有三个长章节开启了“与麻烦共存”之旅。每章都记录了一些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的故事和人物,以切断与人类世和资本世的联系。鸽子在所有世俗的多元性中——从帝国生物,到养鸽人的赛鸽,到战争间谍,到科学研究伙伴,到三大洲的艺术活动合作者,再到城市的伙伴和害虫———这是第一章的指南。
在它们的家族历史中,鸽子导向了“触手思维”的实践,这是第二章的标题。在这里,我展开谈了这一论点,在科学、政治和哲学内的许多受限的个人主义(bounded individualism),最终在技术或其它方式上已经变得无法思考,真的不能再思考了。共在——制造-关联——是这章的关键词,我会探索理论家和叙事者所提供的有必要进行思考的礼物。包括有我在科学研究、人类学和叙事上的伙伴——Isabelle Stengers、布鲁诺·拉图尔、Thom van Dooren, Anna Tsing, Marilyn Strathern, Hannah Arendt, Ursula Le Guin等其她人——都是我触手思维的伙伴。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介绍了本书的三段时期:人类世、资本世和克苏鲁世。太平日的章鱼、美杜莎、唯一的凡人蛇发女怪,被认为是动物世界的女主人,与她结盟,拯救了今天,也结束本章。
第三章“共生和与麻烦共存的生动艺术”围绕共生展开了线索,在生态进化发展生物学和艺术/科学活动中,讽刺了四个麻烦的地方:珊瑚礁生物群落、纳瓦霍人(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的黑山煤田和霍皮人(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印第安村庄居民)的土地和其它化石燃料开采区,对土著人民、马达加斯加复杂的狐猴森林栖息地、受新旧殖民地控制正在遭受冰川迅速消融的北美极地土地和海洋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本章用生物学、艺术和多物种复兴行动的往复能量的线索来制造花绳图形。这里,关注且行动的持续创造力激发了行动。不足为奇的是,当代土著居民和其他人在与多种伙伴的冲突与合作下已经产生了明智的变化。生物学家,从无以伦比的林恩·马古利斯开始,加入了本章的思考和游戏。
第四章“制造亲缘”既是对人类世、资本世和克苏鲁世时间的重演,也是对“制造亲缘,而非婴儿”的呼吁。长期以来,各种肤色和来自各个民族的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一直是争取性和生育自由权利运动的发起人,特别关注针对贫困和边缘人群的生育和性秩序的暴力。女权主义者一直在争论性和生育自由意味着能够让孩子(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其她人的孩子)在社区中健康和安全地成年。女权主义者在历史上也独一无二,她们坚持每个女性,无论老少,都有选择不生孩子的权力和权利。认识到这种立场是多么容易重复帝国主义的傲慢,我所相信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母性不是女性的目的,女性的生育自由胜过父权制或任何其他制度的要求。食物、工作、住房、教育、旅行的可能性、社区、和平、对身体和亲密关系的控制、医疗保健、可用的女性友好的避孕措施,关于是否生孩子的最后决定,享乐等:这些都是是性权利和生育权利。这些权利在世界各地的缺席令人震惊。我认识的女权主义者抵制人口控制的语言和政策,因为她们显然往往更关注生命政治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女性和其她人民的福祉,无论老少。人口控制实践中的丑闻并不难找到。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女权主义者,包括科学研究和人类学女权主义者,并不愿意认真对待人类数量的大加速,担心这样做会再次滑入种族主义的泥潭,阶级歧视、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泥潭。
但这种恐惧还不够好。避开自 1950 年以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紧急情况,可能会陷入类似于基督徒躲避气候变化的紧急情况的方式,因为它过于接近一个人的信仰的根本。如何解决紧急情况是为与麻烦共存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一个危险麻烦的多物种世界中,什么是去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生育自由?无论多么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反阶级主义和亲-女性,它都不能只是人道主义事务。它也不能是“未来主义”的事情,主要关注抽象数字和大数据,而不关注实际人民生死的差异化和阶级分层。尽管如此,如果幸运的话,人类在 150 年中增加了 90 亿,到 2100 年达到 110 亿,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并且不能通过指责资本主义或任何其它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来解释它。迫切需要跨越历史位置以及各种专业知识的差异重新思考。

《克苏鲁世的圣像》(Icon for the Chthulucene)
图源:http://www.engramma.it/eOS/index.php?id_articolo=3154
第五章“尿中充盈”,从个人和亲密关系开始,这一章涉及服用雌激素的后果,使一个老女人和她的老狗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和我的伴侣,还有研究助理 Cayenne。在花绳图形的绳子得到深入追溯之前,记住它们的赛博格兄弟姐妹,女性和她的狗在兽医研究、大型制药公司、用雌激素的养马场、动物园、激进女权主义和相关的动物权利和女性健康行动等历史中发现她们自己。核心主题是,集中居住在特定的身体和地方,作为培养回应世俗紧急情况的能力的手段。
第六章“播种世界”,出现了厄休拉·勒古恩、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以及蚂蚁和金合欢种子[2]。本章任务是讲述一个以金合欢及其同伙为主角的科幻冒险故事。事实证明,勒古恩的虚构的背袋理论(carrier bag theory of narrative)与生物学家Deborah Gordon关于蚂蚁的互动和群体行为的理论相得益彰,阐述了生态进化发育生物学和非等级系统理论在塑造最佳故事方面的可能性。科幻小说和科学事实在这个故事中愉快地共存。勒古恩作为她们的抄写员,金合欢种子的散文和地衣的抒情诗在最后的段落中让位于岩石的无声诗意。
第七章“一次奇妙的实践”谈及了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动物人类学学生和文化理论家 Vinciane Despret,因为她具有与其它生物(无论是否为人类)一起思考的奇妙能力。Despret 在协调和动物的工作使彼此在实际遭遇中引发了出人意料的技艺表演,这对与麻烦共存来说十分必要。她关注的不是生物通过自然或教育应该能做的事情,而是关注生物之间相互唤起的东西,而这在自然或文化中本来是不存在的。她的思维方式扩大了所有玩家的能力;那是她的世界性实践。人类世、资本世和克苏鲁世的紧急情况要求以平实具体的方式超越既定范畴和能力进行思考,就像阿拉伯人及其科学家在内盖夫沙漠所做的事情一样。Despret 教我们如何保持好奇心,如何通过让死者积极存在以进行哀悼;在我写下《与麻烦共存》的结局前,我需要她的抚摸。她的好奇实践让我准备写关于堆肥社区和为死者言说的任务,因为她们为地球上的多物种恢复和复兴工作。

Maripose mask, Guerrero
https://brooklynrail.org/2017/12/art/DONNA-HARAWAY-with-Thyrza-Nichols-Goodeve
本书以“卡米尔的故事:堆肥的孩子”作结。一个集体的展望式虚构,邀请了五代人类儿童和王蝶的共生结合,它们沿着在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昆虫迁徙轨迹的许多路线和节点行动。
这些路线追踪了对于濒临灭绝的生物的生死存亡来说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以便它们可以继续生存。堆肥社区致力于培养回应的能力,发明了使彼此能够回应的方法,该社区揭示了21世纪早期全世界范围内被毁坏的陆地和水域。这些社区努力要在数百年内从根本上减少人口数量,同时开展了无数种关于多物种环境正义的实践。每个新生儿至少拥有三位人类家长;怀孕的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动物共生体时行使了生育自由。这一选择分化了所有物种的世代。参与共生的人类和未参与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令人诧异,其中某些关系是致命的,但大概最令人惊喜的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在象征意象的复杂性中跨越地球上的全生物群落。
许多麻烦,许多亲缘,正在继续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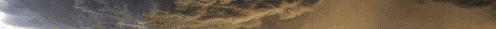
注 释
相关文章
哈拉维|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
哈拉维|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二)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