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复的快感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何啸风 译
选自Robert A. Glick and Stanley Bone(eds)Pleasure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Role of Affect i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感谢译者授权
出版于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推翻了弗洛伊德早年提出的快感在人类的驱动力中的优先性。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提到了一些无法用快乐原则来理解的强迫重复。他把无处不在的重复现象,与寻求满足的愿望割裂开来。《超越快乐原则》用二元理论(寻求快感的驱力,总是被死亡驱力所打断和阻断)替代了一元理论(现实或想象中的快感的实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目标)。在《超越快乐原则》结尾,似乎塔那托斯战胜了厄洛斯,寻求死亡的驱力规介、主宰了寻求快感的驱力。
在这本极具争议的作品中,弗洛伊德把自己展现为思辨的形而上学家。他使用的词汇,让人想起启蒙运动的哲学争论,让人想起《伦理学》、《论灵魂的激情》中对人类的激情和目标的思考。为了扮演形而上学家的角色,弗洛伊德使用了原则、本能、驱力这些词汇。虽然它们建构、推动了人类行动,并且显现在人类行动中,但是,严格来说,我们无法在人类行动、话语、姿势之外直观、认识它们。原则、本能、驱力这些词汇所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这些词汇的一个维度,要在本章中重新思考。这个维度就是,这些词汇歪曲和限制了我们解读“重复的快感”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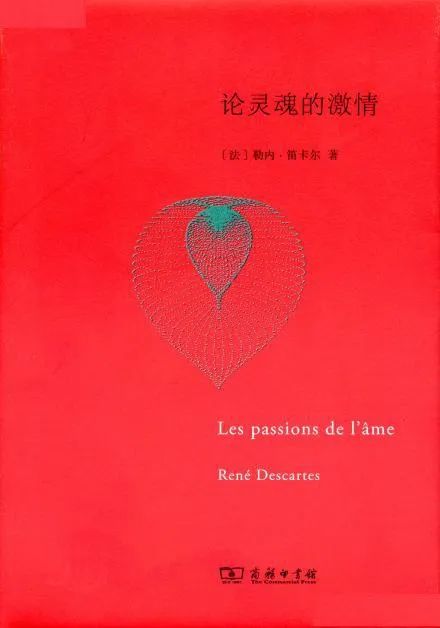
批判地看,如果死亡驱力的唯一证据就是死亡驱力所解释的那些现象,那么,死亡驱力在本体论上的完整性就是成问题的了。弗洛伊德给读者举了几个强迫重复的案例,证明(a)这些案例不是快感的案例,而且(b)这些例子展现了一种恢复最初状态的驱力,一种回到出生之前、自我形成之前的驱力。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死亡般的静态,是这种驱力的“目的”。因此,强迫重复不仅是中断当下的时间,回到“更好的”时间,而且是彻底否定时间,否定生命本身。但是,为什么这种愿望(a)在起源上与快感无关,而且(b)是导致一切强迫重复的普遍原则?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逻辑观点:如果这种原则只能用各种重复现象来证明,而且这些现象是有待解释的,那么,弗洛伊德的论证就是循环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死亡本能”被设定为决定各种特殊的、经验的现象的普遍原则,那么,哲学困惑就出现了。在这里,我们不能说,因为一些重复行为体现了恢复最初时间的愿望,所以一切重复行为都是同样的恢复。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说,强迫重复体现了恢复最初时间、实现被否认的快感的幻象。
虽然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死亡本能的假设,认为它是无法确证的纯粹思辨概念,但是,更明智的做法是,接受弗洛伊德的思辨,思考这个原则能否完成解释强迫重复现象的任务。对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我提出的质疑是,有一些现象既是愉快的,又是强迫重复的。如果弗洛伊德是正确的,那么,强迫重复不是由快感所驱动的,而是由回溯到出生之前的时刻的愿望所驱动的。那么,“重复的快感”呢?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寻找死亡本能的证据,他找到的“案例”是施虐狂。因为他主张施虐不是由快感所驱动的,所以,他被迫修改了《性学三论》和《本能及其变化》的理论。他在《性学三论》和《本能及其变化》中说,施虐是一种自我保存的策略,而不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策略。虽然本文会考察弗洛伊德理论的几个关键转变,但是,本文不是对弗洛伊德对施虐的心理学-性学意义的分析的全面总结。相反,我们考察的是,作为一种愉快的重复,施虐如何推翻了死亡本能这一构造?我会说明,强迫重复的快感如何推翻了那些让弗洛伊德误入歧途的思辨概念?而且,我会在现象学的基础上给出一个替代的出发点。借助现象学,不是为了替代精神分析的框架——事实上,我们对“意向性理论”与“客体关系学派”进行对比——而是为了让精神分析的洞见立足于经验之上,而不是思辨构造之上。事实上,我们给出的现象学方法,恰恰体现了弗洛伊德解读快感的破坏性的作品的特征。

1. 快感还是重复?
当弗洛伊德说强迫重复的起源是某种不同于快感的事物,他提到了再现恐怖的经历、不愉快的经历的梦境。在他看来,这种不愉快的重复,甚至也出现在“愉快的重复”之中。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fort-da游戏,儿童通过把玩具从小摇床上扔出去再捡回来,愉快地重复他与母亲的分离。儿童首先用玩具替代了母亲,其次掌控了玩具的扔出和回归。这样一来,fort-da游戏就让儿童感觉他掌控了他与母亲的分离。虽然这个游戏确实赋予男孩无可争议的快感,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掌控我们最初无法掌控之物的快感,主要不是由快乐原则所驱动的。事实上,弗洛伊德极具争议的主张是,寻求快感的驱力,不可避免地从属于寻求死亡的驱力。比起自我保存的本能,死亡驱力是一种更强的、更基础的有机体的强迫力量。因此,即使这种掌控无法掌控之物的强迫重复,也受制于死亡的本能或原则。这种驱动力不仅与快感是分离的,而且对快感而言是对立的、多余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
本能的终生目的就是要引起死亡。采用这种观点,自我保存、能力、自我突出的本能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它们是生物体特有的用来保证通向思维道路的部分本能,又是避免回到无机物的可能性,生物体不管整个世界而要保存自己的神秘斗争都消失了,这种斗争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整本《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知道他的理论是思辨的,推翻了他早年的本能理论。在《超越快乐原则》结尾,弗洛伊德希望读者不要错误地认为他改变了立场,而且他在整本书中都捍卫他的研究的思辨性。弗洛伊德说,“鉴于目前在关于本能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的模糊不清的状况,拒绝可能对于本能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的观点,就是不明智的”。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当理论模糊不清时,更广泛的思辨是应该被阻止的,但是,弗洛伊德提出了“死亡本能”这种更广泛的构造。
更成问题的强迫重复行为,包括了施虐和受虐。事实上,弗洛伊德说,“这些施虐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死的本能,它们是在自恋性的力比多影响下被迫离开自我的,以致最后只能在与对象的关系中出现”。仅仅6年之前的《本能及其变化》,弗洛伊德还说施虐是“要控制的冲动形式”,施虐体现了自我保存的本能。当时,他认为施虐不仅是为了“痛苦的惩处”,而且是为了“屈从对象或控制对象”。受虐狂是施虐本能的反面。受虐的主体扮演了被动的角色,“促使”另一个主体扮演施虐狂的角色。在这两种案例中,这出戏剧的主要计划都是,控制某种危险、痛苦的局面。
我在写这段话时“多少”有些不安,因为1914年弗洛伊德认为,施虐和受虐主要不是为了对抗痛苦,而是为了把当下的痛苦“性化”,而且通过“性化”让痛苦屈从于愉快的性爱幻象。我们看到,在1914年思考施虐和受虐时,弗洛伊德认为某些痛苦可以成为快感的来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痛苦的感觉就像其他的不愉快感觉一样,会发展成性的兴奋并产生令人快乐的条件。为此,主体甚至愿意体验痛苦的不愉快”。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不再认为施虐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效果。弗洛伊德问道:“这种以伤害对象为目的的施虐本能,何以能由生的本能所产生,即由生命的保护者所产生呢?”1914年弗洛伊德的答案是,这种伤害对象的欲望,是在危险的、危及自我的对象面前的自我保存。但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明确把“施虐式保护行为”同“自我保存的意图”分开。1914年,弗洛伊德区分了自我保存的自我本能,以及寻求快感的性本能。从自我的角度看,性本能是先于自我本能的。弗洛伊德说,“一开始,外部世界、对象、被憎恨的东西是一码事。以后,对象表现为快乐的来源,它就成为被爱的,而与自我合并”。自我保存、憎恨的本能与性本能的区分,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变成死亡本能与性本能的区分。《超越快乐原则》认为,自我保存就是倒退地重现自我发展的最初阶段,重现自我发展之前的力比多组织阶段。扩展之后的“自我本能”带来的实践后果是,强迫重复不再是一种控制、自我保存的计划,而是一种快乐原则和自我保存原则所无法解释的倒退努力。
1914年,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与我们憎恨的对象之间,“有一种要加大对象与自我之间距离的倾向,并且恢复以前的关系,即有一种原始的努力要逃避外部世界及其刺激流”。因此,施虐就是自我保存的原发冲动的重复,就是与危险的、有害的对象所组成的外部世界的第一次相遇。把施虐狂“性化”的做法,是混淆施虐本能与性本能的一个标志,而且凸显了一种掌控了最初的有害局面的愉快体验。这种掌控局面的快感——在某种意义上,当下对过去的胜利的快感——体现了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矛盾组合。
但是,我们似乎有必要质问,这两种“本能”在本体论层面是否截然不同?毕竟,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本能是“原发的”,性关系似乎是自我本能的延伸和外显。如果一个对象是令人愉快的,那么,自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吸收”它,把它合并到自我中。此后,自我与令人愉快的对象的关系,不过是自恋的延伸,自我“仿佛对象就是自我一样”去“保存”这个对象。因此,性本能是自我本能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当快感的对象被否定或丢失了,当自我发现它的吸收策略失败了,性本能才发挥作用。就像弗洛伊德说的,自我对对象的第一反应是憎恨,接着是吸收,最后是掌控。施虐狂就属于本能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事实上,施虐狂就是寻求快感和寻求安全之间的调和,但是,寻求安全是对于危险的情感记忆,它呈现为一种当下的威胁。因此,在施虐狂看来,性快感就是对外部事物的“原初”憎恨的重复和再现。
1914-1920年之间的理论转变,导致了作为“掌控”的重复与作为“倒退”的重复的区分。在前者中,重复是为了修复过去的伤害而回归过去。我们可以说,这种回归策略,是重写、重构一段在当下依然痛苦的历史。因此,这种回归总是与重来、修复的欲望有关。重复是一种痴心妄想的修复,是把当下同化到过去之中,从而用当下的状况填补过去,对过去进行幻象的重构。
但是,到了1920年,弗洛伊德认为,重复不是回归个人过去的特定伤害,而是更一般地回归自我与外部世界尚未区分的时刻。死亡本能不是朝向未来的,而是把死亡作为个体化之前的自我的“无边界”状态。虽然“原发状况”在《本能及其变化》中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但是,它在1920年与“无快感”有关。是什么导致了这一重大转变?
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是一种保守的倾向,它让自我本能屈从于死亡本能本身。虽然快感总是被描述为一种兴奋和刺激,但是,“无快感”是一种平衡和安宁。在区分厄洛斯(性本能)和塔那托斯(死亡本能)时,弗洛伊德认为他解释了人类生命的二元机制。强迫重复所揭示的是,一种回归快感问题尚未出现的状态的“原发冲动”。强迫重复既不是在兴奋中得到片刻安宁,也不是对过去进行幻象的重构,而是彻底毁灭快感问题。换句话说,强迫重复不仅是对死亡的渴望,而且是对“从未出生”的渴望。1914年,弗洛伊德认为,外部世界引发了自我最初的敌对反应。因为这个外部的、不受自我控制的世界,代表了不满、痛苦、危险的永久可能性。彻底否定外部世界,可以带来永久的保护。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消除外部危险的欲望,来理解从自我到死亡本能的过渡的逻辑。事实上,自我本能的终极胜利,将是自我本身的死亡,因为如果自我的终极目标是自我保存,那么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否定自我与世界的区分才能实现。事实上,自我在世界面前的终极保护,就是自我的毁灭。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说,死亡首先不是摆脱自我的努力,而是消灭(让自我岌岌可危的)世界的努力。
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拒绝把这种“无世界”的状态等同于愉快的状态。“无世界”状态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平衡,既不是愉快的,也不是活着的,而是对外部的快感和危险的排除。作为一种安宁,“无世界”状态既对立于兴奋,又对立于快感-危险。但是,作为一种死亡,“无世界”状态彻底超越了二元机制。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及其回溯机能,是在性本能之外的,是在生命的机制之外的。但是,他还做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举动:他让性本能从属于死亡本能,从而把死亡本能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论原则:
让我们最明确地区分机能与倾向。快乐原则是一种倾向,它对一定的机能起促进作用,就是说,使心理器官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摆脱兴奋,或者使兴奋的程序尽可能降低。我们无法判定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样定义的机能将参与所有生命物质中最普遍的倾向——回到无机世界的宁静中去。
接着,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看来直接促进死亡本能”。这个说法,打破了两种本能的对立。作为从属于机能的倾向,性本能总是在死亡本能“回到无机世界的宁静中去”的全盘计划之中。因此,性本能不再是独立的,在本体论上独特的力比多外显,而是从属于一种本能或机能的倾向。性本能和死亡本能在理论上的结合说明,双重本能理论、二元本体论受到了弗洛伊德自己理论的质疑。但是,二者的区分,在《超越快乐原则》对施虐狂的讨论中受到进一步质疑。
虽然弗洛伊德用“本能”来描述死亡冲动(力比多活动的静态),但是,他对这种本能活动的描述,无意中质疑了“双重本能理论”。这种描述,不仅质疑了一种目的论的本能的本体论地位,而且推翻了“双重本能理论”。我认为,这种做法的后果,是重新把施虐视为对过去的掌控。脱离了本能理论的理论负担之后,弗洛伊德的分析说明,施虐狂是自我的一种具体策略。根据这种修改后的理论,作为施虐欲望的场所,身体把未修复的伤害的历史、世界本身再现为一个永久危险的场景。

2.施虐狂与死亡欲望
作为回归无机状态的本能的表现,施虐狂不过是“由保守性本能所忠实保持的通向死亡之迂回曲折道路”。严格来说,施虐狂的“意图”,就是重现这种宁静的“原发状况”,让有机体的未来致力于重构“原发状况”。上文说过,施虐狂是弗洛伊德用来证明他的思辨的“案例”,它表现了这种迂回曲折的目的论(有机体最初的无机状况,重现为它的目的)。
弗洛伊德所说的施虐,明显是性爱方面的施虐,而且这种施虐体现了性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共同操作。但是,如果性本能是肯定生命、创造生命的,那么,它在从属于死亡本能的过程中颠倒了它的“意图”。在通常的性爱中用来实现“贯注”的事物,在施虐狂的案例中,成为一种“疏离”的手段。施虐狂作为一种性行为的悖论在于,它能够消除一切既定的“贯注”。死亡本能打破、推翻了性爱的“贯注”可能性。它寻求回到需求、快感、性爱之前的无机状态。以这一框架来理解,施虐狂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性爱构造,是性爱的k/not,是一种被迫走向失败的性本能。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等早期作品中认为,受虐狂起源于施虐狂。受虐狂把最初与他者的憎恨关系,“内化”成与自我的憎恨关系。虽然施虐狂来源于“原发的自恋”,但是,施虐狂是对“原发状况”的彻底颠倒。但是,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认为,或许,就起源而言,施虐狂是一种反射性的本能,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本能。它是性爱方面的施虐狂的前提条件。按照这种观点,性爱方面的施虐狂体现了死亡的冲动,虽然这种冲动“被迫离开自我”。因此,死亡本能把施虐狂作为一种外在的、性爱的外显。然后,这种施虐狂以受虐狂的形式,实现了二阶的反射性。受虐狂是一种倒退,它已经受到死亡本能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或许存在某种原发的受虐狂(他以前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种语境下,受虐狂的含义和范围,彻底改变了。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欲望对自我而言是基础的,从而排除了对死亡欲望如何形成的研究。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为,施虐行为可以追溯到某种不变的、非具体的原发的自我否定关系。因此,内化为“心灵”一部分的各种具体关系,都可以化约为某种普遍原因。这种普遍原因,说明各种具体关系是“原发本能”的工具和手段。在施虐狂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说,伤害自我的倾向,不是一种“内化的”惩罚,而是一种“外化的”本能。不仅如此,我们不能认为,施虐狂是一种想要掌控过去的策略,是对过去的惩罚场景的重现。现在,我们应该用更加普遍的框架来解读施虐行为,不仅要展现施虐个体的历史,而且要展现有机体的普遍历史。作为一种准生物学本能的表现,事实上,施虐狂代表了有机体的欲望。分析地来看,我们只有根据施虐狂普遍的、非具体的起源,才能充分地解释施虐狂。
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原则,“死亡驱力”这一概念无疑是整全性的。但是,确立这一概念的本体论有效性,是困难的。弗洛伊德知道他的研究是思辨性的,而且他知道,他的理论建构是否有用,取决于他的理论能否澄清强迫重复中那些含糊的层面。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结尾说,“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术语处理,也就是说采用心理学特有的隐喻表达方法”。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思辨建构所提供的思想广度,是否削弱了理论的分析实践性?在发展关于施虐狂的本能理论时,弗洛伊德远离了早年的立场,不再认为施虐狂是一种掌控和修复的欲望。既然施虐狂表现了有机体回归原初静态的欲望,那么,对施虐狂的解读,就要在一般化的层面进行。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弗洛伊德对早年立场的反转,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反转,从而恢复这一理论的分析有效性。我们可以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施虐狂首先寻求他的死亡;这个目标与性本能发生冲突;这个冲突通过让性本能从属于死亡本能得到解决。这样一来,施虐狂的性爱维度,始终是死亡本能的工具或手段。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被迫离开自我的施虐性倾向,已经为性本能的力比多成分指明了道路,后者就是跟随它才到达对象身上的”。性本能的“跟随性”说明,在施虐狂的策略中,性本能是一种非蓄意的、非必要的“机能”。它还说明,性爱维度和施虐维度,都是由死亡本能来组织和规介的。
这种解释,具有很强的生存论维度,我们可以用这种恢复原初静态的冲动,来解释各种宗教体验。不过,虽然我们用一种普遍原则解释了施虐现象,但是,我们似乎无法在个体层面解释施虐现象。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何种框架,在个体成长的语境下,解释施虐狂的策略?既然人人都是施虐狂,那么,他们是否由于同一原因成为施虐狂?看起来,因为弗洛伊德对施虐狂做出普遍性解释,所以他的理论无法解释施虐狂的特殊形式。施虐狂采取性爱形式是纯粹“附带性的”吗?还是说,快感和痛苦比弗洛伊德所想的更加紧密相关?
上文说过,对早年立场的反转,需要进一步的反转。在个体成长的经验中,什么事物既决定了死亡欲望,又决定了死亡欲望在施虐现象中的“外化”?显然,我已经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词汇,用更现象学的“欲望”,替换了自然主义的“本能”。但是,如果我们想保留弗洛伊德的经验洞见,同时摆脱他的思辨的自然主义,那么,词汇的替换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死亡欲望与掌控他者的施虐努力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依然怀疑死亡本能的本体论优先性,以及性本能的“从属性”。在早年的理论中,弗洛伊德认为施虐狂是掌控对象的努力。事实上,如果我无法把对象合并成我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就会用武力和强制征服对象,让对象成为我的意志的工具。于是,施虐狂就是未能吸收对象,就是把他者作为我的意志的延伸,就是拒绝他者的他者性。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早年的理论和《超越快乐原则》都认为,施虐狂是由重复所构成的,施虐行为想要恢复过去的时刻,从而让过去未满足的愿望得到满足。在这里,弗洛伊德指出了(1920年的理论中丢失了的)施虐狂和修复的联系。
根据“原发自恋”理论,一切外部性都对既定的自我做出敌对反应。弗洛伊德在1914年对此说了很多。但是,构成个体性欲的施虐意图的敌对性的历史呢?这种敌对性如何被吸收到欲望之中?对敌对性的基础的描述,是否足以解释人类性行为中的各种施虐形式?
作为一种重复性快感,施虐狂既是“贯注”,又是“倒退”。它既是结合又是拆解,既是关联又是分离,既是性又是非性。虽然施虐狂的悖论性揭示了它所表现的冲突,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冲突在本能的生命中平息了。施虐狂核心处对快感的否定,或许不能轻易等同于死亡欲望;施虐狂的意图“首先”是快感的死亡。我们可以因此认为,(a)否定快感的努力就是否定生命的努力,而且(b)否定生命的努力是恢复原初时间的倒退努力。但是,这两个结论不一定能从对施虐狂的现象学描述中得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性行为之中征服、伤害他者身体的努力,是自我与自身的外化关系。自我所征服、伤害的身体,“首先”是施虐者的身体,“其次”是他者的身体。但是,指出施虐关系的“原发的反射性”,不等于接受了施虐狂在本能上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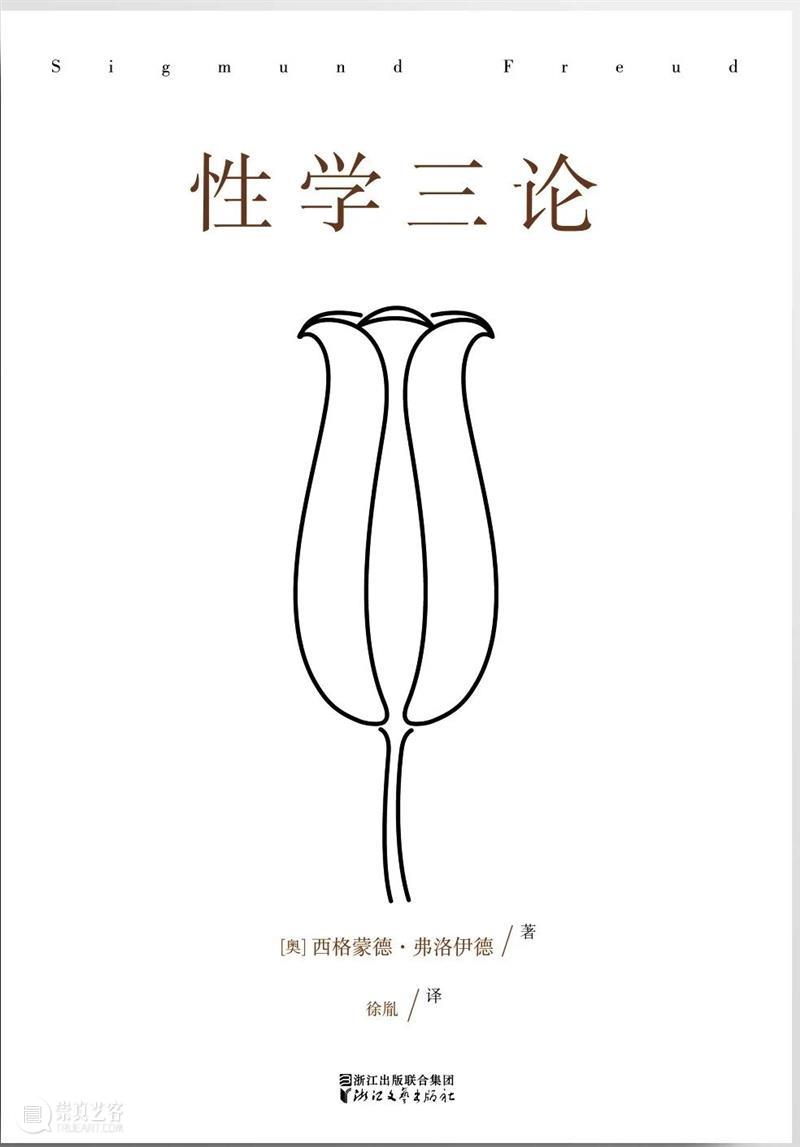
3.对重复性快感的现象学解读
弗洛伊德用来奠定施虐狂的基础的,是本能理论。虽然本能理论是思辨性的,但是,它是“心理学特有的隐喻表达方法”的一部分。虽然弗洛伊德有时说,他希望用神经-生理学的框架来奠定本能理论,但是他同时似乎认为,描述心理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语言有某种必然的模糊性。我不想争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不是科学,而是提出一种不同的出发点,来理解我们要考察的这种现象:重复的快感。我宣称这种不同的出发点是现象学的,因为它立足于经验,而且它认为心理生活是“意向性的”。虽然“意向性”一词通常指有意识地做X或y的心理倾向,但是,它在现象学中的用法是多样的。就像胡塞尔说的,意识的意向性,就是意识与世界的“关联性”。用胡塞尔的话说,“意识总是对于某物的意识”,也就是说,意识不是完全自我指称的。只有“自我”被投射、被确定在对抗性的世界中,意识才能把自身作为对象。在意向性的前提下,哲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不能认为,我们意识到世界的各种方式,仅仅是与客观领域无关的心理表象。有意识的思维、各种觉知模式,都与外部领域有关。这种关系是人类生存的特征。事实上,这种关系是人类经验的“原发结构”,因此对心理生活的一切解读,都必须以某种方式预设这种关系。
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类似于客体关系理论的主旨。客体关系理论认为,具体的关系是心理学解读的出发点。根据萨特的说法,在现象学框架下,我们不可能把人类描述为仅仅关注自身的。即使最孤僻、隐居的人类,也处在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哪怕处在拒绝的关系之中。对“在世”的拒绝,依然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对他者的“否定”依然是一种与他者的关系。否定关系的努力,在萨特的分析中,恰恰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关系。根据萨特对现象学哲学的心理学延伸,人类不可避免地“在世”。不管个体是拒绝、憎恨还是施虐,个体都想打破与世界的意向性关联。个体把意向性颠倒过来,试图否定个体的关联性,但他必然会失败。不同于弗洛伊德对厄洛斯的看法,意向性理论指出了我们与外部对象的“原发的关联性”。事实上,如果像弗洛伊德说的,施虐狂是把厄洛斯颠倒过来,那么,现象学解释与此类似:施虐狂是打破一种不可打破的关联(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经验本身)的努力。弗洛伊德把厄洛斯视为“贯注”的看法,似乎得到梅洛·庞蒂的肯定。梅洛·庞蒂认为,意向性是我们不断“拥抱”世界的“世内”方式。
我们注意到,萨特的现象学观点,故意把我们与具体对象和他者的关联,同我们与世界的关联混为一谈。萨特在《情绪理论纲要》中说,在我们与外部事物的每种具体情绪关系之中,我们与世界的普遍关系都暗中起着作用。事实上,在各种具体的爱、憎恨、恐惧之中,我们不仅展现了与现成在手的对象的情感,而且展现了与世界的更一般关系。萨特早年的现象学作品,没有吸收精神分析对依恋客体的形成方式的理解,也没有考察我们对世界的构想如何建构了我们对客体关系的错误的一般化。萨特的理论,对于精神分析的读者而言,或许太抽象了,没有解释性用途。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对重复的快感的现象学解读,可以为精神分析的洞见提供什么?
只有当我们认为快感是寻求“贯注”的驱力,重复是寻求“去贯注”的驱力,“重复性快感”才是一个术语矛盾。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人类欲求”的两个相反方向,一个是通向关联和牵连的运动,一个是远离关联的运动。对这两个运动的现象学描述,并不预设它们在本体论上有不同起源。事实上,我们的现象学任务是,理解这种本质上对抗自身的“人类欲求”的结构,理解这种不断击败自身、引发重复的快感。但是,除此之外,现象学解读不认为,快感是一种先于对象的“状态”或自由漂浮的“能量”。换句话说,快感必然是“关于”外部对象或事件的快感。不同于认为快感的意义要在肉体起源中寻找的观点,意向性学说认为,快感的意义要在快感的“意向对象”中寻找。快感的意向性,不是否定快感的肉体、生理基础,而是认为快感在活生生的经验中才有意义,在与对象有关时才能被感觉到。换句话说,快感不是在语境之外仍有意义的实体或状态。事实上,快感的生理、肉体前提,不等同于快感本身,因为快感是一种经验、一种意向关系。这种观点的后果是,我们不能说,快感是在经验之前就具有本体论完整性的原则或本能。如果我们把“快感”归入前经验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把一个适用于活生生经验的术语,错误地用在活生生经验的生理条件之上。虽然很可惜,萨特的论点反驳了无意识,但是,他的理论对“快感”、“欲望”、“情绪”等术语给出了更一般化的观点。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理论给出了一个后来客体关系理论的主张:快感的结构、意图、策略,是在与原初客体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主张的后果是,快感只有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才是可理解的;快感在本体论层面是指称性的、意向性的;快感既不是本能,也不是状态,而是(不断重复的)与客体的关系。
因为意向性是一种多方面的结构,所以,快感的意向结构有各种对象。因此,《超越快乐原则》中关于强迫重复的快感的问题,有至少两个方面的意向对象:“非贯注的对象”与“时间本身”。对于承受快感的重复和挫折的个体而言,不仅过去的对象、与对象的关系无法恢复,而且时间本身反抗着人类意志。在快感和满足之间,引发了对快感的禁止和否定,从而导致受挫快感的不断重复和增殖。重复就是徒劳地想要停在原地,想要颠倒时间;这种重复揭示了一种对于当下的怨恨。
从现象学角度看,反抗当下,是掌控时间性结构(过去、当下、未来)的徒劳努力。事实上,中断、打破时间连续性的努力,是个体的自我否定的策略。成为个体,就是“在时间中”:在时间的紧迫性中。拒绝经验的时间连续性,就是拒绝自我本身的结构。
因此,从现象学角度看,快感的意向结构是多方面的。快感不仅与(过去的、当下的)对象有关,而且与时间本身和世界本身有关。时间本身和世界本身,构成了快感的意向性的生存论维度。萨特的问题——自我否定的姿态所表现的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说明追求快感的主体同样打破和拒绝了快感,而且这种基础的矛盾性是一种意向性关系,而不是某种本能在现象层面的表现。同样的,主张这种矛盾性来自一种关系,不是对快感的起源和重复性进行因果解释。事实上,这种主张仅仅说明,意向性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意向性的优先性说明,关联性是无法摆脱的,否定关联性不过是以否定的模式与世界产生关联。显而易见,针对重复性快感,现象学的结论是,厄洛斯(人类主体无法克服它)是第一位的。
因此,从萨特的现象学看,虽然强迫重复的快感引发了意向性的危机,但它没有推翻意向性。只有我们“非意向性地”与外部性决裂,才会产生两种驱力或本能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有我们不认为“非关联”是“关联”的一种模式,才会产生两种驱力或倾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意向性作为理论出发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对快感和关联的否定是它特有的一种关联,是它特有的一种快感。
对重复性快感的考察,可以超出强迫重复的体验。1924年,弗洛伊德似乎把快感与驱力的满足、力比多能量的释放关联起来。弗洛伊德把这种释放与“引发新的贯注的非贯注”关联起来。事实上,弗洛伊德认为,重复与对过去的再现有关,而且重复体现了“自我无法栖居于当下”的事实。与此相反,快感与全新事物有关,与未来的时间场域有关。那么,是什么事物排除了重复的快感、回忆的快感?是什么事物排除了笑话、音乐节奏、诗歌押韵的快感?这些重复体现的,是一种完全过去的快感吗?或许,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过去和未来,从而为过去的重现和当下的显现提供了仪式性的、感性的场合。事实上,除了重复,还有什么方式,能产生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时间连续性的快感”?
如果说本能和死亡本能不再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建构,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可解释的经验的证据。在思考快感和重复的冲突时,弗洛伊德意识到,某些并不起源于快感的强迫行为,摧毁了快感。因为施虐狂是弗洛伊德给出的案例,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观点,看看我们是否可能从现象学的术语重新描述施虐现象。

4.理论的具体要求
无论是死亡本能学说,还是意向性学说,都没有提供一种方法,让我们理解快感与强迫重复的结合。如果说施虐者把死亡欲望戏剧化了,那么,他为什么把死亡“外化”为掌控、伤害他者的形式?他为什么采取性爱的形式?有其他一些解释认为,对快感的反对,恰恰是在我们最期待快感的行动之中。死亡欲望,可以指一种回归(排除外部世界的焦虑可能性)封闭状态的欲望。作为一种与子宫有关的对保护的渴望,“死亡本能”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欲望,不如说是对保护的欲望。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渴望的首要原因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本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了它的具体诱因。我们有可能认为,死亡欲望是一种物种欲望,或者它是对一种“最佳处境”的回应。事实上,我们会说:“如果不去死,还能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欲望的非本能的基础,就是让死亡成为最佳选择的“具体的危险”。
施虐狂的重复性,体现了施虐狂核心处的不满。施虐行为之所以必须重复,是因为它不能实现它的意图——通过让他者静止下来,从而实现彻底安全。作为一种重复,施虐行为不断打破当下的面纱,破坏他者身体的表面,从而穿越当下的顽固的“事实性”。在(施虐者的徒劳重复所体现的)当下和过去的汇合之中,他者的身体成为时间本身的“不可穿透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身体,就是排除了“对过去的修复”的当下的标志。对他者身体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同时性”的伤害。类似的,他者的身体就是反抗本身,就是让自我失去快感和保护的世界的“外部性”。但是,这种外部性,不仅是“世界的外在性”这一生存论事实,而且是自我的情绪世界所遭遇的具体的敌对和挫折。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身体,就是各种损失、失败、敌对、挫折的历史。否定身体,其实是否定消极情形,产生积极的补偿性幻象——把一段挫折的历史重写为一段满足、圆满的历史。因此,伤害、征服他者,其实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策略,是对曾经伤害自我的那段历史施加伤害。因为他者的身体“外化”了这种“原发的反射性关系”,所以,他者的身体成为失去的自我的标志。征服、伤害、摧毁他者的欲望,揭示了自我摆脱一段挫折的历史的更基础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施虐狂对外部对象持敌对态度,同样的,萨特认为,施虐狂是与外部性、快感的意向结构的不懈对抗。
弗洛伊德早年认为,受虐狂不过是“内化”了原发的施虐关系。在推翻这一立场之后,弗洛伊德打开了把施虐狂视为与自我的外化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显而易见,萨特认为,施虐狂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对意向性的反抗(在消灭对象的欲望之中,我们的消灭所针对是依然是对象)。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理论,并不是复活“原发的受虐狂”,来作为一种解释反射性关系的方式。通过把死亡本能作为施虐狂的“原发基础”,弗洛伊德指出,施虐狂只有在它的表现中才是性爱的,而且这种破坏冲动受制于人类内在的生理构造。因为我们不再把一种本能视为施虐狂的起源,所以我们可以思考,施虐狂能否被视为一种内化的关系,把外部的摧残重复为“自我造成的伤害”,把外部的摧残内化为“自我惩罚”?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放弃了性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二元论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说,快感既不是偶然地与施虐狂有关,不是一种分离的本能力量,也不是死亡本能表达的渠道。恰恰相反,施虐行为的苦恼重复,证明了一种修复不满的历史的欲望。要想把握这种快感,需要一次回归:不是回归到本能,而是回归到具体的伤害的历史(这正是性斗争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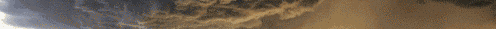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