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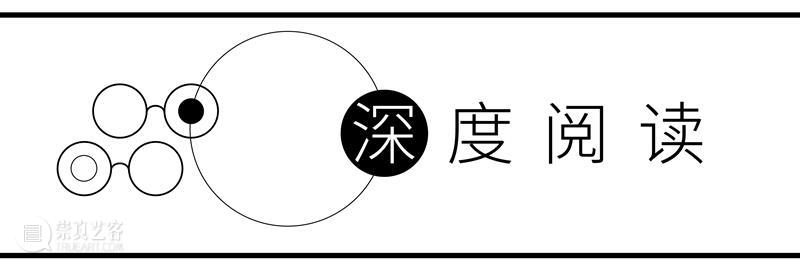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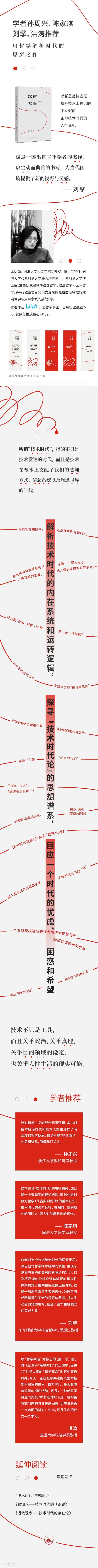
○●○●
我们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技术是工具吗?如果技术是工具,那么人类掌握了这个不断改进、加速改进的工具来增进自己的福利,岂不是既合理又最可向往的吗?技术工具论也就意味着技术中立论,因为既然只是工具,那就不涉及目的,那就意味着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有待检讨的不是技术的惊人发展,而是人类的伦理观念,有待展开的单单是目的领域的讨论,是应用伦理学。而这不正是目前我们讨论此类问题的惯常方式吗?
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一直与人类的普遍解放这个政治哲学的主题相关。早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前,基督教已经为古代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型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基督教对于技术的意义在于,它废除了奴隶经济,一度充足而廉价的人类劳动力现在变得稀缺,于是要用各种自然力来取而代之。”基督教信仰所鼓舞的解放人类的需要促进了对自然的操纵,而只有当科学—技术开始有理论、有组织地操纵自然,人类才得以进一步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现代技术兴起之后,技术与进步、自由、发展、创新和未来等典型的现代意识一起组成了我们所处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核心议题,技术进步被视为人类自由得以不断实现的物质基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力量保障。于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技术显然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与现代人类的生存理想、与整个现代性方案紧密相关的要素。而在现代性方案中,它又特别地以工具的形态呈现,正如科学以真理的形态呈现、而资本以世俗利益的形态呈现。技术工具论和中立论成了现代技术最具欺骗性的伪装,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一定要从目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以技术为工具所要实现的那个“目的”,恰恰是一个非目的论的“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借助这个看似悖谬的历史实情,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论证来反驳技术工具论:(1)运用技术工具的人事实上同时被工具化了,技术工具论因此瓦解了自身的逻辑基础;(2)取代所谓人类目的而成为现代技术动力的是这个系统的自我增长,技术工具论所预设的手段—目的论恰恰已被现代技术所抛弃。有关第一个反驳,我们可以径直引用海德格尔的论述:“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经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置——不论这个护林人是否知道这一点。护林人已经被订置到纤维素的可订置性中去了......”人自以为是这个系统的主宰,因此而持有一种工具论的技术观,可事实上,技术的本质从来不是工具。古代技术并非一种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知识形式;现代技术更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因为人自己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系统的一个环节。是我们用技术,还是技术在用我们?这个问题并非初看上去那么简单。作为人力资源的现代人和他所掠夺的自然资源一样,都是等待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开采的原料,都被不断地投入系统的高速和加速运转中去。如果说第一个反驳所针对的是技术工具论中所预设的那个特殊目的,即人类的福祉,那么第二个反驳则力图指出,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事实上的非目的论特征,一个非目的论的自我增长系统替代了一切目的论系统。增长之所以不构成目的,是因为增长之为增长是同质的和无限的。而手段—目的必定得是一个有限性系统,不能无限性后退,否则会陷入“恶的无限”。换言之,只有确定了至善,才能让一系列的目的成为目的,手段成为手段,而不至崩溃为无意义的链条。这样一个系统也必定不是同质的,因为手段目的系统有着一个朝向至善的内在秩序。而增长的无限性想象其实无法也不需要设置至善,它需要的是克服阻力,形成一个快速运转、更快运转、乃至自动无限运转的系统。而克服阻力的根本是抽象化,(1)即将事物和人类从手段—目的—至善系统中抽离出来;(2)也从具体的生活情境和视域中抽象出来; 抽象成一个个“原子”,使之可以标准化处理。这些原子没有一个世界或宇宙中的属己的位置,而是只占据一个无限系统中的空间。这个意义上的抽象化是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并且搭建了整个现代性基本架构。如果说现代资本—科学— 技术系统确实实现了人的解放,那也是从一切习俗和传统对于至善的超越性规定中解放出来,是从一切宗教和权威、从一切目的论系统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随即又将人类置入一个原子化、同质化、抽象化的增长系统。即便不说解放意味着新的奴役,也必须得说,解放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规定了人类的生活。看不清这种新的规定性,或仍然从旧的规定方式来理解这种规定性,就会导致种种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从古代到现代,转动世界的阶层从依据于某种目的论的“哲人—教士—武士”转变成了植根于一个非目的论系统的“科技精英—政治明星—传奇商人”。整个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就是告别目的论,其构造模式是(无限)增长而非(有限)善好。所以,看似“科技精英—政治明星—传奇商人” 在转动世界,其实他们也是被转动的。只不过他们在被转动起来之后,再来转动他人。他们是这个体系的传送带。他们同样服从这个体系的不断抽象化和无限自我繁殖的运转逻辑。这个系统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Ge-stell),集置即集原子间的各种订置关系(be-stellen)于一体的系统。
当斯蒂格勒说,“和手段范畴格格不入的技术体系性在现代技术之前就已存在”,他首先在吉尔(Bertrand Gille) 的意义上运用“技术体系”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是历史学的,一方面着眼于不同技术体系或系统的更替,另一方面着眼于技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联。其次,斯蒂格勒仍然坚持现代技术的独特性,他沿用海德格尔的说法,称之为herausfordernd[促逼的],他问的因而是:“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和描述现代技术特有的促逼性的体系功能?”这种“促逼”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不断抽象化和无限自我繁殖的运转逻辑”。
总而言之,现代技术决非工具,而是系统。工具论从根本上误解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是诸多非反思的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要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就必须从蕴含了手段—目的论的工具—中立论转向非目的和抽象化的系统论。这个系统的动力是资本,根据是科学,而最强有力的现实形态则是技术。故而我们将之命名为“资本—科学—技术”,技术是这个系统的实现形态,资本是其系统动力,而科学则是其知识根据。当代技术的发展,离开技术与资本和科学的勾连,是断然无法得到理解的。因为当代技术的发展机制本身绝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受到资本的不竭推动,并有着现代科学所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作支撑。分言之,则现代资本是“科学—技术—资本”,现代科学是“资本—技术—科学”,现代技术是“资本—科学—技术”。此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结构,舍弃其他两者都会使其中任何一者丧失其自身的本质,只有在这个三位一体关联中,其中的任何一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不但如此,这个三位一体结构还构成了我们当下最大的现实。它是真正在推动这个世界的力量。现代人的强力和无力、命运和危险都基于这个结构。
只有从资本—科学—技术的三位一体结构出发,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技术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我们无法在此对人工智能和生命技术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仅满足于提出一个总体上的看法,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看似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改进,可事实上是将人类更深地卷入这个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前者是从技术工具论的眼光去看,后者则是从非目的论的系统论眼光去看。前者基于现代资本—科学— 技术系统的虚假意识形态,只有后者才是看待当下技术发展的恰切视角。也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对当下急速前进的技术发展做出一种冷静的批判。如果说,人工智能还是这个现代订置系统的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生物技术,尤其基因工程就意味着人不只是作为终端被纳入这个订置系统,而且人自身成了订置的对象,原则上成了商品。基因编辑面临巨大的伦理风险,可最大的风险还不在于对个体权利的侵犯,而在于将人身上最后的自然出让给了“资本—科学—技术”系统。资本从细胞层面深入到了基因层面。相应地,这个系统所带来的最大危险并不是现代价值系统之下的伦理风险,而是更深刻的人性危险。如海德格尔所担忧的那样,人由此“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可是,恰恰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订置一切的现代主体也将自身置入订置关系之中,订置者在订置之际复被订置,登峰造极的现代主体恰又被客体化了。这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订置辩证法”。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