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现代传媒与1943年曹禺演讲
《悲剧的精神》之版本问题
彭韵 凌孟华
内容摘要:《悲剧的精神》是曹禺1943年(《曹禺全集》误作1942年)受邀演讲产生的重要戏剧理论成果,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与复杂的版本问题。《悲剧的精神》有三个版本系列,即李家安笔记版、海鸥笔记版与曹禺删改版。全面还原和综合把握《悲剧的精神》的不同版本,才能准确理解曹禺抗战时期的悲剧思想。《悲剧的精神》近八十年来的传播历程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传媒对作家演讲传播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曹禺 悲剧的精神 演讲 版本 现代传媒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2)04-0053-09

彭韵

凌孟华
► 彭韵(2001-),四川宜宾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19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传播学研习。
►凌孟华,四川宜宾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负责人,重庆市高校抗战大后方文化与文学协同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文献,特别是抗战文学与文献尤有兴趣。先后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CSSCI收录30余篇。出版专著《故纸无言》《旧刊有声》,曾获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为重要的剧作家。钱谷融先生曾在追思文章中盛赞曹禺“才华盖世”,是“为中国的话剧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艺术巨星”。[1]然而,纵观近年的曹禺研究,既颇有收获,又颇多尴尬。收获如《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发表段美乔大作《版本谱系: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谱系的建立为例》,长江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刘川鄂、刘继林主编的“曹禺研究资料长编”丛书(共十一卷)等;尴尬如期待已久的新版《曹禺全集》迟迟未见公开露面,写入《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研究方向》的“曹禺作品全编与文献整理规范研究”事实上流产等。识者在盘点关于另一重要作家茅盾的研究成果时,曾高屋建瓴地指出“研究茅盾,解读历史语境中的茅盾,依然需要我们对茅盾相关的史料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2]。沿此逻辑,可以说曹禺研究、现代戏剧研究更需要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近来看到同行对冰心1926年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的精彩讨论,[3]不由想起此前留心过的曹禺重要演讲《悲剧的精神》之版本问题。乃奋力捉管,梳理其三个版本系列并论析其背后的现代传媒影响,以就教于方家。
《悲剧的精神》是曹禺最为重要的戏剧理论成果之一,先后收入曹禺的《论戏剧》[4]《曹禺论创作》[5]和《曹禺全集》第5卷[6],以及许觉民、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论》[7]与黄健编著的《民国文论精选》[8]等。值得肯定的是,《新概念语文中学读本》第4卷[9]也选入《悲剧的精神》,惜乎缺乏对选文出处的明确交代。傅光明主编的“感悟名家经典散文”系列之“曹禺卷”(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书名就是《悲剧的精神》,封面也以《悲剧的精神》之金句为元素,可见编辑团队的慧眼识珠与高度重视。已于2001年英年早逝的重庆学者胡润森先生曾指出“这篇讲演对我们理解他的悲剧观念,进而研究他的悲剧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10]可谓不刊之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曹禺研究界,还是戏剧研究界,对这篇重要演讲记录稿的版本问题都缺乏专门的关注和研究,导致当年曹禺演讲的部分内容和相关信息长期湮没不闻,不利于曹禺行实的认识还原和曹禺悲剧思想的深入研究。以下从三个方面试作钩沉讨论。

图为曹禺先生
一、《曹禺全集》的疏漏与《悲剧的精神》之民国版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曹禺全集》是目前仅有的一套曹禺先生全集,在基本文献保障方面为推进曹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首套《曹禺全集》,也难免存在不完善之处。
《曹禺全集》第5卷第154—161页收录《悲剧的精神》,文末括注“原载《储汇服务》第25期”,并有“作者附记”称“这是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的讲词,经李安家同志记录……但我在原讲话里说‘悲剧的精神是要极端的’。这个观点,只代表我的心情,我删去了”。这就将演讲时间确定在1942年2月。
查《储汇服务》第25期,标注的出版时间却是“民国卅二年四月十五日”,《悲剧的精神》作者署“曹禺先生讲李家安笔记”。演讲词一年之后才得以刊出么?似乎不合情理。查《曹禺全集》主编田本相先生集四十年曹禺研究之大成的巨著《曹禺年谱长编》,1942年2月并无相关记载,翻至1943年2月19日,方有谱文:晚七时半,于重庆上清寺储汇大楼应邀为重庆银行界同仁进修服务社邮政储金汇业局支社讲演,讲题为《悲剧的精神》,会场“听众颇为拥挤……讲至八时半始毕”(《曹禺先生讲:〈悲剧的精神〉》,《新华日报》第3版,1943年2月20日)。讲演经李家安记录,发表于4月15日《储汇服务》第25期,后转载于《半月文萃》1943年第2卷第2期。后收入《书报精华》1945年第8期。[11]可知《曹禺全集》注释的《悲剧的精神》演讲时间是错误的,当是曹禺先生的“作者附记”出现记忆偏差,而编者一时失察。而本文开篇提及之《中国现代文论》《民国文论精选》《悲剧的精神》等收录曹禺此作的图书,也遗憾地沿袭了《曹禺全集》的错误。好在田先生在《曹禺年谱长编》中进行了不动声色的修订。
值得追问的是,“作者附记”作于何时呢?《曹禺全集》之《出版说明》末句为“最后,经曹禺先生亲自审定”,那么“作者附记”是审定全集时所作吗?查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论戏剧》,所收《悲剧的精神》文末已有“作者附记”,所记文字相同且同样没有附记之时间。再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禺论创作》,标题后有脚注“这是作者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储汇大楼对银行界‘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有关人员作的讲演”,文后括注“原载《半月文萃》1943年第2卷第2期”,也有“作者附记”,所记文字略有差别,为“这是我到重庆后在‘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的讲词,经李安家同志记录……”,末有落款“一九八四年二月”。可知《曹禺全集》参考了《论戏剧》,也延续了其时间疏误;而至少在1984年2月,曹禺已经写有关于《悲剧的精神》的“作者附记”。只是附记起初是为张有煌编《曹禺论创作》所写,还是为李致编《论戏剧》所作,尚不得而知。
查《半月文萃》1943年第2卷第2期,出版时间标注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份出版”,《悲剧的精神》作者署“曹禺讲李家安笔记”,文末括注“转载《储汇服务》第二十五期”。可知《曹禺论创作》虽然出版在后,但在此问题上并未参考出版在前的《论戏剧》,也没有按图索骥,寻找《储汇服务》第二十五期或直接标注原始出处。查《书报精华》1945年第8期,出版时间标注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果然载有《悲剧的精神》,署名“曹禺”,未标记录者。查《新华日报》1943年2月20日第3版,确有消息《曹禺先生讲:〈悲剧的精神〉》,强调“悲剧的主人所遭遇的悲哀,必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所走的道路,必须是反抗暴力的道路”。
至此,《曹禺年谱长编》1943年2月19日谱文著录《悲剧的精神》的四种民国版本,都已经一一验证补充,即《新华日报》消息版、《储汇服务》初刊版、《半月文萃》转载版与《书报精华》重刊版,显示了田本相先生广阔视野与深厚功力。
更令人佩服的是,《曹禺年谱长编》1943年5月21日谱文还有如下记载:重庆《国民公报·剧坛第1期》刊曹禺《悲剧的精神》一文,文尾注“本文经曹禺先生亲为校阅,并允在本刊发表”(文系本年2月19日曹禺对银行界爱好戏剧者的讲稿)。文中,曹禺提出“悲剧的精神是绝对积极的、热烈的、雄性的”的观点。[12]这就点明了又一个《悲剧的精神》的重要民国版本。查《国民公报》副刊《剧坛》第1期,头条就是曹禺的《悲剧的精神》。值得补充的是,原文在尾注之前,还印有“海鸥笔记”字样,可供《曹禺年谱长编》修订时参考。谱文“《国民公报·剧坛第1期》”之“第1期”或应放在书名号外面。
此外,民国报刊浩如烟海,曹禺《悲剧的精神》完全可能还有其他未被《曹禺年谱长编》著录的版本。至少笔者就偶然翻检到一种,即《成都剧刊》1943年第22期(4月26日出版)起头条连载的《悲剧的精神》,署名“曹禺讲李家安记”。前有“编者按”,称“《悲剧的精神》系曹禺先生在渝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讲演,讲词大意,本刊重庆通讯员曾简略寄来,于本刊第十六期发表,兹承曹禺先生亦[13]讲演原稿见赐甚为感谢,惟所歉仄者,本刊篇幅有限,原稿长约六千字左右,不能一次发排完竣,特分三期刊毕”。遗憾的是,《成都剧刊》第22期和第23期漫漶比较严重,第24期无缘寓目。浏览所见二十余期《成都剧刊》,未见编辑者及发行者署有姓名。有研究者指出“发行人裴心易”,[14]不知所本何处。创刊号发表有《表叙一番》,署名编者,结句为“在本刊出版之初,谨略陈数语于上,敬献给我们亲爱的爱好戏剧研究戏剧的同志们和我们亲爱的读者”。但更见编辑者个性风采的应是第九期的一段《编余小言》:“前已一再申明,同人创办本刊,纯系要[15]护戏剧,地盘绝对公开,欢迎同[16]志参加,既要揭善,复不隐恶,好的要捧,坏的要说,经费全是自筹,不要任何津贴,态度十分超然,不偏不党□[17]暴露,敢建议,敢批评,至于执笔同人自幼束发读书,颇知廉耻,那些捧角儿,靠角儿,享角儿之利,用角儿之钱之类,都是贤者不为,为者不贤的知[18]当,我们当然不会干的,恐有鱼目混珠者,兹再重言了。”[19]“讲演原稿见赐”,可知这位目前不知其姓名的编者与曹禺的密切关系,以及文本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版本系曹禺之演讲原稿,那么他和《储汇服务》版的细节差别就值得注意了。比如第一段,《储汇服务》版作“我们晓得那个人不想避开眼前困难,以谋他的升发之道”,《成都剧刊》版“道”后有“呢”字及问号,为反问语气,表达更为有力。再如第二段,《储汇服务》版作“一是抛去个人利害关系的”,《成都剧刊》版“是”后有一“要”字。参考《储汇服务》版后文“第二个要素,是要绝对主动的”,则有理由认为“抛去个人利害关系的”前面也应有“要”字。同时,这则按语还披露《悲剧的精神》另有《成都剧刊》之消息版。查《成都剧刊》第16期(3月8日出版),果然有消息题曰《悲剧之精神》,可惜内容难以辨识。《成都剧刊》这样的地方性区域性戏剧刊物,目前学界少有关注,但其意义不容小觑,那就是值得重申的“大后方成都的地方性刊物,包括文学期刊与《新新新闻每旬增刊》这样的非文学期刊,都有着重要的中国抗战文学之‘地方路径’意义”。[20]期待更为清晰可辨的《成都剧刊》及其第24期早日浮出水面,期待同好破译《成都剧刊》的编辑阵容,有以教我。
二、 《悲剧的精神》重要版本差异略说
也许是囿于体例,《曹禺年谱长编》对《悲剧的精神》的版本差异未置一词。事实上,前述几个重要版本均存在明显的差别,值得仔细梳理比对,甚至汇校注释。限于篇幅,略加说明如次:
(一) 最完整版本:《储汇服务》版。此版副标题为“本局同人进修服务社第八次特约演讲词”,比《半月文萃》版副标题“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讲”、《国民公报》版无副标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即系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的“特约演讲”,而且是“第八次”。此前有叶元龙讲《当前物价问题》、甘乃光讲《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之趋势》、老舍讲《青年与文艺》、冯玉祥讲《银行界同人与抗战建国》、章乃器讲《歧途与出路》等。此版第一段“诸位先生,不仅是主席觉得抱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抱歉。因为我所要讲的,谅来都是些不关重要的话,却要劳动诸位挤在这里听讲。真是一面觉得荣幸,一面也觉惶恐”,就是《半月文萃》版、《国民公报》版和《曹禺全集》版都没有的内容,是可贵的曹禺演讲之开场白,显示了剧作家的谦逊和气与娴熟的演讲技巧。此外,此版还可还原一些《半月文萃》版转载时产生的异文,包括衍文、脱漏和标点差异等,比如“即如有一个公务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坠楼而死了”原文为“即如有个公务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坠楼而死了”;“可是恺撒以为他们的权势是神给他的”原文为“可是恺撒以为他的权势是神给他的”;“心究竟不比木石”原文为“人心究竟不比木石”等。还可补充的是,《储汇服务》第24期(3月15日出版)“社务动态”另刊有消息《曹禺先生讲悲剧的精神》。
(二) 最简要版本:《国民公报》版。此版正文仅1500余字,而《储汇服务》版有5800余字,《半月文萃》版5700余字,《曹禺全集》版5100余字。显然《国民公报》版篇幅最为短小,没有展开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布鲁特斯之例,以中国历史上的屈原为例也比较简洁,阐发支持悲剧人物之精神的四个要点也更为简明。《曹禺年谱长编》关于《储汇服务》版“后收入《书报精华》1945年第8期”之表述,其实不准确。《书报精华》1945年第8期转载的乃是《国民公报》版,只是未准确说明原刊信息,还漏掉了记录者“海鸥”之署名。有意思的是,《国民公报》版并不是《储汇服务》版的简单删节,而是记载了一些《储汇服务》版没有的内容。比如开篇第一段末尾的“所以悲剧永远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只有那些不甘于事事妥协,不避开严重的试验的人,才会成为悲剧的扮演者”;在以“棉花”为喻,形象表达某些人“打下去根本不起一点反应”之前的“我们知道钢这个东西,需要同样硬的东西夹击它的时候,才知道它是硬的”(“钢”字在《书报精华》版作“铜”,或系转载时误植);以及“极端的表现,就不免愤世嫉俗”“怡然自得那都是有福的人,因为他永远成不了悲剧”等等。特别是整个末段:“欧美的科学家,常常是家传数代,世袭的去研究一种学术,的确是具有一种悲剧精神。不计成功,先不怕失败,则是非才能看得清楚。所以,我说悲剧的精神是绝对积极的,热烈的,雄性的”,都是《储汇服务》版所无且未见学界披露的曹禺先生精彩、明确、风趣的重要戏剧理论主张。这些掷地有声的精彩内容若是真如末尾所言“经曹禺先生亲为校阅,并允在本刊发表”,则无疑是李家安笔记之《储汇服务》版的重要补充,值得特别关注。
(三) 最通行版本:1984年2月删改版。不论是最完整的《储汇服务》版,还是最简要的《国民公报》版,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一直都没能得到有效的整理和传播,只是封存在发黄的民国报刊之中,藏诸图书馆或数据库,有缘摩挲翻阅的读者非常有限。因而真正通行的是曹禺先生1984年2月删改版。此版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等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曹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21]作者附记点明删去的原话“悲剧的精神是要极端的”,实则并未出现在李家安或海鸥的记录版本之中,只是有类似的意思表达。李家安笔记版出现“极端”4处,海鸥笔记版使用“极端”3次,而删改版已经把“极端”处理得干干净净。删改版还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除恺撒外的主要人物名字之音译进行了调整,“安东尼”替换了“安多尼”,“勃鲁托斯”代替了“布鲁特斯”,“凯歇斯”取代了“开达”。删改版的表达调整就更多了,不少句子近乎重写。比如《曹禺全集》版第二段,“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类人,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讨生活,不想国家的灾难,不愿看人间的悲剧,更不愿做悲剧中人物,终日唯唯诺诺,谋求升发之道,取得片刻安乐,对一切事物都用一副不偏不倚的眼睛来揣摩,吃饭穿衣,娶妻生子,最后寿终正寝”[22]就是一个好例。较之《储汇服务》版的“我所以选择它作为我的讲题,就是因为我见到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中活着的,平时就不喜爱极端,自然也不喜爱悲剧。我们晓得那个人不想避开眼前困难,以谋他的升发之道,最低限度他也可在小我范围中求得他的安乐,反正依着一种平坦不偏不倚的路向前进就是了”,[23]可以说是已经重写。材料显示,曹禺删改之际,还随手增加了一些表达。比如《曹禺全集》版第三段:这自然是“悲剧”,一个庸人的“悲剧”,就不曾出现在此前的几个版本之中。统计总体篇幅,《悲剧的精神》之《曹禺全集》版也较之《储汇服务》版少了700余字。
总而言之,曹禺演讲记录稿《悲剧的精神》呈现出三个版本系列:《储汇服务》版、《成都剧刊》版与《半月文萃》版是第一个系列,系李家安笔记;《国民公报》版和《书报精华》版是第二个系列,系海鸥笔记;《曹禺全集》版及其之前《论戏剧》版、《曹禺论创作》版与之后的沿袭版本是第三个系列,系曹禺删改。准确理解曹禺抗战时期的悲剧思想,就应该还原到前两个版本系列,在其版本谱系中进行综合把握。
三、 版本变迁背后的现代传媒影响刍议
从1943年2月19算起,曹禺演讲《悲剧的精神》至今已近八十年,其复杂多样的版本谱系与几次重大的版本变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传媒对作家演讲传播的影响。
(一) 现代传媒改变传播形式: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众所周知,传播形式是指传播者进行传播活动时所采用的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方式,如口头传播形式、文字传播形式、图像传播形式和综合传播形式等。[24]1943年2月19日,曹禺在重庆上清寺储汇大楼演讲《悲剧的精神》,是对现场“颇为拥挤”的听众进行口头传播,在一呼一吸之间一字一句地传达自己关于悲剧的精神之深入思考,采用的是声音符号。《储汇服务》《成都剧刊》《国民公报》《半月文萃》《书报精华》等现代报刊传媒介入之后,就改变了传播的方式。编辑将李家安或海鸥记录的演讲内容进行加工处理,进而借助印刷技术,将演讲内容印刷在报刊之上白纸黑字地与广大读者见面,采用的是文字符号,属于文字传播。演讲者只有曹禺一人,口头传播的信源是单一的,但是记录者不同,就会在记录过程中产生一定偏差,甚至加入某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导致了不同版本系列之间的明显差异。在同一版本系列内部,也会因为原版文字识读与新版编辑排印过程中的失误或瑕疵而形成新的文字标点差别。如果没有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及其周边较为发达的现代传媒业的影响,就不会有这么多媒体的介入,也就不会形成如此复杂的版本变化。
(二) 现代传媒影响传播方式: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曹禺先生1943年的《悲剧的精神》演讲是应“本局同人进修服务社”特约进行的活动。“本局”应指重庆储汇局,全称应该是“银行界同人进修服务社邮政储金汇业局支社”,具体操办者为文化股,股长冯克昌。[25]不论是“银行界同人进修服务社”,还是“邮政储金汇业局”,或是“文化股”,都是典型的社会组织,只是大小不一而已。“特约演讲”,其实是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进行内部成员(群体)间的交流信息,丰富文化生活的活动。曹禺的演讲本身,其实也是组织行为,是先生面向同人进行的有组织的信息交流传播,属于组织传播。即便“拥挤”,也并非向广大社会大众开放。但在行业传媒《储汇服务》、专业传媒《成都剧刊》,特别是大众传媒《国民公报》《半月文萃》《书报精华》等参与之后,已经完全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属于大众传播。曹禺先生的《悲剧的精神》,也借助现代印刷术和传播媒介出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其间每一个现代媒体的介入,往往都会带来曹禺演讲信息的损耗或增值,从而形成《悲剧的精神》之诸多不同的版本形态。
(三) 现代传媒延伸传播链条:从新闻稿到记录稿,从连载到转载,从民国到新中国,从编入个人作品集、全集,到编入多人精选集、教辅资料。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充分发挥其基本功能,即麦克卢汉所谓“储存信息并加快信息传输”。[26]现代传媒最迅捷的产品是新闻消息。目前所见的相关新闻稿至少三种:《新华日报》次日就发表演讲消息,拔得头筹;《成都剧刊》3月8日刊出重庆消息,扩大传播;《储汇服务》3月15日发表活动资讯,持续报道。新闻稿之后,现代传媒推出更翔实的记录稿,继续深度传播。李家安笔记的完整版,首先有《储汇服务》4月15日初刊,然后有《成都剧刊》4月26日重刊,再有《半月文萃》8月份的转载,传播链越来越长。海鸥笔记的简要版,则有5月21日重庆《国民公报》的首刊,以及两年后(1945年8月20日)《书报精华》的转载,传播链条更长。而真正经典的生成,往往并不会因为政治的变迁而中断。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述《悲剧的精神》的民国版本继续在报刊中得到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传媒,继续延伸着《悲剧的精神》的传播链,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果说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戏剧》、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曹禺论创作》、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曹禺全集》与京华出版社2005年出版散文集《悲剧的精神》是在曹禺个人作品集、全集中传播《悲剧的精神》,那么201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论》、2014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民国文论精选》则是在多人合集、在现代文论精选集中接力《悲剧的精神》的传播和经典化。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新概念语文中学读本》选入《悲剧的精神》,则是将传播渠道拓展到了中学生语文教辅读物之中,其影响不可小觑。这些传播路径,是曹禺先生当年难以想象的。越长的传播链条,意味着《悲剧的精神》越复杂的版本变化。曹禺1984年修改版近四十年的大陆通行与一枝独秀,也折射着现代传媒的膨胀、沿袭与遮蔽问题。
总之,以上简要梳理了曹禺1943年演讲《悲剧的精神》的复杂而漫长的版本变化过程及其版本变迁背后的现代传媒影响,可以为现有曹禺研究、戏剧研究,乃至传媒研究形成补充和参考。如何处理三个版本系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对新编《曹禺全集》操刀者之编辑智慧的考验。更为详尽的汇校处理与深入的传媒影响分析,尚有待来者。我们也相信,“研究不同时代异文的版本形态、出版过程与传播情况,将异文呈现的物质形态与其背后组织过程也纳入考察视野,将版本谱系和版本校勘视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将为现代文献学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地”。[27]进而言之,这样的工作,对于现代戏剧研究,尤其是现代戏剧文献学研究其实更为紧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抗战大后方文化与文学研究协同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彭 韵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钱谷融:《曹禺先生追思》,《钱谷融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
[2]杨扬:《茅盾研究点滴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3]乔世华、田泥:《冰心的悲剧观》,《四川戏剧》,2021年第10期。
[4]曹禺:《论戏剧》,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4—123页。
[5]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97—305页。
[6]曹禺:《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54—161页。
[7]许觉民、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论》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5—623页。
[8]黄健编著:《民国文论精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379—386页。
[9]吴康主编:《新概念语文中学读本》第4卷,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第119—127页。
[10]胡润森:《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1]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12]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长编》,第323页。
[13]原文如此,此处疑脱一“以”字,或“亦”为“以”字之误。
[14]王绿萍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0页。
[15]原文漫漶不清,或应为“爱”。
[16]原刊作“周”,明显有误,改之。
[17]原文此字漫漶至空白,以“□”代之,疑为“敢”字。
[18]原文如此,或应为“勾”。
[19]《编余小言》,《成都剧刊》,1943年第9期。
[20]凌孟华:《新见夏衍力作及其记录的重要广州大轰炸史料——由“隐现”而“消失”的佚文〈在轰炸中生活〉脞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21]袁联波:《论曹禺戏剧序跋的“对话性”及其演变》,《戏剧艺术》,2021年第1期。
[22]曹禺:《曹禺全集》第5卷,第154页。
[23]曹禺先生讲、李家安笔记:《悲剧的精神》,《储汇服务》,1943年第25期。
[24]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25]《银行界同人进修服务社邮政储金汇业局支社社务动态》,《储汇服务》,1942年第19—20期合刊。
[26][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27]段美乔:《版本谱系: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谱系的建立为例》,《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戏剧艺术》是一份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戏剧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内容希望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尤其期盼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来稿篇幅在万字左右为宜,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本刊实行在线投稿。在线投稿网址:
http://cbqk.sta.edu.cn系本刊唯一投稿通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刊不接受批量投稿(半年内投稿数量大于1则视为批量投稿),更不可以一稿多投。
本刊审稿时间为3-6月,审稿流程含一审、二审、三审、外审等,最终结果有退稿、录用两种情况,其他皆可理解为正在审理中,敬请耐心等候。如有疑问,可致函杂志公邮theatrearts@163.com,编辑部将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附:《戏剧艺术》稿件格式规范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参考2020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① [专著]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② [期刊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③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④ [报纸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
⑤ [外文版著作、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芝加哥格式: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名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
6.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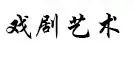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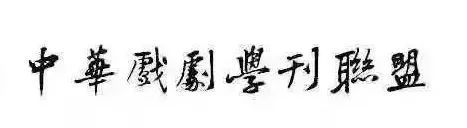

制作:陈婧
责编:计敏
编审:李伟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