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度
胡赳赳 著
选自《跨媒体新论:世界建构》,2022年
跨媒体意义上的“世界建构”发展实在太快了,它总是倾向于“加速”。在这种加速的传感过程中,人的“生物节律”与智能设备的“机械电子节律”是不匹配的。电子节律遵从于摩尔定律,迅速更新迭代,加速抛弃,疾速升级。而人的生物节律则显得老迈而从容,其遵从的是日光与黑夜带给我们的“醒-睡”节律。人的节律不可能24小时全方位开启活跃状态,但电子节律可以,不眠不休,因为金钱永不眠、欲望永不眠。电子节律正是受欲望支配的产物。或者说是少数人的欲望,宰制世界者的欲望。因为电子节律可以通向奥林匹克诸神,那个宙斯之神,获得无穷的神力,以速度优势进入一个更高的维度,于是芸芸众生便被电子奴役在一个低维度的生活场中。想进入更高维度,必须要购买电子设备、智能装置,这便是高维度宰制者给低维度渴求者设下的通行证。
早在1980年代,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便观察到速度带给人的“困惑”。他敏锐地意识到:“运动(mouvement),社会或政治的运动,和速度的运动具有相同的特性:以速度清除思考。于是,在超高度的速度政权之下,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只剩下反射动作。”[1]
为了让被奴役者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奶头乐”这种臭名昭著的媒介产品被发明出来了。这种产品意识到人类对“跳跃的光电刺激”具有本能的受惑性。只不过如今,这种跳跃闪烁的光电刺激,由电视屏幕变成了手机屏幕以及VR全息场景。还是那个比喻,家猫对眼前的飞虫绝对不会视而不见。保罗·维利里奥将这个群体——现代人——描述为“失神癖”。生活在高速景观化的社会,自动会掉入“记忆扑蝇器”之中,就像家猫不停地打那个飞虫。于是现代人的大脑黏成一团、毫无反省的间隙,以及借助使之失神的资讯,落入宰制者的陷阱。维利里奥预言说:“我们继续加速到超音速甚至光速,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都是不可能的最后,速度的暴力连思考和反省能力都消除了。”[2]
显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麦克卢汉的忠告:“媒介对现存社会形式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度和分裂。”[3]在《理解媒介》一书,麦氏警觉地意识到“今天的加速度趋向于全方位”。[4]这指向了“速度”与“节律”带给人类生活以巨大冲击力的本质:“人们在试图使原有的物质形式适应新型的、更快的运动时,开始感到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慢慢在枯竭。”[5]
因此,在我们一方面对“世界建构”抱持激动人心、乐见其成的大胆欢呼之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该为此忧心忡忡,并不知道“加速度”会把人类“形塑”成什么样子。对柏格森(Henri Bergson)来说,思考的前命题必须要有时间的绵延,没有时间就无法思考,也就是说,思考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时间的绵延。然而,新的世界建构带来两种抽离效果:一是时间被抽离和压缩了,个人没有思考的可能;二是由于速度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现实接触被抹除了。
这两种蔽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新的世界建构,我们有理由保持清醒的警觉——个人不再反思;个人与他人不再有现实接触。这多多少少是个悲观的结论,但的确是在这个跨媒体结构中,我们对未来现象学抱持的一种告诫态度。如果我们一旦不能通过世界建构去求真,那么我们就将走向它的反面,层层遮蔽,直至黏成一团,毫无反省的可能,最后成为失神癖患者。
我们也能看到世界建构型的跨媒体艺术家,正是对世界建构抱有相当程度的反思:技术将往何处去?尽管跨越了多种媒体形态,但求真的本质是否在这场较量中取得胜利?人类是否会迷失在“速度”与“时间压缩机”之中,自我的节律是否会进化为机器的节律?“失神的当口”是否会成为精神成长的某个契机?
在这层层叠叠的迷雾中,哲学家斯蒂格勒对“何为世界建构”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在他看来,有些世界建构之所以不成立,是意图去简化这个世界,而简化的冲动则会使个人脱离于共同体,个人参与世界的快感被稀释了,因而缺少一种“共同默契”。世界建构在于产生社会维度,而社会维度需要的是复杂性、复杂化和默契。因此,作为跨媒介的电脑游戏是最好的世界建构过程:“游戏变成了一个不只是复杂性的操作者,而且是默契:共同投入、复杂化、难度、验证,都有一种社会的维度。”[6]
简单化生活即意味着贫乏化生活,因此,我们都渴望产生丰富性的部件,为接入世界、联接他人提供情感的条件、技术的支持和器官的延伸。简单的游戏往往会使人很快乏味,正是由于简单的游戏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复杂性程度较低。如果一个哲学家愿意住在贫乏的乡下,是因为他为了使自己大脑中复杂性的图景得以写作与展现,而必须将“生活”重置到原始初置的状态,从而将世界建构以精神生产的方式呈现出来。
斯蒂格勒将“世界建构”表述为“一个生产默契的装置”。共同投入、熟悉性、情感条件决定了这种默契在共同体之间的交融和兴起。他说:“一个生产默契的装置,创造了一种对文化的附属感。”[7]
在一个世界建构中,我们称一个对象是有文化的,则意味着它不是可随意丢弃的,而是有价值的,意味盎然的。斯蒂格勒接着说:“这样的装置,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可持续性,带来的不只是快感,而是欲望,也就是说,一种上升经历的分享:也就是说,升华的装置。”[8]
在这里我们要回过头来,对“何为跨媒体”作一番探讨,并且对其概念的历史性沿革作一番梳理,同时也要指出,“跨媒体”为何在今天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它必须延舒展它的外延,以求得更大的涵盖与生机。
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跨媒体产生于二十世纪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在中介性、媒体间性(intermediary)的构成意义上,它最初的语义留存在英文文献中,那么其源头有可能产生于17世纪,因为在英语的文本中,这个词被发明了出来,用以解释某种科学性、空间性的、对象之间的构成。它指的是——某物在空间或时间上是居间的,或介于两个对象之间的。也就是说,这个词汇最初是关于某种科学的定义,它为了解释一种位置——一种准确的位置和相互构成的关系而存在。
这个术语也应用在物理与化学的领域中,相对而言比较好理解,它是指通过空间传递能量的一种居间的媒介。而这个语词的移置,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迁移,一直要等到一个诗人的灵感诞生: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于1812年站出来了,是他率先把这个术语“intermedium”进行“挪用”到其文学实践的文本,藉此表达作品中“对其他门类艺术效果的虚拟追求”,以及将隐喻(allegory)定义为特殊与一般之间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感”“互文”与“媒体间性”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产生了,它们互相指涉、相映成趣,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切入角度与侧重点。
在当代意义上,“跨媒体”一词出现在1966年的《跨媒介(体)》一文中,“Intermedia”被首次提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激浪派艺术家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这是一次令人激动人心的描述,因为这预示着一门学科和一种技术飞速发展的可能。艺术家总是具有某种高度预见性,他认为由单一媒介制成的物体正在消亡,转而支持混合工作。
迪克•希金斯认为:首先,跨媒介是一种空间上的“位置”,这个位置介于两种实体之间或两种媒介之间(inter)。显然,这是旨在强调媒介之间的“交互式思辨关系”。其核心问题则是——新发现的方法如何可能——被我们恰当和明白地使用?
然而这个方法很好的应用于对当代艺术的一些辩析和讨论。这种“间性”的媒体效果,如同手术刀剥开了表皮,使得血管和神经的走向清晰可见,也由此能梳理出作品内部空间的构成和系统走向。比如,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便可以理解:现成品艺术不再那么直观了,它有其内在的逻辑与复杂性,它属于“艺术媒介与生活媒介之间的跨媒介”。如杜尚的现成品则介于“生活媒介”和“艺术媒介”之间,却仍然令人着迷。同样,约翰•凯奇的《4分33秒》相当于一个默声装置,它探索的是“音乐与哲学之间的跨媒介”,或者说通过一次无声的演奏,人们获得了跨媒体的感通效果,从音乐进入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得到了一次小小的重新建构,正是由于跨媒体始终倾向于在世界搭建的过程中提供路径生成,于是跨媒体艺术便如此令人着迷,并且走向其复杂性。
也由此,“跨媒体”引入了“复杂媒体”的特点。这个我们知道,跨媒介相对于纯媒介而言,不仅多了“复杂性”,也多了“生态性”。而生态性正是建构复杂世界的一种指标。如果没有生态性,事物无法自如从底部涌现。
跨媒体起初的想法是好的,它旨在打破等级化的纯媒介艺术观及其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但随着跨媒体技术的超速发展,这个论断如今可能已经失效了。因为它或许又重新建构起新的不平等与新的压迫——对于不会使用跨媒体技术的人士而言,失去生态位的状况已经正在发生。
在跨媒体艺术发展的早期,跨媒体由于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因此其内涵促进解放了艺术品的“物性”。使得艺术品展示出不一样的状态,事物迁移、扭转然后又回归、融合。这种编码的过程,使得艺术的创造力得到了爆发。希金斯认为,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尊重这种跨媒介的概念。而且,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未来跨媒体的早期阶段。其时,跨媒介艺术在越界的冲动下,突破了艺术品的雅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藩篱。这是跨媒体艺术阶段性的功绩,它将不同层次的艺术欣赏者整合到具体的艺术品空间中。
无论是柯勒律治还是希金斯,他们具有功不可没的成绩,正在于将这概念由“自然科学领域”的引用转入到对“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中来了。他们二人藉此来解释“文学”和“艺术”。假若没有这次概念上的引流,我们也不会有“跨媒介文本”“跨媒介转换”“跨媒体艺术”这些词汇。世界建构首先是一个概念,其次是对概念的阐释和实践应用。它也有可能是反过来,世界建构首先是一种寻找,一种突破意义的寻找和搭建,然后是对这种寻找的总结和归纳。
在跨媒体概念诞生的初期,它的应用场景开始走向综合艺术、空间艺术,或者说是这种艺术趋势,使人想到了跨媒体概念。跨媒体与艺术具有最早的默契关系。因此,无论跨媒体理论如何发展,它和艺术的关联度根深蒂固,具有血缘般的联系。对它的研究也最早是由艺术实践发展而来的,它看起来具有“剧场化的(theatrical)”的效果,或者说,剧场与空间艺术最适合跨媒体艺术的展露。跨媒体艺术的迷醉特点正在于,各种艺术之间的藩篱正在消失,各种艺术本身终于滑向了某种“最终的、闭塞的、高度称心的综合”。当艺术家试图用综合材料进行创作时,跨媒材便诞生了。但其目的是为了关注媒介间性还是仅仅拼凑起来为艺术图像服务,却产生了不同的艺术分野。后者的意图可能很难称得上是跨媒体艺术,而仅仅是综合材料的艺术。
我们乐意相信,跨媒介是一种艺术形态,因为它最初便是由艺术家指认出来的。然后被媒介理论所借用。所以说,跨媒介经历了自然科学,然后转移到艺术学,最后为社会学中的媒介理论所重视,成为一个跨媒介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说,跨媒介传播学理论和跨媒介艺术学理论之间,本身就有近亲的关系,如果说谁要将其截然分开,认为两个学科应该井水不犯河水,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二者的水源来自于一处。而且将来,跨媒体理论会跟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理论走到一起,用来阐释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前景下,跨媒体与“后人类”之间所具有的美学关系、伦理关系和媒介转换关系。
封图:The Maximum Speed of Raphael's Madonna,
Salvador Dali,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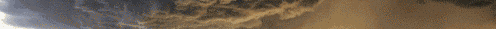
注 释
[1](法)保罗·维利里奥. (2018). 消失的美学 (杨凯麟, Trans.).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法)保罗·维利里奥. (2018). 消失的美学 (杨凯麟, Trans.).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3](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2019).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55周年增订本 (何道宽, Trans.). 南京: 译林出版社.
[4](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2019).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55周年增订本 (何道宽, Trans.). 南京: 译林出版社.
[5](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2019).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55周年增订本 (何道宽, Trans.). 南京: 译林出版社.
[6]贝尔纳·斯蒂格勒. (2020, August 21). 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22, from 悼念 |贝尔纳·斯蒂格勒:快感、欲望和默契 website: http://intermediart.caa.edu.cn/2020/08/21/
[7](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2016). 人类纪里的艺术 : 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陆兴华 & 许煜, Trans.).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8]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2016). 人类纪里的艺术 : 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陆兴华 & 许煜, Trans.).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