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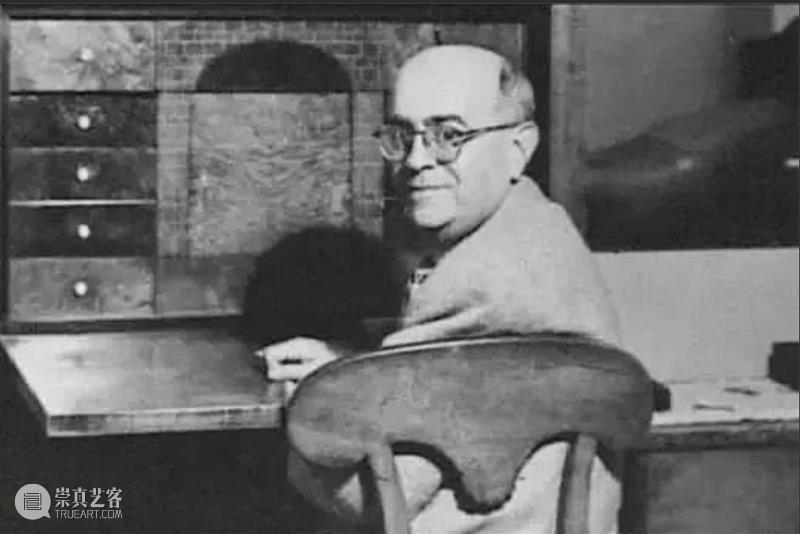
阿多诺与现代性的终结
马克·吉梅内斯丨文 王名南丨译
选自《当代艺术之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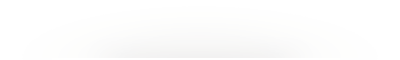
“我对他充满敬意……我们在很多方面观点相同。他为美国犹太协会工作,我在《评论》杂志,我们的办公室在一起,为之奋斗的事业也相同。”格林伯格这样描述他在1940年代中期与阿多诺的相识。
一位是美国艺术批评家,一位是移民美国的德国哲学家,两人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自1930年代末开始,他们都对前卫派艺术持支持立场,也都猛烈批评文化的资本主义商业化,批评标准化的文化副产品在中产阶级阶层——资本受益者——中的传播。此后很快,两人的观点分道扬镳,却又在1960年代末殊途同归。面对艺术创作的新潮流,他们的现代主义理论都不再适合,这需要我们在此仔细审视。
如果说同格林伯格一样,阿多诺也希望防止文化被“廉价甩卖”,抨击那些劣质的、非真实的“替代品”,与取悦大众的“媚俗”做斗争,两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
我们曾经谈到,现代主义、纯粹主义的理论倾向排除一切明确的或隐含的政治与社会参照。对格林伯格而言,支持前卫派并非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对所处时代的独裁统治进行反抗,例如并非要批判纳粹主义对现代艺术家的迫害。在他看来,前卫派将从其自主性、非政治性中获得力量,从而避免对某种偏狭教条的臣服。
阿多诺同样认为艺术不能直接传达任何政治信息。但他对现代艺术以及对某些晦涩作品的维护,却可以被纳入更大的斗争框架之中,即对纳粹和斯大林极权体制下文化清算意图的反抗。如果说1920—1930年代前卫派的形式革命使既有的、资产阶级的、传统的秩序为之愤怒,恰恰是因为这场革命并非在纯粹形式的层面上发生。对于阿多诺而言,形式等同于内容,或者进一步说,形式即内容本身,其意义尤其涉及历史与社会。面对《格尔尼卡》,阿多诺感知到的并非如格林伯格一般是“黑灰一团”,而是在野蛮行径中被肢解、撕裂的人体。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不难看出他们二人的分野:一边是康德式的、形式的、形式主义的观念,建立在主观趣味判断的无谬性之上;另一边则是黑格尔式的观念,将一贯反叛现实的艺术所蕴含的观点、意义、内容视为至高无上。格林伯格赞颂抽象表现主义,以推广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的、严格的艺术形式,他坚信现代主义绘画有朝一日终会呼应美国社会的最高愿景。如此艺术与社会的和解论,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阿多诺时常强调,每种艺术都需要止步于其自身表达手段的边界之内。直至1960年代,他才提到艺术门类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或“边界模糊”,尤其是指后勋伯格式的当代音乐与绘画之间。除了暗中向凯奇的致意,阿多诺不遗余力地从总体上批评那个时代的一切艺术运动,如原生艺术、反艺术、行动绘画、偶发艺术等,认为它们都从根本上质疑着艺术与作品的概念。
阿多诺的核心关注点是艺术在后工业社会中的地位。他明白文化体系的深刻变革不可逆转,很可能危及艺术创作的生存,正如审美理性在工具理性面前不得不让位一样。在他看来,未来的艺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表达历史中“积淀的对苦痛的记忆”。
阿多诺晚年幻灭的观点,以及1970年之后格林伯格的低调,以不同方式显现出他们的尴尬处境,即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已经不符合当时通行的现代艺术标准规范。例如1969年泽曼在“当态度成为形式”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就完全无法套用格林伯格或阿多诺的闸释模式。该展览揭示出以往那种线性、连续、进步主义的现代性建构已经失效。在这种建构中,艺术史会被看作是从马奈到波洛克,中间经由塞尚和毕加索的“一连串作品”的总和,从头至尾不打磕绊。
在美国,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被视为精英主义的、教条的,它与文化艺术界现实的潜在脱节在1970年代逐渐显现。极简艺术、波普艺术、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和超写实主义与新拉奥孔没有什么干系。不同艺术之间的传统边界被轻松跨越,远远超乎“诗同画”的准则。而摄影、电影、录像等技术媒介也越来越多地与古典表达相结合。
在欧洲,总是和美国对着干的时代过去了,前卫派已经国际化。巴黎不再抱怨失掉了艺术统治地位,而前卫艺术对现代艺术的“盗窃”看上去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偷小摸。
阿多诺的观点在《美学理论》(1970年在德国出版,1974年在法国出版)一书中得以闸明,严密、精辟的论证令人折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导向一种悲观的甚至警钟式的闸述,艺术在商业环境中幸存,而其所处社会越来越被经济准绳管控。尽管如此,在多数西方社会都开始大范围实现文化民主化的时代,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与现代性两位伟大理论家早先表达的愿望相反,现代的、前卫的艺术既没有战胜被格林伯格羞辱的“媚俗”,也没有战胜阿多诺厌恶的文化“次品”。整体看去,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热烈维护的现代性本身已经过时了。
阿多诺对艺术的思考同时也受到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困扰。的确,如果说他将艺术看作个人的最后逃避所之一,看作个体的抵抗平台,那么,他并未使之成为陷入非理性的主观性的首要表达场所,更没有从任何形而上或神秘的角度看待艺术创作。艺术呈现了“另一种”理性,而非是理性或合理性的“他者”。何况,为了跟上其时代(即现代),借用兰波的说法是“激进的现代”,艺术还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技术、工业的合理性相联系。阿多诺说,艺术需要适应其时代的技术标准,否则就会倒退。然而,如果艺术自身便建立在严格的合理性之上,它又如何抵抗主流的合理性呢?
让我们短暂地回到阿多诺理论的这块真正的绊脚石上来。阿多诺最主要的参照是现代艺术,从工业革命时代发端直至1960年代。那是在材料、程序、形式上渐进并趋向合理化的艺术,一点一点地超越成规和传统经典。在西方,这种合理化进程从文艺复兴便开始了,触及到各种艺术形式。工业革命加速了这一从种种陈规中解放的进程:模仿、对自然的忠实再现、透视技法或音乐调性的“自然化”规范。现代时期,艺术创作也应该是现代的,在阿多诺看来——重新使用他的马克思主义语汇——艺术生产的力量与非艺术生产的力量相辅相成。
然而先前的问题又出现了:假使艺术融入主流的合理性,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理性,它又如何保持对于现有社会的反抗、争鸣与批判特性呢?艺术与日益精致、技术高度复杂、和科技进步同步的文化产业生产又有何区别呢?这种艺术在被吸收、工具化、商品化和消费之后,难道不会与其他一切文化产品一样,变成其本该批判的“物化”的牺牲品甚至同谋么?
在阿多诺看来,答案就在于艺术本身的模糊属性,即艺术既是自主的,又归属于社会现实。艺术创作和艺术品是自主的,因此不受将人类活动整体导向合理化、可控化、利润化社会的科技与商业决策的制约。正因为此,尽管艺术的存在及其特性已经受到威胁,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它。
但同时,艺术创作与艺术品还归属于社会现实:艺术形式与材料浸入历史与社会之中。艺术始终可能被整合到特定社会、特定时期主导的文化表达形式中。
结论如何呢?
只要我们考虑到阿多诺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矛盾与悖论便可以轻松获得解决。
不过这一有关现代艺术的理论(处在现代艺术的末期)宣告着现代性的新阶段,即所谓“后现代性”((Postmodernite)的开启。它标志着宏大审美论述的终结,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是各种宏大的社会政治、人文主义和意识形态话语统统失效的时代。
正如格林伯格将绘画的自我纯粹化观点树立为一种有关现代性的普遍观点,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也反映出其历史局限性,因为他显然不可能承认(哪怕由其前提来看),现代性可能会将其自身动力应用到反对自己之上。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