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的前言和后记(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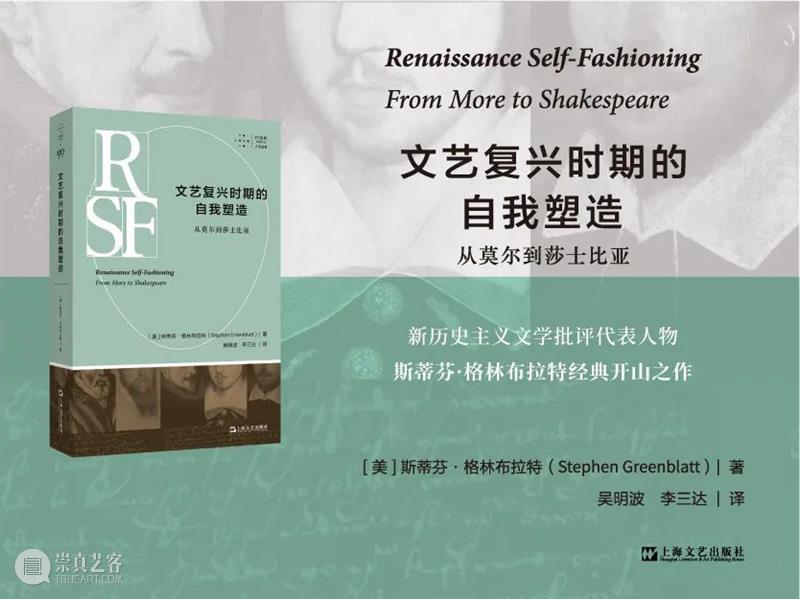
此书目前已上架拜德雅微店进行预售,欢迎大家前往微店预订,预计11月7日前发货,感恩大家的支持。
前 言
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是让我第一次找寻到自己的声音的著作,我本应愉快地宣称这本书是我根据总体规划所做出的深层次结构设计的结晶。但不幸的是,它并不是。这部书的出版有某种偶然性,缘于我职业生涯早期的偶然机会。我曾两次收到英语学会(English Institute)的邀请,这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在热情而又挑剔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说,这触发了我写作关于马洛(Marlowe)和《奥瑟罗》(Othello)的文章,最终这些文章被收入此书;1977年由霍普金斯和马里兰大学联合主办的“从执笔到付梓”(Pen to Press)的研讨会促使我思考廷代尔(Tyndale);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参加了两场有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会议,其中一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一场在华盛顿,这两场会议让我着迷地将精力投入这位非凡人物的作品和生活。甚至“着迷”这个词(虽然它足够准确)也给我带来了超出我应得的赞誉:我记起我从墨西哥度完假直接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会议,我丢失了我的眼镜,我以为我会戴着那副根据医生处方配的潜水面罩发言。在最后一刻,我的眼镜出现了,帮我避免了那场金斯利式的闹剧。
不管这些特殊的机遇多么偶然,我实际上也有潜在的规划,但是这种规划仅部分在我的掌握中。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奇怪:有自主性的行动力(autonomous agency)只是一个梦(哪怕人们对它的体验很强烈而且信念也很坚定),这是本书的基本信条之一。我的确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无法摆脱制度、知识和历史力量的强大影响。与此相反:这些在快乐和痛苦中感受到的力量,帮助我的声音产生了共鸣,并且把我推向了我无法预料的方向。我的最初动力是这样的:当我作为富布莱特奖学金学生在剑桥学习,为“1579—1603”荣誉学位论文做准备时,我被罗利的长段诗歌残卷《欧西恩对辛提娅之爱》(Ocean’s Love to Cynthia)的奇异之处深深震撼了。更确切地说,我看到了罗利的诗歌与艾略特的《荒原》之间的巨大相似性,它们都有对世界和自我的碎片化的痛苦感觉,我对此深感震撼。(这和我们熟悉的感觉一致,古典绘画大师作品中的某些要素就像一幅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比如墙上的阴影、穿衣镜中的倒影、大理石装饰板的旋涡状抽象图案。)我想要强调,我对《欧西恩对辛提娅之爱》的第一反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好奇而是出于对审美惊奇的快乐体验。我无法理解,为何罗利1590年代的挽歌听起来如此像现代主义盛期的作品。出于这点惊奇,我想要知道:罗利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这个问题转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讲求实际的廷臣、专权者和冒险家会写诗,更不用说为什么这诗还能让人想起现代主义实验了?
在我的论文和几年后写的书中,我试图从罗利所扮演的角色上(他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角色)寻找答案。从女王那里失宠后(作为秘密婚姻的结果),他把自己当成了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因失望的爱情而疯狂。他甚至尝试过自杀——根据一个挖苦他的观察者的说法,他在右乳下刮出一些划痕——他以同样的精神写下了痛苦的诗行来表达他的心烦意乱(distraction)。(正如文艺复兴诗歌的机敏学徒艾略特理解的那样,心烦意乱以断断续续的语言、扭曲的修辞和突然爆发的悲伤的方式得以呈现。)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且非常具有现代感的一点是,诡计多端的廷臣试图让人听起来有些神经质。这场表演并非彻头彻尾的欺骗:罗利被盛怒的女王囚禁在伦敦塔,他很可能感到绝望。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将这种绝望转变成文学表演(这场表演反过来成了他毕生呈现自我的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实践在断头台上才告终:他冷静地检查了刽子手的斧子,说了几句毫无疑问经过精心排练的俏皮话,然后把头横在板子上,张开他的手臂,喊道:“砍吧,伙计!”
这种刺激了我整个计划的审美惊奇并没有在写作中消失,但我没有试图把它当成我的解释的一部分。我只是利用它来强化我对所关注问题的热情。为了写有关罗利的书,我曾满足于描述一个杰出人物“充满戏剧感的人生”所产生的文学效果。但是我仍然有种挥之不去的不满足感。因为不管罗利多不寻常——他让同时代人和我都感到震撼和不安——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仅作为更大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种文化现象允许像他这样的个性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因此,当我坐下来为英语学会和其他会议撰写论文时,我总是回到这个问题:在16 世纪的英格兰,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让人们能够在生活也在写作中把自己当成可塑造的角色。
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e)发表于1968年的优秀论文《文艺复兴文学中自我的灵活性》(“The Flexibility of the Self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 in The Disciplines of Criticism, ed. Peter Demetz, Thomas Greene, Lowry Nel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241-64])为那个时期的思想史提供了一些关键方向。在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让·杜维那(Jean Duvignaud)出版于1965年的另外两本书中,我也发现了许多感兴趣的东西,这两本书是《表演者:演员社会学概述》(L’Acteur: esquisse d’une sociologie du comedien)和《戏剧社会学:论集体的阴影》(Sociologie du theatre: essai sur les ombres collectives)。(我看到杜维那的书纯属偶然,归功于一个多年来让我受益匪浅的习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浏览最新的,还没有最终上架到其所属的学科区域的书。在一次漫无目的的闲逛中,我拿起了杜维那的《歇比卡:马格里布小镇的变化》[Chebika: mutations dans une village du Maghreb],我迫不及待地想阅读它因为我当时刚去过摩洛哥。然后,我为这书的魅力所倾倒,于是去找了这位作者的其他书。)杜维那的戏剧研究强调中世纪社会角色的严格性,因此与格林描述的易变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我问我自己这如何可能:一个有着如此精细的宫廷礼仪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明确指定了谁在君主穿越英吉利海峡晕船时扮演端水盆的角色)是如何变成罗利的世界的(在后面这个世界里,他可以不断更换角色,自觉地建构了人们所谓的“罗利”现象)?
当我在为英语学会和其他会议写作论文时,我感受到一阵越来越强烈的兴奋:与其说是一个占据主导的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某一事物正在萌发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写作的真正困难出现前,一直是我写作中最快乐的时刻:你对每件事情变得警觉,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长期以来认为无聊或不重要的事情,以及你碰到的所有事情,不管这些事多么偶然,似乎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事情似乎真的跃出了纸面。我知道,这本书在我知道它将如何集合之前就会集合起来;在我为这个主题找到合适的词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摄的主题。我相信这种奇妙的警觉之感,因为我相信它会给写作带来活力。从过去到现在,我都相信只有在写作中,人们才能够发现他想说什么。
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极大地加强了这种感觉。第一次是1975年米歇尔·福柯到访伯克利。我碰巧已经读过《疯癫与文明》并为其所深深折服——这是我闲逛的另外一个收获——但我可能错失了他到访校园的时候。因为校园规模大且人情淡漠,我总是在几个月后才听说有人发表了很好(或糟糕)的演说。我法语系的朋友告诉我,福柯没有做讲座,而是主持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左拉的研讨班。因为我的教学安排有空闲的时间,于是我决定去旁听。我对左拉没什么兴趣,后来发现这无关紧要,因为据我回忆,在那个学期的课程中,福柯没有一次提到他的名字。那场研讨会有关中世纪天主教忏悔观念的转变——从一劳永逸的、终身的公共状态到一个惩罚量刑系统(量刑的根据是所忏悔的原罪的确切本质)再到一个关于忏悔实践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尺度(其严重程度取决于犯罪者内心认可还是抵制他或她犯下的罪)的转变。牧师依靠一整套牧师技术来推断忏悔者的内在性情,这套技术包括为隐私创立专门的忏悔室和为告解牧师写作越来越复杂的小册子。设计这些小册子的目的是教牧师如何引出对心理状态的有意义的描述——的确,福柯证明,这些册子帮助创造了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内心世界——但同时,这些册子也教导旁敲侧击的艺术,以帮助忏悔牧师掏出最痛苦和最难堪的忏悔,而不像以前那种把无法想象的罪灌输到信徒心里。
福柯智性上的整个表现非常激动人心:我从没听过任何人像他那样讲话,两小时没有停顿(他不喜欢提问)而且极其精确、敏锐而严谨。我会带着几近狂热的兴奋匆匆跑去给我朋友复述这个论点,但他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怀疑态度并且拒绝我的请求,即希望他们参加这个人数稀少的研讨班的下一次研讨。(知识界风尚莫名突转,第二年福柯突然变得非常有名。当他回到伯克利开始下一个访问学期时,巨大的礼堂取代了小教室,这么大的空间仍然无法满足人群,他们挤在门口想有机会听一下用法语发表的复杂而枯燥的演说——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是关于斯多葛学派的演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无法理解。)
在这场我偶然参加的研讨会中,我觉得特别引人入胜的是福柯的论点,他认为个人最内心的体验——潜藏在黑暗中的感受——并非后来受到诸种社会力量打磨的原始材料。相反,这些体验由声称仅仅管理它们的机构产生和塑造。由此,这些体验并非不具有本真性;他认为,有关本真性的信念由制度及其教条、等级秩序、结构安排、程序、关于周期性和话语的充分性的观念构成。简而言之,自我感知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隐藏的和必然的联系,这种社会制度要求拥有奖励和惩罚的权力。这种对内在生活本性的看法是非常悲观的——人们为了逃避总体化的制度而希望退回的隐蔽的地方也是由同样的制度创造的——但是这种悲观主义似乎是围绕着一个微小的、不可化约的希望内核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建立的,因此,原则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会如何崩溃。
这个无法完成的梦想引起我的共鸣,因为像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的生活深受越南战争和我参与的抗议活动影响。我不想夸大我在这些抗议活动中的作用。我没有焚烧我的兵役卡,我没有故意弄伤自己,我也没有计划逃到加拿大。我用学业延期以及后来一个时间上的幸运借口成功地避开了第一次征兵:我的入伍体检(这可能是我要么战斗要么流亡的开始)被安排在了我26岁生日几周以后,我超过法定年龄了。我在加州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最初几年,我参加游行并(相当不自在地)高呼口号;我分发传单并参加群众集会;我主持宣讲会并参与了无休止的公开讨论,讨论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和颠覆它的可能性。在加州伯克利,这构成了一种非常温和的参与形式。但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知识生活。
在1975年春天——正好在这个福柯改变了我的知识视野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唾手可得。尼克松总统在前一年下台,很快被他的继任者福特赦免。尼克松的许多高级助手面临起诉和监禁。已经有两次暗杀福特总统的企图了。1975年4月30日,美军从西贡撤离,把这座城市留给越共和北越人。人们疯狂爬上撤离直升机的画面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接下来几年看似非常动荡:索维托(Soweto)的起义被暴力镇压了;美国决定出资研制中子弹,它可以用来杀死所有生物,同时保持建筑的完整;沙阿(Shah)逃离了伊朗,被霍梅尼取代;苏联入侵阿富汗;三里岛核电厂部分反应堆熔毁。也许我可以通过回忆我最喜爱的一个伯克利学生来表达这个时代的陌生感。她上过我的课程,莫尔的《乌托邦》是那门课中的重要内容。1977年,她来拜访我并且告诉我说,她要退学,去加入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团体,该团体由洛杉矶的一个魅力超凡的社会激进分子吉姆·琼斯(Jim Jones)创立。(作为告别礼物,她送给我一本惊悚小说,安部公房[Kobo Abe]的《他人的脸》[The Face of Another]。)第二年,我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了琼斯镇(Jonestown)自杀者或者被谋杀者的名单上。
现在阅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时,我在这本书中感受到了这个极度迷茫时代的许多痕迹。当我看到巨大的邪恶力量决定碾压所有反抗时,当我解释他们以陌生人为目标并且操纵他们感受到的威胁,将其作为巩固权力的借口时,当我不安地感觉到反对这种权力的人概括了它的某些突出的特征时,这些痕迹十分明显。我试图用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的许多奇闻逸事都有特殊的当代意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马洛那章一开头提到的塞拉利昂烧毁的村庄,在当时会不可避免地唤起电视上的画面,美军点燃的越南村民房子上的茅草屋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会有这样的联想吗?我不知道。但是我采用这个故事时所怀揣的激情、被我纳入对《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的解释的那种激情,直接受到这令人不安的历史时刻的影响。
在我看来,在这本书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潮流中,我曾经参与的代际反叛也显而易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人们往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非常悲观地解释了遏制颠覆,痛苦地认识到了表面的自由选择实际上由制度决定,不抱幻想地承认末日变化是不可能的。(“颠覆是存在的,颠覆没有尽头,只是不为我们。”)的确,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新千年。我的书出版的那年刚好也是里根击败卡特那年。的确,我没有看到一种容易的、未受污染的反对立场——甚至马洛的渎神,我证明其中也有几分顺从的成分。但是有个关于希望——不同形式的希望,不管发生什么,经常被粉碎,但之后又冒出来的希望——的根深蒂固的原则贯穿于这些章节。我认为,在作品的后记中陈述的信仰宣言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但这并非反常现象;正是对一种秘密的信心的承认让这部书的写作不是冷酷而是有趣的。我相信那些敢于对抗粗鲁军队的衣衫褴褛的力量,最终会取得胜利。我相信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身份形成的一些机制时,我以微小而学术化的方式,参与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计划不仅是描述性的:它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摆脱我们厌恶的东西,拥抱带给我们惊奇、希望和快乐的东西。对我而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快乐都包含了美学上的愉悦,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精力的主要来源。
2005年1月13日
后 记
很多年以前,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飞机准备起飞时,我坐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他正专注地看着窗外。那趟航班没有固定座位,我选择了他的邻座,因为他最不可能打扰我。我想重读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这是我回伯克利后下周要讲的内容。但是,当我系上安全带,刚把思绪转向巴厘人的斗鸡时,这个人突然开始和我说话。他说他要去波士顿看他在医院的已经成年的儿子。一种疾病损害了他儿子的语言能力(这是该疾病的后果之一),所以他仅能够无声地吐字;更严重的是,因为他的病,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他告诉我,他想让儿子重拾活下去的意愿,但困扰他的是,他可能无法理解儿子的意图。因此,他想问我:我能否用哑剧的方式说几句话,让他练习读我的唇语?我愿意无声地说“我想死,我想死”吗?
惊讶之余,我开始构思词语,这个男人专注地盯着我的嘴:“我想[……]”但我无法完成这个句子。“我不能说‘我想活着’吗?”我信心不足地建议他,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这个时候安全带指示灯灭了),他可以去卫生间,在镜子前进行练习。“这不一样。”这个男人用颤巍巍的声音回复道,然后将头转向了窗户。“对不起。”我说道,在接下来旅程中,我们都保持了沉默。
我无法按照那个男人的要求去做,部分原因是我害怕他是个疯子。一旦我表达出死的意愿,他就会拿出一把藏着的刀子把我捅死,或者启动某些藏在飞机上的装备把我们炸成碎片(根据我过去十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经验,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比起说妄想症影响了我的整个反应,我的拒绝有着更为复杂的理由。比起害怕身体的攻击,我迷信地认为,如果我默念那个男人的那句可怕的话,它会具有法律判决的力量,那句话会像刺一样一直扎着我。并且在迷信之外,我更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比起我的学术研究,我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语言相符的,我想要形成我自己的句子,或为我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朗诵别人的话。即使是在一个孤独且需要帮助的人的请求之下,表演不是我自己的台词、违背了我自己的愿望的台词也是不可接受的。
在多年前第一次构思这本书时,我想要探讨16世纪的几个主要的英语作家如何创造他们的表演,分析他们在表现自己和塑造人物时的选择,由此理解人类自主性在建构身份时扮演的角色。在我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就是中产和贵族男性开始感觉到他们对生活有这种塑造的权力,我把这种权力和它所意味的自由当成理解自己的要素。但是当我在推进这项工作时,我发现塑造自我和被文化体制(家庭、宗教、国家)塑造无法截然二分。就我能说的而言,在我所有的文本和材料中,没有纯粹的、无约束的主体性;的确,人类主体本身一开始看上去是非常不自由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每当我关注明显自主的自我塑造的时刻,我就会发现没有一种身份的显现是自由选择的,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造物。如果有自由选择的迹象,那么这个选择的可能性的范围也是由有效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系统所界定的。
我写下的这本书反映了这些想法,但我相信它也——虽然是以一种多少比我最初预想的更不确定且更讽刺的方式——反映了我最初的动力。我在这里写下的所有16世纪的英国人实际上都依附于人类主体和自我塑造,即使他们表明了自我的吸收、堕落或者丧失。他们还能做什么?过去有什么——或者说现在有什么——替代的选择?因为,我们所关注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理解这一点:即使自我被认作一种虚构,在我们文化中放弃自我塑造就是放弃追求自由,就是放弃他们自己固执地坚持的自我,就是死亡。对我而言,我之所以提起我在飞机上遇到的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的小故事,是因为我想在本书结尾时见证我的当务之急是维持这种幻觉:我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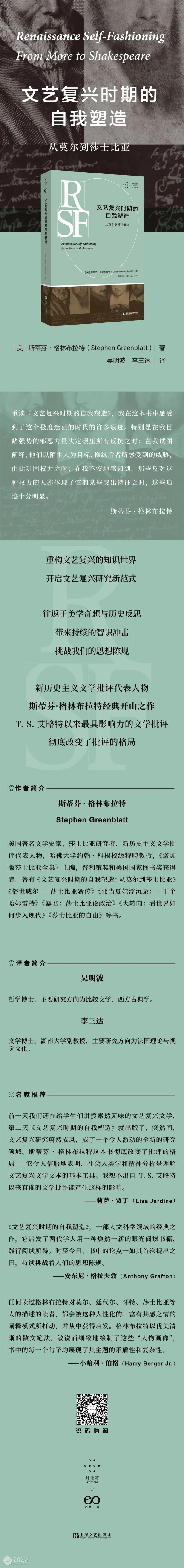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