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2年10月7日下午1:00(北京时间)
2022年10月7日下午13:00,我们于线上开展了一次有关不同边地文化语境的圆桌论坛,当天上百位热爱这个议题的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以西藏艺术平台/机构的视角基础,去对话来自不同语境的当代实践,邀请琴嘎、马星、刘劲勋、张云峰,摩瑟伊萝一起,看见在非主流地区发生的当代艺术是如何深植于本土文化语境而不断泛起涟漪。


拉姆: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今天,我们希望可以从西藏的当代艺术语境出发,看向更广阔的边地视角,看到在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的背景之下,艺术作为方法时呈现出的多元/独特的民族志/民族性。今天的圆桌有幸邀请到了琴嘎,刘劲勋,马星,张云峰以及摩瑟伊萝,各位老师将把他们自身的在地文化视角作为叙事,以一同寻找边地当代艺术在今天的共同境遇。
伊萝,可以先邀请你介绍你们的项目‘山谷回音’吗?
————————
摩瑟伊萝:
大家好,我是伊萝。今天我很荣幸代表‘山谷回音’项目组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家乡大凉山做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我目前常驻北京,很荣幸能够通过这个线上平台与大家聚在一起。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山谷回音——发展中的社群文化实践”。把‘发展’一词加入标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始终基于发展的视角展开一系列活动,同时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当地的发展。其实这与我自身的专业背景有关,我研究生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专业是Global国际发展,寓意是结合全球视野与在地实践来促进发展(Global Vision and Local Practice),所以我希望把我所学运用于我的家乡,用国际化视野促进在地化发展。
山谷回音是2020年在疫情背景下成立的。疫情爆发后,我从国外回到国内,在大凉山家里待着上网课。‘山谷回音’的另外两位创始人,一位是音乐人莫西子诗,另外一位是律师沙玛诗哲。疫情期间,我们三人聚在一起聊天,讨论了家乡文化活动匮乏的现象,于是就一起合作创造些可以促进交流的好玩儿的事。
“回音”是
彼此冲击后的
交互与交鸣
关于山谷回音名称的由来,山谷值得就是我们深爱的家乡大凉山,但为什么会有‘回音’呢?
我们认为,回音是在内部与外部的接触、交互、交鸣过程中产生的,是诞生于彼此交流的过程之中的,所以我们对山谷回音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在内部自说自话地创造意义,我们愿意与更多外界的人分享、交流。
山谷回音实践中,我们是组织方、策展人也是、观察者,三个不同的身份在一个时空当中串联了起来,不同身份之间的转化有助于我们的活动从不同的视角中展开。
我们希望山谷回音能够凝聚我们作为凉山人的这个共同体意识,这是山谷回音一系列活动的基本逻辑起点。凉山的文化是多元而深厚的。凉山不仅是主要的彝族地聚居地,同时也有蒙古族、藏族、汉族等朋友,每个人都是自己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在组织活动时,我们看见每个人带来的东西都能体现他的社会身份认同,在活动过程中,每个人的参与、表达和创造又能进一步促进自我身份认同和彼此沟通尊重。所以我们并不把“山谷回音”定位成一个“彝族人”的活动,而希望它是一个“凉山人”的活动,我们更强调地域性而非族群性。
 山谷回音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山谷回音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山谷回音是在2020年的3月左右开始策划的,4月份落地了第一期活动,是以“婚姻与性别”为主题的文化沙龙。五一劳动节时我们做了个特辑活动,包括复古集市、观影会和盛装Party分享会。5月到8月上旬,我们主要开展了系列观影活动。
 山谷回音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山谷回音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山谷回音·火把节特辑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山谷回音·火把节特辑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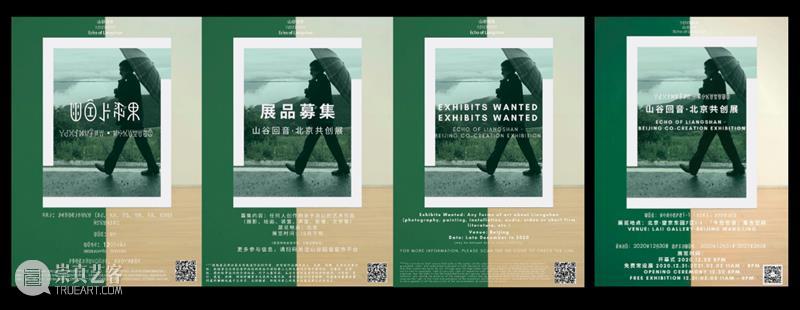 山谷回音共创展海报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山谷回音共创展海报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艺术和文化间的关系、
艺术与群众间的关系、
艺术与青年间的关系
 黄伞计划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黄伞计划 图源自摩瑟伊萝分享 致谢分享者————————
琴嘎: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与这次分享。首先简单介绍一下造空间,造空间发起创立于2011年底,我称之为游牧空间。它没有实体空间,是一个在生活中、社会中任何地点任何位置任何角落都可以策划的实验性艺术项目——我们走出白盒子,在生活中搭建和艺术的关系。
到今年已经10年,十年间我们陆续发起了大概7个项目,早期的‘包装箱计划’、‘一个梦想’、红旗小学、“造事”系列,一起飞,义工计划,一起游牧等等,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一起游牧。每个项目之间时间跨度约有一年到几年,这些项目不同于展览,项目的意义诞生于项目启动到发生实施的过程当中,它们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生长,这也是我称之为游牧空间的原因之一。
在美术馆、画廊的机制里
我们也许无法发出真实的声音。
今天,我将主要根据圆桌的议题介绍两个项目——一个是12年到13年造空间最早发起的“一个梦想”项目。“一个梦想”这个名称基于当时的语境而来,即中国当代艺术通过二三十年的沉淀,在05~09年市场化的井喷后遭遇了一个过度商业化的阶段。当时有很多我所认识的年轻艺术家,在美术馆、画廊的机制里无法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契机下,我与高峰联合发起了这样一个项目,参与人数也比较多。有25组艺术家,大多数都来自于当时北京的黑桥艺术区——这个艺术区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时,黑桥聚集了全国大量的,来自各地的年轻艺术家,非常活跃。当然,它也同时具备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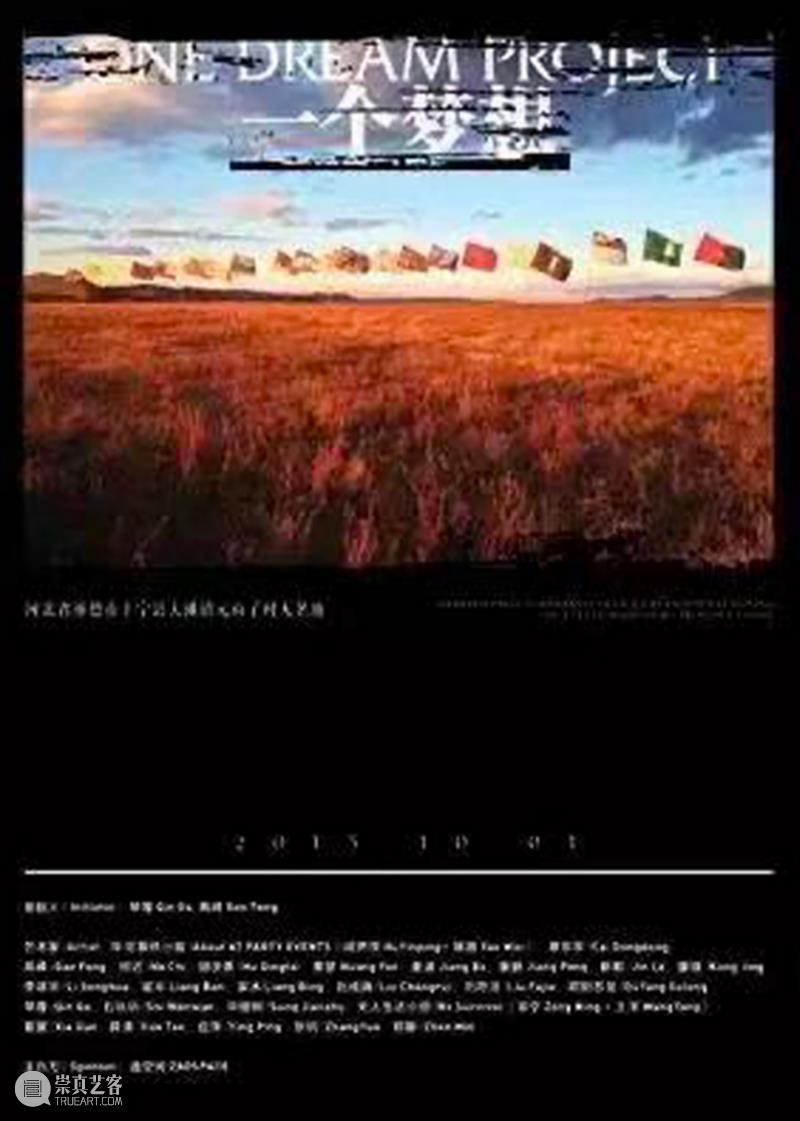 “一个梦想”项目海报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一个梦想”项目海报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在这个项目里,我邀请了我所熟知的25组艺术家,其中有两个艺术小组。在一年的时间中,艺术家们自主选择地点、时间,去实施自己的一个梦想。一年后,把每个人的作品变成一面旗帜,把自己计划转换到一个平面上去。
历经一年后,我们在13年10月1号。组织艺术家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大滩镇元山子村乌兰布统草原,下午4点至5点30分在两处无名地实施了《旗阵》,呈现了一个临时性的大地艺术行动。
在这之后我们边烤全羊边展开了研讨会,特邀策展人崔灿灿作为主持人。讨论的过程非常激烈,持续时间很长,这些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都有。




“一个梦想”项目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因为内容量之大,我无法在此一一详细介绍。这个项目其实探讨了,在每个人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梦想会遭受什么样的改变?这抽象的东西,是否能被可视化?这25组艺术家的表现形态各异,丰富且真实。其中有一位艺术家持续一年,来回反复,最终发现自己已然没有了梦想。当然,还是有很多艺术家在一年之中完成了梦想,还有的艺术家的梦想一直在持续。艺术家刘成瑞的梦想持续了8年。最终,他的梦想依旧无法实现。他把它转换成了一部虚构性的小说作为呈现,具体的内容在造空间的公众号上有专门的详介。
一次集体出走
——从固态化的艺术生态中抽离
这是艺术家们的一次集体出走,是从非常固态化的艺术生态中的一次抽离。他们回到自然,和自然相处。虽然这是一个临时性或暂时性的项目,但我觉得,这些痕迹留在了大地上。持续至今,这些艺术家也都不再年轻,都成为了中生代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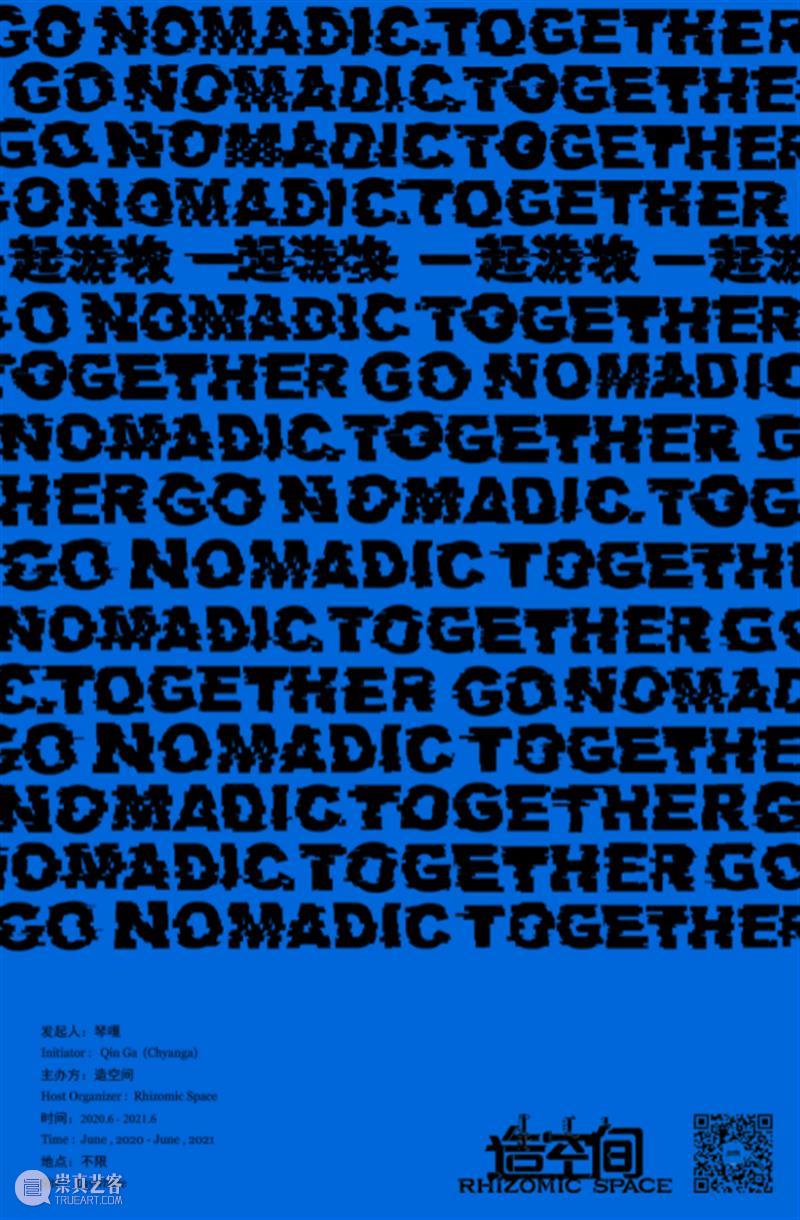 “一起游牧”项目海报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一起游牧”项目海报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接下来,我谈谈目前还在持续进行的项目——一起游牧。这个于20年启动的项目遭遇了疫情。恰好,我在当时做了一个决定,除了邀请中国的艺术家之外,还邀请蒙古国、德国、美国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提是一直以来以游牧,对游牧文化或游牧方式来持续进行艺术实践的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以及所处位置、地点、时间发声,在这跨度一年的媒介里实施自己对当代性游牧的看法。
历时一年后的呈现还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影像等等,都在互联网平台上了进行发布。我觉得这是一次聚会,是一次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以艺术项目作为形式的一种集结。大家一起探讨游牧文化在今天的当代性意义,它涉及到我们今天看待所谓传统和当下现实的方式,以及搭建可供讨论和交流的通道的方式。
很多人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一个蒙古人的聚会?其实我觉得,在今天,整个北方文化是处于一种互相的融合交流或者说覆盖的状态之中的,它取决于文化的主体性是否足够强大,那么,它是否还存有活力去改写对当下的生活与现实,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每个艺术家把公众号的平面空间作为一个项目实施或布展的空间,其中包括艺术家的自述,对自己项目的看法,或对艺术的看法,或对游牧文化在今天的现实处境的看法。26组艺术家都在独自游牧,在不同的语境里,不同的时空里,却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共同体。在造空间的平台上,大家互通有无,去观察“共同体”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空间?
今年7月份,受abC艺术书展创始人之邀,我和艺术人类学学者李雨航从“一起游牧”的项目里提取、策划关于“仪式与日常”的主题展。在北京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殖民化的、仿西洋的建筑里实施了主题性的展览。在展览现场,我们提供了和游牧文化相关的一些艺术书籍,有人类学的、社会学的、艺术学的和设计相关的等等。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展览,它是一个大众化的艺术书展。观众在游走当中,在移动当中临时性参与,我们希望可以以此构成一个对话。
 “仪式与日常”第七届abc艺术书展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
“仪式与日常”第七届abc艺术书展 图源自琴嘎分享 致谢分享者最后,游牧计划是一个在2018年启动的持续性、综合性的文化活动,由导演乌尔善、杭盖乐队队长伊立奇,人类学者宝力格教授和我共同发起的。
游牧计划分4板块,有学术讲座、电影放映、艺术展览、音乐演出。每年6月份的某一天,我们以游牧文化为核心,构建起一个理性的民间交流活动。在这一天,我们展开学术讨论,聚焦于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文化中的当代性展开探讨。
————————
刘劲勋:
首先感谢拉姆邀请,能和大家有这样交流的机会。今天的圆桌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板块——甘肃和青海这两个板块。以后有机会,其实可以让甘肃和青海的一些实践者来加入这个圆桌的讨论。我是甘肃人,以前一直是在甘肃工作。在甘肃的当代艺术和在地的融合过程中,有许多非常好的艺术家做了很多非常好的实践。例如我之前任职的谷仓当代艺术馆也是从2008年开始,我在那里做馆长是做到12年,也主要是以图像为主要的介入口,在兰州做了很多的项目。
在甘肃,有靳勒大哥做的石节子美术馆,他在那里做了很多艺术项目,对整个西北的当代艺术产业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庄辉大哥也是在他的出生地玉门的区域里做了很多非常好的艺术项目,这也是甘肃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部分。尤其今天的这个话题,让我想起甘肃的评论家、学者张畯。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关于边地当代艺术有非常好的文本总结,都在他的公号——「时间图鉴」里面,对边地当代艺术和艺术中心地带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全面的阐释。此外,在青海,高原先生做的西宁当代,这些年来也一直邀请艺术家做驻留,在那里发生过许多好的作品。
在西北
一个值得珍惜的艺术业态
我是去年到的宁夏。当时,我本来是来做一个驻留项目,结果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宁夏居然有一个艺术资源聚集性业态的出现,这让我很惊讶。也是我今天想着重说的现象——边地当代艺术首先脱不开的是它的基本面的问题,也就是它的艺术生态的问题。
因我之前在新疆创作之故,青海、甘肃这几个西北省份走的比较多,对每个省的当代艺术背景也都相对了解。到了宁夏之后,我其实还有点吃惊,宁夏是个比较小的省,银川人口也非常少,到目前为止不到300万人。但我在贺兰山天籁艺术村里看到的现象是我之前在西北其他的省会城市没见过的——这里居然形成了一个聚合性的艺术生态。
兰州也好,乌鲁木齐也好,西宁也好,这样的城市里往往能诞生好的艺术家,也会有很多机构、空间来做事儿。但是能在一个园区里聚合,是我在西北其他城市没见过的——包括西安这座在西北唯一一个过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也不曾在现在还保有这样业态。
基于我对这种艺术业态的兴趣,在驻留之后便留在了银川,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年了。这一年的感受,我就用这个字“鬲”来说明。如果对黄河文化有了解的话,会知道它实际上是陶器时代的一种容器,长着三只脚。
 鬲
鬲
它是用来煮饭,煮粟米藜麦的一个炊具,我觉得它很形象,这三只脚分别像园区里的美术馆、艺术空间和艺术家的工作室。
目前为止,这个园区里面有三个美术馆,除了贺兰山美术馆以外,去年做了西北第一家专属于儿童的「山边儿童美术馆」,现在为止也运营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之后马上会成立一个新的空间,也许会改造成和葡萄酒产业相关的美术馆。我们现有大概六七个艺术空间,大象艺术公社,青年艺术营等等,它们会做为一些展览空间存在。在展览空间之外,目前有 22位本土艺术家入驻,我所说的贺兰山的艺术聚集业态也就因此出现。
实际上,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特殊性是,我们不像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单体空间,我们是一个园区,作为实体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所以我在这的一年,生态作为基本面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事情。在西北这样一个城市里建立一个艺术生态,是我的工作重点。这种集聚性液态在西北非常稀缺,也是非常珍贵的,它一旦消失,真是一件非常可惜事情。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保护生态,如何让生态发展更多的实践。
于我而言,好的艺术生态不在于艺术家体量多大,或艺术家职业化的程度多高,我觉得这只是生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最主要的点在于交流,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艺术家与公众的有效交流,如果这种交流能出现一些频繁的、通畅的、平等的、公开的语境,这样的生态才是好的生态。
中心的“偏地”
把石子投进湖水
我用「中心的“偏地”」指代宁夏艺术生态的一个现状。
如果我们把中国地图想象成一张纸,把东南西北4个端点对折,会发现这个纸的中心点就在银川。可以说,银川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国的地理中心点。但作为艺术生态来讲,它就是个偏地,对外对内的交流都比较少。展览空间和渠道的提供也是比较少,有点像一潭平静的湖水。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对宁夏艺术生态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心的“偏地”」。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子投进湖水里重新激活它,通过艺术活动不断地促进它的活性,让它不断产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这是一个过程。
园区最基本的呈现面,展览是第一位的。我们以展览为核心来推动这个园区,这个园区距离银川市市区30公里,有点像从北京市区到草场地的距离。如果一位市民要去看30公里外的展览,我们只呈现一个展览的话,爱好艺术的市民朋友来讲,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
我之前提到,聚合性业态非常重要,当美术馆、艺术空间和艺术家工作室能同时呈现时,我们可以一次做出6~7个展览同时呈现,这样才有可能吸引城市里喜欢艺术的年轻人驱车30公里,花一天时间来到这里来看展览,来和艺术园区的展览空间、艺术家工作室以及艺术家产生一些联系。所以我们是以展览为核心的,一般来讲一个美术馆一年做4个、5个展览基本上算饱和了,但我们这里的展览密度极高的,基本上不到两个月就要更新一个展览。而且我们这种展览往往都是节会性的,我们在美术馆做一个主题展览,然后在其他艺术空间做一些外延的展览。
 在贺兰山美术馆发生的展览项目《宁夏首届小版画作品展》、《Hi你好吖!首届贺兰山儿童艺术节》《珍藏年代——酒标艺术展》、《天籁影像艺术周》、《刹那间,万物静默如谜》、《天籁桃花源》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在贺兰山美术馆发生的展览项目《宁夏首届小版画作品展》、《Hi你好吖!首届贺兰山儿童艺术节》《珍藏年代——酒标艺术展》、《天籁影像艺术周》、《刹那间,万物静默如谜》、《天籁桃花源》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艺术家工作室如果愿意的话,也会参与其中的部分来做一个展览,整个展览的层级因此丰富起来。比如说我们《天籁桃花源》是我们每年跨年时的年度品牌展览,是由驻村艺术家共同集合完成的展览。
「天籁·女性艺术展」是在三八节时由女性艺术家主导的展览,因为我们需要激活最基本的艺术生态面,让更多喜欢艺术的人有机会加入展览里来,所以我们邀请了本土50多位女性来参加这个展览。
天籁影像周是我们在五一时专门以影像为一个核心介质来做的展览。还有我们结合本土做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酒标艺术展。这个展览做出来后效果非常好,因为在国内的艺术机构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机构拿酒标做展品。宁夏目前有酒庄100多家,展览展现了从80年代到现在近40年发展史中非常珍贵的酒标。这个展览与市民的互动性非常好,内容也非常有意思,酒标虽然只是个平面的,小小介质,但里面会涉及到绘画、音乐、文学、建筑,它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连接非常多,因此成就了这个有趣的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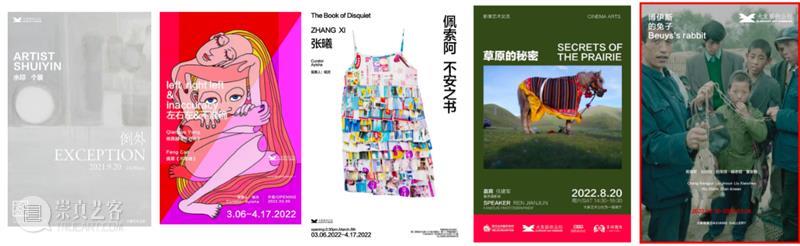 在艺术空间里发生的项目《例外》、《左右左&不准确》《佩索阿 不安之书》《草原的秘密》《博伊斯的兔子》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在艺术空间里发生的项目《例外》、《左右左&不准确》《佩索阿 不安之书》《草原的秘密》《博伊斯的兔子》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在艺术空间里,我们主要做的是本土年轻艺术家,年轻艺术家都很活跃,他们很多是从海外留学回到银川。还有像「草原的秘密」这样的展览,都是青海艺术家和甘肃艺术家来到宁夏所做。在甘青宁整个文化区域、文化带之间产生交流。
展览「博伊斯的兔子」是宁夏本土做影像的中生代艺术家的和年轻影像艺术家们的群展,对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创作脉络进行融合。
驻地项目的观察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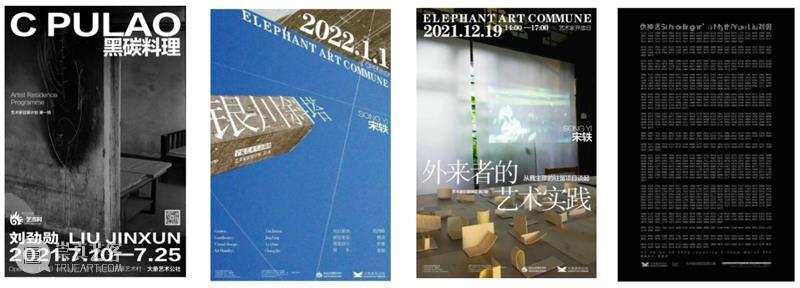 驻地项目《黑檀料理》、《银川斜塔》、《外来者的艺术实践》、《伪神话》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驻地项目《黑檀料理》、《银川斜塔》、《外来者的艺术实践》、《伪神话》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构建
联结
激发
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驻留项目?是因为这三个关键词——构建、联结和激发。构建:我们通过活动自我构建,通过驻留项目外部连接,比如我们邀请假杂志来银川做书展,假杂志的《巫术修辞》第一次来到银川。
 “激发”:《从这一页开始:假杂志艺术书展》、《张素英的“城堡“》、《”内与外的联结》、《中国风景》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激发”:《从这一页开始:假杂志艺术书展》、《张素英的“城堡“》、《”内与外的联结》、《中国风景》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我们还邀请了很多艺术家带来新媒体的介质,来产生一些内与外的联结。
此外,“画廊”是我想着重说明的。在一线城市,画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业态环节了,但在整个西北,依旧少有商业画廊能和艺博会发生连接。但是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我们觉得,如果西北真的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当代画廊,那么对本土艺术家而言,将会在艺术生态闭环的形成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因为画廊能非常好地集合到媒体资源、藏家资源和艺术家资源,这对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西北非常缺少这样的渠道,好还是不好暂且不说,这个渠道确实是必须要有的,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画廊代理艺术家孙海霆的摄影作品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画廊代理艺术家孙海霆的摄影作品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我们非常严谨地挑选艺术家,不想只是一些简单的文化符号的直接移植。目前为止,画廊正式代理的唯一一位艺术家是孙海霆,孙海霆是西安人,现在在北京工作,但他这批作品都拍摄于西北。而张岩老师与梅晓阳老师,也是我们非常谨慎地在不断观察他们的创作。张岩老师的作品很有意思,它以西北独具代表性的皮影戏为一个主要创作的素材对象,并做了解构和扁平化的处理。我们现在仍然和张岩老师不停地交流,观察他未来的创作动向。

 艺术家张岩(上)与梅晓阳(下)的作品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艺术家张岩(上)与梅晓阳(下)的作品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通过外来艺术家的一些活动,这些“激发”也会给本土艺术家带来一些新层面的展示。我们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吸引到当地的年轻人,能共同经营艺术生态的整体发展。当激发完之后我们会把我们做的每一次活动,向社会面做更大的一个拓展延伸。在淘画季,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场所来做艺术跳蚤市场。我们园区是在度假区里面,有很多非遗工作室,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规模比较大的这样的活动,每个工作室里都会有和公众,和孩子们一起发生的艺术体验。旅游季的艺术节里有内容很多了,有展览,有体验,有艺术市集,有文化市集,也有音乐弹唱,以及和孩子们规划的互动。淡季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很多生活美学相关的活动,涉及到有机蔬菜、手冲咖啡等等,让园区能不断产生声音来和市民发生一个互动。我们做这些活动也是让不断让艺术的各个门类、各个方向能走出美术馆,走出园区,和周边发生更多的关系,这是我们做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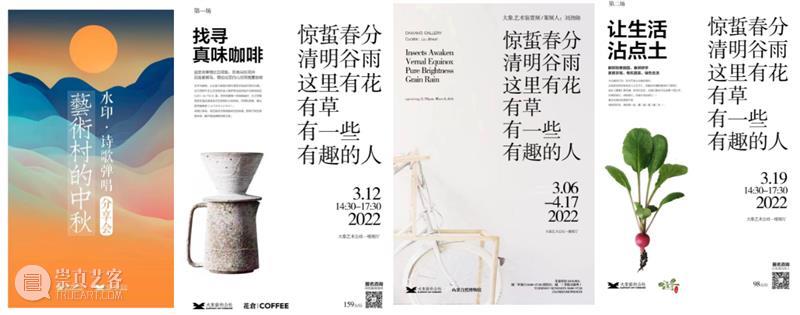 “延伸”:《艺术村的中秋》、《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这里有花有草有一些有趣的人》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
“延伸”:《艺术村的中秋》、《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这里有花有草有一些有趣的人》 图源自刘劲勋分享 致谢分享者这就是我们这一年来努力在做的事,在不同的空间层面填充内容。最后,我还是会拿个“鬲”这个器皿来比喻我们的现状,我希望它能成为“鼎”,多一条腿也会站得更稳,体量也就会更大,就能包含更多东西,它的蓄能也会有更好的提升。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