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小说辩护,再来一次
萨曼·鲁西迪 著,张佳 译
选自Salman Rushdie “Step Across This Line: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 Random House, 2002
最近在英国出版商协会的百年大会上,乔治·斯坦纳教授满嘴说道:
小说让我们很累了……流派兴起,流派衰落,史诗,诗篇史诗,正式的诗篇悲剧。伟大的时刻,然后它们退潮。小说会继续写很长一段时间,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混合形式,我们将粗鲁地称之为事实/小说……今天有什么小说可以与最好的报告文学和最好的即时叙事(immediate narrative)媲美?
品达(是)记录在案的第一人,他说,“这首诗将在创作它的城市不复存在时被传唱”。文学反抗死亡的巨大夸耀。在今天说这话,我敢说,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会深感尴尬。文学伟大的古典虚荣——但多么美妙的虚荣。“我比死亡更强大。我可以在诗歌、戏剧、小说中谈论死亡,因为我已经战胜了它,因为我或多或少是永恒的。”这已经无法寻得了。
所以,这种说法再次出现,被包裹在最精美、闪亮的花言巧语里——没错,我指的是那种漂亮的老生常谈[1]:小说的死亡。斯坦纳教授还补充说,读者的死亡(或至少是彻底转变),变成某种电脑神童,某种大书呆子;以及书籍本身的死亡(或至少是彻底转变,变成电子版)。几年前,作者在法国被宣布死亡——以及斯坦纳教授本人在早些时候的讣告里宣布的悲剧的死亡——使舞台上散落的尸体比《哈姆雷特》结尾还多。
然而,在这场大屠杀中,仍然站着一个孤独、威严的人物,一个名副其实的福丁布拉斯[2]。在他面前,我们所有人,无作者文本的撰写人,后文学的读者,鄂榭府[3]出版业——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4],那就是出版业——以及书籍本身,都必须低下我们的头:即,自然,是批评家。
最近几周,一位杰出作家,这位著名的从业者,也宣布了形式的消亡。V.S.奈保尔不再写小说,他告诉我们:现在“小说”这个词本身就让他感到不适。和斯坦纳教授一样,《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作者认为,小说已经过了它的历史时刻,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并将被事实写作取代。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奈保尔先生现在站在历史的前沿,创造了这种新的后虚构(post-fictional)文学。[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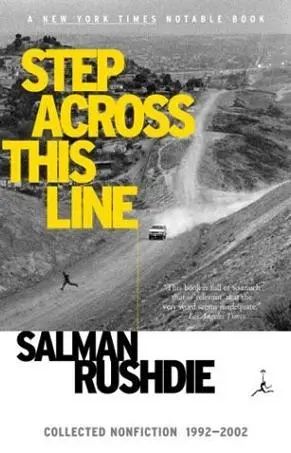
另一位英国大作家这样说:“几乎不用指出,小说此刻的声望极低,低到‘我从来不读小说’这句话,在十年前说,往往还带有一丝歉意,现在说却总带有骄傲的语气……如果不能把最好的文学头脑引回小说,小说可能就会以某种潦草、可鄙和无望的退化形式存在,就像现代墓碑,或《潘趣和朱迪》[6]。”
这是乔治·奥威尔在1936年写的话。看起来——事实上斯坦纳教授也承认——文学从来就没有过未来。即使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早期的评价也很差。好作品总是受到攻击,尤其是被其他好作家攻击。最粗略地瞥一眼文学史就能发现,没有哪部杰作在出版时不受到攻击,没有哪个作家的声誉不被同代人损害:阿里斯托芬说欧里庇得斯是“一个陈词滥调编选集的……和做破布偶的”;塞缪尔·佩皮斯[7]认为《仲夏夜之梦》“乏味而可笑”;夏洛蒂·勃朗特对简·奥斯汀的作品不屑一顾;左拉对《恶之花》嗤之以鼻;亨利·詹姆斯抨击《米德尔马契》、《呼啸山庄》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每个人都对《白鲸》冷嘲热讽。《费加罗报》在《包法利夫人》出版时宣布“福楼拜先生不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尤利西斯》“下流”;《敖德萨信使》(Odessa Courier)评价《安娜·卡列尼娜》:“多愁善感的垃圾,让我看看哪一页有点思想”。
因此,当今天的德国批评家攻击君特·格拉斯时,当今天的意大利文坛得知伊塔洛·卡尔维诺和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8]崇高的国际声誉而“惊讶”时(就像法国小说家兼批评家Guy Scarpetta[9]告诉我们的),当美国政治正确的大炮对准索尔·贝娄时,当安东尼·伯吉斯在格雷厄姆·格林死后不久就贬低他时,当斯坦纳教授一如既往地雄心勃勃,不仅研究少数个别作家,还研究战后欧洲全部的文学作品时,他们可能都患了文化上流行的黄金时代主义:这种反复出现、令人作呕的文学怀旧(文学的过去在当时似乎从没比现在好多少)。
斯坦纳教授说:“今天,伟大的小说来自遥远的边缘地区,来自印度,来自加勒比地区,来自拉丁美洲,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人会觉得惊讶,我对这种中心枯竭、边缘活跃的观点提出异议,部分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哀叹。只有西欧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文学不再是地球上最有趣的,而为整个艺术形式写下哀叹。(不知道斯坦纳教授认为美国是在中心还是遥远的边缘地区;这种扁平地球(flat-earther)[10]文学观的地理学有点难以理解。从我的位置来看,美国文学似乎状态还不错。)只要伟大的小说不断涌现,它们来自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位好教授所生活的扁平地球是什么呢,中心是疲惫的罗马,边缘潜伏着天才的霍屯督人[11]和食人族吗?斯坦纳教授脑子里的地图是一张帝国地图,而欧洲的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了。对斯坦纳和奈保尔来说,这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证明了小说的衰落,这也是后殖民时期的第一个五十年。一种新的小说正在出现,一种去中心的、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小说。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或混乱中,我们找到了对当代小说状况更好的解释,而非斯坦纳教授那种有点自以为是的黑格尔式观点,认为“遥远的边缘地区”之所以具有创造力,是因为这些地区“处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早期阶段,处于更早、更粗糙、更有问题的形式。”
毕竟,正是佛朗哥政权成功地扼杀了十年又十年的西班牙文学,才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拉美的好作家身上。因此,所谓的拉美爆炸,既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腐败的结果,也是新的所谓原始创造力的结果。把印度古老、成熟的文化描述成比西方“更早、更粗糙”的状态也很奇怪。印度拥有庞大的商业阶层、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爆炸性的经济,拥有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资产阶级之一,而且至少和欧洲一样悠久。在印度,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有文化的读者阶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的是,出现了一代天才的印度作家,他们用英语写作。新的是,“中心”已经屈尊注意到“边缘”,因为“边缘”已经开始用语言的无数变体来表达,让西方更容易理解。
在我看来,就连斯坦纳教授对枯竭欧洲的描述,也是简单而且明显错误的。过去五十年里,我们看到了许多人的作品,例如阿尔贝·加缪、格雷厄姆·格林、多丽丝·莱辛、塞缪尔·贝克特、伊塔洛·卡尔维诺、艾尔莎·莫兰黛[1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丹尼洛·契斯[13]、托马斯·伯恩哈德、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我们都能列出自己的清单。如果我们把欧洲以外的作家加进来,就会发现,世界上很少有这么多伟大的小说家同时在生活和工作——斯坦纳-奈保尔立场的轻易悲观,不仅令人沮丧,而且毫无道理。如果V.S.奈保尔不再希望,或者不再能够写小说,那是我们的损失。但毫无疑问,就算没有他,小说的艺术也会继续存在。
在我看来,小说的艺术没有危机。小说正是斯坦纳教授渴望的那种“混合形式”。它部分是社会调查,部分是幻象,部分是忏悔。它跨越了知识的边界,也跨越了地形的边界。然而,他是对的,许多优秀的作家已经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雷沙德·卡普钦斯基[14]关于海尔·塞拉西[15]的巨著《皇帝》,就是这种创造性模糊的例子。汤姆·沃尔夫[16]等人在美国研发的所谓“新新闻主义”[17],就是直接窃取小说外衣的尝试,在沃尔夫自己的《Radical Chic &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和《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里,这种尝试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旅行写作”的范围也已经扩大到包括文化深思作品:例如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多瑙河之旅》,或Neal Ascherson[18]的《黑海》(Black Sea)。面对罗伯托·卡拉索[19]《The Marriage of Cadmus and Harmony》这样的非虚构杰作(它对希腊神话的重新审视,达到了最佳小说的所有张力和智力刺激),人们只能为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散文写作的到来而喝彩——或者,更好的是,狄德罗和蒙田那种百科全书游戏的回归。小说可以欣然接受这些发展,而不觉得受到威胁。这里容得下我们所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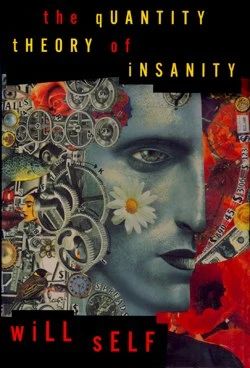
几年前,英国小说家威尔·塞尔夫[20]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短篇小说,名为《疯狂的数量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Insanity)。文中提出,人类可用的理智总量可能是固定的,可能是一个常数。所以,精神病是没法治疗的,因为一个人恢复理智,就会导致其他地方的人失去理智。就好像我们都睡在一张床上,身上盖着一条理智的毯子,但这条毯子不够大,盖不住我们所有人。一个人把毯子拉过来,另一个人的脚趾就露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想法,它在斯坦纳教授可笑的论证里反复出现,他非常严肃地提出,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存在一个创造性才能的总量,而目前,电影、电视甚至广告的吸引力,正在把天才的毯子从小说身上拉走,小说因此露出来了,穿着睡衣,在我们文化的寒冬深处瑟瑟发抖。
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假定所有的创造性才能都属于同一类。把这种观念用到体育运动里,其荒谬性就显而易见。马拉松运动员的数量并没有因为短跑的流行而减少。跳高运动员的质量跟撑杆跳拥趸的数量也没有关联。
更有可能的事,新艺术形式的出现,让新的群体进入创作领域。我只知道个别几个电影人,他们可能也是出色的小说家——萨蒂亚吉特·雷伊、英格玛·伯格曼、伍迪·艾伦、让·雷诺阿,就这些。要是没有塞缪尔·杰克逊和约翰·特拉沃尔塔给你念词,昆汀·塔伦蒂诺那些黑帮在巴黎吃巨无霸的段子[21],你还能看多少页?最好的编剧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他们不从小说的角度思考,而是从画面的角度思考。
简而言之,我不像斯坦纳那样担心,这些新的高科技形式会对小说构成威胁。也许正是写作行为的低技术含量将拯救它。电影、戏剧、唱片,它们的艺术表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技术,这种依赖使它们很容易被审查和控制。但一个作家在房间里孤独创作的东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轻易摧毁的。
我同意斯坦纳教授对现代科学的赞美:“今天,这就是这就是欢乐所在,是希望所在,能量所在,世界对世界开放的强大感觉,”但讽刺的是,这种科学创造力的爆发,是对他“创造力的数量理论”的最好回击。这种认为潜在的伟大小说家已经被亚原子物理或黑洞研究湮没的观点,和它的对立面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上的伟大作家——比如简·奥斯汀,或詹姆斯·乔伊斯——如果他们转向不同方向,可能轻易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
在质疑现代小说的创造力时,斯坦纳教授给我们指出了错误的方向。就算当代文学存在危机,那也是一种不同的危机。
小说家保罗·奥斯特最近告诉我,所有美国作家都必须承认,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美国,不过是少数人的兴趣,就像足球。这一观点与米兰·昆德拉的抱怨不谋而合。昆德拉在新文集《被背叛的遗嘱》里说:“欧洲在保卫和解释(耐心地向它自己,也向别人解释)最典型的欧洲艺术——小说艺术——时无能为力。解释小说艺术也就是解释欧洲自己的文化。‘小说之子’放弃了曾培养造就他们自身的艺术。欧洲这个‘小说的社会’抛弃了自己。”[22]奥斯特说的是,美国读者已经对这类读物丧失兴趣;昆德拉是讲,欧洲读者与这种文化作品之间丧失关联。再加上斯坦纳笔下未来的文盲、沉迷电脑的小孩,也许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阅读本身的衰亡。

也可能不是。因为文学,好的文学,一直都是少数人的兴趣。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不来自某种收视率大战的成功,而在于它成功地向我们讲述了,其他地方听不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事。而这少数人——准备阅读和购买好书的少数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庞大。问题是如何引起他们的兴趣。发生的事,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读者的困惑。1999年,美国出版了五千多本新小说。五千多本!如果一年写出五百本能出版的小说就是个奇迹。如果它们当中有五十本是好的,那就够了不起了。如果有五本——只要一本是伟大的,那就值得全世界庆祝。
出版商过度出版是因为,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里,好编辑被解雇或替换,对营业额的痴迷替代了分辨好书的能力。
太多出版商似乎认为,让市场来决定,我们把东西放在那儿,一定能发生点什么。所以,在传媒机器不充分的火力掩护下,它们去商店了,五千本书进入了死亡之谷。这是惊人的自我毁灭。就像乔治·奥威尔1936年说的——你看,太阳底下无新事——“小说正在被呼唤消失”。读者无法在垃圾小说的雨林里穿行,他们会被书里浮夸的堕落语言逼得愤世嫉俗,于是放弃。他们会每年买几本获奖的书,也许买一两本他们认识的作家的书,然后逃掉。过度出版和过度炒作导致阅读匮乏。这不仅是因为太多小说追逐太少的读者,更因为太多小说在把读者赶走。如果像斯坦纳教授说的,出版第一本小说成了一场“对抗现实的赌博”,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分散、无差别的方法。最近,我们经常听说出版界新出现一种无情金融的精神,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编辑的无情。我们要索回判断力。
文学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危险,斯坦纳教授对此只字未提:那就是对知识自由本身的攻击。没有知识自由就没有文学。这同样不是新危险。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凡的当代智慧,原谅我大段引用他的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自由的理念正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它的理论敌人,极权主义的辩护者(今天可以说是狂热主义),另一方面,是它直接的现实敌人,垄断和官僚主义。在过去……反叛的概念和知识诚实的概念被混为一谈,一个政治、道德、宗教、美学上的异端,是不会违背自己良心的。
(如今)一个危险的命题(是),自由是不可取的,知识上的诚实是一种反社会的自私。
知识自由的敌人总说自己在捍卫纪律,反对个人主义。拒绝发表意见的作家总会被扣上利己主义的帽子。他会被指责,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或者想炫耀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抵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浪潮,企图抓住不正当的特权。(但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作,就必须大胆思考,如果一个人敢于思考,他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传统的(orthodox)。
垄断和官僚主义的压迫、社团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压迫,限制和缩小了出版的范围和质量,这是每个作家都知道的。关于偏狭和审查的压迫,我个人在过去几年得到了太多的认知[23]。当今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斗争:在阿尔及利亚、 伊朗、土耳其、埃及、尼日利亚,作家们遭到审查、骚扰、监禁、甚至谋杀。即便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敏感的”风暴兵[24]也企图限制我们的言说自由。继续捍卫那些成就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小说的死亡可能还很遥远,但许多当代小说家的暴死,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作家们已经放弃了后世。乔治·斯坦纳漂亮地称作“美妙的虚荣”的东西,仍然会激发我们的热情,哪怕像他所说,我们因为深感尴尬,不好意思在公共场合这么说。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结尾写下这些伟大而肯定的句子:
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
它将与日月同寿;
我的声明也将永不磨灭。[25]
我相信,每个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同样的抱负:希望将来有人会想起他,就像里尔克想起奥尔弗斯[26]一样:
只有谁曾伴着死者
尝过他们的罂粟,
那最微妙的音素
他再也不会失落。[27]
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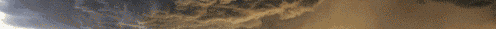
注。释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