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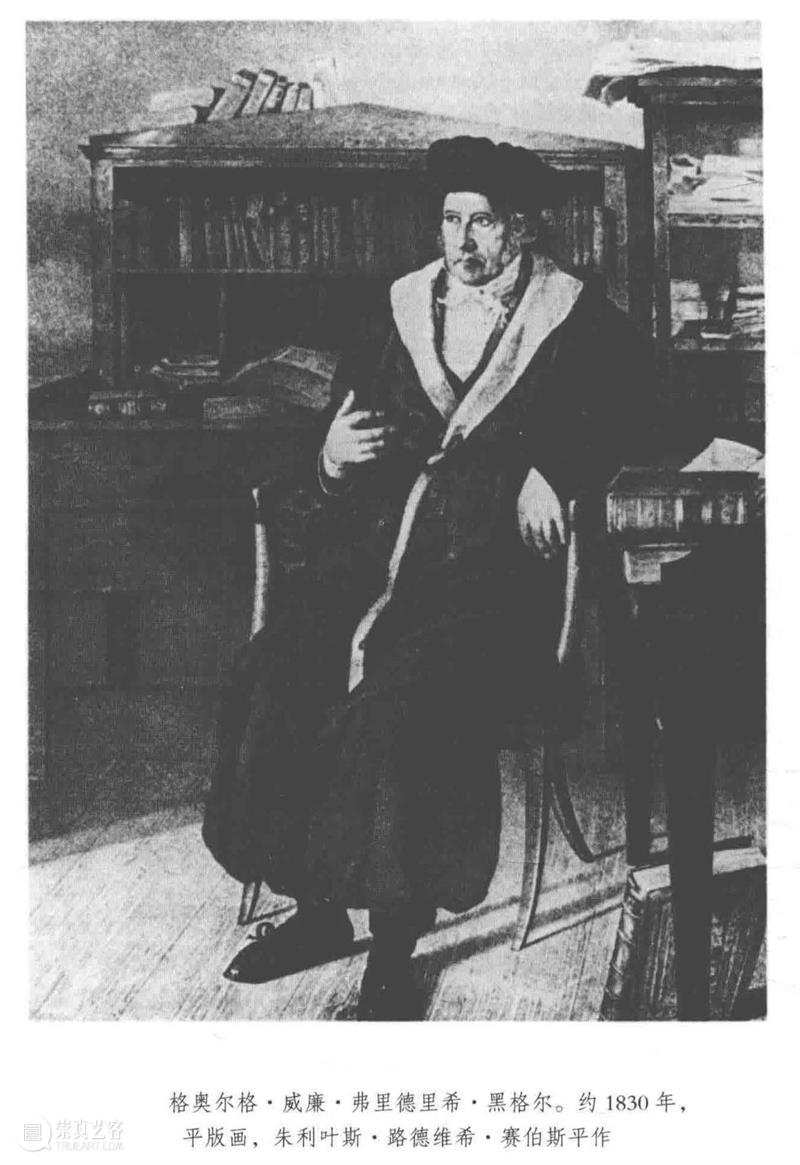
“艺术史之父”
读G.W.F.黑格尔(1770-1831)的《美学讲演录》
贡布里希丨文 杨思梁 徐一维丨译
选自《敬献集——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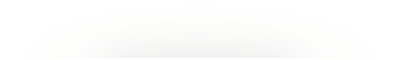
一 温克尔曼的影响
黑格尔是艺术史之父,至少是我一贯理解的艺术史之父。儿子造老子的反,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依据心理学家的说法,他们造反的原因是希望而且感到有必要摆脱父权绝对专制。我一直认为,艺术史也应该摆脱黑格尔的权威。不过,我坚信,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他的强大影响,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把通常属于温克尔曼的角色放到了黑格尔身上。我把黑格尔称为艺术史之父,是因为我觉得正是他的《美学讲演录》(1820—1829年),而不是温氏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构成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奠基文献,因为这部讲演录包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世界[造型]艺术历史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所有艺术的历史。黑格尔对温克尔曼十分敬仰,他曾写道:温氏“在艺术的领域里唤醒了一种新的感觉器官,引进了探索人类心灵的全新方法。”但是,温氏的艺术观念与黑格尔大相径庭。在前者看来,艺术的本质存在于古希腊人的理想之中。跟他的前人瓦萨里论述艺术理想的复兴一样,温氏关注的是这种典范艺术向绝对完美的发展。同时,他视自己的著作为理论文章,目的是借助希腊艺术说明美是什么。假如容我把问题简化片刻,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运用了温氏理论,但限制了它的有效范围。在他看来,赋予感性美以古典形状的业绩理所当然地归功于希腊人。但是,古典主义只能代表艺术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艺术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不可能停滞不前。
那么,黑格尔究竟从温克尔曼那里继承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扩大温氏的静态体系的范围以形成我们如今所知的艺术通史的呢?我欲就此作一概述。我认为黑格尔从温克尔曼那里继承了三种基本思想,并且把它们融化进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三种基本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坚定地信奉艺术的神圣高贵性。温氏讴歌《眺望楼的阿波罗》之美,其实,这一著名篇章是在颂扬神性在人工作品上的形象显现。同他一样,黑格尔最终也在所有的艺术中看到了超验价值的体现。柏拉图曾清醒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新柏拉图主义却使这一观点再度在欧洲知识界流行。依照这种观点,艺术家便具备了观照超自然王国中的理念并向别人揭示这种理念的天赋。也许,我可把这种对艺术的形而上信仰称作“审美超验主义”[aesthetic transcendentalism]。不过,必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跟康德的先验美学[transcendental aesthetics]相混淆。这种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审美超验主义”在温氏的朋友和对手安东尼·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的哲学中比在他本人身上更为明显。然而,温氏从中找到了对美的崇拜理论依据。
黑格尔从温克尔曼那里吸收的第二种基本思想是“历史集体主义”。我指的是分派给某个集体、某个民族的作用。对于温氏而言,希腊艺术与其说是个别艺术大师的作品,不如说是希腊集体精神的表现或反映。不过,这里的精神概念尚不具有黑格尔那种形而上学的意味,而更类似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律精神”[Esprit des lois]意义。第三,即使在温氏那里,这种最高表现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它是一种内在逻辑可以被理解的发展最终结果。希腊艺术的发展阶段,它的风格的演化,必然趋向温氏所谓的“美的风格”;经由高贵严肃的风格阶段,然后由于向感官愉悦让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衰落。这第三种思想可以说就是一种“历史决定主义”,它说明为什么希腊艺术纵然完美无缺,但已在自身孕育着衰亡的种子。
显然,这种决定主义[理论]跟温克尔曼自己的使命,即号召模仿希腊作品,向艺术的黄金时代复归,有点格格不入。温氏学说中的这个缺陷在其德国同代人的眼中尤为明显,因为他们竭力想唤起人们对自己民族艺术独立性的认识。这里,我主要想到了赫尔德[Herder],当然还有席勒[Schiller]。在《论朴素诗与感伤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中,席勒在对古典希腊黄金时代作出恰当评价的同时,试图避免将其视作绝对的顶峰。
二 进步的哲学
正是在那些岁月里,这个黄金时代的古梦不期而至地成为流行话题。好像人类只需勒紧理性的绳,美梦便可成为现实。我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实际上,黑格尔也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宇宙大事。他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这样写道:
自从太阳升空,行星环绕它转动以来,人类从未这样使用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并相应地构造现实……一切有思想的生灵都庆颂这个时代……精神的热情使世界充满敬畏,仿佛神性最终与世界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我确信,只有与这个事件相联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我想称之为形而上学乐观主义[metaphysical optimism]。跟许多同代人一样,黑格尔从这一巨大事变的角度来看待理性胜利之前的各个历史发展;他甚至从无生命物质经由植物、动物界一直到人这样的自然进化阶段中,为自己的理论,即整个历史进程势必导向自知精神[self-knowing spirit]的出现,找到了证实依据。
和其他观点一样,黑格尔在此也采纳了少年时代朋友谢林的信仰:艺术在这个宇宙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黑格尔早期难懂的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6年)中,有三个部分讲到艺术宗教,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极为抽象的术语写成,以至实际的艺术史在其中根本没有位置。然而,在我看来,这部书就像1817年的《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一样,抽象概念之下隐含着温克尔曼的三种基本思想。因为在此,艺术同样从本质上说是神性的显示,同样与某种历史集体息息相关。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艺术必须不掺杂质地提取民族的内在精神,才能成为一种神性的表现。这样,如同审美超验主义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力学原理的地位,温克尔曼的发展逻辑也被提升到了宇宙决定主义的地位,因为精神的自我创造以三段论的强制力推进,艺术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一份作用。由此,艺术史也可被看作是“揭示了真理……可在世界历史中明显看出的真理”。
这类言词中的形而上学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另一个原理。我指的是相对主义。它对黑格尔的艺术史观念以及他对所有历史事件的解释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黑格尔著作中,相对主义原理则是辩证法的产物。就艺术史而言,这种辩证相对主义(其本身又是相对的)只有在《美学讲演录》中才初显其真正的重要性。
三 美学讲演录
黑格尔在柏林作了四次美学讲演,流传迄今的本子是他的学生霍托[Hotho]依据他的讲稿笔记和其他学生的记录精心整理而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在字面上作过多的计较。从整体上看,这部演讲录真实可靠,不容置疑。跟黑格尔别的著作一样,该书文字深奥难懂,表达抽象。对此我无须举例说明。然而,每逢读者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某个似乎是源于生动经历的段落又吊起了他们的胃口。
黑格尔对绘画有真情实感,对音乐偶尔也是如此。但是,他实际的艺术史知识如此缺乏,以至于他居然听信误传,以为布列达的拿骚二世恩格尔布雷希特伯爵[Count Engelbert Ⅱvon Nassau in Breda]的坟墓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尽管如此,黑格尔十分明白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精熟古今各件艺术作品这一广阔领域。”依照他的说法,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不但要求“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要求“非常专门的知识;因为艺术作品的个性总是与其他个别的东西相联系,所以对它的理解和说明需要详尽的知识”。他怀着感激之情说到鉴赏家,同时又不无道理地指出,他们的知识往往局限于艺术作品的外貌,对其真正的本质“不甚了解”,他们“不知道更深入的研究价值……因而轻视这种研究”。不言而喻,这种更深入的研究在黑格尔心目中极为重要。他的目的是要证明对普遍理性信仰的正确性,而这种信仰在他看来不但必不可少,而且宽慰人心。在他的哲学中,决定一切历史事件的乃是那些稳步进化的原理。黑格尔试图表明艺术的历史也可以根据这些原理来看待。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即便如此,读者不会不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在抽绎每一种艺术形式、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风格的特定意义时,黑格尔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为了突出其学说的真正核心,即辩证法,这种一致性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辩证法把形而上的乐观主义锚定在相对主义之上。
我们依然可以参照古代古典主义来轻易地解释这一点。对黑格尔来说,古典主义在希腊雕刻上达到了顶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雕刻处于建筑和绘画之间。建筑仍与物质不可分割,而绘画却体现了精神意识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因为它的真正主题是光——这个思想也许源于赫尔德。
当然,对于黑格尔来说,绘画只不过是进入音乐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音乐是一种全然摆脱了物质桎梏的艺术形式,但它也必须让位于表现纯意义的诗歌。然而,一切艺术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因为“艺术绝不是精神表现的最高形式”。它为沉思所瓦解,为纯思想,为哲学所取代,因而艺术属于过去。
和温克尔曼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古典艺术构成了真正的艺术史中心。但是,由于古典艺术依然把神表现为视觉可见的形象,所以它的完美仅仅代表了精神生活的一个有限阶段。而早于古典艺术的艺术则代表了一个更为缺乏自我意识的阶段——东方艺术。黑格尔称之为Vorkunst[前艺术]。他步新柏拉图主义者克洛伊彻[Creuzer]的后尘,认为东方艺术乃是一种特殊的象征艺术,不适合于表现精神。当黑格尔论述古埃及艺术时,它的象形文字尚未被破译,因而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看法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他的大幸,或者说,是他的不幸。在黑格尔的心目中:
埃及是象征的国度,她为自己规定了译解精神的神圣任务,但没能真正达到这一目标。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我们可以提供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把埃及艺术之谜及其象征作品视为一个埃及人遗留未解的问题……我们可以将那狮身人面像看作是这一埃及精神恰当意义的象征。它可以说是象征的象征……横卧的动物躯体,人体渴望从中挣脱而出……人类精神试图从兽性的无声暴力中奋勇冲出,但尚未完美地表现出自己特有的自由和生动的形状。
在黑格尔的眼中,一座不可言喻的艺术遗迹便成了揭示整个时代精神的隐喻。一旦他坚信那时的精神就像狮身人面像一样依旧受着兽性的束缚,他便可以说:
像蜜蜂营造蜂房那样,埃及人本能地修建他们巍峨的宗教建筑……自我意识尚未盛放结果,尚未达到自我完善之境,但是,它前进着,摸索着,猜测着,不断地繁育着,没有达至绝对的满足,因而永不停息。
不难看出,这幅精神奋斗的戏剧性画面在多大程度上是辩证法原理的产物。从本质上说,这幅画面是对古典理想的一种否定。而黑格尔跟温克尔曼一样,认为这种古典理想只是在古希腊艺术中才得以实现。但是,不管黑格尔在自己的篇章中多么经常地引证温克尔曼,他还是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们相隔的六十年里,人们对希腊雕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对爱琴岛,尤其是帕特侬神庙雕刻的新认识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关注的重点。实际上,黑格尔是最早轻视《眺望楼的阿波罗》的人之一。他用英国杂志上的玩笑把这座雕像描绘成“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他也是头一个把《拉奥孔》说成是一件晚期作品,认为它已退化到手法主义。很可能他对这些作品不屑一顾。他从没去过意大利,从没设法寻找原因,解释“为什么古典古代雕刻给人以有点冷漠的印象,而绘画则立即使人感到更为亲切……在绘画中,我们看到某种活跃了我们自身的东西”。
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关键点是雕刻属于异教古代时期,绘画属于所谓的浪漫时代基督教时期。这种观点完全奠基于这一偶然性上:大理石雕像比绘画更易保存下来。黑格尔当然知道,古希腊人尊重宙克西斯、阿佩莱斯这样的画家,就跟他们尊重雕刻家一样。其实,把绘画解释为一种主观的、浪漫的艺术形式,黑格尔对此并不满意。但是,正如他谨慎地说过的那样,“比之其他任何艺术,希腊观念的内核与雕刻原理更为合拍……这样,不难预料,绘画自然落后于雕刻”。不论事实如何,黑格尔力图依据它们表现特定精神价值的能力来考察每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努力引导他去描述画家的媒介,其描述之清晰,在艺术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我们来说,“绘画性”这个观念与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名字相连。沃尔夫林在《美术史的基本概念》[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中明确地描述了艺术风格从雕刻向绘画的发展。我们应看到,黑格尔也相信,“雕刻性”必然先于“绘画性”。因此,在一个几乎好像是出于沃尔夫林之笔的段落中,黑格尔谈到了绘画中的雕刻—塑造[plastic-sculptural]成分和绘画构图问题。他写道:
下一种类型的布局依然完全是建筑式的,即人物的平均并列,或人物本身、姿态、动作有序对立和对称组合。金字塔组合形式在此极为普及……在《西斯廷圣母》[the Sistine Madonna]中,这种组合方式仍然保持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说来,就视觉而言,这种组合平静舒适,因为,金字塔形通过其顶点把本来分散排列的东西集中了起来,使群像从外部上看具有统一性。
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借用一切可用手段的画家,即“绘画性”画家,依旧可以发现更多的发展前景。因而,在黑格尔详尽描述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十七世纪荷兰绘画自身实际上变成了目的。厌倦于枯燥无味的论述,黑格尔在一些段落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绘画的自发反应。把这些段落搜集成一小册,的确值得这么做。他那概念磨坊碾机的嘎嘎之声停息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艺术作品的真正热爱。举个简短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本质上,古典艺术在表现它的理想时仅仅赋予固定的东西以形状,但在这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色:一条溪流,一道瀑布,大海的波涛浪花,光斑散落的杯盘之类的静物等。特定情境中精神现实的外部形态:烛光下穿针引线的妇人,一群正在劫掠的盗匪,一个姿态中最转瞬即逝的方面——一个农夫的哈哈大笑;在表现所有这一切上,奥斯塔德[Ostade]、特尼尔斯[Teniers]、斯梯恩[Steen]都不愧为大师……但是,即使心灵和思想得不到满足,更仔细地观察对此可以作出弥补。因为,正是绘画和画家的艺术应该使我们高兴和激动。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绘画,我们必须观看这些小画,这样我们才能谈论这个或那个大师:现在,他真正会画画了……
黑格尔去过尼德兰,显然,他对荷兰绘画充满感情。如果说他对意大利艺术的描述主要是建立在出版不久的鲁莫尔[Rumohr]重要著作上的话,那么,他对荷兰绘画的描述完全是依赖自己的观察。也许,其中仍带有一些意识形态因素。不少人认为,对纳扎勒派[Nazarenes]的罗马化同情[Romanizing sympathy]减少了人们对新近发现的所谓的“原始性”意大利画家的兴趣,而黑格尔在荷兰则能够从绘画本身,并且通过绘画,欣赏新教主义的胜利。“在其他任何环境下,任何其他民族都不会把我们在荷兰绘画中所见的那些题材当作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来描绘。”黑格尔指出,他们选择这些题材是出于“他们对自己赢得的自由意识,通过这种自由,他们获得了富裕、舒适、公正、勇气、欢乐,甚至对自己快乐日常生活的自豪感。”
温克尔曼曾把希腊民族理想化,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甚至也可以从这种对荷兰民族的赞扬中看出那种理想化的回声。同时,跟温氏的情况一样,我们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繁荣内部隐含着自身瓦解的种子。绘画的“色彩魔力”是向音乐的一个必然过渡期。在分析这种艺术形式时,黑格尔显示了对莫扎特和罗西尼的强烈热爱,而这种热爱跟他费尽心机地去建立纯粹的概念系统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使我们大感惊异。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黑格尔来说,他的美学范畴理论是他整个哲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正如他在《美学讲演录》中写道:
只有哲学的整体可以等同于作为自身独立的、有机整体的宇宙知识……在这个科学必然性的王冠里,每一个单独部分一方面是向自身旋转的圆圈,另一方面同时与其他各部分保持着必然的联系——前者是一种从中导出自身的向后运动,后者是一种推动自身向前的运动——只要它富有成果地从自身生产出“另一个部分”,并使之能够进入科学知识。
显然,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诱人的地方,因为,在它那里,每一种可以设想的自然现象、精神现象和历史现象都各得其所。正是因为黑格尔是这种体系的最终、最一以贯之的营建者,所以当他的形而上学失势时,这种哲学仍然没有丧失影响力。
四 艺术史中的决定主义
并非仅仅是那些同意其《哲学全书》中每一定义的哲学家们接受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论。众所周知,例如卡尔·马克思虽然与黑格尔精神第一性的命题针锋相对,但他提出了物质第一性的反命题,以便——用那著名的辩证法双重意义来说——既取消又保存这个体系[aufheben]。马克思试图改造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使之世俗化,但至少不因此而牺牲那关于一切历史事件的概观。马克思的这一尝试影响最大,但绝非是这方面唯一的尝试。我在《寻求文化史》[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一文中,力图说明德语国家中艺术和文化史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强大影响。从卡尔·施纳塞[Carl Schnaase],经由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rak]至欧文·潘诺夫斯基[Ewin Panofsky],他们都致力于通过艺术“重构”时代精神。我的分析虽然简短,但在此不想也无法重复。不过,我心中有一事必须申明。那就是我不愿让人觉得我对这些伟大学者缺乏敬意。其实,我认为,对于一位学者的最大敬意莫过于严肃认真地看待他,不断地重新检验他的论点。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我坚决反对艺术和文化史研究放弃寻找现象之间的联系,仅仅满足于罗列事实。假若罗列事实是我的目的,我肯定不会关注黑格尔了。在此使我踌躇的不是我认为这类联系难以建立,而是太容易[建立]了。这听来似乎自相矛盾。但黑格尔的庞大体系恰恰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言而喻,黑格尔善于雄辩,但我们已经察觉,在解释埃及艺术时,他是怎样从隐喻滑到实际事实的。我们又看到,他是怎样把阿佩莱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推到希腊艺术的边缘,以便符合他自己勾勒的艺术历史次序的。
甚至专业史家也很容易受到corriger la fortune[饶幸]的诱惑。归根到底,任何历史记述都是,而且必须是选择性的。因此,史学家注重意义重大的事实,忽视非本质的东西,这是自然而然的。伟大的科学方法论者卡尔·波普尔使我对这类危险诱人的说法保持警觉。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寻求证实自己的假说,他首先时刻注意反证。一种不可能与任何东西冲突的理论不会有科学内涵。黑格尔遗产的危害恰恰在于它诱人的易于适用性。毕竟,辩证法可使我们从任何矛盾中轻而易举地脱身。由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像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所以任何一种解释方法都可以声称成功。在此,首先取决于一个看似有理的出发点。例如,我们在莱辛的著作中读到“艺术家必须吃饭”,的确,艺术家不吃饭便不能画画。这样,肯定可以在肚子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信的艺术史体系。
所有这类解释的企图常常使我想到那个古老的逸闻。有位农夫,卖掉了一头猪,得了三百克朗。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小酒店里,眼前摆着钱袋。他把钱币倾倒在桌上,开始数钱。“一个,二个,三个克朗。他数到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克朗,开始打哈欠,然后数到一百五十、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一个克朗,他突然把钱统统聚在一起,扫进口袋。他的同伴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农夫答道:“数到现在没错,其余的准对。”
当然,我并不以为自己是第一位,甚至是唯一的艺术史家提倡检验。恰恰相反,我常常扪心自问,在黑格尔死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今天,我对某些历史解释的反驳是否在与假想中的敌人论战。然而,我经常发现,我们不是在向假想中的敌人开火,而是在与真正的巨敌交战。我已提到五个这样的巨敌,我用古怪的名字称呼它们:审美超验主义、历史集体主义[historical collectivism]、历史决定主义[historical determinism,一译历史决定论]、形而上学乐观主义[metaphysical optim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它们都是神秘的普罗托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或河神,以多种化身出现——译注]的眷属,万变不离其宗。
超验主义,即艺术作为启示的观念,以一种世俗化形式幸存了下来。艺术作品虽已不再被视作精神自我实现的显现,但依然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表现。这种时代精神透过作品的表现而显现。“表现”一词,词义多性,捉摸不定,但却为这种转型提供了便利,使史学家能够揭示隐含在艺术作品背后的时代哲学或经济情况。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与集体主义相联系。个别的艺术作品是根据风格加以考察的,而风格又可以解释为一种征候,显示了阶级、时代、种族和文化的面貌。
决定主义对这种方法起了明显的,或者说至少是隐晦的关键作用。黑格尔遗产的本质在于一种先验信仰,即哥特式风格是封建主义或经院哲学的必然产物,或者认为,这三种现象只不过是相同的基本原理的不同显现而已。诚然,不容否定,这三种不同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在此,问题仅仅在于发现无聊变为荒谬——用黑格尔特别喜欢的说法变体来说——的转折点。确实,历史决定主义已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以致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如果一个问题可以真正得到解决的话。我们无须对历史因果问题、自然法则的正确性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做出任何决断才能否定历史发展依照着一个必然过程的观念。哥廷根[Gottingen]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曼弗雷德·冯·艾根[Manfred von Eigen]最近强调指出,我们可以承认自然法则的正确性,但无须把这看作是充足的理由而断定历史沿着不可改变的、预先规定的道路前进。我经常喜欢把对艺术创造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跟气候对植物的影响作比较。这种依赖关系无可否认,而植物反过来也影响气候,这一事实可以介绍给那些辩证法的倡导者。从古树的年轮里,我们甚至可以了解气候变化。然而,这种推算的正确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并非仅由这两个因素促成。无数其他无法事先预计和重构的事实都起了作用。值得牢记的是,在澳大利亚偶然引进一对兔子,几乎导致整片国土片草不留。人们无法回避这偶然现实。
诚然,我知道黑格尔在第二版《哲学全书》中解释了他的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中的一句名言:“凡是理性的[vernünftig]都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都是理性的。”他的大意是,他所理解的真实“并不是掺杂着偶然性的纯粹经验存在,而是与理性概念不可分割的存在。”但是,这一解脱困境的努力最终是建立在循环论证基础上的。因为,假如偶然性与哲学无关,那么历史肯定也与哲学无关。因为历史总是一再应验古老的谚语:“小因大果”[Kleine Ursachen,grosse Wirkungen(small causes,great effects;tall oaks from little acorns grow)]。这句有效的咒语可以永远驱除历史决定主义鬼魂。
这一点本来是如此明显,以致我们必须自问,为何人们要经常抵制这个洞见。也许,偶然的威力损伤了我们的自尊。我们谈论生活和历史上难以觉察、荒唐可笑的巧合事件;我们甚至发现,只要把生活和历史上的不幸事件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些不幸都将比较容易忍受。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乐观主义想让我们相信,一切终归会导向完善。如果我们分享这种信仰,一切会变得多么轻松!愿望产生思想。不论以何种方式,人们总可以表达对[人生这部]宇宙之剧预先设定的美好结果的信念。当然,并非是一切决定论者都是乐观主义者。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虽然在许多方面与黑格尔相似,但他预言了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没落。可是在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乐观主义的实质性观点是,任何衰亡退化都是在为更高形式的发展铺平道路。
只要这种相对主义包含着决定论成分,我便可以将它描述为当代艺术史教学的官方教条,我认为自己这样说不会大错特错。[根据这一教条]人们不该指责不可回避的东西,正如地理学家不该指责冰川时期一样。无疑,在艺术史家采取这种态度以前,它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从它的水平趋势[levelling tendency]而言,它的存在甚至早于黑格尔。依照黑格尔,衰落是自然存在的,即使衰落确实为进步铺了路。今天,人们认为科学的态度就是要尽可能清除艺术史家语汇中衰落的观念,以便于赋予每个曾遭谴责的时代在发展之链上以合理的位置。十八世纪对哥特式艺术的平反甚至为黑格尔所接受。此后,沿着布克哈特的道路,沃尔夫林为巴洛克艺术平反,维克霍夫[Wickhoff]维护罗马艺术,李格尔偏袒晚期古典古代艺术,马克斯·德沃夏克为墓穴绘画和埃尔·格列科辩护。而瓦尔特·弗里德伦德尔[Walter Friedlander]使手法主义艺术摆脱了衰败的污名;米勒德·迈斯[Millard Meiss]则对十四世纪晚期绘画作了肯定的评价。眼下,我们甚至看到对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绘画的尊重正在复兴,而在不久以前,这类绘画仍被看作是庸俗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不容置辩,我们从这种种努力中获益匪浅:我们摆脱了偏见,学会了更仔细的观察。
我热爱和平,只要那五位巨敌不逾越各自的界限,我乐意让其各有玩物。我甚至愿向形而上学乐观主义承认,的确存在着一种将自然与历史系连的进步形式。自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懂得,这里无须目的论,只需适者生存的残酷机制。在艺术领域里,一个意外的变化有时或许会引出充满希望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反过来又会导致进一步的选择。首先是在古典时期,然后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一直是[当时的作者]根据不断进化的观点撰写的,温克尔曼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应该承认,这些观点认为是衰败的东西也可以根据相对论意义被解释为另一个适应过程。但适应什么呢?毕竟,并非是每一个集体、每一个群体都会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标准提出相同的要求。关于这一问题,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不无道理地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真正的艺术史与艺术语汇和风格的历史相混淆。当然,较之掌握艺术这一现象,风格史更适合假说性重构的尝试。如果没有运气帮忙,甚至艺术杰作也不能产生。不过,在这一点上我愿向审美超验主义认输。最高的艺术成就必定升华到这样一个境界:即使在原则上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五 艺术批评的让位
黑格尔提出的问题一直为人关注,我认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只有把这些问题跟当前的艺术情景相联系时,它们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此提到“历史”这词的复杂多义性。而这个词也进入了本文的标题。黑格尔,“艺术史之父”可以指他与艺术史学史的关系,正如本文至此所讨论的那样,它也可以表示黑格尔影响了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这个问题无疑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记住,历史的写作也能影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进程。正是这种黑格尔也许会描述为“辩证法”的反馈可以说明为什么黑格尔历史哲学具有这样决定性的影响。让我们回想一下,黑格尔在艺术中不但看到了神性的反映,而且看到从艺术家身上穿过的、不间断的创造过程的一个侧面。因此,古典古代主要赋予诗人的角色落到了每位真正的艺术家身上:他是先知、预言家,不但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且辅助上帝实现上帝自身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座中比在美学讲演中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看待这种神圣使命的历史作用的。的确,他所谓的“世界上的历史性个人”更直接地指涉政治领袖。他主要想到了镇压法国革命但同时却保存了革命成就的拿破仑。在一封写于耶拿之战之后的著名信札中,黑格尔称拿破仑是“这个世界的灵魂”。但是,当黑格尔谈到伟人时,我们也可以把艺术家包括在内。无论如何,艺术家不愿把自己排除在外。依照黑格尔所言,他所谓的“这些世界精神的经营者”的任务是“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将必然迈出的下一步,将这一步看作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奉献力量……他们仿佛代表着早已被内在预示的下一个人种”。
在当前预见未来,这显然是凡夫俗子无法认识和理解的。因此,他们只能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世界精神追求的东西,必然是新东西。这样,旧事物被贬值,而未知的、未经尝试的东西必然包含着孕育未来的种子。被自己的时代否定成了天才的标志。伟大的艺术家必须走在时代前面,否则,便不是伟大的艺术家。
我们之中不把风格、潮流和时尚变化看作是一种更高目标启示的人必须扪心自问,如何才能真正知道未来将欣赏什么?的确,我们甚至会纳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设想下一代肯定比我们自己具备更好的艺术趣味呢?不过,对那些拥护黑格尔形而上学乐观主义的人来说,这个选择过程已由现在转向未来。只有未来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才是经受住了神意志的考验。这样,从理论上说,对同代人的批评已完全不可能了,因为这种批评总是担着风险,在将来会证明是亵渎神明。最终,批评家唯一可做的是看清风向。于是,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一个更加危险的巨魔从形而上学的背后出现:形而上学机会主义[metaphysical opportunism]。
波普尔和我本人都不会断言,艺术中的进步哲学即先锋派理论完全是在黑格尔哲学刺激下培育出来的。但我相信,可以证明黑格尔传统对此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我在别处已提醒大家注意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一段话。海涅从黑格尔哲学中明确地得出了艺术批评的这一后果。海涅把黑格尔看成自莱比尼兹[Leibniz]以来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把他放在康德[Kant]之上。在黑格尔逝世那年,即1831年,海涅在他关于这年巴黎沙龙展的文章中与一些批评家辩论,因为他们抵毁德斯康普[Descamps]的一幅画,认为其素描功底太差。海涅坚持认为:“我们应以艺术家自己的审美标准来评判每一位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对于每位艺术天才来说更应如此……色彩和形状……只不过是理念的象征符号,当神圣的世界精神触动心灵时在艺术家胸中浮现的象征符号。”海涅谈到了艺术家的“神秘束缚”,[他认为]从这一缺乏自由的角度来看,任何批评都是自命不凡,卖弄学问。
的确,在艺术批评领域里,经过很长时间,批评家才自认失败,由此而走到黑格尔会称之为“艺术批评的自我瓦解”的地步。但是,十九世纪的每一个此起彼伏的艺术革命浪潮都给乐观相对主义以新的推动。对进步的信仰,不但把政治界,而且把艺术界两极分化;剩下的只是前进的动力和反动的惰性。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任务不再是批评,他们的使命是为运动助战,成为新时代的信使,尽心竭力把预言变为现实。请记住,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宣言是以怎样的狂热,大肆运用启示录式言词宣告新的黎明、新的时代、新的体制[的到来]。黑格尔也为这些宣言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埃卡特·冯·西多[Eckart von Sydow]在1920年的《德国表现主义文化与绘画》[German
Expressionist Culture and Painting]的小册子中写道:“我们可以不受太多限制地说,正如在中世纪的岁月里一样,德国精神又一次建立了与世界灵魂的直接联系。”
请勿误解,上述的评论并非是反对表现主义的,而仅仅是反对表现主义在审美超验主义中的形而上学基础。我甚至愿意进一步承认,形而上学信仰的确可以激发艺术家,激发艺术运动。几乎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宗教性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宗教成分同样具有激励人心的作用。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艺术史家必须研究黑格尔,就像中世纪宗教艺术学者必须精熟圣经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比如说)理解现代建筑的兴起及其当今危机。
以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话为例,1923年,他在《民族包豪斯的观念和结构》[The Idea and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Bauhaus]一文中写道:“一个时代对世界的态度在其建筑中结晶,因为,在这些建筑中,这个时代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同时得到了表现。”从他在第一次包豪斯学生习作展开幕式的优美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梦寐以求的是怎样一种表现:
代之以庞大的学术机构,我们将目睹那些小型的、秘密而自我独立的团体、房舍、工场和[建筑]方案的兴起,它们旨在守护作为信仰核心的神秘,旨在赋予这一神秘以艺术形式,直到这些孤立的群体再次融入一个涵盖万象、生机勃勃的精神和宗教愿景,而这个愿景必须最终结晶为一个伟大的Gesamtkunstwerk[综合艺术]。然后,这个伟大的集体创造物,这座未来的雄伟教堂,将会光芒万丈,照亮日常生活中每一最细小的物体。
我希望,每位读者都可以从这位伟大建筑师的话中觉察到浓厚的醉意。但是,酒醉之后,往往伴有头痛症。我们无须等待多久,便可看到这一点。1976年,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史家和批评家之一,约翰·萨莫森爵士[Sir John Summerson]在接受英国皇家建筑学院金质奖章时谈到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英国狂热倡导现代建筑,他评论到,现在他发现自己某些文章中的想入非非乐观主义使他“倒胃”。另一位重要的英国批评家在同样的场合坦率地承认,在为现代建筑奋斗期间,他时而赞扬了一些他实际上并不认为出色的作品,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现代的,而非保守的。这些坦诚之言值得最高的尊敬。只要人们仍在从事建筑实践和教学,我们就应该欢迎如今发生的一切辩论。只有通过批评讨论,我们才能从过去几十年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绘画和雕刻这样的视觉艺术中,要恢复这种批评讨论实非易事。因为它们毕竟缺乏建筑作品所遵循的实际标准。批评家完全可以自说自话。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批评家不抱任何偏见,摒弃对未来的梦求。但是,从理论上说,他们无权使用“我们的时代”之类的口号,更无权使用“未来时代”的口号来从事批评工作。
康德固守下述严厉逼人的原则: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减轻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负道德责任的重担,哪怕是黑格尔在历史中所见的神的显示也不能。“因为”,他写道,“无论一种存在能够以哪种方式被描述为神性……并且显示自身”,这都无法使任何人摆脱“自行判断是否有权把这样一个存在视作上帝,并如此加以崇拜”的责任。康德的要求也许超过了凡人的能力,但是,如果艺术世界能够认识到康德言之有理,那么,我们可以取得许多成就。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