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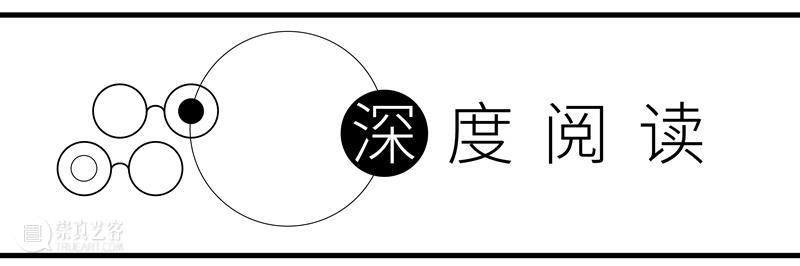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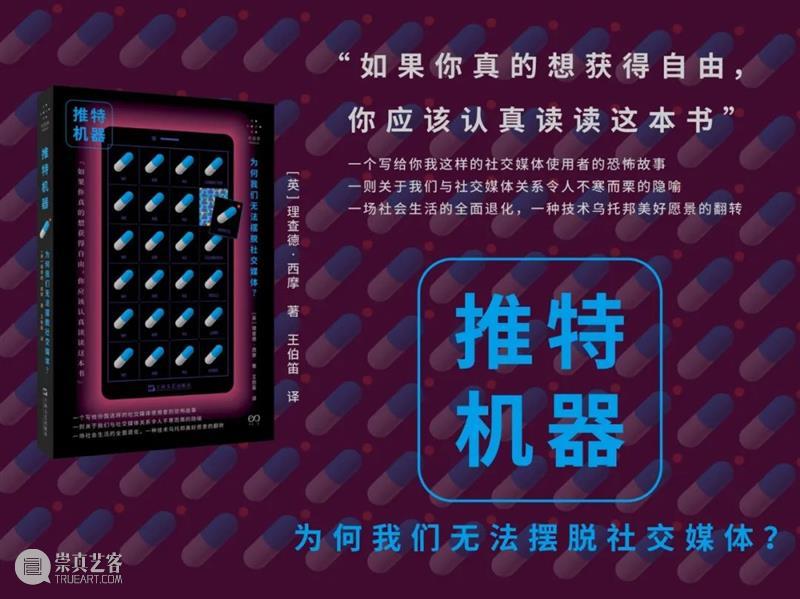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理查德·西摩)的书评。原文见http://mediatheoryjournal.org/review-richard-seymours-the-twittering-machine-by-sean-phelan/。作者:肖恩·费兰(Sean Phelan,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传播新闻与市场营销学学院助理教授,写这篇文章时兼任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传播学学院高级研究员)。译者:王伯笛(也是这本书的译者)。中译文主标题系拜德雅微信公众号编辑所拟。
从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概念谈起
评理查德·西摩的《推特机器》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哲学特色最鲜明的著作《帕斯卡式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一书中,解释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符号暴力指的不仅是无需对肉体强加武力就能调解社会关系的话语权力形式,它还代表了暴力目标本身就是暴力同谋的暴力形式。“符号权力只有在遭受这一权力的人的合作下才能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帮助构建了这种权力。”布迪厄认为,“最危险的理解”莫过于将这种共谋解读为“有意识的、清醒的”“自愿奴役行为”,仿佛个人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其自我支配一样。恰恰相反,符号暴力指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形式,这种支配源于随时间累积而成的习惯性的社会存在模式。“其本身就是权力的结果,通过认知和(尊重、敬仰、爱慕等)倾向被持久地刻入被支配一方的体内。”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在成为习惯后实际上被默认的信念,对身体的训练则是这些习惯的源头”。
当我开始阅读理查德·西摩精彩的《推特机器》时,我立刻就想到了符号暴力。每章标题都捕捉到了我们自己与当今互联网文化中反乌托邦特质的纠葛:“我们彼此相连”,“我们都是瘾君子”,“我们都是网红”,“我们都是喷子”,“我们都是骗子”,“我们都在消亡”,“我们都是书写动物”。布迪厄所说的受训的身体习惯,被重新想象成驱动着我们不断触摸手机和电脑的力量,我们担心与媒介化的世界失联,而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对发生在网上的最新动态表达仰慕或不屑。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西摩不需要听人赘述是怎样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构成了我们的数字生活;他的书与只把网暴当作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心理缺陷来对待的道德化评论截然不同。不过,即便是在剖析不同的结构力量(平台资本主义、监控文化、大数据、算法威力)产生的腐蚀性影响时,西摩仍会不停地回到共谋这一主题上。“《推特机器》或许是个恐怖故事,但我们所有人都是与这个故事有关的用户。”“尽管社交媒体常常令人厌恶,但我们却对此上瘾,或者正是这一特质导致了我们上瘾,就像我一样,这说明我们身上有些东西正在等待上瘾。”
在“作者的话”中,西摩说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作散文来阅读,而不是像一篇论战或学术论文”。但他在需要抨击时也毫不拐弯抹角。此外,正如熟悉西摩其他作品的人知道的那样,他笔下的内容充满了政治关切。《推特机器》一书富有想象力的论述力量在于它直接提出的问题,不在于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直截了当的答案,或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号称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本书提出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存在的问题: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媒体世界中,我们把如此多的时间花在表演和筹划上,尤其是花在把我们当作首要剥削对象的平台上,这种书写对人类集体意味着怎样的后果?正如西摩在前言末尾写道的那样,“这本书的故事算是提出了一个勉强带有乌托邦意味的问题:如果不参与社交媒体,我们还能用书写来干什么?”
书的标题为审视推特提供了特定的视角,但西摩的论述着眼的对象则更广。标题《推特机器》源于保罗·克利(Paul Klee)1922年的一幅画,画的影印版也出现在这本书的开头。画描绘了几只盘旋在火坑上方、棍子形状的机械鸟,它们是为了将受害者引入坑的诱饵。在西摩的解读中,这幅画比喻了互联网文化的诱人之处其实也是圈套。我们在被自身版本的“鸟鸣圣乐”吸引的同时,将自己暴露在我们看不清、也无法任意忽视的隐患和危险之下。我们的欲望变得与机器密不可分,即便“没人有意将自己献给机器,成为对它欲罢不能的瘾君子”。我们一方面屈服于结构精密的支配体系,另一方面借此肯定我们的个人自主权。“我们与机器互动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源于选项随意被设定,但却仍被视为自由选择的愉悦体验,不管是令人抑制不住的自拍潮,还是凌晨3点让人发狂的争吵。”
西摩可能没打算写一本学术专著,但对理论的敏感和洞见在他的书写中比比皆是。散文式的开放结尾让以事件为核心的分析形式比许多学术作品都更犀利,也更有启发性。他严谨地引用了众多学术讨论来支持他在书中的不同论点。他以新闻记者的风格生动地呈现了不同的事件经过和网络混战,这些都证实了这台机器的惩罚性倾向。
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术语是精神分析学;西摩的理论洞见与他的文学修养相辅相成,让人回想起最富有启发性的那些精神分析学作品。他想理解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欲望究竟如何组合在一起,驱动着我们将自己的大量时间与注意力花在“社交工业”上——他更倾向于这样称呼“社交媒体”,常用的形容中带有谄媚的味道。他尤为感兴趣的是探究书写工业化语境中书写与欲望的关系;我们养成的这一阅读体验让我们读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没耐心,我们只想从阅读中搜刮更多能被书写和评论的材料。《推特机器》是“一个有关欲望与暴力,也有关书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讨论的媒体生态中,“突然间,我们都成了书写动物——被不断书写的暴力欲望的所占据。”
与大部分数字媒体方面的学术和大众评论不同,最让西摩感兴趣的技术是书写本身。书的第一章是一部书写简史,而在最后一章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西摩强调的是书写的物质基础:“由绳结讲起只是想强调书写是物质的,以及我们的书写材料的质地如何塑造并刻画我们能够书写的内容,而这点让书写不再无关紧要。”西摩对技术发展的辩证特征的警觉是这本书最具魅力的特点之一。他回避了明显的技术决定论陷阱,没有让“社交媒体”听上去像是我们当代所有顽疾的根源。但他也回避了完全相反的陷阱,即约翰·杜尔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指出的:批评家们想要证明他们自己的分析完全免于技术决定论的“谬误”,但这样的愿望轻视了技术的决定性力量。
西摩讨论的重点是推特机器的放大效力。如果说是这台机器“带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如上瘾、抑郁、‘假新闻’、喷子、网络霸凌、极右亚文化,那么这台机器只不过是在利用和放大这些在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问题”。小报文化“将私生活转化为有利可图的信息”,这就是“监视经济”的前身,它支撑着社交媒体企业的商业模式。伊斯兰国娴熟地将推特用作他们的宣传工具,但他们“并没有在威尔士小城里、瑞典青少年中、或是法兰西岛大区城郊被呼来喝去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中,制造出这一滩能被恐怖组织招募活动加以利用的苦难”。线上霸凌和小道消息盛行的现象,不过是强化了职场文化和专业八卦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倾向。
西摩认为,推特机器“以全新的方式”将现有的社会问题“集体化了”。“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打乱了原有的等级制度,人们不会再因违背了中央权力结构认可的“权威神圣文本”规范而受惩罚或遭社会排斥。“排除异己与道德恐慌,以及进行惩罚和羞辱的权力被移交与下放。”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社会景观正被重构,其形式不再遵循从上至下传递命令这一“大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模式。相反,社会景观被重新集中在我们为社交工业书写和分发信息的形象上。我们的集体社交体验越来越被机器的逻辑所左右。我们按照机器的奖励机制和它中意的写作用语为我们的公共人设编排剧本。大型科技企业将我们的参与式劳动转化成商品,而我们成了这些商品中抽象的数据点,可我们却还试图通过互联网中“地位股票市场”的复杂等级提升我们在其中的文化资本。我们对这台机器的瘾称不上“灾难的根源”,它更应被视为当今注意力经济中的“生产方式”。即便我们在社交工业平台上谴责新自由主义式自我身份的必要性,但我们其实都内化了企业家式自我的教育理念。
在这台机器的特点中,最令西摩感到担忧的是其法西斯潜质。“我们应该开始认真思考,社交媒体业是否有可能本身就具备早期法西斯特质,或者说,社交平台尤其适于培养早期法西斯主义。”他在谈到极右翼如何成功利用YouTube打造了瑞贝卡·刘易斯(Rebecca Lewis)所说的“影响力替代网络”时提到了这一点,该网络模糊了更极端和更主流的政治身份认同形式间的差别。游戏化的YouTube算法能解释网上极右翼的崛起。但西摩认为,如果我们局限于单一的技术决定论解释,“我们就错过了真相。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新纳粹内容或者阴谋论式的信息娱乐如此引人入胜?”
这个问题让我们再度意识到,人类欲望在塑造我们对机器的投入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网络极右翼就是“正在兴起的技术政治政体”的例证,这一组织松散但具备意识形态潜力的联盟,通过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分享他们嘲弄共同敌人(如“社会公义热心人士”、“激进女性主义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社会建构论者”等形象)的乐趣而成为现实。社会生活被呈现为无止尽的对抗。“击败敌人”成了驻足于这台机器的部分乐趣,被我们常态化了的社会互动模式“放大了我们的暴力、我们对一致性的要求、我们的施虐癖、我们一心只能接受自己永远正确的怪脾气”。
就像在书中其他地方一样,西摩就推特机器的法西斯潜质进行的论述让我们欲罢不能。“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只与像网络喷子、黑客和右翼恶霸这些显而易见的坏蛋有关,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他引用了每一位推特用户都熟知的线上风格,也就是“转发式批评”来说明这一点:即我们转发别人无以复加的愚蠢推文或无脑推文,并借此将他人的注意力导向我们才是正确的这一做法。这种极度缺乏宽容的做法竟能让无比平庸的线上互动生机勃勃,这让西摩感到十分震惊。宽容的缺失能质变为以施虐为形式的反政治。“我们邀请他人加入对话,但我们却将分歧当作恶意与愚蠢的表现或是来自一事无成者的哭诉,而不是将其当作对社会有建设意义的声音。”
推特机器对情感的影响力如何能阻碍被威廉·康纳利(William Connolly)称为“争胜式尊重”(agonistic respect)的政治观念?西摩对此的讨论颇具启发性,因为该讨论描述了同样在网络左翼身上能被明显观察到的党派主义倾向。该话题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但作为一位本身写作背景着眼于左翼战略问题的作家,我们不难想象西摩能写出一本更偏论战风格、聚焦于该话题的完全不同的书。西摩在讨论身份政治时以更晦涩的方式提到了一条类似的论述线索。西摩对这类讨论的处理方法构造出了比左右两翼对身份政治反击式的批判更有趣的对象。他对身份政治的看法,与推特机器的所有使用者有关;“社交媒体的内在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因为在媒体平台上,我们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表演某种身份。”这番话指的是许多网络政治中的压抑倾向。在操纵之下,我们对身份/差异关系进行着重复单调的表演,而表演本身与这台机器的运转逻辑和线上社群内“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认同问题进行表态”的状况密不可分,这样做“既能激发热情洋溢的团结感,也能导致敌意的突然爆发”。西摩好奇我们是否需要某种能鼓励我们“时不时地忘记自己”的“‘反身份’政治作为解药”。这一观点响应了那些对身份概念保持警惕的政治批判理论,如雅克·朗西埃(Jaques Ranciere)和之前提到的康纳利这样的学者。此外,这一观点或许还含蓄地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被机器放大了的冲突,尽管从战略上看通常对左翼有利,但也可能拖累在不同的左翼身份和派别间建立有效政治同盟的进程。
《推特机器》不是一本旨在列举数字文化利弊的书。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这是一则恐怖故事,是那种最吓人的恐怖故事,因为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所设定的世界。不过,或许通过深度剖析我们与网络生活毁灭性的一面的共谋关系,我们能找到某种政治希望。这是西摩这本书的人文主义立场,它要求我们反思自己在一个就目前状态而言,不需要民主的“新民族国家”的诞生中代理的角色。至于我们还能用这些时间干点儿什么,这个问题无疑会在我们读完这本极具感染力的书后找到有政治意义的新答案。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Connolly, W. E. (2005). Plur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wis, R. (2018). “Alternative influence: Broadcasting the reactionary right on YouTube,”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s://datasociety.net/wp-content/uploads/2018/09/DS_Alternative_Influence.pdf (accessed 22 April 2020).
Peters, J. D. (2017).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Representations vol. 140, Fall, pp.10-26.
Ranciere, J. (2009).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London: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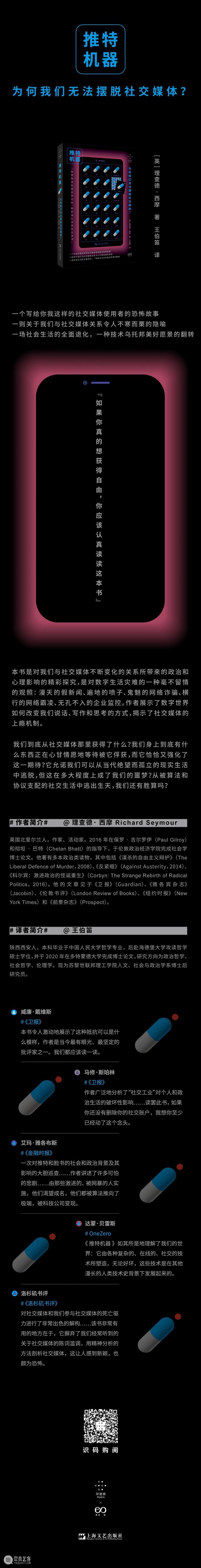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