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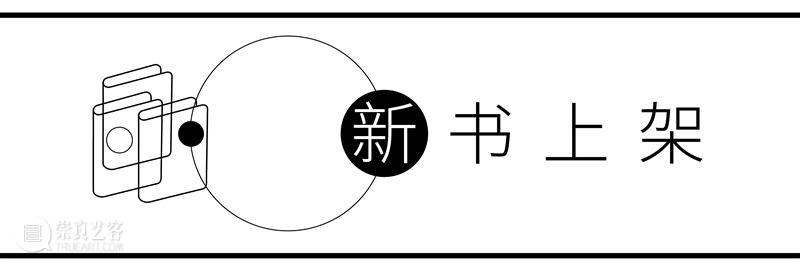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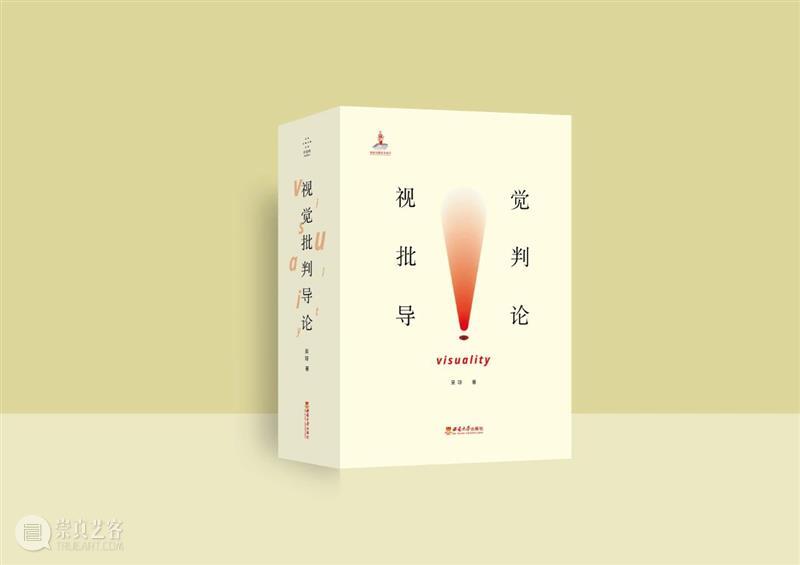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视觉批判导论》(吴琼)的书摘,节选自本书第四章“观看与主体性”的第二节“他者的目光”(第537-543页),注释从略。
目前此书已上架我们合作的西南大学出版社的微店,欢迎大家识别文末新书海报中的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行购阅。此书由西南大学出版社直接发货。
实际上,在拉康那里,纯粹的镜像式观看是一个神话性的时刻,因为人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其认同必定离不开在世结构的纠缠,离不开这个结构提供给他的认同环境、手段以及尚待理想化和对象化的认同中介的作用,就连镜像观看中的“镜子”也已然是一个社会之物,一个已经注册了社会标记的程序化装置。所以,对认同及观看与认同的关系的思考应当考虑到更为复杂的语境运作,“三界”框架(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的提出就是为此服务的。
对拉康而言,“三界”不但是构成主体之无意识的三个界域,也是支配主体日常行为的三种秩序,亦是结构主体之欲望的三重界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同生共死的纽结;它们在主体身上共时性地发挥着作用,使主体成为一个多元决定的东西;它们每一个都以自身的逻辑建构着主体不同的存在维度,同时每一个都在主体的身上嵌入了异化和分裂的因子,故而它们之于主体的功能是悖论性的。总之,它们就像猎狗一样,四处捕获着主体的点滴欲望,使主体最终沦为其狡计的牺牲品。“三界”是拉康为主体的欲望追逐设立的一个祭坛,是他为主体登上死亡之舟敷设的一个神圣的仪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由于“三界”的引入,拉康把观看的问题变成了存在的问题。
“三界”的运作是一种拓扑学运作,即它们总是以共时态的方式对主体性的存在交互发挥作用,它们相互扭结但又相互切割,且以其扭结和切割方式的不同而在主体身上造成不同的效果。拉康在晚期的研讨班中对他的拓扑学有十分繁复而又多样的阐述,其技术的不断翻新和论述的艰涩回转令人一时之间难以索解。在此我要暂时搁置那些技术细节,继续把问题集中于主体性的认同。
前面已经讲了镜像阶段的想象性认同,现在需要把象征界的作用考虑进来,在象征界和想象界的拓扑结构中进一步思考观看与认同的关系。
对拉康而言,纯粹的想象性观看并不存在,因为镜像观看中的镜子本然地就是一个象征“机器”,一个结构观看欲望的象征化装置。同时,任一主体自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已然被象征界所铭写,例如父母对“它”的命名——甚至在“它”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其实已经是作为他者代理的父母的欲望以要求的形式的先期送出;进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这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向镜中窥看的时刻,常常伴随有父母指给“它”的某个理想的认同形象,比如父母指着婴儿的镜中形象说:“看,这就是我们的漂亮宝宝”、“这就是我们的小天才”等;或者当婴孩以父母的形象以及父母的期许、认可与赞赏作为参照来“完形”自己时,象征界的他者就在此发挥作用了,主体在这个镜像认同中完成的就不再只有“理想自我”(ideal ego),而是还有“自我理想”(ego ideal)。
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是精神分析学讨论认同时的两个基本概念。简单地说,所谓理想自我,即是主体在自恋性认同中实现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而所谓自我理想,指的是主体通过将社会化的指令内化为一种超我力量,并用它作用于自我而形成的自我要求或自我的理想参照。在拉康的意义上,不论是理想自我还是自我理想,都是认同的构成物,是主体的想象界和象征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理想的“我”的形象(理想自我),后者形成构建理想自我的指令(自我理想),前者是自己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对体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换用拉康喜欢的拓扑学方式来说,与自我理想对应的观看方式是“我”“想象地”看那“象征地”看着我的他人,由此而形成了我“想象地”看自己的“象征形式”。在这个时候,至少可以说,触发主体进入象征秩序的东西不仅有言语或他者的话语,而且还有他者的看或凝视,因为那在看“我”的人(比如父母)已经是象征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对“我”的看已然是象征界的看,是以看的方式先期地把“我”注册到一个象征秩序中。
如果说理想自我是现实自我把自身所欲望的某一理想形象外投到外部对象之上的结果,那自我理想就是主体把自己在外部对象身上,且通过外部对象指认出来的某一理想形象内投到自身的结果,在此主体把外部对象以指令形式指示出来的某一特质内化为自身的一个结构性维度。更具体地说,自我理想是主体认同所谓的“父亲功能”的结果,它使主体进入法的象征世界,以缓和自恋和侵凌性的两难。和理想自我的构成一样,自我理想的运作也离不开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交互作用。不妨说,正是自我理想提供给了理想自我一种预期的“形式”,即理想自我不过是属于象征界的自我理想在想象界的“重构”,后者就在这个重构中被内化为主体的“现实”。在第一期研讨班(1953—1954)中,拉康说:
我的欲望是什么?我在想象的结构中的位置是什么?这一位置只有当人们于想象界之外、在象征界的层面、在合法交换的层面找到一个指导时才是可以想象的——那种合法交换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换中才能得到体现——这一主宰主体的指导就是自我理想。
由此拉康得出结论说,对于观看的主体而言,若是没有“另一个维度”即象征维度的介入,其真正有效和完整的“想象性调节”就不可能确立起来:
正是象征性关系决定了作为观看者的主体的位置。正是言语这种象征性关系决定了想象的完善程度、完整程度和近似程度。这一表象使得我们可以区分出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自我理想主宰着关系的互动,而所有与他人的关系都有赖于这一互动。想象的结构的满足特征多多少少也取决于与他人的这一关系。
自我理想的形成有赖于主体对他者世界的象征性认同,有关这一认同,拉康依照精神分析经验称其为对“父亲功能”(paternal function)的认同。
何谓“父亲功能”?在拉康那里,“父亲功能”、大写的“父亲”(Father)、“父之名”(Name of the Father)、“父法”(Law)这些说法大体是等义的,它们都意指一种权力,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一种超我的指令或律令,其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象征法则和象征秩序,菲勒斯(phallus)则是这一秩序的优先能指,指示着父亲话语发出的位置。之所以以“父亲”之名言之,乃因为象征界的指令大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宣讲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在发出话语,父亲功能指示的只是发出话语的他者主体的位置,许多时候,居于这个位置的可能恰恰是已然屈从于象征秩序的母亲,是母亲在代行父亲之职,这时不妨称这个母亲为“菲勒斯母亲”(phallic mother)或“母亲他者”(英语世界通常写作“mOther”),以指示母亲作为他者之代理对孩子行使的“父亲功能”。
父亲功能代表着理想他者的位置,与在想象性认同中发挥作用的理想“小他”不同,象征界的他者是大写的他者(Other),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异性存在,是需要“我”以牺牲的方式去加以认同的东西。从观看的角度说,大他的这个位置是他人象征性地看“我”的位置,主体对它的认同实际就是“我”以他人看“我”的目光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他人眼中可爱的或值得爱的形象。主体性的构成总离不开他者的目光,离不开他者场域中父法或父亲功能的规定。
父亲功能意指着一种秩序、一种命令,它不仅要求你应当怎样做,还告诉你不准怎么做,在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功能也代表着禁止,代表着“不”。禁止什么呢?禁止主体的一切僭越性欲望以及主体对欲望满足的过度要求,拉康以精神分析学的隐喻称此为“对母亲的欲望”。而实施或实现这一禁止的根本策略就是提供一个优先能指,即象征的菲勒斯。父亲承诺主体在将来可以拥有代表着权力与权威的菲勒斯,可以借菲勒斯能指的意指功能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一个主体性的位置,可另一方面,这一象征位置的获得不是必然的和无条件的,而是需要主体付出代价,需要主体做出牺牲,那就是接受父法的阉割,放弃对母亲的欲望。
所以,对于拉康描述的象征性认同,我们应在结构化的层面来加以理解:就社会的方面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机器对个体欲望的回应,以及在这一回应中执行的对个体的询唤;而就主体的方面而言,它指的是个体对社会的符号性召唤的内化,是个体的社会化和主体化。这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象征性认同的发生需要社会以语言或言语的意指结构作为中介,这个意指结构构成了他者场域的能指链条,它以指令的形式向主体发送社会要求,并在主体的欲望与欲望对象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充当着调停者的角色,使主体的社会化身份在此可以获得某种确认。
第二,主体在象征秩序中获得确认的并非其作为存在的本质,而只是他/她在这个秩序中的某个符号位置,就是说,主体在此成就的只是一个“位置主体”,其在言语结构中占据着某个位置,能指链在该位置通过某个主能指的统摄而被锚定或扭结在某个意义所指上,然后再把这个意义缝合到主体的身上,使主体获得了某种身份性的存在。
第三,象征性位置的获得是以主体的牺牲为代价的,主体要想进入象征秩序,就必须接受属于这一秩序的父法对他/她的阉割,他/她必须学会有所放弃,这样才能有所得。象征秩序的这一切割使得认同的主体最终成了一个分裂的主体,因为他/她的存在或他/她的欲望总有一部分无法被象征秩序所接纳,无法在象征秩序中得到实现。这就是说,象征界对主体的结构效果是悖论性的:它在使个体获得某个象征的主体性位置的同时,也在他/她身上划开了一道切口。
第四,象征性认同固然可以在社会秩序中指示给主体某一确定的符号性位置,但主体对这个位置的意义所指的内化常常也会把主体变成象征机器的仆役和废料。一定程度上说,符号化的主体是“虚假”的主体,是“僵尸化”的主体,其主体性是“被”主体化的主体性,阿尔都塞称此为“臣服的主体”(subjected subject)。但许多时候,人们很难意识到这一点,或是意识到了也不承认,反而宁可相信那个位置被赋予的一切都是真的,是主体自身所拥有的,进而,为了说服自己,主体甚至把那个信念付诸行动,以种种模仿性的拟态来表现所认同的位置的符号化意义。
第五,象征性认同是对父法的认同,是以父法能指来取代或替换原始的欲望对象,可是,能指对存在的象征性切割或者说社会的他者场域对主体之意义的缝合不可能彻底,而是总会留有“剩余”(residue),并因这个剩余而使得认同主体的欲望满足总处在欠缺状态。更为严峻的是,那个被切割掉的东西,那个被掩藏在无意识结构中无法象征化的剩余,反过来将会作为欲望的原因把主体引向无尽的欲望求证之路,并且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主体在这条路上或是彻底地沦落为象征机器的残渣,沦落为真正的剩余,形如人渣一般,或是最终从象征机器的捕获中逃逸出来,沿着自身欲望的想象轴在那个脱落的剩余上尽情搬演致死的幻象游戏。
第六,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象征性认同可以帮助调节和定位想象性认同,而经过象征界调节的想象性认同也可以帮助维系和强化象征性认同,可这两者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相反,它们之间的循环时常会发生短路和断裂。例如,他者场域总是一个过度的场所,它向主体提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冲突的要求,他者是一个淫秽的、过度要求的他者,一个暴虐的、不断索取的他者,当主体被过度的他者要求逼到绝境的时候,当主体最终意识到他者场域的这一裂隙的时候,就会歇斯底里地对他者世界加以质疑:“你究竟想要怎样?”“你到底想从我这里获取什么?”而这一质疑最终将为主体的欲望求证开启一条新的道路,那就是通向“原乐”(jouissance)的道路,是朝向极致的症状享用的道路,是快感主体用致死的、非人化的“求原乐意志”对象征秩序实施的最后一击。
如同采用镜子装置讨论想象性认同的时候一样,拉康也喜欢用这个装置讨论象征性认同及其与想象性认同的拓扑关系。这显示了视觉性在拉康的话语展开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像上面不断说到的,对于象征性认同的语言学表述,我们同样可以用视觉性的隐喻加以转述:象征性认同就是对他者目光的认同,就是主体学会用他者象征地看他的目光看自己。在第十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中,他干脆以“视界领域”(the scopic field)为论述语境去对主体性的认同加以理论的重述,那一认同拓扑现在被说成是“眼睛与凝视的分裂”(the split of the eye and the gaze):
眼睛与凝视——这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分裂,在那里,驱力得以在视界领域的层面呈现。
何谓“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眼睛不就是看和凝视的器官吗?其与凝视的分裂从何而来?这涉及拉康对“凝视”概念的独特运用。
简单地说,拉康的凝视理论要讨论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和如何去看,而是我们的观看行为是怎样发生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观看——它实际就是“眼睛”的功能——是如何因为“凝视”而可能的,又是如何因为“凝视”而不可能的。就眼睛与凝视的分裂而言,如果说所谓的“看”是指主体(眼睛)的看,则所谓的“凝视”就是指主体想象的自身以外的某个东西的凝视,而且是在他者那里已然失落的原质之“物”即对象a的凝视,是不可能之物的凝视;如果说观看代表着眼睛的功能,那么凝视就是使观看变得可能(我看/我被看)和不可能(看而不见/见而不看)的原因与机制。对于那使观看变得可能的凝视,拉康现在称之为“想象的凝视”,对于那使观看变得不可能的凝视,他称为“对象a的凝视”,那实际就是“实在界的凝视”。想象的凝视涉及象征界和想象界的相互作用,对象a的凝视则是实在界对象征界和想象界的穿刺。至于“眼睛与凝视的分裂”,指的并非两者的分离,相反,它们是不可分离的,(他者的)凝视是内在于主体的观看(眼睛)的,是主体在想象有一个他者的凝视,然后把这个凝视内在化,用它来反“观”自身,通过它来界定自身,也由此而把“分裂”嵌入了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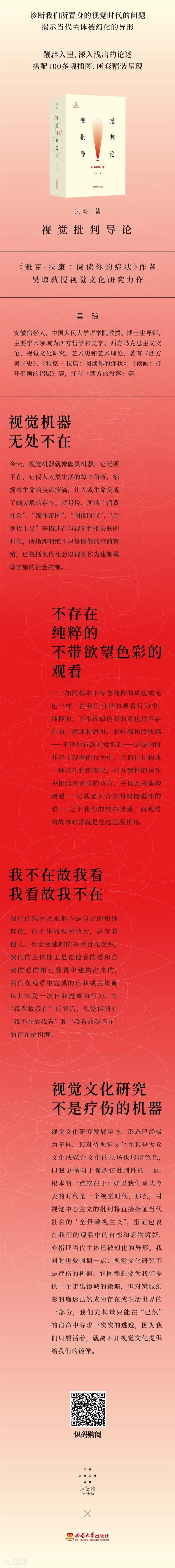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