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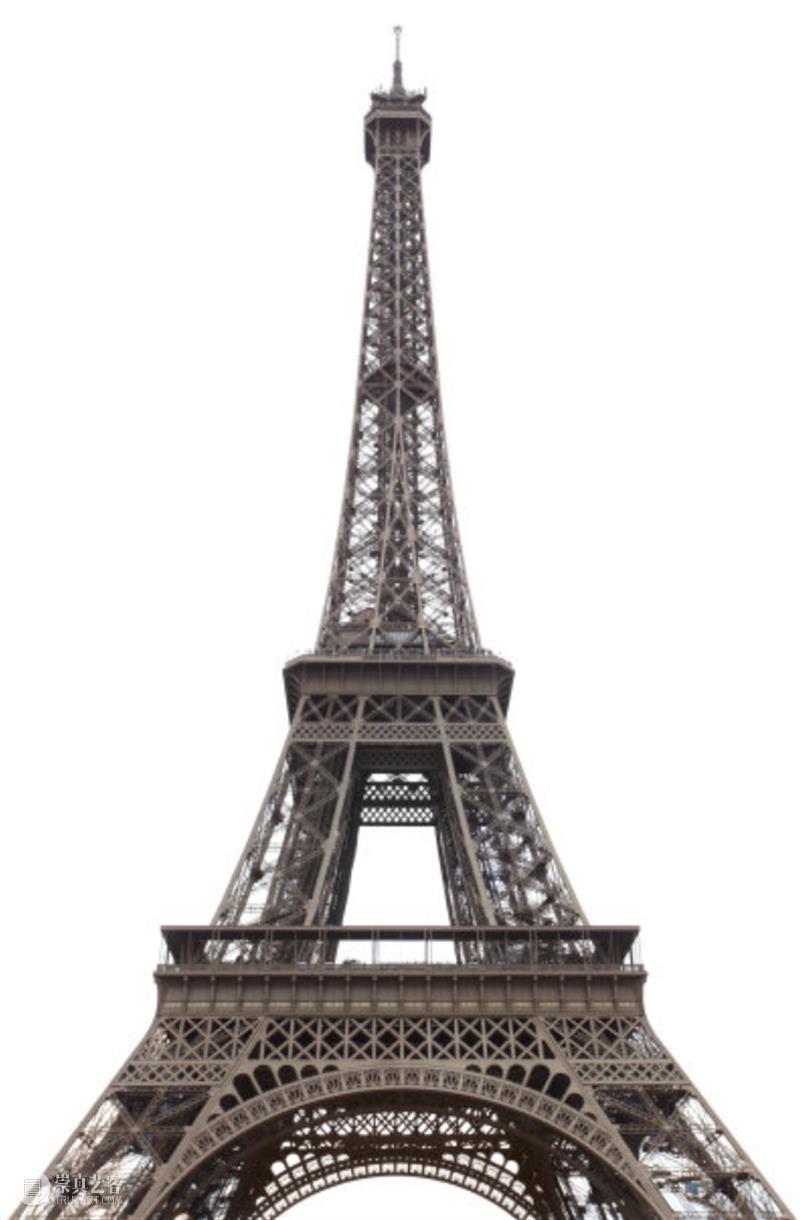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费瑟斯通丨文 刘精明丨译
选自《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译林出版社,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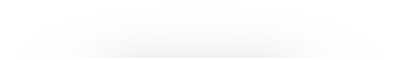
表面看来,这两个词都似乎不幸地介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之间。发展社会学经常用现代化来表示在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结果。现代化理论也常常用来指涉以工业化、科学与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市化和其它基本结构要素的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用法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现代性之第一层涵义非常相近。它根据一个不太严格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来一般地假定,确切的文化变迁(世俗化和以自我发展为中心所导致的现代性认同的出现)是现代化过程之后果。很显然,如果我们由此而转入对后现代化过程的分析,就必须理论地勾勒那些随特定社会过程与制度变迁而来的细微轮廓。因此,我们就完全有可能从上面提到的那指涉新的社会秩序与时代转变的“后现代性”一词的用法中,推导出“后现代化”概念。例如,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仿真世界的描述,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信息技术与商品生产的发展导致了后来扭转决定论方向的“指意文化的胜利”(triumph of signifying culture)。这样,不断发生转换的文化记号(signs)便融入了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面临的,是“社会的终结”:在这里我们再也不能谈论什么具有确定意义的阶级和规范问题了。不过,这里鲍德里亚并未使用“后现代化”一词。
然而,后现代化这个词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指明的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指一个完全的羽翼丰满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在城市研究领域中,便明显存在着一个使用“后现代化”一词的语境。我们可以以菲利普·库克和仙农·佐金的研究为例。对库克来说,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这在一九七六年以来的英国经济中是引人注目的。佐金也想用后现代化这个词,来集中分析在工业、服务、劳力市场和电信领域中,投资与生产的新模式所导致的社会空间关系的重构。然而,当佐金把后现代化看成是相对现代化而言的一个动态过程的时候,她和库克一样,把后现代化当成了资本主义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因而两人都难免不把它当作社会的一个新阶段。他们分析的优点在于,两人都把注意力既集中在生产过程方面,又同时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消费、特殊文化实践的空间维度(城镇与口岸的再开发,城市艺术与文化中心的发展,服务阶层及上流社会化趋势的扩展)。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