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别忘了去参与抽奖(送5种预告新书),明天早上10点开奖。详情戳此(查看文末)。此抽奖活动同时也在豆瓣号进行。豆瓣号抽4位,微信号抽2位。两边均可参与,如果中奖者重合,我们会择其一,再另抽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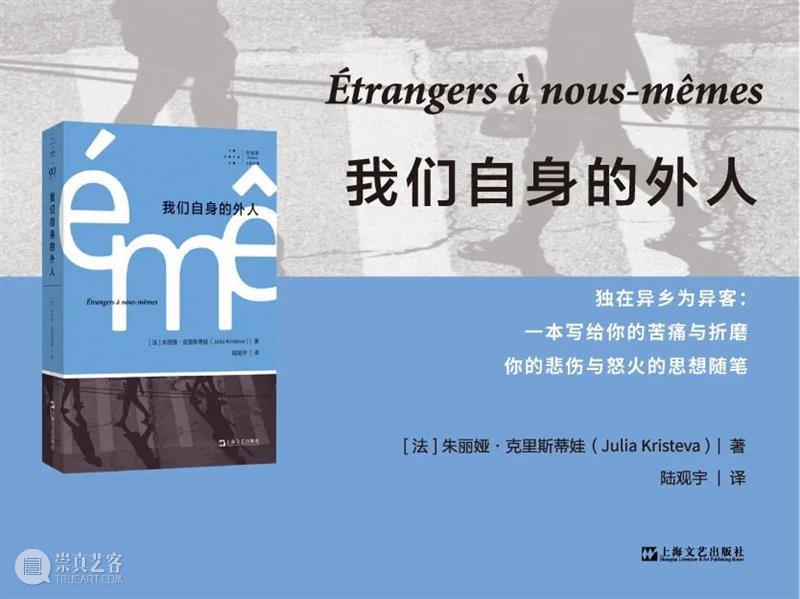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我们自身的外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著,陆观宇 译)的书摘(节选自《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这篇)。此书现已在我们微店上架,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阅。
内心的民族主义:从赫尔德到浪漫派
一本译作,《圣经》的译本,奠定了德国对“教化”(Bildung,culture)的现代概念。确实,当路德(1483—1546)用德语白话翻译《圣经》(“家妇凡夫皆操此言”,他如此捍卫自己的作品)而对德语“去拉丁化”之时,他所反对的不仅是罗马的权贵。他的雄心更加远大,因为他奋力建立的是一种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在一种双重的运动中——既忠实于典范,又放大民族特有的语体,如路德最初所厘定的语言——延续至浪漫时期,并在此达到高潮。[1]在1800至1830年,浪漫派对民族精神(Volksgeist)尤为热衷;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忘记,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始终以一种必要性为基础:它必须发扬自己所特有的(propre),将其与宗教或文学经典做比较,从而对其加以修缮:民族特征因而奠定在一种扩充了的可译性之上,这种可译性与教化的观念相交融,首先在于民族语言的形成。[2]
[1]语体(registre)指人们在不同环境下使用的词汇、句法等。——译者注
[2]参见安托万·白尔曼,《外人的考验:浪漫时期德国的文化与翻译》(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Gallimard, 1984)。德意志民族在与外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这种过程可以与A. W. 施莱格尔(A. W. Schlegel)在法国的见闻相对比:“别的民族在诗歌中采取的是一种彻底合乎习惯的措辞,以至于在他们的语言中作出诗意的翻译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这样的语言例如法语[……]。仿佛他们要求,在他们那里,每一位外国人的言行与衣着都要符合他们的习俗。这样便导致他们永远学不会确切地谈论外国人”。引自安托万·白尔曼,《外人的考验:浪漫时期德国的文化与翻译》,第62页。(译按:A. W. 施莱格尔为德国浪漫派诗人、翻译家。)
在当时,人们已经认为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普世主义过于空洞。赫尔德的态度因而是截然不同的,他以最为直白的语言,首次描述出文化在语言精神中的根基。这位新教牧师始终忠实于某种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关于人类的第一部普世主义的历史,难道不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吗?——他也真正地奠定了让浪漫派如此珍视的、对民族精神的狂热崇拜。
自《论德国新文学》残篇(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1767)起,赫尔德便赞扬德语的原创性,却强调语言的改良应通过与古今语言的持久竞争,而非对经典范例的简单顺从。在《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之后,他在《历史哲学别论》(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1774)中迅猛地开展了爱国的论战,指责普世主义与“启蒙”的专制,也同时抨击启蒙时期“抽象”的理性主义。每个民族——在作者看来,每个民族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其语言与文学之中,之后才关乎习俗、政府与宗教——都依照其存在时间之长短而被衡量、放置在各民族彼此竞争的文明巨链之中。秉持这种精神,赫尔德的“民歌”赞颂了德国中世纪的历史以及德国民俗诗歌的魅力。[3]
[3]“民歌”(Volkslieder)为德国民俗音乐,赫尔德曾汇编为《民歌》一书;在此处或亦有“对民族的讴歌”之谓。作者误作为Volklieder。——译者注
然而,在赫尔德把自己的人类历史理论与生物学相联系之后,最终写下皇皇巨著《人类历史哲学论纲》(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比起1774的路德主义,更接近于一种启蒙的人文主义。赫尔德不再如此关心风土或习俗的差异,即使他认为黑人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也只是归咎于恶劣天气的影响。不过,他主要关注的是神的“不同人民”(赫尔德并不接受“人种”的观念),他们就生理构造而言如兄如弟,可是在各自的语言与文明中彻底分化。
他或许的确创立了对“原始民族语言”的狂热崇拜,因为对赫尔德而言,正如对克洛普施托克而言,这种语言不应受翻译玷污而应维持“贞洁”,它是“一种宝库,储蓄着人民最原始的概念”;然而,他只能说是间接地影响了后来将这种崇拜占为己用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即使是在近几年,人们还是执意将他看作地方主义者。可不管怎样,他是一名译者:他翻译西班牙“浪漫诗”,萌发对英国文学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兴趣,时常思考“自有的”与“陌生的”之间的平衡:“我遵守外国的习俗,是为了将我本来的习俗献给我祖国的精神,正如这么多成熟的果实享受着他乡的阳光”;在一种离心运动中,被翻译的作品需要“按其本来的面貌”呈现出来,却也需要符合它“在我们看来的样子”。[4]这种民族精神所扎根的语言,被看作一个不停变更、始终超越自身的过程;可是,当民族精神脱离了教化的运动,或是为了因其原始的贞洁而大受赞扬,或是为了被进献给不可言说的存在,民族精神便沦为保守而应激的概念。然而,就其本身而论,将语言同化于教化之中,以及相反地(vice versa),强调民族的白话(parler)[5],认为它是公民身份的最小公约数,这两种行为都为这种基督教或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抹去了它们在宗教、自然或契约上的含糊。此外,在这两种行为的作用下,人们得以在语言与文化逻辑的、熟悉的一面中考虑“陌生的”究竟是什么。
[4]参见安托万·白尔曼,《外人的考验:浪漫时期德国的文化与翻译》,第70页。从赫尔德对《雅歌》的翻译到他汇编的《民歌》,期间还有著名的圣经集注《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Vom Geist der Ebräischen Poesie),赫尔德同化着陌生,却始终注意保留它的特性,从而充实这门身处扩张与改革之中的德语。中欧各民族便汲取他的思想,为斯拉夫的语言与文化带来了迅猛的发展。然而,我们能够注意到,德国教化与外国文化的并行——尤其是与希伯来文化的并行——却在浪漫主义晚期达到了临界点。而且他自己也在一种强调政治的翻译法中变得无比强硬,这种翻译法一开始还能带来诸多成果,之后却将他者要么视作彻底拒斥的对象,要么视作同化的对象,以促进德国的“原创性”。(译按:浪漫诗[romance],西班牙文体,为叙事或抒情短诗。《雅歌》[Cantique des Cantiques],《圣经·旧约》篇目。)
[5]德文“语言”(Sprache)一词与“说话”(sprechen)同源。——译者注
从那时起,人们便必须以一种特定的逻辑驯服陌生性,让这种逻辑茁壮发展的,是语言学与文学对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兴趣。这一态度既体现在浪漫派的地方主义中——他们热爱着自己民族在种种细节中所彰显的尊严,又体现在歌德的普遍主义中——他拥护着某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就这样,陌生性得以被承认,甚至被认作是积极的。将这样的陌生性放置在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之中,这种行为之后会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重新出现。谈及自己的无意识理论时,维也纳的这位大师表明,自己所依循的是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逻辑。我们甚至也能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语文学主义中看到这一点。[6]他用希腊词汇的回响来阐释希腊思想的诸多概念,似乎是在呼应受赫尔德启发的这种民族精神的语言学。
[6]语文学主义(philologisme),或是依照“滥用哲学”“哲学主义”(philosophisme)而新造的词,或语出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克罗齐曾使用“语文学主义”(lologismo)来指代对历史材料的无序累积,与以历史的方法整理、诠释材料的语言学(lologia)相区别。——译者注
不过,赫尔德之后的几代却扩充了这种文学自足的观念——这种观念诚然出自这位先师,可他的这种观念却服从于人类文化的整全性——从而证明并颂扬“德国文学品味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因而被理解为一种优越性,彰显着文化绝对的彻底实现,也因此要置于其他民族、语言与文化之上,从而论证德国要求拥有文化霸权的合理性。人们此前注意提升的民族“优越感”,现在却支配着普世主义的观念,使其堕落,我们知道,出于民族主义的角度败坏普世主义,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础。[7]
[7]就赫尔德而言,贯穿其前后矛盾的立场的,实则是对此的戒备:“德国人通常以表现出君子一般的谦逊为荣耀,曾经冷静而公正地衡量外国人的功勋,可现在竟然无理而粗鲁地蔑视其他民族,尤其是他们曾经模仿借鉴的民族——他们究竟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引自马克斯·胡燮,《引言》,载于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论纲》[Max Rouché, Introduction J.G. Herder, Idées po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Aubier, 1962, p.33])。他还写道:“那些研究他们的习俗与语言的人,需要着重关注这些习俗与语言最为显著的时刻,因为欧洲的一切都倾向于逐渐削减民族的特性。不过,做此种工作的人类史家仍需警惕,不能特别选取自己所偏好的某个民族,而由此轻视那些未受时运与荣耀眷顾的族系”(同上,卷16,第309页)。
赫尔德将特殊根植于普遍人性(人类的语言天赋)的多样性(各种民族语言),而浪漫派与其相辅而行,认为普遍可见的自然拥有不可见的基础。他们设想,既属于自然本身,又属于人类灵魂的这一根基(Grund),比起理性求知,更容易通过感性的、直观的、内心的寻求而抵达——通过性情(Gemüt)而抵达。浪漫派关注超自然、心理玄学、疯癫、梦境、命运(fatum)的费解动力,甚至是动物心理学,种种兴趣都源于对把握奇异的渴望。[8]他们还渴望通过驯服奇异,能够将其融入人性之中。对差别和奇异的移情(Einfühlung)——对其带有认同的同意——因此成为高贵而有教养之人的专属特点:“完美的人应该能以同一种方式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诺瓦利斯写道。[9]
[8]心理玄学(parapsychologie),或译超心理学,指对无法通过科学知识解释的心理现象的研究。——译者注
[9]《新残篇》,第146篇,载于《作品与书信集》,第452—453页,引自亨利·E. 艾伦伯格,《无意识的发现》,第170页(Neue fragmente, n° 146, in Werke und Briefe, Munich, Winkler Verlag, p.452-453, cité par Henri E. Ellenberger, A la découverte de l’inconscient, Simep-Éditions, 1974, p. 170)。(译按: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浪漫派诗人。)
就这样,浪漫主义英雄的奇异性便具备了形体。在这样的温床中,无意识这一不合常规的概念也将横空出世——它是人与自然隐晦基础的深层联系(卡卢斯与舒贝特),是潜藏在诸表象下的意志(叔本华),或是黑格尔式的具备智能的动力,在表面的世界之下盲目地行动着(哈特曼)。[10]
[10]保罗·卡卢斯(Paul Carus),美籍德裔哲学家。戈特蒂尔夫·海因里希·冯·舒贝特(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德国医学家、博物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德国哲学家。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就弗洛伊德而言,虽然他只介入精神病学的领域,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他与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联,便无法了解他的贡献。通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内蜷于心理之中的奇异不再被视作病症,而是在人类假定具有的统一性中融入一种既属于生理又属于象征的他者性,而成为同一的一部分。此后,“外人”不再是种族,也不再是民族国家。“外人”不再被颂扬为隐蔽的民族精神,也不再被贬斥为理性礼仪的搅乱者。怪怖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外人——我们是分裂的。在浪漫派的影响下,在内心中对奇异的恢复,大概也融汇了《圣经》对作为外人的神与启示神意的外人的强调。[11]弗洛伊德的个人经历——他本是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后漂泊至维也纳,终定居伦敦,期间暂住巴黎、罗马与纽约(在文化与政治陌生性对他的考验中,这些只是几个关键阶段)——促使他从我们身上“另一现场”的内在性出发,面对他人带来的不适感,即“不自在”(mal-être)。[12]我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不适感——我的陌生性、他的陌生性——建立在一种被扰乱的逻辑之上,而这种逻辑所调节的这一组对象,包括欲力与语言、自然与象征,正是始终已被他者塑造的无意识。只有解开这种迁移——他者性的主要动力、对他人的爱/恨的主要动力、构成我们心理的陌生性的主要动力——我才能通过他者同我自己的他者性-陌生性和解,才能化用它,才能靠它生活。[13]精神分析便显现为在他人与自身的陌生性中的一场溯游,向着一种尊重不可调和者的伦理游去。我们要是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之外的人,怎么可能还会容忍外人?横穿乃至反抗宗教齐一论(uniformisme)的这一小条真理,竟然需要这么久才会启迪当下的人们!在它的引导下,有欲望的、可欲望的、终有一死的、致死的,因而是不可化约的人们是否能够彼此容忍?
[11]参见本书第95-111页。
[12]加利西亚(Galicie),中欧历史地名,今属乌克兰与波兰。弗洛伊德的父母来自加利西亚,他自己却是在当时奥地利帝国摩拉维亚(Moravie)的弗莱堡(Freiberg,今属捷克)出生。另一现场(autre scène, audere Schauplatz),弗洛伊德术语,用以描述梦境发生之处。——译者注
[13]迁移(transfert),指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主体将对他人(往往是其父母)怀有的爱意或敌意,迁移至对精神分析师的爱意或敌意的行为。在此所指的,大概是我将对我自己陌生性的爱或恨迁移至外人身上的“动力”(dynamique)。——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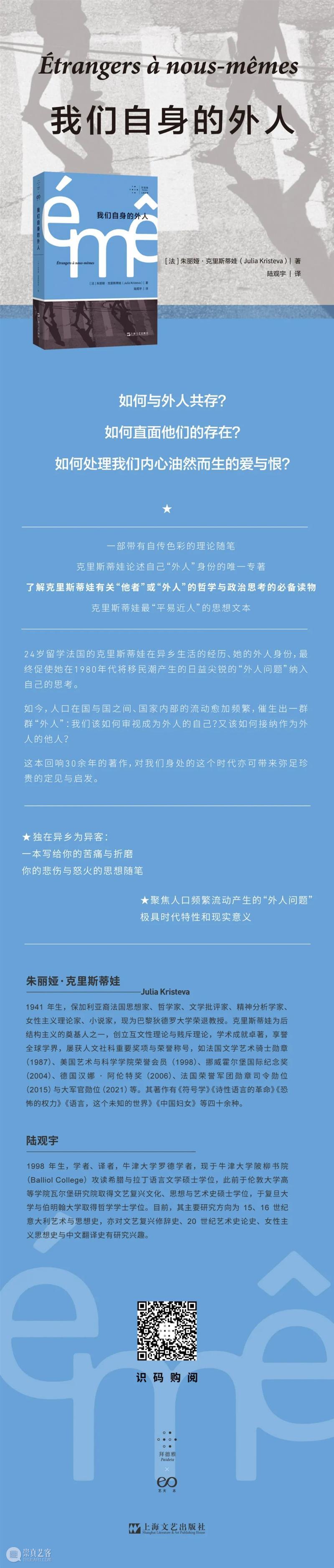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