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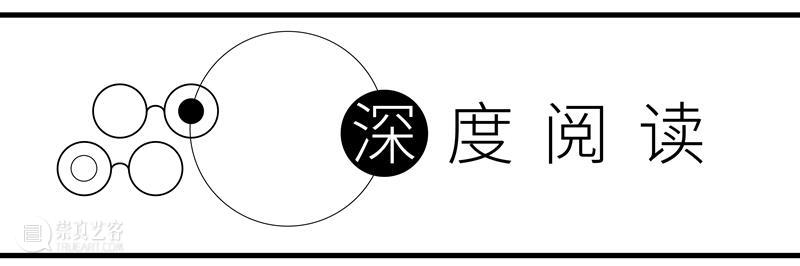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柄谷行人的专访《原地不动,就无从批判》(‘Critique is impossible without moves’: An interview of Kojin Karatani, 2012)的第二部分(此文颇长,我们分三次为大家推送,第一部分戳此:柄谷行人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康德“目的王国”的延续)。访谈者:乔尔·怀恩莱特(Joel Wainwright)。原文见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1), 30-52。译者:陈荣钢。
原地不动,就无从批判
(中)
乔尔·怀恩莱特:在讨论你“反对国家和资本的新运动”(国家と資本への新対抗運動,NAM)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对黑格尔、资本主义和公民社会的解读。你在《跨越性批判》土耳其语译本的“前言”中写道:
黑格尔率先掌握了“资本—国族—国家”(capital-nation-state)的三位一体本质。黑格尔提出了唯心主义的见解,而马克思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反转它。因此,马克思把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视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把国家或国族视为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这样一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被取代,后者将自动消失。显然这并不正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国家和国族的问题时屡屡犯难。因为马克思本人都没有看到,国家和国族有一个坚实且真实的存在基础。如果我们要真的取代资本、国族和国家,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它们是其所是。简单否认它们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你如何概念化公民社会(马克思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资本—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我的解读,“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在你的分析中被取代了。与“资本—国族—国家”不同,自黑格尔以来,我们所称的“公民社会”在“交换”中缺乏真正的基础,而只是“资本—国族—国家”整体的一种表达。在我看来,你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公民社会”的基本批判,因为你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后者把每个主体看作整个社会宇宙中自由漂浮的原子。因此你也反对引发公民社会的“资本—国族—国家”的组合。你能澄清一下你的观点吗?
柄谷行人:马克思在早年阐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1821)的时候,就使用过“公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在那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但又停留在黑格尔的思维模式中。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公民社会是“可理解的”(verstandig)国家,而不是“理性的”(vernünftig)国家,后者理性地调节着无政府的市场经济,并实现人民的“共同体属性”(communality)。“理性的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口号的实现,也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分析大概以英国为模型,因为这种国家在普鲁士并不存在。《法哲学原理》描述的那种国家是一种福利国家(warfare state),这种福利国家的理论至今仍然有效。所以,我要从批判黑格尔开始。但是我认为,虽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但他把“资本—国族—国家”把握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而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抽象化。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换句话说,他把公民社会理解为基础设施,把国族和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前者决定后者。他认为,取代了公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经济,上层建筑(国族和国家)就会自动消失。但这不可能发生。如我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国家和国族的问题时屡屡犯难。这在1848年的革命中屡见不鲜。这些革命产生了国家制度——它同时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时是法国的波拿巴和普鲁士的俾斯麦。也就是说,“资本—国族—国家”是1848年革命的结果。在这之后,古典的革命运动在欧洲已不再可能,“巴黎公社”只是最后的闪光点。
现如今,“资本—国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扎根。不承认“资本—国族—国家”,革命运动就没有意义。1979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黑格尔的论点为基础,宣布“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这意味着,“资本—国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就是最终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没错。许多人拒绝他的历史终结论,并试图改变社会(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倡导),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只是“资本—国族—国家”的一部分。
乔尔·怀恩莱特:所以你的目的是重新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柄谷行人:是的。我一再强调,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资本—国族—国家”当作关联整体来把握的人(参阅《法哲学原理》)。为了修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我们一方面必须追随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方式颠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形成及之前的唯心主义见解(关于“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要保留黑格尔对“资本—国族—国家”的体认。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交换方式(mode of exchange)的角度来阐述“世界历史”。
乔尔·怀恩莱特:“交换方式”,与“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相对吗?
柄谷行人:没错。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家,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当然,这并非完全错误。毕竟,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导言”中总结了他的研究结论:
人们在自己生活中、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地,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易克信、杜章智译)
这一陈述和其他类似陈述产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该流派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但我认为,这种立场在政治上是一种灾难。
乔尔·怀恩莱特:因为这种观点认为,革命只需要由先锋党使用国家权力来推翻资本主义,是吧?
柄谷行人:对。但这其实只是为国家和国族添砖加瓦。而且,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压抑下去,它们也并没有被超越。我要从政治角度批判“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同时我想强调,我们必须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因为后者并没有严格遵循先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继续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来讨论。
乔尔·怀恩莱特:在《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写道:“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盛行的社会。”
柄谷行人:是的,但紧接着那一章的分析(价值形态的阐述)就完全不限于生产了,而是以运动中的资本为中心。
乔尔·怀恩莱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在于商品交换。
柄谷行人:正是如此。他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其特殊性源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两个方面都至关重要。
重读马克思,我们可以根据关系的交换形态分析来阐释他的方法。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他经常使用“交往”(Verkehr,或译作“交通”)这个词来描述交换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1845)中,他用“交往”来描述社群之间的沟通、交通、贸易乃至军事。换言之,这个词指涉广义的“交换”。第二个例子来自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著作。他用“代谢”(Stoffwechsel)的概念来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这个概念是他对人性及其自然历史概念的核心。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交换关系是马克思的根本。
在完成《跨越性批判》之后,我想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阐述这些想法。在论述“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的时候,我把四种交换模式的概念作为基础。我认为,所有具体的历史社会形态都是这四种基本交换形态的变化组合,它们可以按两种方式分成两类——其一,非互惠和互惠;其二,不自由和自由:
A:礼物和互惠;
B:掠夺和再分配;
C:商品交换或市场交换;
D:“X”
比如,交换形态A,礼物和互惠,这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交换模式,植根于较早的人类社群,它只不过是对给予和接受的普遍期待。这是一种互惠交换的手段,一种创造社群的手段,当然也处处受到传统规范(宗教、父权制、老人政治)和可识别的社群界限(归属和排斥,朋友和敌人)的制约。
乔尔·怀恩莱特:礼物和互惠是强制性的交换形态,因此不自由。
柄谷行人:没错。这种形态的互惠不应该被阐释为善意(goodwill),而是一种使他人服从自己意愿的手段。这里的礼物可以包括简单但基本的行为,用来承认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但这种形态总是包含排斥,所以从另一个人(被排斥者)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不自由。
接下来是交换形态B,掠夺和再分配。这种交换方式既不自由也不对等,至少对那些被掠夺的人来说是如此。尽管如此,只要涉及到物质交换(奴隶、土地或农作物)以及随后的价值重新分配,它就是一种交换形态。
然后是交换形态C,市场交换。这种交换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的发明者。但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笼罩之下,市场交换变成了决定性的事。这就是《资本论》带给我们的教诲。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以交换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它只是以交换的形式存在,是由价值形式组织起来的商品交换。但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形式的交易已经消失,它们并没有消失。可以说,其他交换形态与市场交换混生。不过,今天的社会与早期的社会历史形态不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A和B从属于C的世界。
乔尔·怀恩莱特:交换形态D似乎很难把握。
柄谷行人: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种由自由和互惠交换定义的交换模式,这种模式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称之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但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些词要么带有负面含义,要么意义不明,因此我更愿意使用“X”这个符号。“X”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念”(Idée)。
乔尔·怀恩莱特:交换形态“X”引出了超越“资本—国族—国家”的可能性。我认为,《跨越性批判》的结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一方面,你有力地分析了环环相套的“资本—国族—国家”,并指出要创造“X”的实践来超越它,因为“X”是基于自由和互惠交换关系的社会生活。然而,你似乎辩称,我们无法实现“X”, “X”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否可以说,“跨越性批判”的自相矛盾(antinomy)在于,“X”必须存在,但“X”绝对不存在?你最近在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复杂性:
D是A的复苏,或者说是一种更高维度的互惠。D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果它存在,也只是暂时存在。互惠的复苏是“被压抑者的回归”。因此,就像弗洛伊德(Freud)所言,有某种强迫性的东西超越了人类的意志。
简而言之,道德和宗教虔信并不存在于上层建筑中,而是深深扎根于经济基础结构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的条件由现存前提产生。因此,交换形态A、B、C会一直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共同体(国族)、国家和资本会一直存在下去。我们无法将它们剔除出去。但我们不必悲观,因为只要交换形态A、B、C持续存在,交换形态D也会持续存在——不管它如何被压抑和掩盖,它都会不断回来。这就是康德的“规约理念”(regulative idea,或译作“规导性理念”)。
关于这一点,我的一位朋友指出,你没有提出抵抗资本主义的真正战略。我的回答是:“当然,柄谷行人承认他的战略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但我看不清柄谷行人提出的那种‘道德—政治批判’的替代方案。我认为他和马克思、德里达一样,不承认‘资本—国族—国家’之外的观念同构。”
我不清楚有没有正确理解你的观点。然而,即使我的回答没有歪曲你的观点,我想知道我们如何向人们解释“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悲观”。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缺陷,大多数人(包括各种左派)都会退缩回宗教和自由主义。因此,当我们说“我们不必悲观”,只因“交换形态D也会持续存在”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加上“但我们要有超越‘资本—国族—国家’的动力和意愿”?
柄谷行人:是的,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资本—国族—国家”三位一体的研究使你认识到取代它是多么困难。比方说,过去的人们想要通过国家或国族来取代资本主义。一开始并不难,但这些尝试的结果却让国家或国族的冲动发挥作用,这反过来又使资本主义复苏。这就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困难迫使我们承认“资本—国族—国家”的终极性,它让我们想到,现在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在该范围内一点一滴地改变社会。这就是1989年“历史的终结”的内涵。
我从这时起(1989年)开始思考康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后现代理论中回荡着一种咒语,认为“理念只是一种表象”。我注意到,康德的“构成理念”(constitutive idea)和“规导理念”之间存在区别。后现代理论家提到的“理念”其实是“构成理念”。那些试图重新创造社会以符合他们理念并遭遇灾难性后果的人们完全拒绝这种“理念”。但对我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规导理念”,而不是一种“构成理念”。这个永远不会实现的“规导理念”一直在迫使我们取代“资本—国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这种“规导理念”不是来自我们的愿望、不满和简化——它迫使我们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而且这不会停止,直到它完全实现。
为什么呢?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解释为在更高维度上原始共产主义或共同所有权的(迫不得已的)回归。但为什么共同所有权需要“回归”?辩证的“否定之否定”无法解释这一点,它听起来只是类似“失乐园”的神话。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交换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的角度,结合弗洛伊德“被压抑者的回归”概念来阐释这个问题——曾经被压抑的驱力(drive)以不同形态和冲动回归了。如果交换形态A(互惠原则)被压抑,它就会带着某种冲动回归,哪怕在交换形态B和C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会采取不同的形态。
乔尔·怀恩莱特:但是,当你把交换形态D说成交换形态A的“回归”时,这并不是“浪漫地”回到以前的社群生活,对吧?
柄谷行人:没错。虽然每一次浪漫的“复苏”都以肯定现状和恢复传统秩序为结局,但这种“被压抑者的回归”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被压抑者的回归”显然是来自于未来,而不单纯是过去的复兴。1986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试图将马克思主义重构为“未来的哲学”,这是正确的。为了批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他提出了“尚未意识”(“the not-yet-consciousness”),但这其实和弗洛伊德的“被压抑者的回归”没有什么不同。
当古代世界帝国出现时,普世宗教成为“被压迫者的回归”,成为脱颖而出的反帝抵抗运动。它的出现不是人类的愿望,而是来自“上帝”(God)的要求。此后的社会运动几乎都以全民宗教的形式出现。19世纪末,当交换模式成为主导时,交换形态D失去了宗教层面,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但交换形态D在本质上是一种“规导理念”。如果失去了这个理念,“科学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构成理念”,就会被贬低(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但是,“规导理念”永远不会消失。
乔尔·怀恩莱特:你对交换形态A和互惠的讨论把我们带到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问题。如你所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讨论民族主义的关键段落:
共产党人还因想要废除祖国和国籍而受到进一步的指责。工人没有祖国。我们不能夺走他们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获得政治优势,必须成为国族的领导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族,因此它本身就是国族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国族。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将共产主义与19世纪中期欧洲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立起来。他们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奇怪的是,为了实现历史目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获得政治优势”,必须成为霸权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族”。你如何解释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无产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超越国族边界,并将不同群体重组为一个包容的整体。因此,他们肯定跨国主义的共产主义伦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肯定“属下群体”(subaltern groups)的斗争,以阐明跨国共产主义作为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
柄谷行人:我同意。但让我详细阐述一下“国族”是什么。“国族”对应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博爱”(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资本”和“国家”对应于“自由”和“平等”。因此,国族是一种模仿“社群”互惠模式的东西(交换形态A),它在某些方面与交换形态B和C相抵触。所以,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交换形态D。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
然而,民族主义当然不同于交换形态D。例如,国族有排他性,也有平等性。在这个意义上,国族和乡村社群如出一辙。国族的目的只是为了回归交换形态A和传统秩序。可以说,交换形态D是对A在更高层次上的复苏,而“国族”是对A在较低层次上的复苏。
尽管国族貌似对交换形态B和C,对国家和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但它也肯定了它们,而不是取代它们。因此,它们形成了“资本—国族—国家”。民族主义或浪漫主义是对交换形态A的“复苏”,但不像D那样处在更高的层次上,于是它很快就从属于B和C。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然而,这句话是为了反驳一种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共产主义剥夺了无产阶级的国族。无产者没有被当作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公民对待,这就意味着无产者没有国族。然后,马克思发问,我们怎么能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没有的东西?
马克思并没有正面提出无产阶级国族的必要性,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现实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是公民,他们有责任为祖国服务。马克思的话是对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讽刺性反对。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总是强调民族主义)放话,无产者没有被当作公民对待,因此没有祖国。把无产者当作公民对待,就等于取代了“资本—工资”劳动者的阶级关系。
乔尔·怀恩莱特:所以根据你的解读,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族”的概念是取代资本和国家的同义词。
柄谷行人:正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共产党宣言》所处的时代。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欧洲出现了将无产阶级视作公民的运动。英国首先出现了这种情况,随后法国的路易斯·波拿巴和普鲁士的俾斯麦也采取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政策。这是对1848年革命的一种反革命。就这样,“资本—国族—国家”的三位一体首次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因此,不要盲目把马克思在1848年之前说过的话应用于之后的情况。马克思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当时欧洲的社会运动因民族主义而分裂。有些民族想要实现民族团结,比如意大利人。对于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族”就变得不可或缺了。因此,“第一国际”的特点是由民族主义引起的冲突。在巴枯宁主义者(Bakunists)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背后,是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对立。“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完全解体,当时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支持他们各自的国家参加战争。
民族主义总是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错综复杂的问题。民族主义是一个类似交换形态D的难题,它似乎很喜欢批判资本和国家。否则,民族主义就不会对人们产生吸引力。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取得胜利的原因。民族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通过“国族共同体”来超越资本和国家的手段。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现在占上风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也是与资本和国家对立的东西,因此也类似交换形态D,但它只能导致神权,而不是D。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