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是背叛者最后的依靠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选自《一个男人的位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父亲去世了,就在我当上教师正好两个月的那天。当时他六十七岁,和我母亲在Y市车站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打算一年后退休。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过了中午。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口,她用餐巾擦拭着眼睛,那可能是她吃完午饭回卧室时带到楼上去的。母亲淡淡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记得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记得父亲那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身后远处的什么东西,还有从那蜷缩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龈。我记得我请求母亲合上父亲的双眼。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身体变僵硬之前做好。母亲建议给父亲穿上三年前我结婚时他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只有母亲红肿的眼睛和时不时的苦笑。我们的动作安静柔和,有条不紊,伴随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姨妈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或是“他变化太大了”。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好像他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像新生的婴儿那样。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呼唤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尸体拉起来,举着,以便我们把他身上穿着的脏衬衫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父亲的头向前耷拉着,布满老年斑的胸膛赤裸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衬衫的衣角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我可怜的人儿。”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缠上一串念珠。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姨妈说:“他这样看上去更好”,意思是说更整洁、更体面。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唤醒正在午睡的儿子,轻轻地说:“姥爷睡着了。”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我已经不记得前来签署死亡证明的那位医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无法辨认。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塑料地板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西装,活像一只躺着的大鸟。他死后的那张睁大眼睛、凝视的脸已经渐渐消逝。即使是那样一张脸,我也再无法看到了。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发讣告,做弥撒,准备葬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父亲丝毫无关。这只是一场他因某种原因而缺席的仪式。母亲的状态很激动,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拥吻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还说:“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星期一那天,尸体开始散发气味。这是我从未闻到过的。开始时气味淡淡的,但越来越重,有点像被遗忘在花瓶里已经腐臭的水里的花所散发出的味道。
母亲只在葬礼当天才让咖啡店歇业一天。否则她会失去顾客,而她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就这样,我死去的父亲躺在楼上,母亲仍在楼下继续卖她的茴香酒和红葡萄酒。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眼泪、沉默和尊严是当亲人去世时人们应有的表现。而母亲像邻居们那样遵守丧事礼节,但与尊严的考虑丝毫无关。父亲是星期日去世的,星期三下葬,这期间,咖啡店的常客们进来,刚坐下便会小声地、简单地说上两句:“他走得太快了。”也有的人半开玩笑地说:“好啦,这下老板真的让自己解脱了!”他们表达了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情绪:“我真是心里难过!”“我悲痛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他们想以此宽慰我的母亲,让她知道对于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的不只她一个人,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礼貌的形式而已。许多人在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努力追忆着他们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如见面的确切地点、时间、当时的天气以及交流的话语。在一个生命自然逝去的时候,如此这般地详尽回忆他的往事,有助于表达他们对我父亲的死感到震惊。他们出于礼貌提出要见一见父亲的遗容,母亲没有答应所有人的要求,她只接受了那些真正出于同情的人,拒绝了那些出于好奇的非善之人。几乎咖啡店所有的老顾客们都得到允许向父亲告别。但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工厂主的太太被拒绝了,因为父亲在世时就对这位善于甜言蜜语的太太没有任何好感。
周一,殡仪馆的人员到了。厨房通向卧室的楼梯太狭窄了,棺材无法通过。于是,只得把棺材停放在楼下咖啡馆的中央,尸体被包裹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与其说是被抬着,还不如说是被拖下楼,咖啡厅因此关闭了一个小时。殡葬员们不停地对下楼的最佳方式、转弯时的支点等发表着意见,整个过程简直太长了。
枕头被压出来一个凹陷,自星期日以来父亲一直躺在上面。只要遗体放在那里时,我们就一直没有收拾房间。父亲穿过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我从他的工作服带拉链的衣兜里掏出一沓钞票,那是咖啡店上周三的收入。我扔掉药片,把工作服和脏衣服放在一起。
在下葬的前一天,我们为葬礼仪式的用餐烹制了一大块小牛肉。如果让那些前来参加葬礼、给你增光的人饿着肚子离开,那是不合适的。傍晚,我丈夫来了,他晒得黝黑,因这场与他无关的葬礼而感到有些拘谨。他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格格不入。晚上,我们就睡在家里唯一的一张双人床上,就是我父亲去世时躺的那张。

教堂里挤满附近街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家庭妇女和午休一小时的工人。当然,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打交道的那些有地位的“大人物”们一个都没有来,其他的店主也没有来。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除了每月向商业联合会交一些会费外,什么组织活动他都不参加。牧师在致悼词时,他用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人”。
接下来是与死者家属握手表示慰问的仪式。要么是神职人员在安排上有误,要么是他想用这种方式能够使参加吊唁的人数显得多一些,总之我们经过了两轮的握手。不过第二轮,人们不再表示慰问,所以队伍转得很快。到了墓地,当棺材在绳索间摇摇晃晃地下降到墓穴时,母亲突然号啕大哭,就像我出嫁那天做弥撒时一样。
葬礼后的餐会就选在咖啡馆,我们把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拼在一起。人们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大家随意交谈着,午睡过后的小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在花园里嬉闹着,互相交换着在园子里拣到的花、石子什么的。我父亲的弟弟,坐得离我很远,侧着身子朝我喊道:“还记得小时候,你父亲骑自行车送你上学的事吗?”他说话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一样。将近下午五点钟,客人们都走了。我们默默地收拾好桌椅,我丈夫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去了。
我又在母亲家里待了几天,办理了有人故去后的那些常规手续。到市政厅注销户口,支付殡葬费,回复吊唁信函。新抬头的名片,孀妇A...D...。我度过了一段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思想。有几次,在大街上走着,我会突然想到:“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母亲从前常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因为我已经来了月经。)
我们把父亲的衣服整理好,分发给那些需要的穷人。我在挂在地窖里的他平时穿的衣服里发现了他的钱包。里面有不多的钱,有驾驶证,在折叠的部分还有一张照片,用一张剪下的报纸包着。那是一张发黄的、带锯齿边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工人们都戴着鸭舌帽,排成三排,目光投向镜头。这种相片“展现”了历史书中所描写的工人罢工或是人民战线的那种典型的情景。我认出了父亲,他站在最后一排,样子很严肃,几乎有些担忧。很多人在笑。剪报的内容是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名单,名单是按名次顺序排列的。第二个名字,是我。
母亲又重新变得平静。她一如既往地为顾客服务。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脸上便露出了淡淡的忧伤。每天清晨,在开门营业之前,她都先去墓地,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星期天,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方设法逗我的儿子开心,为的是让他安静不要吵闹,因为乘头等车厢的旅客不喜欢噪音,不喜欢小孩子走动。突然,我惊奇地意识到,“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布尔乔亚”,而且“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夏天,在等待我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日子里,我想,“有一天我必须解释清楚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一段时间后,我便开始创作以父亲为主角的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
最近,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叙述一个受生活所迫的一生,我没有权利采用艺术的形式,也没有权利试图呈现某种“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的东西。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
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中性的写作对我来说很自然,这正是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所使用的风格。
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的几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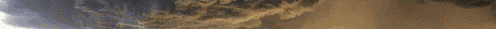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