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游戏
Bernard Suits 著,姜帅Spacelawyer 译
选自 Philosophy of Science, Jun., 1967,
Vol. 34, No. 2, pp. 148-156
感谢译者授权
在批判地考察了对游戏本质的众多看法之后,得一定义如下:玩一场游戏,就是投身于某活动,该活动以实现事件的某种特定状态为目标,而且只能采取被某些规则所允许的方法,若没有这些规则,这些方法的运用会更加不受限制,并且,接受这些规则限制的唯一理由,就是让该活动有可能(本段为全篇之导语,正文自下一段开始)。
在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最近对游戏突然产生的兴趣之推动下,也被如下这样一个最谦虚的念头怂恿着,即哲学家聊点能让科学家感兴趣的东西,这也不是明显在痴心妄想,我在此主张给“玩游戏”构建一个定义。

1. 作为低效方法之选择的“玩游戏”
有古训曰,探求知识须自我们可知之处(knowable to us)推及其自身可知之处(knowable in itself),所以我先从这样一条常识出发,即“玩游戏不同于工作”。游戏在某种关键意义上,可能被看成是工作的反面。眼下,我先直截了当地给工作贴个标签,就叫它“技术性活动(technical activity)”吧,我意思是指这样一种活动,在其中,一个主体(作为理性的工作者)寻求以可用之方法中最有效率者,来实现被欲求的某目标。既然游戏也明显有目标,既然一些方法也明显地被用来促成其目标的实现,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游戏之所以与所谓“技术性活动”不同,就在于游戏中使用的方法并非最有效率。这样说吧,游戏是目标导向的活动,在其中,低效方法被有意识地(或理性地)选择。比如在赛跑游戏中,人们自愿地绕着圈,奋力跑向终点线,而不是“敏锐地”抄近路,径直跨越内场。
接下来的思考,似乎要流露出对上面这个观点的质疑了。可以说,一场游戏的目标是赢了这场游戏。举个例子吧,在扑克牌游戏中,牌局终了之时,我的钱比牌局开始之时更多,就算赢了。但是假设有一位同场的玩家在打牌的时候把他之前借我的一百美元还给了我,或者假设我把另一位玩家的头砸晕,把他身上所有钱都抢了过来。那么,尽管我整个晚上都没开和,我不还是个赢家吗?这显然不行,因为我多出来这些钱不是打扑克赢来的。为了当上赢家,其中的一个标志和结果当然是钱的增加,但是这里有某些条件必须被满足,收债或者非法袭击,可配不上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一些扑克牌规则,告诉我们对这些牌,还有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赢了牌局,就是仅仅使用被规则允许的方法,让自己的钱增加,尽管对规则的纯粹因循本身无法确保胜利。好的方法和坏的方法,同样被规则允许。因此在换牌扑克(draw poker)中,把一张A连同一个对子一起留在手里,跟打出这张A却把对子留着,两种操作都是规则允许的,尽管通常来说,一种办法总是比另一种更好。因此,赢得扑克牌局的办法是被规则限制(limited)的,却不是被规则完全决定(completely determined)的。尝试赢下牌局,可相应被描述为尝试用最有效率的可用之方法增加手里的钱,但是在这里,只有被规则允许的那些方法才是可用的。但这样一来,玩扑克牌就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了,就像先前那个定义讲的那种活动一样。
但这似乎是个奇怪的结论。把工作和玩游戏看作两类截然不同的事,这个信念已流传得太广泛了,但我们似乎不得不说,玩游戏不过是另一种工作,照样得尽职尽责。在放弃“玩游戏包含了一种对效率的牺牲”这个论点之前,让我们再多考察一个例子。假如,我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把一个小小的圆球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送入地面的一个洞里。用我的手把球放到洞里面,会是一种被自然采纳的方法。我肯定不会去找根一头带着铁片的棍子,走到离洞三四百码远的地方,然后再尝试用这根棍子把球打进洞里。那样做在技术上是不明智的,但是,它可是个极端流行的游戏啊!而且,刚才描述它的方式也很清楚地展示了游戏与技术性活动的不同之处。
不过当然,刚才说的这些还都不搭界。把一个球送进地面的洞里,甚至更精确点说,送进排列好的许多个洞里,这还没有正确描述高尔夫球游戏的目标。高尔夫球游戏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击球次数来实现这一点。而“击球”不过就是高尔夫球杆的某些类型的摆动。因此,如果我的目标仅仅是让球进入地面的多个洞里,我可能不太愿意使用高尔夫球杆达到这个目标,也不愿意选个和每个洞口都拉开一段显著距离的位置站着。但如果我的目标正是在距每个洞口都有一段显著距离的情况下,使用高尔夫球杆把球打进洞里,这就给我使用高尔夫球杆还有站在那样的位置提供了确实的理由。一旦认定这个目标,我就会竭尽所能,以最大效率实现它。显然不会有人在这里钻牛角尖,认为如果我让自己以达到极限的效率去追求这个目标的实现,我就不是在玩一场游戏,情况其实是这样,即直到我让自己绷紧的弦松弛下来的那一刻,我都是在玩一场游戏。这里也并不是说,我使用高尔夫球杆来实现我的目标,是比用我的手更低效的方法。在把高尔夫球打进洞时,明明有高尔夫球杆,却就是不用,这也不能说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一来,“对低效方法的选择”就显得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玩游戏”的解释了。

2. 遊戲中規則與目標的不可分割
针对上一章论题的进一步反对意见,以这样一个思考为基础(也是它让这个思考浮出水面),即规则在游戏中的地位:它们(规则)似乎与游戏的目标有着特别的关联。扑克牌游戏的目标不单单是赢钱,高尔夫球游戏的目标也不单单是把球打进洞里,而是按照规定的方式(in prescribed)去行动,或者说得更精确点,不要违抗禁令(in proscribed)去行动。即仅仅遵循规则去行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游戏中的规则与目标是不可分割的。打破一条规则,即是让目标之达成变为不可能。所以,即使你打高尔夫球时凭借谎报分数而折桂,你也根本没有赢了这场比赛。但是在我们所称的“技术性活动”中,通过破坏一条规则而达成目标却是可能的;比如借谎报分数而在高尔夫球赛中夺魁。在技术性活动中,可以打破规则而不伤及该活动的初始目标,但在游戏中,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一旦游戏的规则被打破了,游戏的原初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为谁也不能(真正)赢一场游戏,除非去玩它,而谁也不能(真正)去玩一场游戏,除非遵守这场游戏的规则。
接下来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史努泽教授在校园僻静一角的灌木丛荫凉里睡着了,被一旁小路上的我看到了。我还发觉,他蜷曲其下的灌木,其实是一种食人植物,并且我根据它的动作判断,它就要把史努泽这个人吃掉了。当我横穿草地朝他跑过去时,我发现有块牌子写着:“远离草坪”。我没理会,毫不犹豫冲过去,救了史努泽一命。为何我会做出(当然是下意识地)这个决定?因为拯救史努泽生命(或者说拯救一个生命)的价值,超过了遵守禁止践踏草坪这一禁令的价值。可是这个选择与目前所讨论的游戏中的选择有根本的不同。游戏当中,我无法将游戏的目标——赢——与游戏的规则剥离开来,正是藉这些规则,“赢”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当然我也可以为了赢钱出老千,但这样一来,我也就修改了游戏的目标:我不再是为了在游戏中赢,而是为了多捞钱。因此,在决定救史努泽一命时,我的目标并不是“救下史努泽一命,同时遵守校园关于步行路线的规定”。我的目标是救下史努泽的命,而这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比如我可以仍然停留在一旁的步道上,大声呼喊史努泽,把他弄醒。但这样会白白浪费很宝贵的几分钟,或者搞不好史努泽这个人,尽管他平日极力掩饰,其实已经接近全聋了。很明显,史努泽这个场景的关键,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救下史努泽,以及遵守一条规则,至于是关于法律(law)的规则还是关于草地(lawn)的规则就不展开了。两个目标中,我可以在达到其中一个的同时,抛下另一个。但是游戏中的目标和规则可不允许这样去解耦。我不可能在赢下游戏的同时,又打破它的某条规则。我并没有对自己开放这样两个选项:要么诚实赢得游戏,要么靠作弊赢得游戏,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我根本就算不上在玩游戏,也就不可能——哪怕在更宽泛的意义上(a fortiori)——赢下它。
现在,如果史努泽这个场景被看作一次有且只有一个目标的行动——既要拯救史努泽又要远离草坪,那么可以说,基于这一点,这次行动被改造成了一场游戏。既然没有了互相独立的可选择项,没有选择可以做了,那么就不能实现目标的一部分同时又落下这个目标的另一部分,因为那样就等于彻彻底底失败了。让我以对史努泽这个场景的这一解读为基础来想象一下,我收到了一位满怀感激的同事的热心致意,这当然是由于我对史努泽的及时救助。对此我的一个天衣无缝的回答或许是这样:“我配不上您的感谢。没错,是我救了史努泽,但因为我践踏了草坪,所以那不算数”,这个口气,跟我承认把球打进了第五果岭的球洞里似的。或者,还是借着这个解读,让我重来一次,在开头就另辟蹊径,换一种非常不同的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既救下史努泽,又不践踏草坪?”想象一下,我以最快的速度(但决不违反规定去抄近路)狂奔到大西洋大厦,向那里的撑杆跳运动员借了一根长长的撑杆(还很仔细地在簿子上签了字),想用这玩意儿来合法地把史努泽捅醒,而当我匆匆赶回,我看到史努泽已被掩在那堆植物中了。“好吧”,我说到,还带着点自得的情绪,“我是没赢,但是起码,我玩了一场游戏。”
但这里有一点我必须挑明,即这个事例是严重误导人的。“救人一命”和“不得践踏草坪”这两者,在份量上判若云泥,非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史努泽这个场景之所以能够支持我的核心论点(即游戏与技术性活动的不同,在于游戏当中的目标与规则的不可分割),只不过是因为它的两个选项中的一个相对来说是无足挂齿的。不过,这个事例的独特性也可以这样来补救一下,只要假设,当我决定遵守“不得践踏草坪”的规则时,我是作为一个极端的康德主义者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我降伏在这样一条最重要的哲学信念之下,即对所有的律令(law)都应加以平等的尊重。但是既然读者们可能并不是极端的康德主义者,所以我还得再引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没有史努泽那个怪诞不经,却还是一套逻辑。
我们假设,史努泽的生命威胁不是来自食人草,而是来自斯莱特教授,他被发现正接近小寐中的史努泽,并且表现出谋杀后者的明显动机。我仍然想救史努泽一命,但是,如果我不杀了斯莱特,这就办不到(姑且先这样认为)。但是这里有一条我强烈服膺的规则,它禁止我再去取走一条人命。因此,尽管(也巧了)在自己站的地方我可以顺手就杀了斯莱特(用一把恰好在我手上的,子弹上了膛也开了栓的手枪),我还是决定用别的办法拯救史努泽,因为我有一个遵守“禁止杀人”这条律令的愿望。因此我奔向斯莱特,想要夺下他手中的武器。但我慢了一步,他已经杀了史努泽。这似乎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展示了前面讲过的那类活动,那些活动的目标是与规则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样的活动,让我们一点也没有将其称之为游戏的兴致。正如高尔夫球游戏的目标不仅仅是将球打进洞里,我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救下史努泽,我的目标是救下史努泽的同时还不能违反某些规则。我想合乎规则地(fairly)击球入洞,我想合乎道德地(morally)拯救史努泽。或许,正是以这样一种别致的方式,道德规则才通常被看作对指导人类有很重要的意义。所谓道德性(Morality),即是说,如果一件事只能不道德地去做,那这件事就一点也不应该做。如圣经所言,“有什么益处呢(What profiteth it a man, Mark 8:36)”。因此,规则与目标的不可分割性也不像是游戏的一个完全独有的要素。

3. 遊戲規則並非“一定之規”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刚才的批评意见,仅仅要求部分地拒斥它所针对的那个观点。尽管批评者说明,并非所有符合那个公式的事物都是游戏,但是仍旧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所有的游戏都符合那个公式。这样一来,我们应该不必全盘拒斥那个观点,而是应该先尝试给它加上一条恰当的区别性原则来对它的范围加以限制。或许,通过说明前后两集史努泽的显著不同,可以把这样一条区别性原则给出来。从食人草的口中努力救下史努泽,却又不能去践踏草坪,这第一集是像个游戏,因为和拯救一条人命相比,保护草坪显然是太过琐屑的一件事。但在第二集中,“远离草坪”被“不得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Exodus 20:13)”代替之后,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这个不同可以这样来陈述:远离草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而远离杀戮则是。这样一来,游戏就不仅仅是规则与目标不可分割的一种活动,而是还要补充一点,即在游戏这样一种活动中,对这些规则的忠诚从来不是根子上的。对一个玩游戏的人来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游戏规则给一条非游戏的规则让路。因此,史努泽的续集就不是个游戏,因为被救人者服膺的那一条规则,对他来说是根本性的,即便为此牺牲掉史努泽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规则就是我们画下的线,而在游戏中画这条线时,我们总是不照着最终的目标或更高层级的指令去画。因此可以说,游戏是这样一种活动,对规则的遵行是它目标的一部分,且这些规则并非一定之规;也就是说,游戏里面那些规则总是可以被其他规则替代:换句话,玩家始终可以退出游戏。
下面这个反例考虑一下。假设有这样一名赛车手,在一场比赛中,有个孩子爬了出来,正好就在他的赛车道上。要想不碾压到这个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变道,而这就犯规了,会让他被罚出局。他选择了从这个孩子身上碾了过去,因为对他来说,比赛规则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别的规则比它们更重要。照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就否定他在玩一场游戏。当然毫无疑问,说一个这样做事的人(仅仅)是在“玩”,这个想法确实太奇葩了。但关键在于,说这名赛车手“玩”,不是在一种漫无节制的意义上。他是在玩一场游戏。并且他确实在全心投入地玩,比那些准备下场玩玩的普通票友投入得多。按他的观点,一个选择变道,不从孩子身上压过去的赛车手,就是在比赛中玩(playing),换言之,这就不算是一位正经(dedicated)赛车手。但对一件事太过正经,也会害了这件事,这确实也有点儿悖论的意味。你看这人,把一整颗心掏出去,真是破釜沉舟(digging a ditch)了。
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反过来回一嘴,相比破釜沉舟,游戏的特征不是恰恰在于无法要求绝对的忠诚吗?这正是眼下被我们考虑的那个关于游戏的观点的力量所在,而这或许还让人觉得挺靠谱。既然说靠谱,应该指出下面这一点来对这份靠谱加以支持,即大家通常认为,游戏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严肃的本质。所以我们必须追问,游戏在何种意义上是严肃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不是严肃的。当我们相信游戏并不严肃的时候,我们在相信什么?当然,游戏中的玩家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并不总是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一个乱出牌的桥牌玩家,可能会被指责为拿这局牌不当回事;也恰恰因为他不拿这局牌当回事儿,他也的确会被指责为根本没有在玩牌。更有可能是这么一回事,认为游戏“不严肃”这个信念的意思,和眼下所考虑的关于游戏的这个观点所暗示的一样,即一个游戏玩家的生活中,总是有比玩游戏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他总有理由不玩了。这个信念,是我现在要诘问的。
让我们设想一个高尔夫球玩家,乔治,他是如此地沉迷高尔夫,为此忽略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终致妻离子散。而且,尽管乔治意识到了自己耽溺于自己爱好的后果,他也并不认为他家庭的悲惨遭际是自己改邪归正的好理由。一个支持“游戏不严肃”这个观点的人,可能会把乔治的例子作为证据提交上来。既然乔治的确不把自己生活中其他任何事看得比高尔夫还重要,那么对乔治来说,高尔夫就不再是个游戏了。乔治妻子的抱怨可能也会支持这个论证,她说高尔夫不再是乔治的游戏,而是他的活法(way of life)。
但我们不需要认为乔治妻子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不过,高尔夫对乔治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消遣的形式,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倒是可以保证。但如果说出于这个原因,乔治打高尔夫就不能算是一场游戏了,这倒假设了最关键的一点,即对一个人来说,不管这人是谁,游戏可不可以是至高无上的。高尔夫肯定占据了乔治生活的全部。但毕竟也是游戏,而不是别的,占据了他的生活。的确,如果不是游戏,而是别的什么让乔治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职责,他妻子或许也不会这样狂怒;比如说一份好工作吸引了乔治,或者对玩游戏下定义的尝试吸引了乔治。如此深居简出的冥思式生活,无疑仍旧会招来妻子的抱怨,但是老公因为一个游戏而搞得蓬首垢面,肯定作为一种级别迥乎不同的遗弃方式,打击了她。
对一种游戏的极端投入,如赛车手的例子和乔治的例子中所表现的,会激起几乎所有人的厌恶。既然我们的恨是被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即游戏篡夺了我们认为更值得去追求的那些目标的位置,那么这就是肯定的了。因此,尽管它告诉我们,对于这般德行的游戏玩家,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但是我认为,对这些玩家玩的游戏,它可还是啥都没说。我相信,这些考察足以驳倒这样一个论点了,即游戏规则对玩家来说,并非一定之规。
4. 方法的非终極性,
而不是規則的非终極性
有个观点让我心悦诚服,即在游戏中,有些东西显然并非终极性(non-ultimate)的。对游戏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但我还认为,这个条件是扣不到游戏规则头上的。非终极性(Non-ultimacy),无疑在一个十分特异的点上戳中了游戏。但这不是说那些指导玩游戏的规则一定缺乏终极的指导性(short of ultimate commands),而是说那些为这些规则所允许的方法一定缺乏终极的可用性(short of ultimate utilities)。比如,一个跳高运动员放弃了跳跃,因为他发现跳杆放在了悬崖边上,很显然,这说明跃过跳杆并非是他人生的首要目标。但是,能显示他对游戏的真实态度的,并非他对这赴死一跳的拒绝,而是他对使用梯子或者弹射器这一类装置的拒绝。那个正经赛车手也是一样。使这场汽车拉力赛成为游戏的,并非是宁可输掉比赛也不杀害孩子的决心,而是对,比如说(inter alia),在内场抄近路超车的拒绝。因此这里有一种意味使得游戏可以被称为是不认真(non-serious)的。很自然地,我们可以谈起那个拒绝采用梯子或弹射器的跳高运动员,说他对到达跳杆另一头去这件事是不认真的。但我们也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这个运动员对不借助这样的辅助到达跳杆另一头去这件事,是极端认真的;这一点跟“跳高”是有干系的。但是,如此这般的游戏和其他的事情相比,是不是少了那么一些严肃和认真,好像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的游戏研究能回答的了。
我们来设想一下史努泽之死的第三种可能。面临着斯莱特对史努泽的谋杀威胁,我做了如下决定,即尽管我可以使用足以致人非命的方法去救他,并且我也没有让自己去服膺任何禁止杀人的律令,我还是给自己设了限,让自己解救史努泽时不得采用致命的方法。(在赛车的例子中,相当于内场里面没有布满地雷。)我做了这个抉择,但说不准搞到最后,我可能还是不得不使用被自己禁止的方式去救史努泽。我是这样来给自己设定目标的,即不是要单单救下史努泽,而是要在救下史努泽的同时,还不能杀害斯莱特,尽管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强迫我这样做。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行为该怎么解释。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是无法解释的,这就是一种独断。不过,决定给规则允许的那些方法独断地划出一条线,这个决定自身却不必是独断的。决定去选择独断,这样的决定可以出于某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可以是玩游戏。而且情况可能是这样,即在游戏中划出的那个线,实际上一点也不独断。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看这条线划了没有,我们还要看它划在哪里,而这不仅对该场游戏的类型有重要影响,对它的质量也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把这条线画得充满技巧(因而也不算独断),是游戏开发者(gamewright)的手艺。游戏开发者必须避免两个极端。如果他把这条线划得太松弛,游戏就会显得很弱智,因为太容易赢了。松弛到了完全放任的程度,游戏就彻底消失了,因为已经没有规则对可使用的方法加以禁止性限制。比如去发明一种巡航导弹式的喷气推进装置,用来确保高尔夫球手一杆进洞。另一方面,规则这条线也可以被划得太严,这就让游戏变得很难。如果这条线划得太严,游戏也就被压榨得不存在了。比如这样一个游戏,它的目标是越过终点线。它有一条规则要求参赛者保持在跑道路径以内,而另一条规则却把终点线设计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参赛者不离开跑道就不可能到达。因而,眼下我主张游戏是一种活动,其中游戏的规则与游戏的目标不可分割(在先前约定的意义上),但是还得加上一个限定,即被规则所允许的方法的外延,要比这些规则不存在时要小。

5. 規則讓活動成為可能,
又靠這些活動讓自己被承認
尽管规则在游戏中起的作用,是对达到游戏目标的那些方法加以限制,只让其中一部分成为被允许的,但是仅仅凭这个,似乎还不足以把那些算不上游戏的东西排除出去。当我因为不愿采取不道德的行动去杀人,而最终没有救下史努泽时,那个不得杀人的规则就对我达到目标的方法加以限制。在那个跳高运动员和赛车手的事例与我想合乎道德地拯救史努泽之间,或者与一位不想靠撒谎当选的政治家之间,起区分作用的是什么东西呢?答案是,遵守规则的理由,在这两类事情中是不同的。在游戏当中,我之所以遵守(obey)规则,仅仅因为这种遵守(obedience)是一个必要条件,让我可以投身一场靠这种遵守(obedience)才成为可能的活动。但在其他活动中,比如在道德行动中,总是有别的理由让我们去遵守规则,可以称之为一种外在原因(external reason);一个道德目的论者会觉得遵守规则是因为对规则的违反有损其他目的,而一个道义论者(deontologist)会觉得是因为规则自己确立自己,不假外求。在道德中遵守规则使行为正确(makes the action right),在游戏中遵守规则使行为可能(makes the action)。
为进一步解释这一点,我们再来考察规则起作用的另外两种方式,它们都与游戏中的规则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规则可以是达到一个给定目标的指南(“如果你想改进你的击球质量,你就得目不转睛盯着球”),或者规则可以是一种限制,去限制对达到目标那些方法的选择(“不要对公众撒谎,这样他们才会投你的票”)。在后一种方式中,比如道德就经常作为技术性活动的限制条件而出现,尽管某个干涉性(supervening)的技术性活动也可以起到同样的限制作用(“如果你想按时赶到机场,就开得快一点,但如果你想安全地驾驶,就别开得太快”)。想象一张印了横线的书写纸。我按这些横线去写字,以便写得整齐一点。再想像一下,现在规则从书写纸上的横线变成了硬纸板,而且这些硬纸板拼成了一座迷宫,硬纸板变成了迷宫的墙,当我希望置身迷宫之外(be out of the labyrinth)时,我不想破坏这些纸板墙。这些墙就是我置身迷宫之外的限制条件。回到游戏,我们来考虑第三个例子。我还是身处迷宫内,但我的目的变了,我不再想置身迷宫之外(如果Ariadne在等我的话,我想会这样的),而是想走出迷宫(getout of the labyrinth),亦即迷宫式(labyrinthically)地出去。那么这些墙的地位是什么呢?很显然,它们无关我置身迷宫之外的手段,因为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置身其外。如果这时一位朋友突然出现在我头顶的一架直升机上,我会拒绝放下来的梯子,尽管换一种情境我就可能接受它了。我的目的是走出迷宫,并且仅仅接受它强行设定的条件,不作他想。这里也不像第一个例子那样。在那个例子里,我并没有兴趣非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一行不违反规则(越过横线)的字来,我只是利用那些横线,以便写得整齐。
因此我们可以说,游戏是这样的行为,它合乎规则,而规则限定了追求目标时被允许的方法,并且规则之所以被遵守,只是为了让这样的活动能够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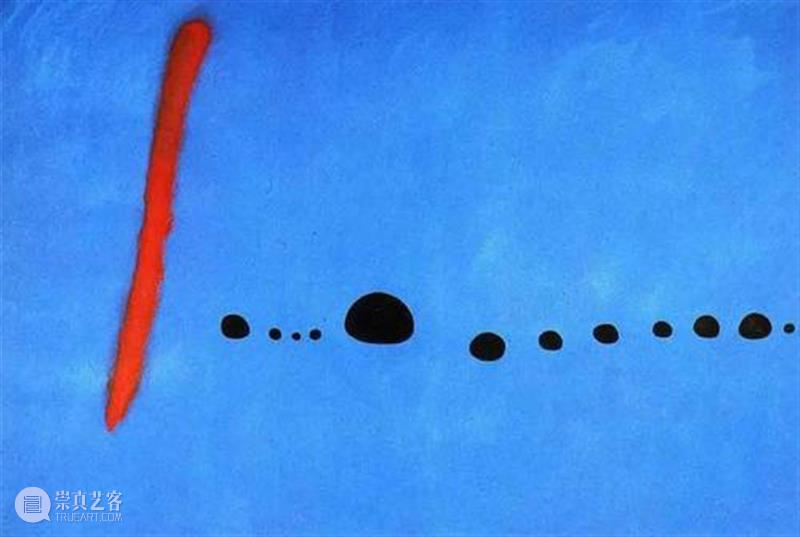
6. 規則對方法的限制讓贏本身不是目的
还有最后一个难点。一方面,将规则描述为一种多少是有些放任的针对方法的操作,似乎顺着发明游戏或者修改游戏的方向去了。而另一方面,说游戏当中那些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凌驾于那些被规则允许的手段之上的,却似乎一点也没意义。考虑一下国际象棋。棋手追求的目标好像是赢棋。但是赢棋意味着按照国际象棋的规则在棋盘上落子。但是既然对规则的破坏就意味着达不到这个目标,那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可走吗?正是出于这个推理,本文第一章的那个论点才被驳斥了:使用高尔夫球杆打高尔夫球,这不是一种更低效的,因而可替代的实现目标的方法;它是一种(逻辑地)独立的方法。
我相信,有反对意见可能会提出,国象游戏本身就有一个目标,可以分析地(analytically)区别于作为目标的赢。好吧我们换个有点不同的角度,从头再来一次。我们说,国象的目标,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是把你的某枚棋子放到棋盘的某个位置上,叫对方的王(king)动弹不得,当然是根据国象的规则动弹不得。现在,只要不跳出国象的游戏之外,我们就可以说,要制造这种局面,方法是挪动棋子。很显然,国际象棋的规则说明了棋子应当如何挪动,它们区别了合法的挪动与非法的挪动。比如,既然一枚骑士(knight)只被允许以一种很严格的方式挪动,那么很显然,被允许的(permitted)挪动方法,在外延上就比可能的(possible)挪动方法要小。下面这点应该没人反对,即挪动骑士的其他方法,比如走对角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去用骑士,就把规则破坏了,就不算是赢的方法。而眼下讨论的关键,不在于这样去用骑士是一种赢的方法,而在于这是一种挪动骑士的可能方法(尽管不是被允许的方法),它可以使得骑士去占据一个位置,去根据规则将对方一军,让对方的王动弹不得。一个这样走棋的人显然不算是在玩国象。或许他是在国象里作弊吧。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我在尝试营救史努泽的同时,放弃了我的独断决定“不杀斯莱特”的话,我就不是在玩游戏了。国象,和我对史努泽的第三次营救努力一样,都是游戏,因为对达到目标的可用之方法,存在一个“独断的”限制。
关键在于,这里所讨论的目标(end),不是“赢下游戏”这个目标。肯定存在着一种区别于“赢”这个目标的目标,因为正是对达到其他目标之方法的限制,才让赢成为了可能,并且也在任何给定的游戏中定义了什么是赢(What it means to win)。在定义游戏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两种不同的目标,而且,正如我们一会要看到的,还有第三种目标也要考虑。首先,有一种在某些情形下存在的东西,可以称之为目标,比如在一块板上拼接贴片,搭救一个朋友的性命,冲过终点线。然后,如果有一个对规则的介绍,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做出一些限制,就有了第二种目标,赢。最后,当对“什么是赢”做出限制的时候,第三种目标就出现了:尽力去赢的活动,也就是“玩游戏”。这里有一点值得强调,有些活动里,可以只追求其中一种目标,不必理会其余,但有些活动就不行。所以打桥牌时你可以追求拿到尽可能多的牌墩(trick),把这当做你的目标,而不管能不能赢,因为你是可以靠作弊去达到这个目标的。但是,不去寻求打出一定(相对的)数量的牌墩,是不可能去寻求赢下桥牌的,也不可能一边寻求去玩桥牌,一边不寻求其他两种目标。
7. 定義
我的结论是,玩一场游戏,就是投身于某活动,该活动以实现事件的某种特定状态为目标,而且只能采取被某些规则所允许的方法,若没有这些规则,这些方法的运用会更加不受限制,并且,接受这些规则限制的唯一理由,就是让该活动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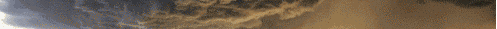
注 释
略。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