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将与大家分享高古轩艺术家Harold Ancart(哈罗德·安卡特)与小说家Andrew Winer(安德鲁·温纳)的对谈摘录。其中,他们讨论了 "存在和存在者(Existence and Being)"、如何在紧张中寻找自由以及病态逃避主义。这篇文章已发表在高古轩季刊网站中。
5月3日,Ancart的个展「Paintings」将在高古轩纽约展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对谈内容,一起了解这位艺术家的创作思考。

Andrew Winer(以下简称AW):关于存在和存在者(Existence and Being)——有时候,当我进入一种不受目标支配且处于“存在者”状态的工作方式时,是我感到最自由的时刻。这让我想起了 E. M. Forster(E·M·福斯特)曾经的发问: “直到看到我所说的之前,我如何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这是否也是在讨论你创作一幅画时的经历——对于你希望某幅特定的画能做些什么,你有多了解?
Harold Ancart(以下简称HA):确实,我无法预知任何事情。尽管我还算年轻,但我还是以艰难的方式了解到,我很幸运没有达成年轻时曾经执着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并非是因为取得了成功;相反,而是因为不顾一切,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走到这一步)。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绘画如何创作或者它最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会有很多看法以及预设的规范概念。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包含着情绪冲突以及身体和经济方面的困扰。我记得我会因为事情并不如我所愿而变得很生气。
AW:虽然我朋友经常开玩笑说我总是爱这么那么形容,但你听起来很像尼采!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理由感激失败,并为他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负责。他还告诫人们不要为某个特定结果而奋斗,甚至对设想的 “目的”或“愿望”进行了些许嘲讽。
HA:是的。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这些内心冲突,我开始意识到生活就像绘画一样,和我自己认为的我想要什么几乎没什么关系。我开始意识到绘画是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继而是关于所做事情的观察。也就是说,在开始绘画之前,我总是会有某种自己想往哪里去的想法。
AW:所以你确实会先有想法......

HA:但我倾向于保持简单的想法:它可以是一个图像、一个形状或一片蓝色。然而,我现在明白那些想法、那些头脑里投射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也无法抵达特定的目的地。和Forster一样,我坚信如果一个人在真正画之前就知道自己要画什么,那么绘画就毫无乐趣了。我猜写作或生活也是如此?难道我们的想法或故事不正是在迷失于写作中时才逐渐展开吗?它几乎就像是一场个人冒险或是一天的记录,只有当我们开始讲述或用语言记录时才算真正开始。
AW: 我想同时迷失在经验和我对它的理解或诠释中。但矛盾的是,迷失即意味着在场。或许这也算不上一个悖论,因为迷失会迫使我们非常清醒,不是吗?对即将展开的一切保持清醒。
HA:我同意。在绘画时,我尽可能地拥抱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会考虑到失败,而如果那不算是福气的话,至少也是促成改变或成长的机会。然后,我可以一边创作、一边看着这幅画在眼前慢慢呈现。在以这样的态度创作时,我手中的颜料可以真正去到它们本该前往的位置,而不是我希望颜料往哪个方向去。正因如此,我在完成一幅画后很少会产生内心纠结。毕竟,一个人只能完成一个人能做的事。我也尝试在生活中保持这样的态度,比如我有一个模糊的想法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便恣意沉浸于其中,看着生活随着我走过的步伐而徐徐展现。
AW:我觉得你的绘画为何如此丰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你的挣扎。我感受到一种在创作时经常涌现出的某种默许。
HA:如何理解你说的这句话?
AW:举个例子,就像Clyfford Still(克莱福特·斯蒂尔)作品中那种锯齿状图形的美,在你的画里也有这样的美感:不仅是在图形边缘,也可以在色块中看到。然而在我看来,就像是你在色块被过度使用前便离开了那一步,通常留下的是不和谐的痕迹。我一位已故的朋友,诗人Adam Zagajewski(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写道:“人必须反思自己,否则就不是自由的。”你的画确实散发出一种自由的光芒,但其中又有一些摩擦和碰撞——由那些厚重的、半干的油画棒颜料所形成的坚硬物。这就如同写作,或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媒介会予以回击,回击你要的自由。这让我想知道,你在作画时除了感受自由外,是否也会感到焦虑甚至恐慌?
HA:我唯一感到焦虑的时候是我在工作室踱步时,因为抽了太多烟而不是在工作。于我而言,这通常发生在我即将开始一件新作品且画布完全还没动过时,我会思考太多东西,就好像会有把它搞砸了的风险。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事先搞砸任何事情。感到焦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事先”面对的可能性范围会比真的开始实施时要宽泛很多?
AW:没错!

HA:我不知道。这有点像在炎炎夏日里跳进湖里。如果你想慢慢进入冰凉的湖水里,可能会花很长时间才能下水。你必须用另外的方式,纵身跳入水中。至于你是否是脑袋先入水,其实并没有关系——一旦你跳入其中,最终都会觉得很不错。我称之为“地带”,那个地带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其中一些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描述。但如果有一件事不属于那个“地带”,那就是焦虑或自尊问题。当然,这其中会有挣扎。但我甚至认为这种挣扎是建立一切的必要条件。
AW:我想多听听“地带”这个概念。
HA: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地带。这种张力存在于两件事之间:你的头脑需要什么是其中之一,而手能做什么是另一回事。头脑总是否定手所做的事情,而这就是我找到自由的地方。
AW:这个解释非常棒,而且不知为何让人感到舒适。你认为,艺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我们引向所渴望的事物或地方吗?
HA: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小时候,我从不满足于此时此地的现状。我一直想要创造某个替代领域,而我能成为那里万能的统治者。我猜几乎每个孩子某种程度上都会这么做?我觉得这很好。除了我不再是孩子外,其他并没有太大变化。
AW:对你,还有许多成年人来说。
HA:一个人必须会做梦。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做梦到什么程度呢?我非常受困于逃避现实的问题,近乎病态的程度。有时候我在想,有渴望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人在这里,却希望自己在别处。最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别处”是不存在的,现实只属于此刻此处。这是很残酷的。人类的处境是残酷的。我不能理解,如果一个人无法逃回自己的思想中,那这个人该如何生活。但是,回到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有着它具体的规则和需求。这就像尝试用叉子喝汤。
AW:这就是我之前想问的:绘画应该向我们展示一个与我们的愿望相同的世界吗?或者,它应该改变我们的渴望?我的意思是,我们常说梦想一个与现实不同世界的人——如John Lennon(约翰·列侬)的《Imagine》或Martin Luther King(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尝试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将想象强加于现实世界之上。你认为有这样的画家存在吗?还有另一种梦想家,他们让世界自主地在他们身边显现、成形,而且这类梦想家会着迷于任何出现在身边的东西。你觉得自己属于其中哪一类梦想家吗?
HA:我觉得自己对这两种人都能产生共鸣——第一类人的梦想是如此强烈而执着,最终改变了他们周围的环境;第二种,他们在平凡中发现了迷人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两种类型是齐头并进的。当我意识到所有一切都一直在那里徘徊着,等待着我最终发现它们的时候,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想成真了。我个人认为,绘画既要有梦想别处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提炼、分离和撷取日常视觉环境元素的能力。这些都是梦想的构成部分。这种重新组合或重构的能力,能够让你将“别处”具形化,无论它是一个人形、一朵云、一个窗台或是抽象的事物。

AW:你之前提到梵高打开了一扇门,通往绘画主题之外的某个地方,这也表明他看到了画布或眼前风景中的替代可能性。我对此很感兴趣。几天前,我为我正在写的小说做了一条笔记,写道“一幅完成的画,尽管它可能已经都完成了,但自相矛盾式地包含了一种替代可能性的简陋。”基于此,画家知道画已经完成了,而画本身也获得了一种必然性的氛围。完成一幅画对你来说是否有这种关闭了其他可能性的感觉?即使它留下了空隙,或是暗示着通往另一幅画的途径?
HA:对我来说,完成一幅画与开启一幅新画作息息相关。事实上,当一幅画成功预示下一幅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幅画已经完成了,即无论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或是被如何定义,它都开始引出了更多并不属于或永远不属于这幅画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都属于下一幅,那张还未被描绘出的作品。
AW:你的画令我感到愉悦,它们就像是美好的回忆,关于颜色以及简单的形式,我有点说不清。他那些画会让你思考,“我以前见过这些东西。我去过那里。” Simon Schama(西蒙·沙玛)在《Landscape and Memory》(风景与记忆)一书中写道,“在依赖感官体验之前,风景是记忆的作品”。风景既是岩石层构成的,也是由层层记忆形成的。你在创作这些画作时,是否使用或考虑过记忆?记忆对绘画重要吗?
HA:风景是由记忆构成的,就像它是由岩石构成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说法。2014年,我进行了一次横穿美国的公路旅行。我买了一辆车,从东部开到西部,开了一个来回。那是一辆吉普车,所以后备箱离地很高。我一路上都在后备箱那里画画,最终画了大约二十七幅。我之所以会进行一次自驾游是因为我已经在纽约生活了六七年,但却从未到过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我还在某处读到,如果不开车穿行过、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画家。我想这大概是波洛克(Pollock)说的。我天真地听从了他的建议,或者也许我只是需要一个开车的借口。我很喜欢开车,在那段旅途中我开了很久的车,甚至有时一天开 13 个小时。我想你应该读过了我在那之后写的一篇短文,它也是一本摄影书《Driving is Awesome》的引言。我手边正好有这本书,可以给你读一小段:“在那段时间,我已经画了几幅画正在后备箱那儿晾干。汽车散发出颜料味。我的朋友会让我在这儿或那儿停下来,这样就能下车拍摄了。他拍影片的时候,我就在画画。我什么都画,完全没关系。我的眼里已经有了那么多画面,几乎都不用再四处看看了。”就像从那之后我画的大部分风景画,这些公路旅行中的画(除了一幅画的是《Spiral Jetty》这件作品)描绘的都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画中的地方并不存在,而是凭空创造的。我想正是因为它们接近于真实地点的特质,让画面产生了熟悉感。它们是从一堆记忆中创造出来的,是这个世界许多个角落所提供的景象所组成的。我想这应该是它们为何能让人共鸣的原因。
AW:画画对你来说是一种分享吗?也许是分享周围的快乐,分享在此处的快乐,还是一种“此处”之外的快乐?我想到的是Henry James(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宇宙赋予艺术家的刺激,对激发其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煽动’,让艺术家因此无条件地服从于宇宙;除了强烈的被分享的欲望、表明自己是可被分享的从而滋生出最崇高的信仰外,艺术还会是什么?”对此,你怎么认为?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接受的精神形态吗?你作为艺术家,是否有爱存在?
HA:我喜欢我所做的,尽管我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宇宙至高无上的仆人(笑)。我只是一个谦卑的、恰好活在当下的比利时画家。然而,我确实也很喜欢将绘画比作通向更广阔世界的入口的想法。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有近乎病态的逃避现实的问题。我很容易就开始走神,思绪游荡。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经常发现自己将绘画视为容器,或是一种交通工具,带我前往许多不属于此时此地的其他地方。

关于对谈者:
Harold Ancart(哈罗德·安卡特),1980年出生于布鲁塞尔,目前工作并居住于纽约。他的绘画、雕塑以及装置作品探索了我们对于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的体验。同时,这些作品暗指了不少一系列艺术史相关的来源,通常以抽象色彩的过渡为主要特征。Ancart 专注于呈现我们所能辨别的主题,从日常环境中抽离出诗意的时刻。
Andrew Winer(安德鲁·温纳) 是小说 《The Marriage Artist》(2010)以及《The Color Midnight Made》(2002)的作者,并进行着艺术、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写作和演说。Winer是美国国艺术基金会(NEA)小说类的获得者,目前正在完成一部小说和一本有关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中心哲学思想“肯定生命”与当代的相关性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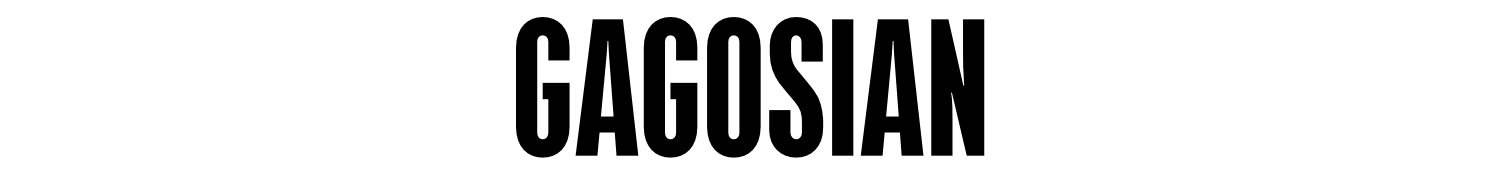
香港中环毕打街12号毕打行7楼
7/F Pedder Building, 12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T. +852 2151 0555
F. +852 2151 0853
hongkong@gagosian.com
开放时间: 周二-周六,11am-7pm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