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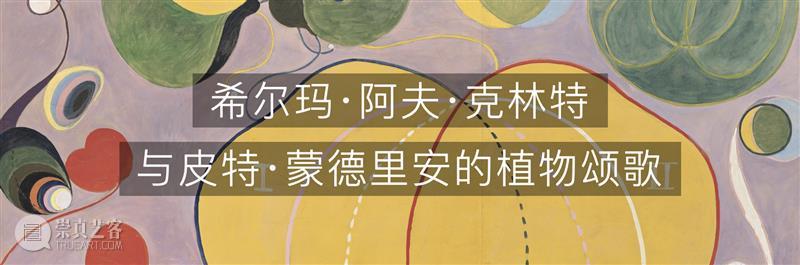

对谈 CONVERSATIONS
刘迎九与朱筱蕤
谈上海外滩美术馆的未来
文、采访 / 刘品毓
一个安静的、可以有思考、有自己逻辑的空间变得更加重要。


上海外滩美术馆。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就艺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上海外滩区域,似乎是到了近期,其能量与定位才又被推上新的高峰。2010 年前后的外滩周边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机构,只有上海外滩美术馆独树一帜;尽管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创立之初曾在这里发生,BANK 画廊也曾在这片区域驻足过几年,但它们最后都纷纷迁离,到别处形成新的聚落。
2014 年,佳士得上海入驻安培洋行,加码了外滩作为艺术聚落的可能性。即使该拍卖行在 2022 年迁至外滩一号,其决定依旧说明了外滩的重要性。2016 年,复星艺术中心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成立;2018 年,贝浩登、里森画廊、阿尔敏·莱希进驻琥珀大楼,为外滩赋予了上海国际艺术埠口的地位,追忆过去外滩曾有的“十里洋场”风光。

上海外滩美术馆艺术总监朱筱蕤(左)与馆长刘迎九(右)。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在环境更迭中,上海的艺术聚落,如莫干山路、安福路、UCCA Edge、西岸、外滩乃至浦东,早已呈现多中心样态。现今也发生了如张培力不再续任 OCAT 上海馆长的情况,而上海外滩美术馆作为上海最早成立的民营非营利美术馆,在日前也对外发布了最新的人事任命。从开馆前期就担任副馆长的刘迎九,正式成为馆长,美术馆同时也迎来了新任的艺术总监朱筱蕤——她自 2014 年起一直担任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展人一职。
如此的人事任命安排,也催生了 2023 年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展览计划,包括王水(WangShui)、王伊芙苓韬程(Evelyn Taocheng Wang)、托什·巴斯科(Tosh Basco)、戴安·赛布林·阮(Diane Severin Nguyen)、谭婧与舒比吉·拉奥(Shubigi Rao)等艺术家的展览。展览面积与节奏也有了变化:上海外滩美术馆过往一年举办三个展览,每个展览均使用全馆的展览空间,而在 2023 年的计划中,每个展览只占两层楼的空间,使得上海外滩美术馆可以一直有展览,保持几乎是全年无休的状态——这可谓是一个极大的调整。在新旧交替之际,Ocula 与上海外滩美术馆长刘迎九与朱筱蕤展开对话。


展览现场:“郑明河:暗游”,上海外滩美术馆,上海(2022年11月12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一直以来,你作为副手陪伴外滩美术馆成长,如今成为掌舵者。你在思路与心境上有什么变化?
刘:我从2011年担任副馆长,第二年开始协助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管理和运营美术馆。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和语境下探讨 RAM 的定位和重要议程,逐步形成今天 RAM 的机构理念、工作方式、专业气质和学术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经历也塑造了我个人对艺术和艺术机构基本看法。我珍视这些经过长期实践和团队共同努力积累下的宝贵遗产,希望能够在未来继续维护它,并将之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我们一直秉持自我批判,拥抱挑战与变革的实验精神,这意味着我们也会在运营方式和项目规划上始终尝试开放和突破,在变化的语境下保持 RAM 与当下艺术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我们将美术馆比作一条船,它的生命和价值在于旅途之中,更在于共同参与这一旅程的人,包括团队、投资方、合作和支持者、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以及不同层面的公众。担任馆长,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角色就是以一人之力烛照航向或者力挽狂澜,而在于领导和激励团队的探索、思考,沟通辨析,凝聚共识。这是同舟共济的本义,我也对此充满信心和激情。


展览现场:“王水:生生”,上海外滩美术馆,上海(2023年4月1日至6月11日)。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后疫情时代,外滩美术馆的定位与方向有什么调整?
刘:外滩美术馆是一个活跃在艺术与社会挑战前沿的研究型艺术机构,也是一个在本土和当代的语境下不断拓展其角色、意义和价值的美术馆,这一基本定位不会改变。在后疫情时代,社会面临一系列重要的转变,而一些长期存在的议题仍然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都会是我们未来关注的领域。我们会继续加强对亚洲和新锐艺术家的研究和支持,特别是一些尚处于主流视野之外的区域和实践领域;也会在教育、传播、呈现和运营方式上做更多的探索,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广泛的回应与参与。我们还会积极寻求不同机构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以扩充我们的能量和作用范围。
你如何看待非营利性美术馆的发展前景?
刘:我认为就非营利性美术馆的宗旨和产生的社会价值而言,维持其存续和健康发展,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且首先是制度设计和执行者的责任。遗憾的是,无论是就文化传统而言,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当前中国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实际的情况是,这一责任还是落在了举办单位(个人)及运营团队的肩上。这是不合理的,也是脆弱的,难以抵御经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近年来,我们看到陆续有民营美术馆关停的情况,这是这一困境最明显的表现。在此背景下,作为运营团队,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开发、培育支持美术馆持续运营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我们正在努力开展的社群建设,但更希望得到政府、社会和公众更加严肃的关注和实际的支持。

展览现场:“Wu Tsang: Anthem”,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展期:2021年7月23日至9月6日)。图片提供:古根海姆美术馆。
是什么促使你从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展人,转任至外滩美术馆艺术总监?
朱:有多重原因:一是在古根海姆工作了 8 年之后,很多想要做的——机构建设、馆藏建立、展览策划等——也都发生了,而近几年纽约机构由于多方面因素大大减少了实验性。如果要用我想要的方法来做我想要做的工作,会要花很多的精力来“推”机构。相反,在外滩我有董事会的全力支持,可以真正地做很多尝试,通过长期研究,出版,展览,公共活动等做很多长线的计划。二是去年春天后,在很多人都相继搬离上海之时,一些艺术机构也在消失,我感到其实这里反而成了“紧急地带”,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更好更稳定地营造一个面向社会的艺术机构。一个安静的、可以有思考、有自己逻辑的空间变得更加重要。

展览现场:“王伊芙苓韬程:参差的对照” ,上海外滩美术馆,上海(2023年4月22日至7月9日)。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你过往的经验与学识背景,如何助益外滩美术馆?
朱:更多是一个互惠(reciprocity) 的过程吧。也许我可以提供一种多元视角,我也希望能够和团队一起有更多的累积和尝试。
外滩美术馆 2023 年的展览规划呈现出对于女性与非二元性别艺术家的挖掘,对此你是怎么思考的?有哪些艺术家是遗珠之憾?
朱:我不太会用“挖掘”这个动词来叙述我们和艺术家的关系,也希望可以跳出一个过分简单的身份政治来叙述这些艺术家其实非常复杂的存在状态。和这些艺术家合作的基础是我和她们的长期交流;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来自于同一社群,在建立自己的思想观的时候都经历过比较相近的经验,譬如说由移民经历带来的边缘化经验;中产阶级的生产消费经验;身处在这个时代的社交日常经验等。在这种经验下,以白人为中心的现代性思潮建立的性别分化其实是我们一致在质疑和抵触的议题。所以,与其说今年的展览是在“挖掘”这些艺术家,不如说是通过建立一个包括我(和外滩美术馆)在内的联盟来思考我们当下的政治象征军械库(political symbolic arsenal)。

艺术家王伊芙苓韬程在其行为表演彩排现场。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相比于议题式的群展,外滩美术馆的展览规划倾向呈现艺术家个人展览。造成这样倾向的原因与思考是什么?
朱:我当然可以选择做一个非常大型的群展来体现我上面说的联盟,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贫穷艺术运动的开端或者关系美学运动等。但是,我更感兴趣的也许是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美术馆的空间内让每位艺术家有一个完整的叙述可能,而不是让她们变成群展中的一个小片面,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些艺术家的工作都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我想要给她们创造一个可以行动的场域。而在两位或者多位艺术家的逻辑和世界相互重叠之时,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语境,同时也会看到她们之间的不同,甚至是有矛盾的地方。

展览现场:“美好生活”,上海外滩美术馆,上海(2022年9月29日至11月20日)。图片提供:上海外滩美术馆。
在担任外滩美术馆艺术总监之前,你综合“装置”和“发生”两个部分组成展览“美好生活”,这算是你第一个面对上海社会的艺术实践。除了解构、重思“美好生活”的定义之外,你个人从这样的展览中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
朱:可惜的是,我没能在“美好生活”展览之际和观众互动,也没能看到现场,全程的策划工作都是远程进行的。我希望可以在2024年继续像“美好生活”一样的尝试,更多地介入我们所在的街区,尝试更多带有及时性的项目。我们美术馆内的很多工作是非常长线的研究,但是也很需要一些灵活的、直接回应社会生活状况的项目。—[O]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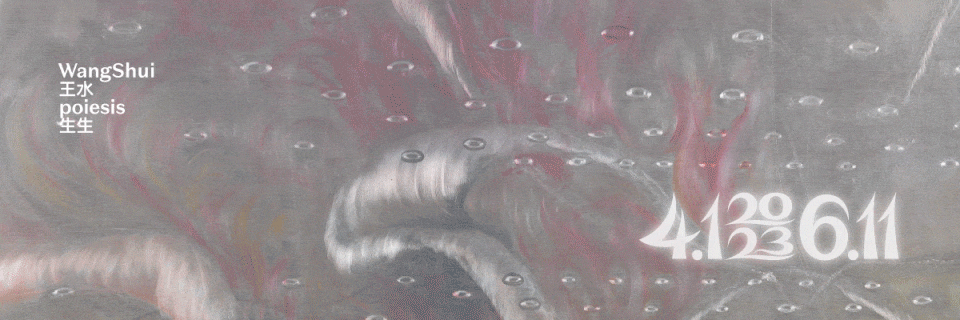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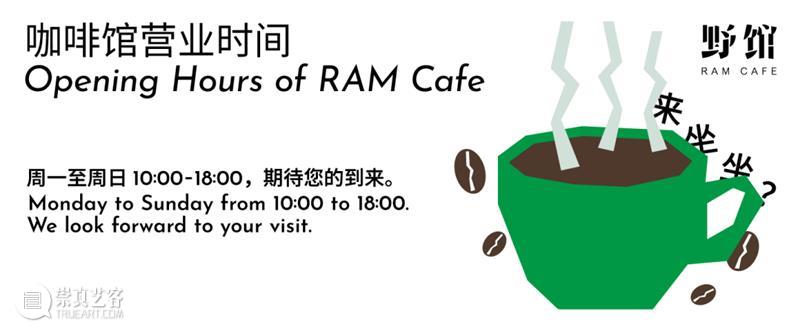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