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雨〉人物谈》的版本流变及其他
汪静波 殷国明
内容摘要:《〈雷雨〉人物谈》数十年间的版本流变是戏剧文学批评发展的一面特殊镜像,在该评论文本的成型过程中,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共同合力。内中有六种版本流变的形式:其一,随着时代变迁,批评家自身看法转变;其二,批评家依据编辑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增补;其三,批评家吸收了同行意见,删去部分文字;其四,批评家读到作家修改的作品,原先的意见发生改变;其五,批评家读到作家的自我评价,受其激发,将原本的意见“雏形”写成文章;其六,批评家依据作家确认的史实,更正原本批评中的讹误。由此既可推进相关个案研究,亦可见出戏剧文学批评在版本变迁的过程中,存在批评家、编辑部、读者、作家间的多重互动及作用。
关键词:钱谷融 〈雷雨〉人物谈 曹禺 文学评论 互动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3)02-0015-12

作者简介
汪静波,女,1995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临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论文散见于《现代中文学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上海文化》《中国图书评论》等,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批评。

殷国明,男,1956年生于新疆伊宁,祖籍江苏武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等多种专著,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
有关钱谷融先生《雷雨〈人物谈〉》的版本变迁这一问题,宫立在《“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和《关于钱谷融和〈〈雷雨〉人物谈〉》等文中,已进行了颇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然而,其文的主要关注之处,在于钱谷融谈周朴园、蘩漪等多篇著述,是如何从50年代的函授讲义中脱胎而出[1],以及《〈雷雨〉人物谈》从单篇论文的发表到单行本出版中间的艰难历程[2],并未对此作收入《钱谷融文集》时的修改加以关注。此外,《〈雷雨〉人物谈》的系列文章,从函授版到初刊版,再到单行本版和文集版的数度修改过程之中,又多有涉及与《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评论》的专业读者,乃至作家曹禺本人的数次往来互动,或仍值得加以进一步补充。
一、生成与流变:关于《〈雷雨〉人物谈》
四种不同版本中的心灵轨迹
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系列文章,至少存在四个较为重要的版本。第一,是收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中,由钱国荣编写的第六章曹禺部分(下文以函授版名之)。此书在《说明》中注明“专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同学试用,请勿转载或引用”[3],由于是编写教材,作为集体项目,无法充分发挥钱谷融本人的学术思想[4],但其中的不少论述,仍然可作为此后《〈雷雨〉人物谈》诸文的雏形加以参考;第二,是散见于《文学评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艺红旗》等刊物上,进行公开发表的初始版本(下文以初刊版名之)。尤其在钱谷融与《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文字往还之中,可以充分见出批评文章在出版过程中与编辑部的互动。第三,是收在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册子《〈雷雨〉人物谈》中(下文以单行本版名之)。钱谷融先生在这一版中的修改,可以见出其对各色商榷文章的回应,也可见到与作家曹禺本人的书信往来,和对自家文章的审慎态度。第四,是收进2013年《钱谷融文集》中“曹禺剧作论”一栏下的文章(下文以文集版名之),虽然相较单行本版未有多少改动,但从其为《后记》补入的四条注释,或也可见出作者心迹之一斑。
正如杨扬所言,“教材有严格的审查要求”[5],今人不应依据50年代函授版中所载的文本来推断钱谷融本人的真实想法,但从函授版到初刊版,乃至单行本版和文集版中的各色慎重修改中,却颇可见出其人心迹之一二。因作者在讲义中的意见表达,若在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后,仍要细细审定并在发表时加以修正,便可见出对此数条意见甚是在意,也可见出其心绪随着时代变迁的流变轨迹——或说从被时代所压抑到得以宽舒和复原的轨迹。
《曹禺和他的剧作》初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依据函授版的第六章第一节《曹禺的生平和创作》和第二节《雷雨》修改而来,后收入单行本版和文集版。四个版本之中改动不少,如在单行版和文集版中,相较以往略调了一些语句表达,将《原野》的情节概述修改得更为洗练[6]等,但更重要的,是从函授版到初刊版的修改之中,可以见出许多评论乃至理论意见的“重订”。
在论述剧本《原野》积极的一面之后,函授版原作“而这一面是并没有为它的宿命论思想和神秘象征的色彩所掩盖住的”[7],从初刊版始,后三版均已改作“而对话的机智生动,动作性与抒情性的紧密结合,也仍保持着《雷雨》《日出》的固有特色”[8]。就原本函授版的语气来看,显然不得不随着50年代的时代要求,对“宿命论思想”和“神秘象征的色彩”持有较为负面的意见,既是论此二者未能掩盖剧作的积极一面,又是意味着以其本身为相对消极。到初刊版中,则已将之删去,并代之以对《原野》其他优胜之处的赞语。在论及《北京人》时,函授版原引了一段人类学者袁仁敢的话,说作者曹禺是借此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论述道,“认为人类的‘文明’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而把希望寄托于人类的祖先,寄托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身上,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返归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必然使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受到损害。”[9]这段论述在之后三版中也已删去,并代之以曹禺本人在《后记》之中所说的一句话:“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10]函授版中称“返归自然”的思想为错误,并且言明此类思想会损害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带有那个年代认定“今必胜昔”“厚今薄古”的明显印记。然而文艺的发展轨迹与所取得的成绩,却未必会与年代的线性前进相一致,就钱谷融本人来说,其喜好中国古典文学与19世纪的西方文艺,也要更甚于当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与之相类,在论述曹禺所写的“剧本《明朗的天》的出现,标志着曹禺的创作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时,函授版作“剧本《明朗的天》已经由批判的现实主义跨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门坎”[11],而之后的三个版本中,则已改为“作者力求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观察所要描写的对象,通过形形色色的剧中人物的创造,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党性和爱憎分明的精神”[12]。虽然钱谷融仍赞成在剧作《明朗的天》中,确实表现了曹禺阶级立场的转变和爱憎分明的精神,却已不愿再重复往日已成套语,但未必正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定高于批判现实主义”。此外,为减少个人崇拜的气息,在单行本版和文集版中,也已将曹禺在参会之后“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伟大正确”[13],改成“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正确”[14]。
除了在这篇作为《〈雷雨〉人物谈》单行本的序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钱谷融的“曹禺剧作论”的总论——的《曹禺的生平和创作》中,有如许修正以外,在散见于各篇的具体人物论中,也有着对意见表达的慎重修改。譬如在论及曹禺为何要以蘩漪而非侍萍,作为周朴园的主要对立对象时,在函授版中,原作“如果以侍萍作为周朴园的主要对立形象,能不能很完满地表达这种思想呢?显然这是不顶合适的。因为侍萍所受的迫害,主要是封建性的迫害,要揭露资产阶级性的一面,就显得有所不足,显得不够有力了”[15]。到了初刊版时,则已改作“那就应该把它放在另外一种背景下来处理,而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要与现在有所不同了”[16]。在收入单行本版时,又再进一步改为“显然这是不很合适的。因为侍萍所受的迫害,主要是地主阶级对在他奴役下的使女的迫害,而作品在这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如我们上面所说,已经不单纯是,而且主要并不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反封建思想了”[17],并依据此版文稿收入文集版中。通过一步步的修改,到了最后的定稿之时,已将侍萍所受迫害的性质定位得更加精确,也将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是如何地不能局限于仅仅揭露“地主阶级”的封建迫害,《雷雨》自有其另一种“主要思想”谈说得更为明晰。此类将意见说得更加深入明确的修订,应该说是贯彻于各个“人物谈”单篇内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可能是应编辑部的要求删改之后,又加以恢复的“本来面目”——与此相类,钱谷融原本只是称蘩漪的斗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18],在单行本版和文集版中,则进一步深化为“因为,在那样的时代,单纯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而不把自己的斗争与整个人民大众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是决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的”[19],显然也已将蘩漪斗争的悲剧性质究竟“成因”何在,予以更深入的点明。
此外,在其他单篇中也有对以往一些表述的修订,譬如在论周萍时,在初刊版中称读者看待周萍有一种意见是“对人物的阶级本质作简单化的处理,对他深恶而痛绝之”[20],但到收入单行本版和文集版时,则已改为“从他的思想本质出发,对他深恶而痛绝之”[21]。修改后的版本更加合乎情理,周萍之所以有如此言行,主要是出自其思想性格上的软弱与摇摆不定,而非阶级上的“优渥”。他在面对周朴园的霸权之时,不能勇敢地挺身反抗,却悄悄与蘩漪发生了关系;在面对鲁大海对周朴园的辱骂时,打了大海两个耳光,后又向他吐露秘密并求取信任;在面对四凤的哀求之时,他也不能当机立断,即刻就远走高飞,最终只得在得知真相后自杀而死。若说表现出这些言行的是来源于他的“阶级”本质,可是如他一般出身富贵的大少爷,却多有敢于反抗威严的大家长,勇于决断地追求爱情甚至投身革命之人,在文学作品中有觉慧,在现实生活中有殷夫,总之是均不乏其例。另外,钱谷融在谈四凤时,原本在初刊版中提到当时曹禺的“强烈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时,在括号里补充“这种思想感情同当时人民革命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21],后在收入单行本版和文集版时,则已改作“从揭露旧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感情同当时人民革命的方向在总的倾向上是一致的”[22],加了一个限定的角度,并补充了一个“总的倾向”,在这样的字斟句酌之下,使得其表述更为准确。
总的来说,《〈雷雨〉人物谈》从函授版到初刊版的改动是最大的,内中存在将教材进行大段的拆分,并重新写入各篇单独刊行的篇目之中,也基本上将因特殊年代编写教材,某种程度上“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均一一改去;从初刊版到单行本版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动,有的是如宫立先生所考订的,将原本应编辑部要求删去的部分恢复了原貌[23],也有的是进行了字斟句酌后的修正;从单行本版到收入文集版时,基本未作改动,但却为单行本版的《后记》补入了四条注释,值得一叙。
补入的四条注释,全是有关《〈雷雨〉人物谈》各篇在发表时的历史情况的补充。钱谷融在此中言明,当时将论周朴园和蘩漪的初稿一开始寄给了《上海文艺》,并交给了教研组,后受到教研组批判,《上海文艺》也不会用此稿了;自己的本意在于对周朴园伪善本质的揭露,但仍然受到“美化周朴园”“人性论”的指责;写周萍的一篇,当时同样受到教研组的批判;对于《〈雷雨〉人物谈》的诸篇文章能够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致谢,绝非客套之语,当时是等着挨批的戴罪之身,哪里还敢指望出版这些“罪行”[24]。
二、互动与增删:关于与《文学评论》
编辑部及读者之间的关系
依据《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的《编后记》来看,钱谷融此文在表面上似乎并未受到编辑部格外的“提请读者注意”。在此期刊物中,编辑部主要想强调的是其中几篇文章对一些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的解释,以及1962年希望多收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纪念杜甫并继承吸收其诗歌的艺术传统和经验的论文[29]。然而,《文学评论》从1962年第6期始,到1963年第5期止,在短短一年的6期刊物之内,“读者·作者·编者”的栏目中有3期均是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进行商榷的文章,分别是刊载于1962年第6期(此期12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数41021册),胡炳光写于11月4日的《读〈〈雷雨〉人物谈〉——和钱谷融同志商榷》,后钱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答胡炳光同志》作为应答文章;刊载于1963年第3期(此期6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数40378册),王永敬写于2月12日的《读〈〈雷雨〉人物谈〉后的异议——与钱谷融同志商榷》,此文已为研究者多所提及;刊载于1963年第5期(此期10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数39859册),楼昔勇的《引文不能削足适履——关于高尔基的两段引文与钱谷融先生商榷》,这篇文章似乎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另外的“读者·作者·编者”栏目一共仅有三期,两期有关鲁迅,一期有关文艺理论,可见钱谷融此文确是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瞩目,而与之商榷的文章也颇具含金量,至少在《文学评论》编辑部看来,具有值得刊载的价值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细读三篇“商榷”文章,会发现其中不少有关周朴园的商榷之处,其实是针对钱谷融先生依据编辑部的意见“补入”的部分而生。钱谷融在回忆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后的情况时说:
不久收到回信,说是准备采用。不过认为我在分析周朴园对侍萍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感情,会不会真正怀念她这一问题时,道理还说得不够充分,要我再加补充。于是我就又加写了将近一千字寄去。从本书第19页上的“阶级本质是渗透在具体的个性中”一语起,到第20页上的“只有更其加深了我们的这一看法”为止,这一大段文字就是后来补写的。[30]
这对钱谷融来说,或许多少有些委屈。原本是依照编辑部意见所进行的增补,而最终得以刊登,应该说是编辑部默认其已达到想要的“将道理说得足够充分”的效果。随后却一连刊载了三篇“商榷”之文,尤其后两篇的商榷之处,又多在于为此“要求”而进一步增补的“周朴园对侍萍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感情”。但这些文字毕竟是钱谷融亲自执笔写的,确实是在更深入地表达自己本人的意见,也就不能多说什么。然而,钱谷融对此有着潜在回应,尤其是对于最后一篇商榷文章,其文以钱谷融补入的两段引用高尔基的文本为核心,颇值仔细分梳。
钱谷融原本在初刊版中所引的两段高尔基的话,为:
正如实际上并不爱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可以本着极大的爱情来创造他的马尔麦拉多夫、喀拉马佐夫等人物一样,[33]这是并不矛盾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喀拉马佐夫等人的爱情,并不能推翻我们认为他实际上并不爱人的结论,而恰恰是——通过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更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结论。[34]
然而,钱谷融在60年代引用这两段与其文似乎不太相宜的高尔基的文字,却并非毫无缘故。或者说,他应该也并非由于在理解高尔基的观点时有错误,才不恰当地进行了引用。1957年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始,钱谷融已经受过数年的批判,必定已具备了对文章中潜伏着“危险”的敏感和小心,他或许是知道在自己补入并加以论说“充分”的这一大段文字中,存在某种日后可能会为自己惹来祸殃的意见,是以必须要援引两段伟大导师高尔基的类似说法,将此用作特殊年代的话语“护身符”,保障自己的“文身”乃至“人身”的安全——虽然残酷的是,即便如此小心,也未必能够如愿。到了1980年,却已可将这两段本就并无必要的引文删去。
仔细对读初刊版——也即放入了高尔基的两段引文的版本——和后来的单行本版与文集版,会发现确以后者为更佳。对于《谈周朴园》的论述而言,原本道理已论说得足够充分,将高尔基的话删去更显简练集中,也使整体的文本语言得到一种更为纯粹的“中土”质地。一般来说,钱谷融的行文节奏整体偏“缓”,常喜将句式相类的平白如话之语,以前后对偶之状成文,读来回环往复且摇曳有致,放入高尔基这两段西洋风味的话语略显突兀,无论是在义理的推进层面,还是在辞章的打磨层面,都并不能使其增色。如非是在特殊年代,为了以此“话语屏障”作人身保险,其实在谈说中国文学人物中的“典型”之时,原就不必刻意援引来自苏联的伟大导师的意见,批评家的“删去”之举,其实也是“复原”之举,如此“本来面目”,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自信与本土自信。
其实,说钱谷融在论述周朴园时,是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刻意地美化,确实是一种上纲上线式的冤屈,即便抛开“阶级”不谈,钱谷融对周朴园这“具体的人”也甚是憎恶。但总的来看,钱谷融的“爱人”似乎总是超过了“憎人”,在最早的函授版中,尽管在《雷雨》一节将其主要情节提炼为“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的悲剧”钱国荣编写:《雷雨》(第六章第二节),[35],后以此版情节概述收入《曹禺和他的剧作》。但在函授版《曹禺的生平和创作》一节中,对《雷雨》的情节所提炼的概述却是“在《雷雨》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塑造了蘩漪这个不幸的妇女形象,愤慨地描写了侍萍为周朴园占有与遗弃的辛酸经历,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冷酷与伪善”[36]。后者更能见出钱谷融在“尝味”《雷雨》之时所体会到的情感,见出他是如何地同情这些旧社会中十分不幸的女子,而周朴园既是一手造就这些不幸的罪魁祸首,那自然便会得到钱谷融的憎恨。不过,钱谷融对周朴园的意见,在1979年又有所变动,而其变动则是源于作家曹禺对《雷雨》的版本改动而来,此外,在《〈雷雨〉人物谈》本身的成型过程之中,又颇多涉及与作家曹禺本人的互动,值得深入研究。
三、交互与改动:
关于与曹禺之间的沟通与呼应
其实,《〈雷雨〉人物谈》系列文本的塑就,与作家曹禺的互动远不止于此。《文汇报》在1962年1月20日曾发表一篇钱谷融的《试说话剧台词》,此文对蘩漪和四凤之间的一段对话进行了精妙的分析。在50年代函授版的《雷雨》部分,钱谷融便已对这段对话能够充分地表现“微妙关系”表达了赏识之情[39],却在《试说话剧台词》之中,将蘩漪与四凤对话及神态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更为仔细地抽丝剥茧,这或许就是因读到之前《文汇报》上曹禺的谦虚之语,方才成就此文的。
在1962年1月10日的《文汇报》上,载有曹禺对《话语戏剧问题》的发言,曹禺很谦逊地说:
我很希望有人指导我们如何欣赏好剧本。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确实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如果有人为我们比较细致地指点出来,这会对我们有好处。[41]
曹禺并不很能明白自己台词的“精炼”何在,反而觉得臃肿,“希望有人指导我们如何欣赏好剧本”,并且曾说自己“不惯于在思想上用工夫”,这固然是作家的谦逊之语,然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也表达了作家的真实心声。作家在提笔写作之时,往往以感性居多,曹禺可能会模糊地感到若这样设计四凤和蘩漪的对白,应该会比较“传神”“有味”,但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知道究竟妙在何处,或说无法十分细致地分析出来,其中“妙趣”,尚还含苞而待点化。但钱谷融却能将人物一言一行背后的心境与意图进行仔细地揣摩,并在准确捕捉之后,十分精到地告诉广大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是曹禺与钱谷融二人的“合力”,才将杰出的话剧作品《雷雨》奉给了当代观众,以供后人反复细品其中佳妙之处。
此外,另有一处有关曹禺剧作“史实”方面的改动,与钱谷融和曹禺本人的往来有关。在50年代的函授版中,钱谷融曾提及曹禺导演过《镀金》[43],并在1979年的初刊版中在《镀金》后加括号补充这部作品为“(高尔斯华绥作)”[44],二版中均曾谈及曹禺翻译了《镀金》[45]。但到了单行本版和文集版时,又将曹禺对《镀金》的导演和翻译删去。
看似只是删去一两处细节,钱谷融在背后所花费的功夫却是甚深。1979年9月14日,钱谷融在给鲁枢元写信时就已道,有关1979年师大学报刊载的这篇文章“其中提到《镀金》的地方还是错的。最近我收到一份材料,据曹禺自己说《镀金》是一个法国剧本,原名《迷眼的砂子》,他曾加以改编而并非翻译。但已来不及改正,只能下期再声明一下了”[46]。9月20日,钱谷融又致信师大学报编辑部,内中道:
我在第三期学报上发表的《曹禺和他的剧作》一文中,谈到曹禺同志翻译并导演了高斯华绥的《镀金》。最近读到四川大学中文系陆文壁同志的《曹禺访问记》,才知道《镀金》并不是高斯华绥的作品,而是曹禺同志根据法国剧《迷眼的砂子》改编的。我已去信向曹禺同志作进一步的了解,请先将此信刊登。
此致
敬礼
钱谷融
九月二十日[47]
结 语
杨扬曾指出,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曹禺话剧《雷雨》的专著,也是享誉学术界的经典作品[49]。在钱谷融的百岁人生之中,其“文学是人学”的坚守从未改变,然而,这是“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宏旨不变,并非在具体理论与批评文本中固执己见。正如《雷雨》存在多次改版一般,《〈雷雨〉人物谈》在数十年间也经历了不断的修改,其中不仅可以见出批评家自身的意见改变,也可见出其与编辑部、同行乃至作家本人的互动。在现当代的优质批评文本成型的过程中,其实涉及多个方面复杂因素的共同合力,单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这一个案来看,就可以见到如下六种“版本流变”的形式:其一,随着时代变迁,批评家自身看法发生转变;其二,批评家依据刊物编辑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大段增补;其三,批评家吸收了同行的合理意见,将原来增补过的文字又删去了一部分;其四,批评家读到了作家修改后的作品,原先的意见发生改变;其五:批评家读到作家的自我评价,受其激发,将原来的意见“雏形”提笔改成一篇文章;其六,批评家依据作家确认的史实之后,更正了原先批评文章中的讹误。它们并存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之中,并最终将之塑就成型,对此个案的分析,不仅对于推进钱谷融研究、《〈雷雨〉人物谈》研究及曹禺研究颇具意义,也可见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在版本变迁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批评家、编辑部、读者、作家之间的多重“互动”及其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宫立:《“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宫立:《关于钱谷融和〈〈雷雨〉人物谈〉》,《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1期。
[3]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1959年。
[4]杨扬:《〈〈雷雨〉人物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
[5]杨扬:《〈〈雷雨〉人物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6]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29页;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雷雨〉人物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页;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7]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29页。
[8]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
[9]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2页。
[10]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107页。
[11]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5页。
[12]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110页。
[13]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5页;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
[14]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5页;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
[15]钱国荣编写:《雷雨》(第六章第二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45页。
[16]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17]钱谷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蘩漪》,《〈雷雨〉人物谈》,第33页。
[18]钱谷融:《〈雷雨〉人物谈》。
[19]钱谷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蘩漪》,《〈雷雨〉人物谈》,第37页。
[20]钱谷融:《“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谈〈雷雨〉中的周萍》,《文艺论丛 第7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98—99页。
[21]钱谷融:《“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谈周萍》,《〈雷雨〉人物谈》,第41页;钱谷融:《“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谈周萍》,《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136页。
[21]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四凤、鲁大海、鲁贵》,《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22]钱谷融:《“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谈四凤》,《〈雷雨〉人物谈》,第89页;钱谷融:《“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谈四凤》,《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178页。
[23]宫立:《关于钱谷融和〈〈雷雨〉人物谈〉》。
[24]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后记》,《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263—265页。
[25]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09年,第16页。
[26]李世涛:《“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访谈录》,《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
[27]宫立:《关于钱谷融和〈〈雷雨〉人物谈〉》。
[28]王保生:《〈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29]《编后记》,《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30]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后记》,《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第263页。
[31]王永敬:《读〈〈雷雨〉人物谈〉后的异议——与钱谷融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32]钱谷融:《〈雷雨〉人物谈》。
[33]此处原有注释:参看高尔基的《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34]钱谷融:《〈雷雨〉人物谈》。
[35]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6页。
[36]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28页。
[37]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四凤、鲁大海、鲁贵》。
[38]或可参见拙文:《“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重读周朴园兼及“钱门”解读史评述》,《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1期。
[39]钱国荣编写:《雷雨》(第六章第二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52—53页。
[40]在收入《曹禺全集》时改作“精炼”,此据《文汇报》原版。
[41]曹禺:《多读书,读透书》,《文汇报》,1962年1月10日。
[42]钱谷融:《试说话剧台词》,《文汇报》,1962年1月20日。
[43]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27页。
[44]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
[45]钱国荣编写:《曹禺的生平和创作》(第六章第一节),钱国荣、翟同泰编:《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下册),第34页;钱谷融:《曹禺和他的剧作》。
[46]钱谷融:《钱谷融文集·书信卷:闲斋书简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47]钱谷融:《来信摘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48]钱谷融:《曹禺先生追思》,《世纪论评》,1998年第4期。
[49]杨扬:《〈〈雷雨〉人物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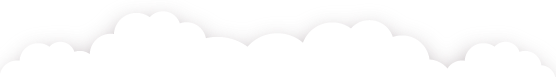
关
于
我
们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投
稿
须
知
《戏剧艺术》是一份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戏剧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内容希望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尤其期盼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来稿篇幅在万字左右为宜,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本刊实行在线投稿。在线投稿网址:
http://cbqk.sta.edu.cn 系本刊唯一投稿通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刊不接受批量投稿(半年内投稿数量大于1则视为批量投稿),更不可以一稿多投。
本刊审稿时间为3-6月,审稿流程含一审、二审、三审、外审等,最终结果有退稿、录用两种情况,其他皆可理解为正在审理中,敬请耐心等候。如有疑问,可致函杂志公邮theatrearts@163.com,编辑部将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附:《戏剧艺术》稿件格式规范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参考2020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① [专著]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② [期刊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③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④ [报纸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
⑤ [外文版著作、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芝加哥格式。作者名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同一页中的英文注释若与上一个出处相同,采用Ibid.的写法。若在不同页,英文注释的所有注项,包括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均不省略。芝加哥格式的范例如下:
有两位作者的著作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241-51.
有作者、译者的著作
Julio Cortázar, Hopscotch, trans. Gregory Rabass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6), 165.
有作者、编者的著作
Edward B. 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ed. Paul Boh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94.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Muriel Harris, “Talk to Me: Engaging Reluctant Writers,” in A Tutor's Guide: Helping Writers One to One, ed. Ben Rafoth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2000), 24-34.
期刊
Susan Peck MacDonald, “The Erasure of Language,”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58, no. 4 (2007): 619.
报纸
Nisha Deo, “Visiting Professor Lectures on Photographer,” Exponent, Feb. 13, 2009.
网络资源
Richard Kimberly Heck,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 last modified August 5, 2016, http://rgheck.frege.org/philosophy/aboutpgr.php.
6.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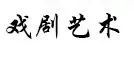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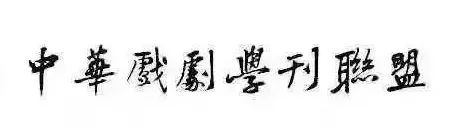

制作|陈婧
责编|计敏
编审|李伟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