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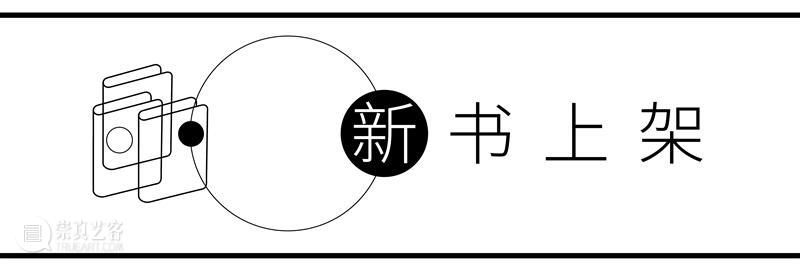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拜德雅图书工作室2023年的第7种新书、“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新品:《看的权利:视觉性的逆向历史》(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著,胡文芝 译)。
本书是2013年“安妮·弗雷伯格开拓性学术奖”获奖作品,是理解视觉文化研究核心概念“视觉性”无法绕开的著作,W. J. T. 米切尔对此书给出了高度评价:“《看的权利》是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杰作,它为这一新兴学科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本书现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美国视觉文化理论家,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和传播系教授。米尔佐夫是视觉文化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其专著包括《沉默的诗歌:现代法国的耳聋、手语和视觉文化》(Silent Poetry: Deafness, Sign and Visual Culture in Modern France, 1995)、《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Bodyscape: Art, Modernity and the Ideal Figure, 1995)、《视觉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1999/2009)、《观看巴比伦:伊拉克战争与全球视觉文化》(Watching Babylon: the War in Iraq and Global Visual Culture, 2005)、《如何观看世界》(How to See the World, 2015)等,其编著包括《视觉文化读本》(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1998/2002)、《流散与视觉文化:表征非洲人和犹太人》(Diaspora and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Africans and Jews, 2001)等。

其《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一书中译本也是由我们推出的,同样收录在“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之中。
今天给大家推送本书的前言(注释从略)。此外,文末还附上了本书的编辑推荐、名家推荐、内容简介和目录,供大家参考。
- 前言 –
不可避免的视觉性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所说的“不可避免的视觉性之不可避免的形态”。这一典型的乔伊斯式用语不禁让我们停下来思索:视觉性为何不可避免?又是谁使其不可避免?该用语是对书中出现过的用语“可见事物之不可避免的形态”的重复,但又有所不同。这两个用语都出自《尤利西斯》的《普罗透斯》(Proteus)一章,是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清晨在海滩上的内心独白。那么,视觉性虽不是可见的,但却是不可避免、无法回避、必然要发生的。简言之,它与当前的流行术语形态(modality)一样,也并不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乔伊斯把视觉性(visuality)与古代不可避免的(ineluctable)事物联系起来,将我们推向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其背后的渊源是亚里士多德,它与迪达勒斯在哀悼母亲并寻找“大家都晓得的字眼”时对生死之间的“隔阂”的忧虑非常契合。因此,视觉性并非可视之物,它甚至不是一个社会事实,这和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的设想南辕北辙。视觉性也不是那种恼人的新词——书评家眼中的合适的靶子,因为——正如乔伊斯可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该词在1840年就出现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一位现代性和各种解放运动的抨击者——的作品中,成为官方英语的一部分。正如卡莱尔本人所强调的那样,英雄(Hero)的视觉化能力不是创新,而是“传统”(Tradition),在帝国主义的卫道士眼中,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要厘清使视觉性不可避免的这种悠久传统和权威力量,理所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那个故事,那个盎格鲁-凯尔特人(Anglo-Celtic)(卡莱尔是苏格兰人)所暗示的关于帝国主义想象的故事,我们在此提供了它的逆向历史。
在试图接受视觉性的不可避免的特性时,我一直想给近几十年来发生的针对景观社会和图像战争的抵抗提供一个批判性的谱系。反过来,这个谱系将为所谓的视觉文化的批判性工作提供一个框架,这并不是因为历史化的方式总是好的,而是因为视觉性有着广博而意义重大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本身也是西方史学形成的关键部分。更确切地说,视觉性及其对历史的视觉化是“西方”对自身进行历史化处理并使自身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方式之一。在这种观点下,视觉文化在学术上所代表的“视觉转向”(visual turn)本身并不是一种解放,而是试图利用其优势,开展视觉化权威的部署。在建立这一谱系的过程中,我跨越了多个“边界”——从字面意义上说,我跨越了不少国界,涉足了三个大洲、两个半球,只为寻找档案或其他研究材料;从比喻意义上说,我跨越了区域研究、历史分期和媒介历史等多个离散的学科。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视觉文化明显缺乏决断,这是对该领域的早期批评之一。但随着视觉文化领域的一些主要书籍的出版,比如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的《图像何求》(What Do Pictures Want?,2005年)以及已故的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的《虚拟窗口:从阿尔贝蒂到微软》(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2006年)等,这些反对意见现已销声匿迹。在本书中,我希望追随前人的脚步,为这一领域建立一个相对去殖民化的框架。促使我这样做的是我在研究伊拉克战争,即撰写《观看巴比伦:伊拉克战争与全球视觉文化》(Watching Babylon: The War in Iraq and Global Visual Culture,2005年)一文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一些问题。那篇文章我写得很仓促,而且可悲地误认为伊拉克战争会是一场短暂的冲突,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一种矛盾现象,即战争产生的大量图像对公众的影响相对较小,我称这一现象为“图像的平庸”。即便是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那些令人相当不适、足以挑战这一观点的照片,也没有对公众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这些照片也未被提及,监狱长级别以上的军事人物随后也没有受到处分:事实上,导致阿布格莱布丑闻的指挥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提拔。与新闻摄影的传统和其他视觉启示形式相反,视觉性似乎已经成为权威的武器,而不是对抗权威的武器。为何这些令人震惊的图像对公众的影响如此之小?为了弄清楚这一显而易见的难题,我必须将它们置入我在此描述的谱系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并非想把实体化的视觉化简化为代码。相反,在我看来,W. J. T. 米切尔在1994年提出的著名主张,即各种视觉材料与印刷文化一样复杂且重要,其中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视觉图像本身就是一种档案。在不扩大讨论范围的前提下,我所遇到的这方面的跨界问题可以被视作所涉及的问题的例证。在许多源自大西洋世界的种植园复合体的例子中,我使用了图像——有时甚至使用了对有些图像已经丢失的认识——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当我借助被奴役者、曾经的被奴役者、属下阶层或者殖民地臣民等群体进行推论时,除了依托视觉图像,我通常无法获得文本支持。因此,我对这些图像的风格、结构和推断进行形式化分析以支撑我的论点,这一方法在西方正典以及其他作品中很常见。我还要声明,在本书中,我会建立更为广泛的历史框架去加强这种解读,正如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当然,我未必正确,但是如何使用视觉档案来为这类属下阶层“发声”并“讲述”他们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说明,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比如,如果在波多黎各不允许正式使用这种视觉档案,那么我希望在罗马也不允许。如果这无法实现,那么在方法论上哪种反对意见会在一个地方有效,却在另一个地方无效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通常来自艺术史领域,在那里,归属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我并不认为本书是艺术史,我认为应该将它视作媒介和中介化的批判性阐释的一部分。书中应用了米切尔所称的“媒介理论”,所有双关语也都是有意为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视觉性既是传递和传播权威的媒介,也是对那些受制于权威的人进行中介化的手段。
本书的正文部分将向读者证明这些主张是合理的,当然,也有可能事与愿违。在此,我想指出一两个读者可能无法意识到的遗漏。我在本书中使用了权威的传统,以之作为框架来囊括全书的内容。起初这一传统对卡莱尔有所启发,之后直接或间接地由他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这是英法帝国计划(the Anglo-French imperial project)的谱系。该计划发起于17世纪中叶,主要针对种植园殖民地,之后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1789—1804年)的爆发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历史问题流传到了美国,一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二是因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卡莱尔进行了改编,出版了《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1850年)一书。虽然一些学者可能会质疑帝国计划的广泛影响力,但它过去曾是(现在也是)一个关于经验、干预和想象力的思绪活跃的领域。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效仿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的17世纪的论著,称之为“大洋国”(Oceana)。另一方面,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领域可能还不够深入。我认识到这个英法美的“想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与西班牙帝国格格不入,在一组来自西班牙语美洲(Hispanophone Americas)的“对比”中,我做了如是表述。这些部分涉及各种形式的视觉形象,这并非因为我把西班牙帝国构想“成”一种意象,而是因为这或许在我的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范围之内。我冒险用这些帝国主义相互渗透的短暂时刻来表明我的看法:一个有前景的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共同探索这种全球化的视觉性的交叉点。虽然我无疑想把研究的区域延伸至南亚和东亚,但以自己目前的能力范围,我并没有把它们写进本书。当下,我认为本书只是一个长期项目的第一步。那么,把当前的这本书看作几本书的综合是否不够慎重?毫无疑问,对于我在此描述的每一种不同的视觉性复合体,我都能写上一本书。如果我在这里所提倡的批判性分析模式能够成立,那么——无论出自我自己还是他人之手——这一领域必然能增添不少书籍。在此,我认为有一点相当重要,即我需要确保这一框架的整体性,对其加以足够详细的阐述,使其轮廓清晰,同时保留日后修改的可能性。另有人建议我针对该主题写一个简介即可,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优先考虑当前的出版时尚,而不是为了持续论证——我不明白,如何能用当今十分流行的百来页的“极短”体例来认真开展对现代性的重新评价呢?至此,本书尚未涵盖的内容和实际呈现的内容(虽有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一目了然。
编辑推荐+名家推荐+内容简介+目录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