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姿态之争,图像之斗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文,大卫·马鲁泽拉 英译,Shun 中译,
选自The Nordic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27 No. 55-56 (2018)
感谢无空间 WU SPACE 授权转载
这篇文章为一种关于“起义 [soulèvement] 姿态”的人类学提供了些许注释。本文认为,如同声音(叫喊、话语、口号)从示威者的口中发出,各种各样的图像也是如此在他们的手臂末端挥舞。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关于“起义之欲”这种概念自身的问题。
让我们从一种假设开始:图像与姿态——这两者在瓦尔堡所提出的“情念程式 (Pathosformeln)”概念中是统一的——它们在冲突、对抗、苦痛与情感中发挥着范式性“接口”或者说是辩证性枢纽的功用 [中译注:“情念程式 (Pathosformeln)”又译“激情程式”,是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创造的术语,它与对瓦尔堡产生深刻影响的尼采的“日神-酒神”学说有紧密关联,所谓“情念”涉及到一种有关表达的强度与极性,而“程式”则意指向一种经年累积的结构,“情念程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心理学层面的概念,是一种理解图像本体性意义的方式]。我将以“起义”的情形作为例证,在政治与社会历史的世界中,显而易见的,“起义”既是冲突亦是对抗,既是苦痛亦是情感。
人们前赴后继地奋起反抗。无休无止的起义:是因为他们会倒下,他们会失败,他们被因循守旧的传统所击溃,他们遭遇到与执法部门的直接对抗。无穷无尽:是因为最终的目标——万事平息,和解达成,欲望终于满足——永远不会实现。但同时这欲望也从未曾减退,与之相伴的,还有违拗的勇气,创造的驱力,“不如此行事”的力量,以及为自身进行重新主体化的能量。通过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显示出的这种丰富的多重性,总和纵观,“起义”因而得以形成伟大的政治艺术,形成无尽的冲突与对抗,苦痛与情感。这既涵盖着它们在构成意义(constitutive)上的脆弱性——或者说是宪定层面(constitutional)上的脆弱性:在权力面前无法定义自身的脆弱性——也涵盖着它们恰恰由此而来的无限潜能。火山激浪之潜能,尘埃浮涌之潜能,飓风过境之潜能。
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结的,“奋起”也许直接地意味着一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的能力。重新开始,不论代价几何,无尽地、无穷地重新开始。这将会是使得一个主体重生的能力,使得它再次行动起来,以创造出令人们不再感受到屈从的生命姿态与生命形式。与此同时,我再次重申,我们会永远不停地开始,不断重新开始,持续地奋进并抗争。在《无以称名之人》(The Unnamable)中,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他那分裂的表达“我必须继续,我不能再继续”之后,不正是以“我将继续”终结了他内心的争论吗?这句话不正是意味着:“就在所有人都向我说不的地方,我将不顾一切地继续尝试、努力、渴望、言说、证实、创造,对‘不’说不”吗?[1] 我们忍耐了那么多,直到某一天,我们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束手就擒。然而,再一次地——正如我们时而能够做到的那样,正如在我们之前的人们常有做到的那样——我们将手臂举过双肩,这肩头仍为异化疏离所烙印,仍为笼罩至今的痛苦、不公和积郁所负累。现在是我们振作起来的时候了:我们将双臂举向空中,向前。我们张开,不断张开我们的嘴。我们哭喊,我们高唱我们的欲望。我们与友人探讨着这一切该如何行事。我们想象,我们前进,我们行动,我们创造。我们从冲突与对抗、苦痛与情感中奋袂而起。
所有的手都举起来了。就像《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中水手们的手臂那样,当他们第一次做出不服从的姿态,他们举着盖过头顶的白布,它意味着可怕的死亡。就像籍里柯所绘的《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中遭遇海难的手臂寻求着希望,呼喊着救援。就像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名作中的自由女神的手臂,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前哨阵地举起旗帜。就像让·维果(Jean Vigo)的《操行零分》(Zero for Conduct)中孩子们的手臂,他们把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都从学校的屋顶上扔下去。又或者,像是戈雅画中那些流民无产阶级的手臂,仍在寻求着该以何种方式抒发他的绝望与他们的愤怒。在一幅现藏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美术馆的画作中,戈雅描绘了类似于《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的大屠杀场面。这是一场空前暴虐的大屠杀:权力(手臂[arms] / 武器[armes]之力)之能力得以杀死所有的力量 [puissance] (尤其是一位女性的力量,她位于画面的左边,张开双臂,她的面孔完全掩蔽在棕褐色的墨迹中,在我们的想象里她便是如此地被她的悲泣所淹没)。

Francisco de Goya, The Disasters of War, 1808-1812
commons.wikimedia.org ©
在更高处,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山上——无疑ta的身影对我们来说只能看得出基本轮廓——ta将双臂举起。在整个画面中,这是一种面对着山下正在展开的暴行的绝望姿态,是一种朝向画面外的最终拯救者的求助姿态,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超越了——或者说贯穿了——所有复仇诉求的悲戚的诅咒姿态。就像是在那幅著名的《1808年五月三日》(the Third of May)中被行刑的那个人,他也是那样地将双臂举起,与其说这是孤立出现的人物的心理意表,不如说这是一个有关于识别画家赋予整幅画作的意义方向的问题:事实上在这样的场景中,它是无名之人面对奴役着、屠杀着他们的武装权力而奋起反抗的力量。毫不意外地,我们在《格尔尼卡》(Guernica)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毕加索笔下的人物那样有力地挥舞着他们的手臂,他们的眼睛和嘴也以同样的动势舞动着,使得他们的身体无论是伤痕累累还是被推倒夷平,都能继续以一种独立的力量回之以疾呼,在“悲恸的死亡形态的煎熬”与“动态的、矢量的生命象征”这二者间构成的恒定辩证之中再次崛起。
这即是历史的无限:积郁与爆发,激流回冲的逆潮,被忽然突破的边界,亡损伴随着起义,所有这一切都无休无止。在这一切之中的,是身体,和它们的姿态,它们的想象,它们的语言,它们的再主体化,它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行动——作为浪潮中的小舟,作为一种政治的媒介,借此,一种后退的动势将会为回冲的激流让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总是以其永恒注定的显现而不断“上演”着,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著的题为《政治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Politics)的文集中以及艾蒂安·塔辛(Étienne Tassin)随后问题重重的评论中都有涉及到这一点。[2] 因而,此种“上演”超越了人们所熟知的政治寓言——或者说实际上是落后于后者,因为它是这样司空见惯,并在多重层面上具备着密切性、弥散性和多形态性——比如所谓的“人民大会”或者是以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为代表的19世纪的创作中常常出现的“自由之躯”形象 [中译注:此处“大卫”指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自由之躯”不仅仅是一种表征,它也是一种有关于对抗、在场、或是说“呈现”的姿态,包括它那公开亮相的时刻,我们用法语恰当地称之为“manifestations [显现/抗议]”(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词翻译成英语中的“demonstration [示威/抗议]”就显得有些拙劣了,因为它的意思过于据理力争)。[3]
在“manifest [显现/抗议]”中,首先是要有“mains [手]”,双手很快地将自身和整个身体武装 [arms] 起来。在拉丁语中,“manufestus”是指一个人“被抓住手”,意思是“被当场抓住”或者说“被抓现行”。它是社会规则的显见违背者,是“manifestatio [显明]”,因而指向所有“表露出来的 [s’expose]”,所有冒着风险的——且根据“表露出来”和“冒着风险”的双重含义,也就确实有违法乱纪的意味——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显现的 [manifest]”或是违规的,作为对秩序的有力反抗。“显现/抗议”因而就是“想要宣告自身欲望”的欲望,进而在行动上,或更确切地说在切实具体的姿势层面上它即是“不服从”。令人讶异的是,如同文森特·罗伯特(Vincent Robert)在他的著作《抗议的方式》(Les Chemins de la manifeations)中所表明的那样 [4],在欧洲有关政治抗议的社会谱系中,是葬礼、行进队列、以及传统节日构成了抗议集会或抗议游行的人类学母本模型。因此“显现/抗议”就是“把控欲望”:将亡损转化为一场起义,将积郁的凝滞转化为流动的行动,将麻痹的恐惧转化为自主的前进,转化为解放的姿态。有众多例证与此相关,其中,在保罗·尼赞(Paul Nizan)1983年的小说《阴谋》(The Conspiracy)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送葬队伍的描写:
大道上人潮涌动:有从边远地区来的工人,还有从人口稠密的城市东部及北部来的人们;他们占据了两岸之间的马路,河流终于涌动起来…这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强劲蓬勃的力量,气力流动,河流奔袭,血液涌动。这条大道在此刻配得上“动脉干流”之称…静止的人不再抗拒行动的人,观者不再抗拒奇观,静默者不再抗拒高歌者;他们走下来感受河水的涌流。拉弗格、罗森塔尔和布洛耶尔放下了对传统的遵从,他们也投身其中,开始歌唱。[5]
当然,在一场抗议中没有任何事会如同预期那样发展:在事件的偶然即兴、历史的未尽无限、对立力量的关系中,一切都是悬置的。然而,这是一场几乎总是以一种“古典”方式上演的戏剧,以其对于时空的统一,让街头或是场所承担着作为主舞台的功能(另,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以“作为舞台的街头”为题)。以法国为例,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丹妮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等历史学家展示了关于“集体行动的策略传统”的演变 [6] [7],从“旧制度时期”的生计暴动及“粮食抢夺”开始,一直到当代的罢工运动、选举集会和其他的街头抗议活动。实际上,我们是依据着不同的公共表达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组织结构进行抗议的:比如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范式——我们须要冲破监狱/堡垒(巴士底狱)——或者是工人运动的组织章程。
就如同之前的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或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一样,保罗·尼赞的描写既是喻意式的(行进中的人群在《国际歌》的歌声中凝聚起来,“革命的气力及命脉”随之高涨)也是形态化的:在这一刻,这条大道“配得上‘动脉干流’之称”,人们最终以一种相同的流动动势在这里循环流通,紧凑而有力。冲突和对抗中的所有一切都关乎于动力形态学,这在针对政治表现之现象的历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印证,包括了从皮埃尔·法夫勒(Pierre Favre)到奥利维尔·菲利略(Olivier Fillieule)的著作 [8] [9],还有关注城市暴乱的阿兰·贝尔托(Alain Bertho)的著作。[10] “抗议”随之便显露出了它在不同方面、在进程以及辩证逻辑上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尤其发生在“抗议”的设置与爆发之间——但凡这“抗议”既归属于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又同时是一种治安警力不仅会试图镇压,甚至还会通过一切可能手段预见并剥夺其合法性的激进的异见行为、一种未经预期的斗争行为。
这些力量所上演的戏码是通过它们自身显现出来的:它们直观地出现在街头,出现在公共广场,在这一点上,如果不经过观察——准确地说,如果不经过一种针对于整体的感知空间的触觉的、声音的、以及视觉的人类学——它就是无法被理解的。一方面是对抗性的过程(出场,就意味着产生接触,也就意味着,争斗),另一方面是激情洋溢的投身参与,或是说深度交流;呼吁的空间伴随着抗拒的空间;希望被理解的欲求伴随着不被理解的感受;“执法机构”伴随着一种与之相对的“执法”行为,后者不仅仅旨在镇压“不当举动”,更是要完全扼杀这类现象本身,而这种扼杀所依据的规定在绝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基础性公共自由的侵犯。随之可见的是,在一种对于政治表现的有力拒绝之下,“抗议”投入了一种以视觉为代表的感知空间:它催生了一种政治表达的出现——用“直观”这个词来形容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它总是借由它的路径选择、口号标语、图像标识、以及或多或少的强制义务行为来进行调介——这种政治表达从根本上挑战了先前既定的政治表现形式,无论是议会或是工会。
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们常常会发明出原创性的手势、歌曲及图像:这是他们自创自制的艺术。手臂高举,但不仅仅是为了像在传统的议会集会中进行投票那样。嘴巴大张,语言消散,但不仅仅是为了宣告狭义上的政治观点。我们行走,我们舞蹈,我们奔跑,我们以姿态示意,我们投掷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我们聚拢,我们散开。我们高歌,我们挑衅。我们为狂欢式存在的回归保留下了一个位置——在今天,这狂欢是声称要将社会彻底颠覆的庆典——就像是库巴·马穆鲁克(Kuba Majmurek)、库巴·米库达(Kuba Mikurda)、雅内克·索瓦(Janek Sowa)在“团结工会运动 (Solidarność)”背景之下所揭示出来的 [11],以及罗西奥·马丁内斯(Rocío Martínez)通过墨西哥恰帕斯的相关史实而阐明的那样 [12]。
身体在冲突、对抗、苦痛与情感中运动。现在,任何抗议的身体都可以被视作“自由之躯”——实际上,德拉克洛瓦就是从被我们称之为行进的“胜利”的古典女神形象中获取了这种动势的灵感。每一具抗议的身体不就像是一艘巨轮的船头那样跟随着它前行吗?这个船头本身还拥有它自己的破浪神:那“挺身而出”的正立面,和“欲望灼烧”的双眼。通常来说还有“嘴”,嘴作为“动物的开端,或者说是动物的船首”,正如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文献》(Documents)中写到的那样:“在一些重要时刻,人的生命仍同野兽一般地聚焦于嘴:愤怒使人咬牙切齿,恐怖和凶残的痛苦使嘴变成发出刺耳尖叫的器官”——所有这些都与那种类似于银行职员一般的表情截然相反,后者带有“一种严苛的人类态度的逼仄板结,道貌岸然的面孔,双唇紧闭,显现出有如一座保险箱似的美感。”[13] 张大的嘴是为了要高喊、呼吁、逾矩,不论它是否借由皮埃尔·费迪达(Pierre Fédida)在其著作《人体之始》(Par où commence le corps humain)中所讨论的、由巴塔耶所开启的那种“回归”进程而实现。[14]
“自由之躯”便如此前行,以嘴在前。张大的嘴高喊激昂的口号及不可替代的诉求。在这个时刻,我们再次看到,高举的手臂:就好像是这些抗议的身体,通过显露在外,向世界敞开了自己,并想要通过它们挥舞的手臂,它们那向前挥出的手臂,将这世界打开。然而,没有什么有关人类的东西——也就更不用说政治了——是不归属于组织架构的一部分、是能够免于调介的。正如伊曼纽尔·苏特侬(Emmanuel Soutrenon)和多米尼克·梅米(Dominique Memmi)分析的那样 [15] [16],抗议的身体永远处在“表达”与“表现”之间,这并不妨碍图像抑或是其他任何类似的事物被用作为质询的媒介,被挥舞在手臂的末端,在一个“起义”的感知空间中发挥它们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要问:在举起的手臂末端有什么?是什么东西会被这样的手臂举起、高高托举、投掷抛出?
先是它们的手,再是它们的拳头。回想一下,在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敖德赛人的拳头因为一位水手不公的死亡而被激起反抗,怒不可遏,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战,再一致地将拳头举起以示抗议,此时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众人一起举起的拳头,从那时起,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诉求鲜明的姿态象征。早在电影《罢工》(Strike)中,朝向天空举起的双臂和张开的双手就仿佛是在宣告着它们对解放的渴望。几年之后,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攥紧右手———这是一种激烈的标志——向着圣热尔韦聚集的人群慷慨激昂地演说,左手紧紧握住那飘扬在他上方的旗帜。他就像是反军国主义版本(这也正是他当时演讲所传达的理念)的《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画中的“自由女神”右手挥舞着旗帜,左手持着刺刀步枪,这样的形象我们在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于1848年“民族之春”革命时期为《民众之安》(Le Salut public)所创作的版画中也能看到。

让·饶勒斯 (Jean Jaurès)
politika.io ©
1938年,威利·罗尼斯(Willy Ronis)在巴黎贾维尔的雪铁龙工厂的鞍具厂房里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一名妇女对着她的同仁们热烈地演讲着。在嘴的终结处,是她向外伸出的手臂。在她手臂的末端,是她指向外部空间的手指。她手里拿着一小张纸。她鼓动女性劳动者们争取她们的合法权利,并为此在那一天进行罢工。正如威利·罗尼斯所见,她正在讲述着由“劳工统一联合同盟 (CGTU)”所领导的“与西班牙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行动,她是CGTU的一名激进成员。她的名字叫罗丝·泽纳(Rose Zehner)。在这场罢工结束时,她遭到解雇遣散,从始至终没有收获到公众层面的认可,直到这张照片终于在1980年被发表刊出;当年这张照片因为曝光不足而未能发表在原定的共产主义杂志《致敬》(Regards)上。似乎在任何情况下,伸出的手臂都与起义的演说相生相伴:当“起义的演说”事关于围绕着某种特定的政治事业而将一个群体聚集起来时——正如它在这里一样——伸出的手臂将它延展,并将它扩散开来。此外,伸展的手臂还凝聚着许多其他行动:它将空间朝着其他的所在开启,它是身体的呼喊,因此,它能够将那些理应“怨声载道”的人们重新主体化,形成为一个能够集体地在公共空间中“诉怨”的群体。

1976年的女性主义抗议活动场景,
塔诺·达米科(Tano D'Amico)摄,tidsskrift.dk ©
在这个意义上,罗斯·泽纳的姿态——以及广义层面上的女性社会活动者(pasionarias)的姿态,从尼科洛·罗霍(Nicole Loraux)研究中的希腊历史中“母亲之哀痛”的悲剧性爆发,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在马德里、费德丽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在巴塞罗那等地著名的激昂宣讲——借由另一个非常简单、但却极其有力的姿势寻找到了它的当代性延续,这个姿势源于19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者们的(重新)创造。正如劳拉·克拉迪(Laura Corradi)提到的,这个手势“属于聋哑人使用的手语:张开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L形,然后两个拇指的末端和两个食指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是阴道的标志,它被应用于我们国家 [意大利] 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抗议活动中。但它实际上是源自古代早期的一个标志” [17],至少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因而它是经过了重新挪用成为了反叛的标志,成为了一种在政治与公共的再主体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女性之性的形象。
伊拉里亚·布索尼(Ilaria Bussoni)将它恰当地称为“自我实现的姿态”。[18] 女性因此而团结起来,在她们手臂末端及自身面前,显露出这样一种姿势化的图像,它所代表的既是她们身体构成中最为亲密的要素——那里是欢愉之所在,但在遭受到男性狩猎所带来的物化和控制时,那里也是共同苦痛之所在——亦是对于她们重新夺回性自由、对性别作出决议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很有助益的再主体化,一种创造出来的“新的性”,正如伊拉里亚·布索尼提及的那样,它从这些女性的双手之间突然地显现于公共空间之中。性的姿态:多么美丽的悖论!这个姿势将不再会是一种升华了的“拥护信奉”的姿势,“完满”而“笃信己见”的,双手直立举起,拳头握紧或是用手比作枪的样子瞄准敌人,就像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这个姿势是一种欲望的姿势,指示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了每一位女性的内心,同时也开放朝向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世界以它自己的方式解构并重构着。这个姿势形成了一个正面(因为这个手势是朝前的),同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通道(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开口)。借此,它标志着对于一种“裂缝”——或者说是一种新的辩证关系——的确认,这道裂缝存在于我们划分主观世界与公共世界、欲望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惯常方式中。
如果说这个创造于1970年代的手势会使人联想到拉康为所谓的“punch”关联而选择使用的菱形符号,这也许并不是无端偶然,在拉康所称的“基本幻想 (fundamental fantasy)”之中,这个符号被用于在主体和欲望客体之间建立或断开连接 [中译注:在拉康关于“幻想”的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a”,其中“$”意为“被符号界所分割的无意识的主体”,“a”意为“欲望之客体-原因”,中间的菱形符号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拉康本人以多种方式表达过这个菱形符号,其中最为常用的是“punch (le poinçon)”,可用“冲孔”作为中文试译;然而就这个符号的涵义来说,它可同时表达4种不同的涵义(与菱形的四角四边形状有关)。中文语境中多见以“主体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来简略概括这一公式,不对“◇”的意义做单独概括]。他在1959年的专题研讨《欲望及其阐释》(Desire and its Interpretation)中说到,此种关系“是确保了支撑欲望的最小结构”。[19] 在这里,这个“最小结构”已经变得复杂化,且必然是辩证性的:它“本身是复杂的,因为在它与‘幻想’的第三种关系中,主体将自身构成为欲望。”[20] 因此,正是这一点使得在之于客体、之于实在的关系中,“主体于主体未能之处现身” 。[21] 这可以作为一种理解女性主义姿态的补充视角:它是一种给定的形式,被肯定的,被提出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破裂的形式”——欲望所内在固有的,正如拉康随后进一步阐述的那样,这种关系从根本上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主体都不是单独的一者。”这就是女性主义者用她们自己的方式向公众所主张的。这种“Punch的姿势 [◇]”因而就是一种既割裂又连结、既分离又聚合的手势。这是鲜明的“分-享 [partagé]”的姿势,从辩证意义来说,这个词 [partagé]——在欲望的结构上,亦是在政治的结构上——呈现于“反抗的形象”和“希望的形象”二者之间。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在我们所谓的“女性主义视觉文化”之中,在诸如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瓦莉·伊克斯波特(Valie Export)、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以及海伦娜·阿尔梅达(Helena Almeida)等艺术家们意义深远的作品中可以得见。

瓦莉·伊克斯波特(Valie Export),《自然的几何速写 II,手形》,
1973. valieexport.at ©
在我们举起的手臂末端会有什么姿势?满怀希望的身体依然双手空空。奋勇反抗的身体寻找着另一只手,以抓住它自己的手,将它的行动延伸。当它不得不放弃并遭受责难的时候,它会再次将双手挥向世界、挥向未来的时代——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反抗姿态。身体被举起,以一种更为明晰而愉悦的方式承载着自身。但这种延展、身体的前行,所依仗的策略和手段是什么?一种永无止境的创造力回应了这个问题,一种关涉着写作、图像与客体的伟大的无限创造。在必然涉及暴力抗议的冲突中,这种创造力即是弹弓、燃烧瓶、鹅卵石,或者实际上也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块石头。在内战或是占领战争的极端情况下,就像戈雅在《战争的灾难》中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创造力即是一只未经世事的手,一只女人的手,当她的身边已是武装斗士的尸山血海,她的手仍不怯于用火炮武装自己。奥利维耶·菲利略为其著作《街头策略》(Stratégies de la rue)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从法国国家警察中央总局获取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张白色毯子,毯子上摆放着从1977年“克雷伊斯-马尔维尔起义”中收缴的物品——弹弓、金属螺母、焊条——作为战利品展示出来。[22]
非暴力的方式则更具创造性和多样性,因为这种方式关乎于借由最为微小的事物而举起双臂、做出手势、制做标志及创造图像。毫无疑问,在抗议者们前方的横幅标语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他们言说。菲利普·阿蒂埃尔(Philippe Artières)对此进行了很有意义的研究,并同时将其简化为“暴露性写作”这一单一维度。[23] 在这里,“标语”既是一个可见的表面,也是一个可读的表面:它可以说是一个“旗帜系统”的一部分,这类系统常常充斥在抗议所发生的感知空间。它通常是比喻修辞式的。如果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能够孜孜不倦地环游世界,极尽可能地拍摄抗议者们的游行——这毫无疑问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历史面前无所终结的艺术——那么在他看来,“身体与标语之间关系”就会是一种作为社会生活典范的人类学形式,每个人都在所有人的起义中、在所有人的眼中行进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于像1968年的学生集会那样,为了言说,或是为了向游行的抗议者们指出他们要走的道路而伸出我们的手臂。在举起的手臂末端有这样一些图像:那里有旗帜,往往是抒情诗意且幽默俏皮的,和大幅的风筝差不多大小;那里有充气气球,有时它相当巨大令人讶异,会让警察对此不知所措;那里会有我们用来敲敲打打的锅盖,不过它们也同样充当作盾牌的形象;狂欢嘉年华式的结构七拼八凑,看上去就像是节日的战车(比如说就像2014年伦敦V&A博物馆的“不听话的物件 (Disobedient Objects)”展览中,展出过一个自行车扩音器,还有一个用巨大弹弓弹射的稻草熊);还会有面具和伪装,比如像是女性主义者或是“Act Up”组织所采取的“zap”类的行动,这一点在1998年维克多利·帕克托维拉德(Victoire Patouillard)发表于《当代社会》(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研究 [中译注:“Act Up”是一个成立于1987年的旨在以行动应对艾滋病危机的社会活动组织,“zap”是该组织的活动方式之一;“zap”最早源于1970年代的同性恋权益促进抗议活动,其特点是直接、激进、针对特定的对象并快速引发公众反应]。[24] 在这些假面舞会中,似乎须要有一种“笑声的政治”的复苏,它从往日的讽刺诗歌及讽喻漫画中沿袭而来,或者说这实际上就是“疯人的节日”的再度重演,福柯曾见证了这样的节日,并指出了它们背后深刻的亵渎意味。

伦敦V&A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 “不听话的物件 (Disobedient Objects)”展览现场,2014.07.26-2015.02.01。vam.ac.u ©
这就是为什么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退伍老兵们会如此耐心地缝制那些象征着他们形象的织物,细心地制作那些融合着传统与政治宣传的人偶娃娃。各地各处的反抗者们都在制作着图像,展示并传播着它们。引人注目的是,在1968年5月,活版印刷机、平板印刷间还有丝网印刷机都在满负荷运转着,摄影师和电影制作者们也在并驾齐驱地活跃工作着 [中译注:此处指1968年5月法国的“五月风暴 (May 68)”事件]。四年后,“马拉西斯合作社”的画家们被迫使用他们在一次展览上的作品作为象征性的横幅旗帜和随手抄起的盾牌——这些画作源于一场由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总统所委任承办的非常官方的展览,艺术家们决议放弃了它——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群时下不知道该归罪于谁、该 [宣之于口地] 谴责些什么的警察。艺术家们也会抗议,他们的抗议也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创造。
从这里可以看到视觉标识与“抗议主题色”的大量出现:比如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所谓的“黑衣阵营” [中译注:“黑衣阵营 (Black Bloc)”指各地抗议运动中出现的以黑衣黑帽、摩托头盔、护目镜之类作为装扮的活动者,他们的主张多以无政府主义、反全球化主义为主]。因而也随之出现了生产着激进社会活动者的T恤、胸针之类的类似产业。但毋庸置疑地,最为触动人心的是抗议者们挥舞的大幅图像,它们所代表着的那些人们,我们哀悼着他们的销声匿迹,我们为他们伸张正义:1962年,在巴黎为夏罗内的死难者所进行的送葬游行就属于这样的情况(这次游行同样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镜头记录了下来),还有1983年的阿根廷为[“肮脏战争”期间]“遭受失踪”的人们进行游行的悲情时刻,以及同年,在争取平等的游行中,游行队伍的前排展示着那些被法国警察所暗杀的年轻北非民众的肖像。
甚至哲学书籍和文学作品也可以被用作图像和抵御警力的盾牌挥舞起来,“书籍阵营 (the Book Bloc)”所做的即是如此。就像他们了解如何用塑料水瓶来制作防御催泪瓦斯的面具一样,抗议者们有时候会用书籍来制作大型盾牌。只需在两层有机玻璃板之间固定两层泡沫橡胶和一层硬纸板,然后在这个盾牌的正面放上你选择的书籍的标题页。在2010年12月发生的伦敦骚乱中就能够看到,一本巨大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是如何保护着一名抗议者免遭警棍的袭击。这些起义的感知空间因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象:就好像是一整座图书馆走上了街头,要让它的诉求为人所知。这难道不又是一种再主体化的现象吗?当面对着警戒线、棍棒、镇暴武器“Flash Ball”或是消防水枪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它们不就是活生生的书籍吗,它们拥有着自己的“声音”,并从那时起大声疾呼,聚在一起,为了让人们的权利得到倾听。正是为此,在罗马,《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与《理想国》(The Republic)并肩抗议,《唐吉坷德》(Don Quixote)与《伦理学》(Ethics)、《死魂灵》(Dead Souls)共同抗争。在伦敦,《革命将至》(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与《尤利西斯》(Ulysses)和《终局》(Endgame)共同前行,所有这些书籍,匆忙地被涂抹成鲜艳的颜色,那些必是读过它们、并决意以手臂之末端举起它们、让这些书籍为他们代言的人们,将自己的面孔掩蔽在书籍之后,不让警察看到。

2010年发生在伦敦的一场抗议活动中,抗议者们手持自己制作的“书籍盾牌”。criticallegalthinking.com ©
意义显著却又颇为老生常谈的一点是,在伦敦抗议活动的图像中,摄影镜头——同时它也是手臂末端的探伸——直接地对准了警方与“书籍阵营”激进活动者之间的接触点。当下,在世界各地,我们将手机当作相机或是摄影设备进行抗议,在现实空间中挥舞着手机并与网络空间实时相连。这个问题关乎于通过一种远远超出其简单的信息性及再现性功能的方式来使用图像:图像也能够在心理层面及社会层面上作用于再主体化的运行。今天,在恰帕斯叛乱丛生的森林里,“妇女参与自治政府”的行动伴随着与图像直接相关的工作,正如《萨帕塔学院手册》中的一整章部分对此的阐述(《手册》采用了“lxs Zapatistas [萨帕塔主义者们]”的表达形式,以 [西语中性复数] 冠词“lxs”体现对于男性女性的兼容)。[25] 正如吉奥马尔·罗维拉(Guiomar Rovira)在《玉米妇女》(Femmes de maïs)中所述,以及罗西奥·马丁内斯随后分析的那样 [26] [27],发生于2001年3月28日的一场由一位原住民妇女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当时所有人都在等着副指挥官马科斯上台讲话——被扩展成为了一种恰帕斯女性发扬自身形象的实践。这些日常生活已是艰辛不易的乡民们为此开始学习如何使用相机和摄像机,以便构建出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斗争生活中的内在视角。早在1972年,墨西哥艺术家弗朗西斯科·托莱多(Francisco Toledo)就在马卡里奥·马图斯(Macario Matus)、艾丽萨·拉米雷兹(Elisa Ramírez)以及维克多·德·拉·克鲁兹(Victor de la Cruz)的协助下,在瓦哈卡州胡奇坦市发生的农民政治斗争背景下进行了一场类似的实验: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手臂之末端——的镜头成为了再主体化的工具。此外,在“康乃馨革命”时期的巴西新电影运动直至葡萄牙的影像实验中也是如此。法国前卫电影团体的激进活动亦是同样,他们与艰苦斗争中的工人和政治行动团体有着紧密的关联。冲突、对抗、痛苦及情感,需要工具和媒介,需要工具和媒介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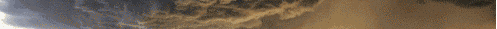
注 释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