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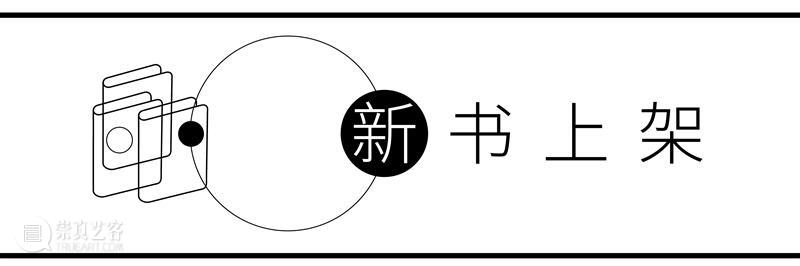
大家好,拜德雅图书工作室近日推出了2023年的第11-13种新书:
《消费图像:当代文化中的风格策略》(斯图亚特·埃文 著,方尚芩 译)
《图题:西方绘画命名的故事》(露丝·伯纳德·伊泽尔 著,黄虹 译)
《批判与超越: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赖纳·温特 著,肖伟胜 编,肖伟胜 等译)
前两种属于“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后一种是单本书。这三种新书均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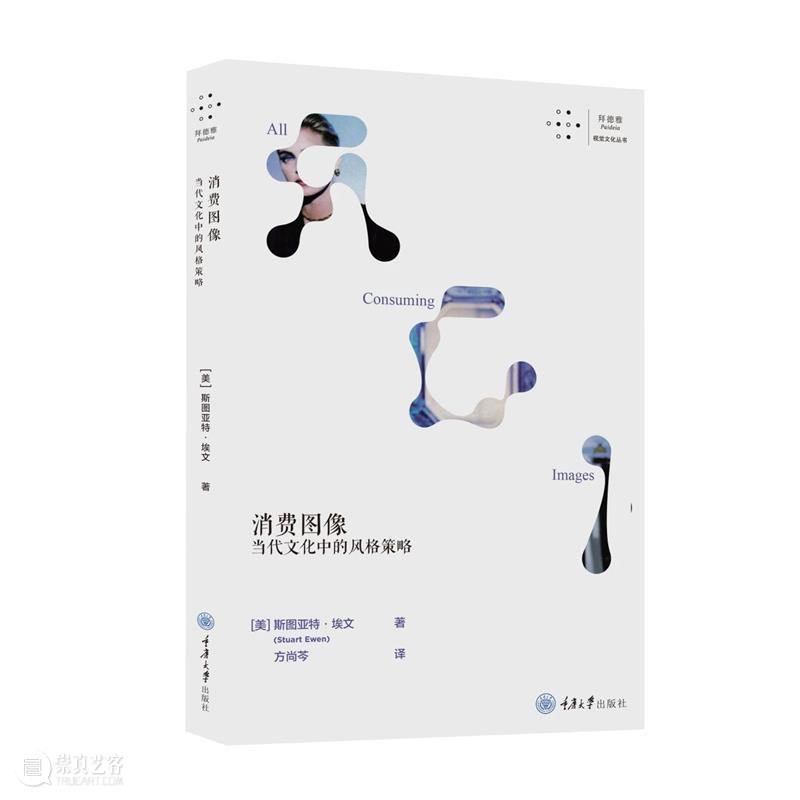
“要使有意义的替代选项成为可能,就要克服外表对物质的支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令人愉悦的景象与令人愉悦的经验连接起来,才能保证‘好生活’的迷人景象来源于人类共同体的原则和实践,才能保证自由、满足、社会抵抗的图像与我们世界中可资利用对资源和实质选择有意义地结合起来。”
今天给大家推送《消费图像:当代文化中的风格策略》书摘(节选自“结论:风格的政治因素”,注释从略)。
作为一种传递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形式,风格把我们放在了危险的位置之上。风格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难忘“事实”的视觉世界,它可以轻易地为几乎任何事物加上一层外衣。在赫伯特·马尔库塞描述过的“封闭话语领域”中,它作为一种有力的要素出现了。由于风格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在,其他可供选择的认知和观看方式变少了。将一切事物(包括牙膏、服装、灭蟑螂喷雾、狗粮、暴力、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思想,等等)风格化的能力促使人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世界,即只关注那些能轻易复制出来的外表,其他的意义都消失殆尽,只剩下挑剔的目光。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当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真切”,真相就变得越来越容易消失。
与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威权主义语言“新话”(Newspeak)一样,风格可以同时包含两种截然相反但表面上没有明显冲突的观点。
战争就是和平,当印着伪装色的军服结合了高级时装的图像学的时候。
自由就是奴役,当镣铐或“奴隶的手链”作为自由性感的闪亮装备戴在手上的时候。
无知就是力量,当卡尔文·克莱恩广告里的一位迷人年轻女性骄傲地宣称“当你失去理智,至少还有一个身体可以好好依靠”的时候。
作为一种信息形式,风格发明了一种诱导我们大多数经验与之作对的意识。重点在于:风格提出了深刻的欲望问题,它承诺会将人们从他们的经验的主观状况中解放出来。精神分析师乔尔·科威(Joel Kovel)说:“风格是自我向本我的致敬。”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在1986年的一则广告中说道,风格“从梦中来,梦是逃离现实”。或许由于它散发出原始的、无意识的吸引力,风格——作为一种信息形式——阻碍了思考。
这种对思考的妨害似乎和我们广泛宣传的以下思想不相符,即我们居住在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人们可以无限度地获取信息,电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堪比光速。尽管有着推广的需求,但信息时代的神话还是充满了矛盾。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提出,所谓新信息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大众获取信息能力的逐渐下降”。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年见证了许多采集信息、存储信息、传播信息的创新技术的兴起。但是与此同时,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情报这些曾被收入公共图书馆和文件库的资源,越来越进入了商业的领域。企业为了获利,将这些资源采集、打包、销售,卖给那些买得起这些资源的人:
信息的商业化运作、秘密获取和销售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材料,根据专门的用途被创建成了各种格式,只要花钱就能买到;由一般税收资助的免费公共信息反而受到私营部门的攻击,被视为一种无法接受的补助形式[……]个人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生存状况的认识能力已经逐渐退化了。
然而,随着获取有条理信息的途径的减少,风格化的信息的潮流又开始涌动了起来。伴随着这股潮流,即便是那些声称向公众提供有关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和信息的机构,也变得越来越风格化了。就如同风格变成了信息,信息又变成了风格。
没有哪个领域比电视新闻更能凸显这一趋势。“新闻编辑部”的布景被设计成了控制中心的样子,这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与正在发生的事件“相连通”的感觉,一种权威感。电视新闻记者的长相是经过挑选的,其荧幕形象也是培养出来的。从一个具有权威感的中景镜头的角度看过去,新闻节目主持人端坐在一张庞大的桌子后面,表现出一副正直公正、无所不知的模样。有时候,摄影机会推近,用特写镜头含蓄地表达一个故事的严重性,并向观众表示,这是新闻记者在乎的事。从开头的节目标识到播放结束,全部的信息和故事都是经过外表的薄纱过滤的。1980年代初的克莉丝汀·克拉夫特(Christine Craft)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女主播被一档新闻节目开除,正是因为她不符合正确的形象造型。当人们期待一个女主播表现得既沉着冷静又有吸引力的时候,美的确变成了真。
除了外表的作用,真相还一直臣服于市场的力量。收视率制度决定了电视台可以从广告商那里收取广告费,这使得新闻节目必须权衡传播信息的职责与吸引大量观众、确保“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沦为了信息-娱乐(info-tainnment)。
1985年纽约“7频道[ABC]目击者新闻”栏目的一次广告活动便体现了真相和商业真相之间的冲突。在这次活动的告示牌顶端的,是熟悉的托马斯·杰斐逊肖像,一位广为人知的正直的楷模。肖像旁是他有力的宣言:“我们不畏惧追随真理,无论它将引向何方。”在杰斐逊智慧的面孔下方,是另一位爱国主义者、“目击者新闻”的女主播董凯悌(Kaity Tong)的座像。她的名言和杰斐逊的名言使用的是同一种粗体字:“我们在这里告诉你真相。”从下方的一些更小的文字中,我们得以进一步看到她想要表达的内容:
真相就是,在电视上,没有什么比真实的人类那戏剧性的新闻更重要、更有趣、更激动人心。
如果杰斐逊代表的是理性时代,那么董凯悌则代表了炒作时代。这里的关键词——有趣、激动人心、戏剧性——是她所意味的真相的附赠品。在收视率游戏里,新闻——出于经济原因——必须被转化为一场喜剧、一部惊悚片、一项娱乐。在这样的语境中,真相被界定成了被贩卖的东西。
新闻本身被塑造成与受到严格监管的风格化环境一致的事物。纽约公共关系从业者乔治·法塞尔(George Fasel)曾用精炼而熟悉的语言描述了新闻内容的呈现套路:
新闻故事由那些著名记者以简短、容易理解的导语形式呈现出来。频繁出现的插入式广告不仅是为了增加财务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把节目切分成让观众保持全神贯注的几个部分。问题通常以便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像游戏节目里说的那样:谁赢了?
外景拍摄的新闻片段和采访保持着快节奏,避免观众对已经呈现出来的画面产生挥之不去的问题或疑虑。经过剪辑后的新闻片段建构出了一个故事,提供了戏剧冲击力和强烈的视觉效果,当然这些都以失去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代价。从长访谈中挑出的“金句”是为了令语言更加经济,而且人们也需要以一个有声的强拍作为结尾——传达出一种结束了的感觉,暗示这个人的话已经说完,并且你看到的画面就是全部画面。出于同样的考虑,在采访中,金句的跳切也是要避免的。剪辑风格有意传达出这一点,即剪辑室的地板上没有任何废镜头。
在这种风格化的环境里,新闻是令人费解的。新闻故事表现为一系列零碎的内容。在悲剧和闹剧之间的切换是将一切粘合起来的胶水。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与事实在世界中的实际关系却从未被发掘。新闻节目的强烈的风格化标志是新闻凝聚力和意义的首要原则。外表再一次比实质拥有了更多的意义。汇编而成的事实,被我们熟悉的、程式化的、权威的“新闻”特质拼凑起来的事实,成了大多数美国人所能获取到的、最容易理解的了解更多现实的版本。对“这个世界”的意识超出了对事件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解,尽管后者才是真实发生的。各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每天都被贴上“好人”、“恶棍”、“幸存者”、“幸运儿”等不同种类的标签,风格成了本质,现实成了外表。
随着画报和杂志的不断发展,每一种期刊都设置了固定的娱乐版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纸质新闻是沿着同一方向前进的。刊登在国家级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上的彩色照片、便于阅读的要点罗列式的风格、电脑绘制的壮观的天气预报图,这些都是纸质新闻媒介顺应电视新闻的结果。发行量和广告收益成了每一期刊物的核心。我们再一次看到信息是由市场法则塑造而成的,真相成了大多数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如果说新闻有助于传播一种持续存在的认知困惑的话,那么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早在安德鲁·杰克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选举的权利便已经延伸到了有产阶级范围之外。政治风格的制造者在统治精英的客观权益和正在兴起的大众的民主诉求之间取得了平衡。社会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已经被政治宣传的魔法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识。
历史学家爱德华·佩森总结了各种资料,将现代竞选政治学的起源追溯到杰克逊时代:
明显具有煽动性的话语开始出现。政客明白普通人有投票权,他“千方百计获得普通百姓的认同,穿旧衣服,宣称自己出生于小木屋,隐藏他的高等教育背景”。
随处可见的煽动性发言在表演技巧的辅佐下,给政治平添了几分“戏剧效果”。一系列戏剧化的方法是为了激发大众的热情,在游行、集会、烧烤和慷慨的烈酒分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19世纪的政治发展和竞选方法塑造了20世纪美国党派政治的轮廓。这些年来,政治风格已经成了协调的、受到精心管理的销售活动的结果。
随着“二战”的结束,政客、政策和政治思想的系统风格化十分普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展的源头可追溯到1920年代,消费行业、现代广告业和市场营销制度的大量涌现导致了消费工程的兴起。那些商业先驱认为,只要人们能够知晓并准确找出心理机制——“大众”的本能按钮,成功的营销就可以被设计和/或建构出来。人们会被视作受到监视、分析、塑造的“观众”。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偏好呈现出一种明确的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大众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介入“二战”,为政治宣传研究提供了动力和资金支持。这种宣传研究的作用有两点。首先,通过收集到的社会科学数据,敌方的成功的宣传就可以被评估、被理解并且潜在地得到控制。其次,与当代形象建设关系更大的一点是,这些研究也可运用于其他宣传活动的构建,或者——用更时兴的术语来说——用作“形象管理”的工具。
这种思考的到来可见于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1947年的一篇文章《共识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伯奈斯是弗洛伊德的外甥,现代公关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一种民主的新视角。随着电影和收音机的出现,随着电视机迅速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配置,伯奈斯重新定义了《权利法案》,其中包含“说服的权利”:
美国通讯系统的快速发展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世界上最灵敏、最好用的思想传播设备。每一位居民都持续地接受着我们这张巨大的传播网络的影响,这一网络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无论那里有多偏僻。词语不断冲击着美国人的眼睛和耳朵。偌大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每一声叹息都会被放大成千上万倍。
对政治领袖或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人来说,他认为,“这些媒介打开了公众思想的大门”:
这些领袖人物,在专研传播渠道运用的技术人员的辅助下,已经能够有目的地、科学地完成我们所说的“共识工程”。
由此,我们找到了伯奈斯最新构想出来的民主的核心,他能够无所畏惧地将意识形态管理技术与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的术语结合在一起:
共识工程是民主进程的本质,也是劝导自由、建议自由的本质。演讲自由、出版自由、请愿自由、集会自由等一切使得共识工程成为可能的自由,是美利坚宪法中最宝贵的保证。
在这篇有先见之明的短文里,伯奈斯已经描绘出了现代美国政治的轮廓。如今,“共识工程”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
自1950年代开始,在更加普遍的消费文化的环境里,竞选政治已经成了又一个可以营销、可以消费的市场。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和消费,广告公司会定期参与政府政策的包装。媒体顾问这个全新的行业出现了,他们会向竞选候选者和公职人员提供关于领导风格的建议。大部分最初运用于产品推广领域的技术,如今应用到了政治领域。情景喜剧、政治演讲、辩论战术和竞选广告会定期地、精确到秒地测试观众反应,由此把握政治信息和政治吸引力的节奏和连贯性,并生产出更加市场化的产品。在一个动辄掩盖根本事实的剧场中,政治的虚拟生产变成了常态。在随之产生的表层含义中,民主本身成了风格。大众的政治参与逐渐被一种观看和消费模式构建起来了。
这种分裂的意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真实感知与外观贩卖者的诱人调和之间的分裂——受到了当权者的信赖。公共政治学越来越变成了形象营销。我们可以在罗纳德·里根的政治生涯中找到最能清晰反映这一问题的例子。1947年,爱德华·伯奈斯宣布,想要在现代大众媒介社会中发展政治选民,就需要系统性的“共识工程”。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便体现了这种政治活动方式的决定性胜利。里根的好莱坞演员身份,以及后来作为通用电气电视节目和现场形象代言人的身份,都是他政治生活的训练。如今回头看当时的政治景观,你会发现,他当选总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未来的野心家和总统的样板。
里根在好莱坞的经历为他带来了诚实可靠的形象和魅力。我们有时候闭上双眼就能听见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热情真诚的声音。在人们呼吁一种信赖感的时候,他可以调动他朴实无华的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式的演出动作,摇一下头,来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啊,哎呀。”作为坚定不移的社会事业的执行者,他成了“最后的怒汉”,忠实地表达他内在的正义感和遭受误解的痛苦感。作为女性权利的扼杀者,他选择了模范夫妻的路线,他和南希·里根成了《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1957—1963)里的克里夫夫妇。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摆出愤愤不平的好人姿态,打算纠正这个世界的错误。在界定美国公敌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权力之争通过著名的《星球大战》或中世纪古装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我们被恳求着加入英勇的斗争,以对抗可怕的“邪恶帝国”;或者与南部边境的“自由斗士”一起同甘共苦。这些场景尽人皆知,事实证明,它们是有效的。可以说,好莱坞叙事为政治觉悟提供了一种风格的模型。
这种朝电影套路靠拢的趋势成了里根主义的普遍特征。例如,在过去十年的美国社会中,正是这种好莱坞桥段担保了军国主义及战士英雄的再度出现。在一阵广泛传播的反越战情绪之后,战败的美国人却借助荧幕上的兰博一角取得了“胜利”。甚至连现实生活里的士兵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都在利用视觉形象捕获人心。尽管他屡次向国会和全国人民撒谎,但在他作出那段传奇般的证词之后、1987年伊朗门事件之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人们会对他那外在的男孩般的真诚作出反应。他恳切地传达出来的对上帝和国家的忠诚实际上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位在情报/军事情景下的冷酷表演者,他破坏、绕过了宪政民主制度。与罗纳德·里根一样,奥利弗·诺思和吉米·斯图亚特在风格上的雷同使那些参与民意调查的人表示,尽管他们反对这些人所说的一切,但同时认为他们的话“鼓舞人心”。
这种形象政治的承诺同样渗透在里根政府对批评的回应中。尽管放松商业管制为意外之财开辟了空间,减少了人们对工业或环境健康安全的关注,然而里根主义偏袒富人的做法仅仅被白宫助手描述为“认识上的”问题。随着长达三十年的民权立法运动遭到系统性的瓦解,人们为里根主义冠上了对少数群体麻木不仁、满怀敌意的罪名,但这个罪同样被视为“认识上的”问题。这一态度表现出政治作为纯粹的公关工作的优势。通过把所有的社会问题还原为认识问题,社会问题统统变成了认识层面的问题。社会变革被图像变革所取代。表面上灵活多样的展现形式掩盖了本质上的强硬态度。
将图像从社会经验中分离出来的冲动,或者说将图像作为经验替代物呈现出来的冲动,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重复着。这种动力的不断重复既影响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也创造了一个把风格作为主要表意工具的世界。这里的危险在于,由于世界鼓励我们接纳图像的自主性,“出现的既定事实”意味着实质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我们自己拥有的经验并不重要,除非这些经验经过了风格世界的认证。在这些文字游戏中,表面和现实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由此产生了一种愈发强烈的迷失感。
19世纪中期以来,大众市场的兴起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经验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图像的丰富多样性为人们拓展了视野,使之看到了各种各样新的可能性,开启了新的想象之道。虽然这些全新的可能性已经对生活的表面产生了影响,但是其潜在的意义却被掩盖起来了。大多数时候,具体的可能性和稍纵即逝的风格通常被混为一谈。
很难想象我们该如何走出这种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史的一部分。然而,要使得有意义的替代选项成为可能,就要克服外表对物质的支配。我们必须调和图像与意义,复兴物质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令人愉悦的景象与令人愉悦的经验连接在一起,才能保证“好生活”的迷人景象来源于人类共同体的原则和实践,才能保证自由、满足、社会抵抗的图像有意义地参与我们所栖息的世界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实质选择。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