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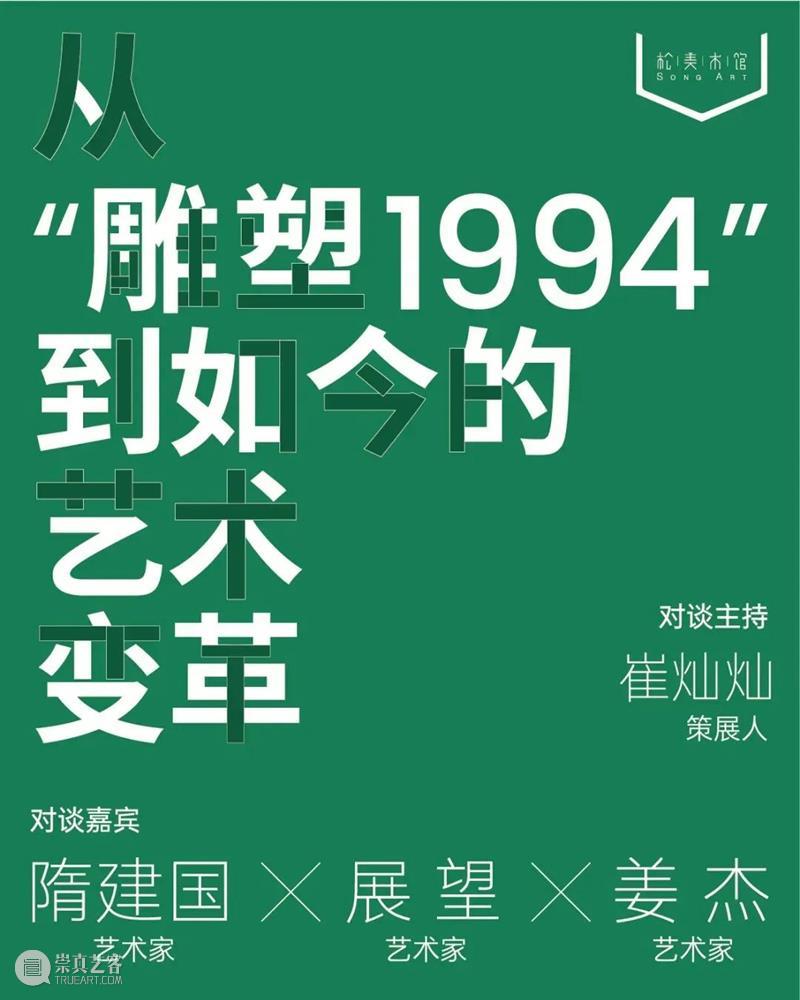
由松美术馆和隋建国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云雕塑——首届学术邀请展”于2023年5月1日-8月27日在松美术馆展出。7月31日,我们邀请到展览总监隋建国以及2位极具代表性的雕塑艺术家姜杰、展望,策展人崔灿灿作为特邀主持,以“从‘雕塑1994’到如今的艺术变革”为主题展开对谈。
对谈回顾根据内容分为上中下3篇,分别是
对谈完整视频
个人与艺术的“进”和“退”
我接着把这个问题再说一下,因为起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在想一件事儿,从“雕塑1994”到今天这个展览是存在一种必然的进步吗?还是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差异?如果我们实现了曾经艺术变革的理想,但曾经我们渴望的东西也在今天被拉平了。比如刚才隋老师说到90年代,那时中国艺术界普遍持一种媒介先进论,做影像的一定比画画的牛,搞行为的一定比做雕塑的牛,那个时候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前后的进化论,但是在今天你发现你去看一个展览,你既很难说一个东西前卫,也很难说一个东西落后。
比如说90年代经常有些做装置的人,一进绘画的展厅就说,哟,画画的,扭头可能就出去了。很多50后一代的艺术家,至今都有一种媒介优越感和前卫的道德制高点。但在今天我们进入一个展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雕塑也不落后,新媒体也不前卫,它是一个拉得特别平的现实。但是在“雕塑1994”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前卫的区别的,挺明确的,“个人”提出“个人性”,当时就能作为他宣称前卫的一部分。我昨天从深圳回来,在深圳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深圳有个艺术圈叫“新媒体艺术圈”,新媒体艺术圈跟深圳的创新产业、科技前沿、人工智能、各种科学家在一块,他们一直聊技术、聊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但我觉得,技术的先进和观念前卫是两件事。
但是在新媒体和科技艺术圈,他们认为技术存在一种先进的科学材料,都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乐观的的科学进步主义情绪。我们说回到雕塑里面的材料,似乎某种技术象征着某种前卫性。但是在今天在北京这个大的人文主义大本营里,我们却很难看到前卫和和落后之间的明确的差异。而当年1994年,你们追求的个体,在这个展览上终于有了这么多个体,但是这个“个体”还是一个问题吗?它可能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就想听听三位怎么看?
隋建国:
像刚才展望说的,就是选择的内容决定了,反正说内容也行,说主题也可以,艺术家他一定会寻找到一个东西是最能吸引他,或者他念念不忘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他即使是不想做,但是这个东西永远会流露出来。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艺术家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你很难靠一件作品一炮而红,是吧?你甚至不得不用你的一生来证明你干了一个什么事儿。
像我们这代人前边各种摸索和误读就更多一些,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方法。现在“云雕塑”里面的年轻人,其实你仔细看,都是这10多年——当然北京艺术家偏多——在北京艺术圈里摸爬滚打,也参加外地的展览,他们大概都在按自己这个方向慢慢的演化。有些艺术家就会比较显眼,有的就没那么显眼;可能他会执着于某种材料,也可能他会一直执着于某种自己的某种性格,就是艺术的性格。你比方说辛云鹏的小录像,他就是那个劲儿,你一看就是他。包括梁硕他搭怒江这个场景,一看他就很擅长。就这个意思。这个是你没有个十年八年甚至一生,跟别人区别开是很难的。这就是你成了主流艺术,你就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崔灿灿:
我发现在你们那个年代有代表作,甚至有杰作。比如说我做陈丹青、袁运生、罗中立、刘香成的展览,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过很多所谓的杰作和跨时代作品。到了90年代,艺术家还会有代表作,每个人都能报几件,大家熟悉的作品名字。特别是你像1994年你们也属于一个年轻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能记住几个代表作的。但是到今天来看,我们看更年轻的一代的展览的时候,好像代表作的概念没有强烈,我能记住的就是就刚才隋老师和姜老师说的一种语法,但是我对这种语法又有一种疑惑,就是在一个普遍个性的时代,你的个性给不给我们看没多大意义,反正我们都有个性,也都不想兼容。
今天的“个性”不具备共振,不同又怎么样,每个人都很不同。在更年轻的时代里,没有一个人是相似的,但是他最后传播出来的东西,是要做什么?艺术最终要表达什么,要交流什么,比如说在波伊斯的时代,在杜尚的时代,通过改变艺术的指征,这个东西过去不是艺术,至此之后它成为艺术,这是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上一代人在艺术史中的使命。第二个就你提供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感知,这个感知在我们之前见所未见,比如埃利亚松的大太阳。但是在今天你看到大量的艺术家,你会觉得这两个都有点不靠谱,你看到都是琐碎的,对艺术史无关紧要的。我说的比较直白,我也不知道年轻一代未来最终能提供什么?但是他又很早就有了个性,他也有自己的感觉,也有自己的语言,甚至颇为熟练。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展望:
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个问题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真的,因为我也很关注国外的艺术家展览。一旦自由彻底打开了以后,你可以说你反而不自由了,在这自由不是特别开放的时候,你有明确的敌人,或者你有明确的要突破的栏杆,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奔向自由了,但是如果让你彻底自由,你随便,你干什么都是对的,这时候我觉得反而是人类另外一个困境,你反而觉得我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其实反而是不自由了,也就是说,你要不给你自己设定一个自我设定的规则,或者自我立法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都在瞎捣鼓。所以我觉得刚才灿灿问的问题,其实我们可能真的回答不了,是这样,他是一个处在现阶段的问题,当下很多人即使表面不承认,内心也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怎么去解决突破,这个要看谁有这个运气能够踏出这一步,就是说我们处在并不是说不自由的困境,而是处在了一个全方位自由的困境下。---再多的我觉得也不是我这水平的人能说的清楚了。
姜杰:
你觉得我们目前是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吗?
展望:
我指的是精神上的,就是你不要把它现实化,就是自由。
姜杰:
现实和精神当然应该有关联。
展望:
这个自由是指的艺术史发展的逻辑走到了一个彻底自由的状态,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现实,这是两回事。
姜杰:
因为我们又不是艺术史学家考虑那么多干嘛。
展望:
不是艺术史家,是说我们做作品做到今天了,该做都做了,是这个自由。
姜杰:
我并不觉得该做都做了。
展望:
这是你个人看法。
姜杰:
那也是你的个人看法。
展望:
我谈的是我感觉到的当下的一种现状,我说的是一个国际问题,不是说只是针对中国,你确实有一种该做都做的这种感觉,而且我特别关注国际上很多包括年轻艺术家在内,比如说就这次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你也能看得出来,那个状况,它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实有所封闭,但是艺术家往往有自己的渠道可以不被封闭,我们封闭的是普罗大众,其实艺术家一直在关注整个国际的当代艺术生态,所以就从我个人立场来说,我的确是有这种深刻的感觉。
隋建国:
说的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难回答。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只能说我制定自己的规则,我做我自己的作品。但是别人看来是不是一般化了,是不是也没怎么跟别人区别开来,你真是没办法,是吧?这个可能就要要找一些历史的经验。
其实你看,我老觉得观念艺术或者观念主义艺术,它这个利害程度,比当年中国的禅宗对佛教的改造革命还厉害。观念主义艺术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禅宗化的对待艺术。你什么都是禅了,是吧?但是你看禅宗在中国这个真正普及开,到了宋末,元明基本上就没了,元还有点明就没了。它一旦普及到那个程度,跟中国世俗的文化生活真正融合下来之后,慢慢就衰减了,衰竭了。我想如果把这个观念艺术禅宗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当它无所不能的时候,它就会确实遇到困境。尤其这些年,你看咱们如果把欧美当做一个对标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停的在寻找新的社会主题,如何再回到社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比方说性别、跨性别、种族这些。它其实在找主题了,在寻找主题,原来审美感性上的革命几乎是消失了。
姜杰: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艺术那确实是应该有一个时间段要呈俯视状去看一些东西,这样你就可以站到一个高点,看到很多的可能性,这个时期是必要的,通过我们己有的认知、知识、常识,看到很多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它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所有的新的材料,新的语言,这些确实可以成为你未来创作的参照物,你见的越多,你的视野就越大,就越应该知道有些人的作品使你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可能性并从中获得灵感。也有些作品它的呈现作用是为了让你避免重复他人或者加强了你对好作品的肯定。但所见所闻多了它不应该是你有将自己的东西轻易呈现它人的二手的机会,模仿的像无论是观念还是样式都不属于创造力范畴。刚才灿灿问 年轻艺术家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特感受,个人的语言 ,这些都有了 ,但很少看见他们有代表作。我个人觉得个性的东西显现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个人的代表作的成立更多的是这件东西除了在你自己创作中的重要性它是不是也能得到业界的认可,我想不是年青艺术家不需要不在乎它 ,对于艺术家而言重要的作品出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人生中不会太多,这其中包括很多机缘,一个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的出现比发明一种样式被认出更不容易。以前我们每次出国都会去看很多美术馆,画廊,那些经典的古典的同时也是艺术家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它除了代表艺术家不可超越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也是一个时代艺术的具体代表之一。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品并不是经典,但它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东西,因为它其中充满着很多未知,有它自己闪光的地方,有它的独特的东西,问题是这一切的闪光点它是不是可以构成了我们的一种创作方式,跟我们所在地的东西发生不发生连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使你有多角度的观看问题的方法,但是它并不代表你挪用过来后就可以是你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觉得,一个新的材料未必能做出新的东西,有陌生感也并不能说明它会提供不一样的感受,这一切很容易混淆,刚才你说的那个深圳什么小组,大家会误以为技术好有陌生感,它就会加强作品内容的不可替代的东西吗?未必,最初我们可能不知道这项技术,它仿佛达到了一种效果,但好的东西应该是通过技术的那种特殊性极限性使用到其它材料达不到的那种极致,极限性的使用,依然是技术,但是之后出现了什么,是很重要。
材料的极限性使作品出现了一个极端特殊的其它的技术不能带来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震撼,如果没有,那它跟使用别的什么材料没做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有一个错觉,以为出现了一个新东西。联想到前面说的,1994年的展览,其实在做1994年雕塑的作品的时候,并不是说要找材料上的区别,其实是寻找本质上的不同。我觉着这次云雕塑展览里头,我还是会看到艺术家,他们源于生活并发现生活中很多具体的一些样式,比如梁硕的作品,他常常带学生下乡,他的作品有很多元素来自现实生活,你能看见他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到的现实中的特有那部分的东西,非常的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这次作品用的很密集的小台阶,用木板做的,很窄很密集,你走上去的时候,不是一步一步的踏上去,而是半步半步的特别窄。它让你想到某种爬山时的经验,那种踩上去不是一个整脚,是半个脚,它的密集度它的窄让人心里会出现莫名的变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我能感觉到它这些来自生活的很具体的一些经验,将它作为作品当中一部分是很强烈。我比较喜欢那种源自于生活中有很多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一个大的,刚才我们说俯视的过程当中,这里头包括你对于艺术,艺术到底是什么而重新思考,无论我们走到了哪个阶段,用了什么样的主义,我都认为知识就是知识。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进入创作的一个人,我们不该满脑子艺术史,我如何创作,如何找到生活中的一些跟我的作品匹配的一些东西,进入个人化,个性化,之后这一部分东西怎么样把它显现出来,让别人看到,让别人感受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崔灿灿:
隋老师、展老师你们在创作的时候,这么漫长的创作历程会考虑自己和艺术史的问题吗?
展望:
有一次我在龙美术馆做完个展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我终于从那个洞里出来了,把展览呈现出来之前,就是在创作当中我有点像在一个山洞里,它是很偏执的状态,你看到的世界就那一点光亮,是处在那个状态的,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只有从山洞里出来说这展览已经布置好了,这时候才能开始聊艺术,但在做的当中你根本顾不上,你要实现的东西细节太多,那些面对的问题太具体了。
隋建国:
我觉得在做的时候,其实是直觉。但是过后怎么认识自己,因为艺术家做出作品,我觉得要去认识它,怎么认识的时候,就是说你需寻找如何解释自己这个作品的时候,要对标一些艺术的系统。就是找支撑,找对立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大师已经都那样,我们就这样。
崔灿灿:
我把这个话题再回到在座的三位,我刚才在你们三个表述的时候,突然在想,你们三个身上完整走过了中国当代雕塑和当代艺术的各种历程,比如说档案文献也做过,装置、绘画、影像、行为也做过。你们三位都参加过“长征计划”和几十年来各种风起云涌的实验项目,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些媒介,在你们二三十年的历程里好像都用过。但在我印象中,张永见老师近几年很少出现在当代艺术界,向京老师和傅中望老师好像雕塑形态的作品更多一些,我不知道他们也做过各种纷杂的延伸吗?
姜杰:
向京其实做了好多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她做了好多事情,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东西以外。她一直在做很多东西,什么时候呈现出来是她自己的事情,但她实际上一直在做东西。
崔灿灿:
我在想从1994年到现在这条路走了那么多年,从1994年的一个挺前卫的形态,到如今你们作品的形态。我要问几个比较愚笨和武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座的三位还追求这种前卫的策略,或者说前卫的艺术,还希望艺术是以前卫形态或者先锋形态出现吗?第二个,再回看1994年的作品,是觉得今天的作品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感觉?但是这三种结论背后都有潜在的艺术价值观,比如说一个艺术家觉得自己进步了,那就意味着艺术是可以通过经验的反思,不断获得更好的可能;如果认为自己退步了,或许是一种进入保守主义的倾向,这在很多前卫艺术家后期的创作中十分普遍;如果觉得每个时期都差不多,我想问一下,那个时期的质感和现在的质感有什么区别?努力的意义在哪里?
姜杰:
我觉得是这样,革命什么时候都需要年轻人,你看在战场上永远是年轻人举着旗子往前冲,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人冲到前面去的,冲在前面的肯定容易死(笑)对吧?是牺牲。谁都年轻过,谁都冲过,但话说回来并不是不冲在最前面就不革命。我们已经过了冲的那个年龄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冲是一个力量,是荷尔蒙,当艺术创作变成一种常态 ,一种必须, 冲只是一种方式,一种行为的样式,更多的时候是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保持自身的敏锐敏感 ,保持创造力。比如我们看隋老师、展老师,虽然他们没有时刻冲在最前沿,但他们的作品不亚于冲,一次次呈现爆破力,看隋老师最近在成都双年展上10米×7米的大雕塑,你说他是不是举着旗子往前冲?也是冲,也是豁出去了。比如展老师在龙美术馆天顶上的大雕塑尺寸也简直了,强烈。再比如刚才说到向京,我每次看向京的展览,都觉着她的力量不亚于一个举着旗革命的年轻人,她的工作量,满场铺开的那些作品,会让人感动。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我觉得无论是生命中还是在工作中与这么样一群人相遇相伴,是战友更是朋友这么多年过来没掉队没倒下,虽然没有每每高举旗帜,也是不易了(哈哈)。
崔灿灿:
我补第二个问题姜老师,在你1994年的作品里面,比如说对蜡的使用,对生命、对身体的关注,好像在你现在的作品里面也有一些,比如那种易碎、临界点、临时的、模糊的感觉一直在延续。您觉得除了跟您现在创作的这种一致性或者某些方面相似性,作品中哪些地方发生了改变,或者哪些过去的想法,你曾经坚信的认为的,在今天你把它放弃了?
姜杰:
经典的完美的完整的作品,一直印在我的生命里,它是很难被放下的一个东西,很坚固,当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幽灵不断出现在我的前,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完整,什么是伟大的作品。假如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也许知道就足够了,但当你是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它的存在而阻碍了你的创造力那肯定是不行的。在工作中,你如何打破这些东西,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你能不能做到不在乎它了,不在乎之后你又还能干什么,这一切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无论从材料、心理、包括行为上,包括制作方法上,如何先把自己击碎,不再在乎你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太在乎有些表面的事情,也更在乎你自己是一个做艺术的人,太在乎你学到的了不起的技能,太在乎别人对你的印象,如何把这一切都放下。记得98年我们一起去台湾,朱铭先生跟我说,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你要学会放下,放下以往的知识,当时我不太明白,心想放下什么呢,我本来也没什么呀,后来想想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坚固的东西,在不断干扰你,如何击碎它,至少从心理上击碎这些东西,也是近些年心理的变化。我不再相信很多东西,我也不再把以往认为的好做为我工作时的标准,但是所有的经典的、好的它依然在那,我只是不再固守那些完美,固守它的所有的好,因为我知道那是别人创造的历史,不是我!对。
隋建国:
好,我补几句。朱铭老师他其实是,因为台湾的道家和禅宗的线索一直在延续。他更多的是在说这方面——禅宗意义上的放下,我觉得。现在我想给你提个话头:如果你(武汉)这个展览,在2000年年初本来你的展览计划实现了,它会是现在这个样吗?
姜杰:
不会,应该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天我跟灿灿在聊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在想,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轨迹,成立需要缘份。对,其中包括最终在武汉做展览,武汉做为世界变化的起始点,所有的一切给予你的感受,一定不同于北京、广州……等地方,它的特殊性让你不可不思考。刚才我们说到雕塑,灿灿也说曾经我们要解决的是雕塑自身的空间问题,这么多年工作的不断推进让我开始思考的不再是雕塑而是作品,其中雕塑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只是做为可视的物,之后更多的是如何赋予这个物体更大的能量 ,并将它存在的空间扩延,加强它的场域感,作品的成立是由很多的关系,很多的物与物之间,物与空间之间的拉扯关系构成了一个体验,它包括时间 、空间、实物、现场及参与者观众的心理空间等,雕塑本身只是作品中的一部分支撑,作品能成立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隐形,我认为这一部分东西非常的重要。我在做《俯仰之间》这组作品的时候,灿灿也去看了,当时我们在工作室的时候,看它就是一件被塑造的物体,无论如何也很难想象,它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你顶多考虑到它摆到那个展厅的位置如何,实际上摆到了展厅里它所有的方式包括灯光、位置、风 、声音、气息这些所有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现场的样子,它是不可知的。作为一个创作者面对展厅一定会尽量的去思考作品的问题,但实际上场域给你带来的这一切只有你在那个地方才可以产生,我是在做一件作品,不再是一个雕塑,是一个作品,雕塑只是整个的场域中可视的那部分东西,构成它的包括声音,包括武汉这个地方它的特殊性在里面,包括观众看到它,与之形成的一些心理上的感受,作品中的所有的空间的显现,材料的显现,材料的使用,它让你感受到有记忆的,有经验的、有心理的、有温度的……,这一切构成了作品的最终全貌。隋老师说,如果在2020年之前做会怎样 ,我想,这些感受是没有的。我努力的破开雕塑本身的一些东西,试图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解决雕塑的问题,空间的问题,很具体的一些塑造的问题,或者包括是不是用现成物,还是用一种可塑性这些问题,与它们相比我觉得支撑这个东西成立的隐形的东西更显重要。只有这样即使没有艺术史经验,没有专业知识为参考,依然可以观看可以感受,可以与之形成共鸣,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崔灿灿:
我就接着问一下隋老师,因为我上次在民生和OCAT都做过您的个展,从1994年雕塑的那几件作品,后来的中山装、made in China,到后来的一系列的观念艺术的变革,基本上你把雕塑能触及的各种流派主义都走了一遍。直到2008年你开始像盲人一样,闭上眼睛,开始了最初我们聊的时候说是反塑造这样一个事儿,当它开始反现代主义的塑造的时候,它仍是一个前卫形态,你现在闭眼系列也做了差不多15年了。今天你怎么看待这种前卫或者说是落后,或者说你个人1994年以来的变化?
隋建国:
其实你(指主持人)看,2020年咱们在顺德,记得有一次在旅馆里面当时有一个对话。我说我大概2017 、2018年就开始觉着这个《盲人肖像》以来这些作品,它不单是一个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泥塑这个东西,不是它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我也是因为重复的去捏,发现其实它就是你手里边的那块空,这块泥就是那个“空”(发“控”音)的一个替代物。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深入挖掘。而且我觉得我借了一个光,就是借了这个3D数字技术的光。如果没有3D技术,这个问题是没法挖掘,它不会成立。因为3D技术它能放大,它能把我手里这个空间的全部细节作为一个证明,给它重现出来。
比方说刚才姜杰说我在成双做了个高7米长10米宽6米的东西,其实它那个尺度只是因为那个空间的要求。我觉得作为一个雕塑家,我不能忍受我忽视这个空间,我必须去跟它要产生一点什么关系。它的巨大,它的表面这些痕迹,这些痕迹其实什么也不表现,它们只是证明这个“空”(控)非常真实,被再现的非常真实而已,但它什么也不表现。当然大家会习惯性地觉得它在表达什么,它在说什么,但这是每个人自己理解的问题。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证明而已。
而且我关于这个“大”,还有一个空间和视觉上的一个要求,就是当你一旦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它没有距离了,因为你看到他了。这应该是雕塑的一个(视觉)空间问题。雕塑的空间、时间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至于说用什么媒介来表现它们,或者说你表现了,你并没有在意它,我觉得不管你在意不在意,表现没表现,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先天的,你是逃避不掉的。如果你要遇到它就挺好。所以我就觉得至少现在还是有事儿干,有一个问题需要我去再去挖掘。
崔灿灿:
好,我接着补一个问题,隋老师1994年您的作品挺塑造的,就是一个石头,外面一圈钢筋,再到2008年反塑造,包括您一直强调“云”这个虚拟概念,但是你又在不断的造物,无论它是以什么方式,它都造了一个物,这种造物和虚拟,塑造和反塑造,在你的作品里面经常同时存在,而且有些时候“前卫”与“保守”在你身上有特别明显交混,比如说您个人是一个艺术家,但你又做了很多关于雕塑的出版组织的这一系列展览。您用3D打印,关心各种新技术,试图让雕塑开放,但就像姜老师说的,您却对雕塑的振兴有一个使命,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维护感。这种在您身上出现的多重的矛盾性是一个什么原因?
隋建国:
我觉得我是时代造成的。我觉得其实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家,他的生命本身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所以他做的事儿跟他的价值观是一顺的。当然也是因为我当过雕塑系主任,还有惯性,觉着你在学校里支撑起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无形的棚子压在这里,你撑的高一点,大家就舒服点。你在社会上其实也是一样,当大家都觉得压抑的时候,你自己也压抑。所以撑起一点,大家活得好一点,自己的工作也就舒服一些是吧?它就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
至于说我现在不断的在制造物体,这在我就是一个恋物癖的问题。你看我现在其实这个作品它没有表达它自身,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指向的是我这个手中已经消失掉的空间。所以它其实是没有表达,就是证实而已。对我来说有这个数字技术,能把这个东西给托住让它实现了,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谓先进的媒体或进步的媒体(比方说你说到的深圳新媒体小组之类的)不重要,但是它有时候反而会解决很古老的问题,这很有意思。
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而且有的时候,往往很古老的问题它一直萦绕在你的内心,要是能触碰到它,那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其实没有3D技术,我触碰不到。你就捏块泥是没有意义的。
崔灿灿:
好,下一个问题,接着还是展老师,我看您1994年那件作品是硬化的衣服被绳子吊着,后来您又创作了不锈钢假山石系列,公海漂流计划,再到前几年数字和数学的偶然成像,也有的反塑造和反人的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您为什么也会对反塑造这件事?我们经常在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展老师还是比较关心前沿艺术,经常你会说国际上的前沿艺术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前沿艺术在发生什么?您觉得在艺术上,包括您个人,追不追求先进和落后、前沿和固守的关系?您和隋老师都用了新技术,在姜老师作品里面好像没看到新技术的存在,一个是3D,一个是虚拟的造像,包括数学……都用到了,这些概念您怎么看?
展望:
刚才我们谈论的对象无论是当代艺术也好,雕塑也好,你刚才问我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词儿,什么词?就是“实验”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在90年代传入中国,当然原来在西方出现是有它的科学背景的,这两个词我有时候讲课也经常说到,它是从科学来的,传统的艺术里没有实验这俩字,(无论绘画还是雕塑)你一笔下去就是你,但是“实验”这词进入当代艺术以后,尤其是90年代开始,我们真的就是(我说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是不是我可以放弃一些我所擅长的艺术方式和感受,比如说我特别善于玩泥,如果你接受了实验这个概念,可能你把你特别擅长的泥就给放弃了。如何超越自我的有限经验,实验显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因为实验意味着一种忘我,就跟科学试验一样,你过于展现自己的强项的时候,你是无法实验的,你必须隐藏起来你所有的经验手法,包括品味,比如说我们受波普艺术的影响,你说难道我们在美院受了多年训练,我不知道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吗?我为什么要用低俗呢?那是因为这种实验的概念,他给了你一个理由,使我们可以把低俗拿到高雅来使用,看看它到底会呈现一个什么结果,刚才我们谈到观念艺术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实际上“实验”这个概念对当代艺术影响也特别大,在这个词汇下,你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做完这个又做那个,甚至有时候做的都是相反的。艺术家可以回答说我在实验,实验那些我没有碰过的东西,我不了解的事,我通过实验去了解。你想想相反的是什么呢?比如我擅长画抽象,我绝对不能实验别的,我一直要越画越好,最后画到全世界最好,其实这不是在实验艺术,而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艺术本身),我不是说好不好,比如我一辈子就画一种笔触也会很好,但是实验艺术会有意识的回避这种(经验带来的)惯性。
现在回到你刚问我这个问题,你看我从衣服(中山装)到不锈钢(假山石)再到公海漂流,又有后来的(素园造石)以及跟数学家(隐形)的这种合作,其实我认为我的很多地方,是跟搞实验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当中也无意识的露出(保留)了我的一些个人爱好和性情,脾性肯定也会露出来。
姜杰:
我先说,试验这个事,以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都特别爱把曾经的很多早期习作藏起来,去他的工作室你是看不见他以前东西的痕迹的,因为显得很老派,所以基本能见的都是很新的东西,但实际上你是谁你就是谁,对不对?展望说到实验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验有一个问题,你以什么作为参考?它才被称之为实验,应该有一个对象为根据。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擅长一种技能,是不是可以把它也是作为实验的一种手段,将它用到极致,极致了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预知的东西,这是不是也算另一实验。在过程中如果只求新意,在面对自己不懂的和不善长的材料使用起来就很困难。有一些东西的极端性是来自于别人的不可能,而你能,极端性就会出来。我喜欢的事物爱好太多,我也被朋友说,能不能专注一点儿,我不知所措但又不知如何使用它们,我也会反思这个问题。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读于北京市工艺美校,当时我们上过很多不同种类的课程,学了很多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没有学到的一些技能技巧和一些技艺,他们学的是纯艺术,只是绘画本身,而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传统的那部分,当时我们下乡看遍了国内几乎所有的石窟寺庙,我们的课程包括篆刻、书法、象牙雕刻、景泰蓝、玉雕、工笔花鸟写意山水、图案及木雕、 石雕……学了特别多东西。记得上了大学 ,依然被认为我们工艺美校出来的学生,做东西匠气,一不留神就朝向了一个工艺美术大师而去,虽然身怀好多技艺但不知如何使出来,我觉得是当代艺术成全了我,它可以把你的这些东西调动出来使用。年青艺术家对于一些现代科技的掌握,有他们自己掌握的技能的媒材的多样性,我们也有我们的技能和多样性。多样性是使作品成立的元素,但它并不代表作品本身的好坏。
崔灿灿:
隋老师、展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隋建国:
(指向松美术馆展厅)这个展览就说完了,说够了?
展望:
你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回答,就是说追求不追求前卫,当然我特想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我就打个比喻就行了,好比是牙膏,我觉得我到了今年60岁了,牙膏挤出来差不多2/3,还剩1/3,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很想把剩下的给它挤出来,什么前卫不前卫的,都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了,我这个人还能干点什么,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它给做出来。
崔灿灿:
谢谢三位嘉宾,刚才隋老师说了一个问题,说今天为什么没有谈这个展览?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三位其实也都不是参展艺术家,今天也因为下雨,我们也没有邀请参展艺术家参与讨论。这个论坛最初的设想是应该邀请几位参展艺术家,几个策展人,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像刚才展老师一开始说的,如果存在代际的话,其实这种对话很难展开,因为大家很容易变成一个很客气的对谈。
所以今天我也是希望,我们对谈的标题是从“雕塑1994“至今的艺术变革,通过三位艺术家在讲述自己的创作,讲述自己对雕塑、观念艺术、当代艺术的理解,让大家看到从1994年我们对雕塑的认知,到今天大家对雕塑的一个认知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1994年的展览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却最早强调了”个人“这件事,今天如果观众足够细心,能从三位艺术家的回应里面听到了彼此的差异和彼此的对抗性。
我觉得这恰恰是“雕塑1994”之后给艺术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关于“我们”和“我”的区别,我们自己对艺术理解的不同的主张,和个人的这种文化和艺术上的立场。今天窗外下了北京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雨,感谢各位观众可以听我们这场原计划1个小时却拖延了两个小时的漫长对谈,也感谢松美术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邀请我们做这样一个对谈,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大家。
(完结)
关于对谈嘉宾
姜杰
艺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活跃于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前沿。主要雕塑和装置作品有《易碎的制品》(1994)、《大于一吨半》(2014)、《俯仰之间》(2023)等。多次举办个展,并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曾获2009年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大奖,2009年 时尚COSMOPOLITAN年度时尚女性大奖、2015年中国ACC艺术大奖提名等。
隋建国
艺术家
隋建国1956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84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得硕士学位。现居住和工作在北京,为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
隋建国在自己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对创作观念、作品形式、媒介选择、时空经验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度理解和认识。2008年以来逐步将精力集中,以手捏泥作为“手中之空”,并将其以3D数字技术放大打印成为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艺术展,并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要艺术群展。
2016年申请发起“北京隋建国艺术基金会”。同年发起“国际现当代雕塑理论译丛”及其编委会,并担任编委主任。2020年注册“云雕塑”公众号,并发起组织编辑委员会。
展望
艺术家
1962年12月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曾任雕塑创作教授,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展望的艺术有着以简单材料形态营造复杂问题的特质。在雕塑、装置、摄影、影像及公共艺术诸多方面有很多实验性创作。1995年开始创作的《假山石》系列为其观念性雕塑的代表作,近年以跨学科叠加的工作方法创作出各类新型作品《我的宇宙》、《隐形》系列、《有限/无限》、《对阵-粒子》系列等,是当代艺术中观念性艺术和雕塑实验并行的实践者。
展望在个人艺术生涯中共举办过国内外个展及个人项目二十几次,曾多次参加威尼斯、上海、新加坡、广州、夏威夷等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和三年展。
关于对谈主持
崔灿灿
策展人、写作者

加入会员


扫码添加微信小助手
即刻加入松美术馆社群
参与互动,不定时发送松粉福利
——————————————
松美术馆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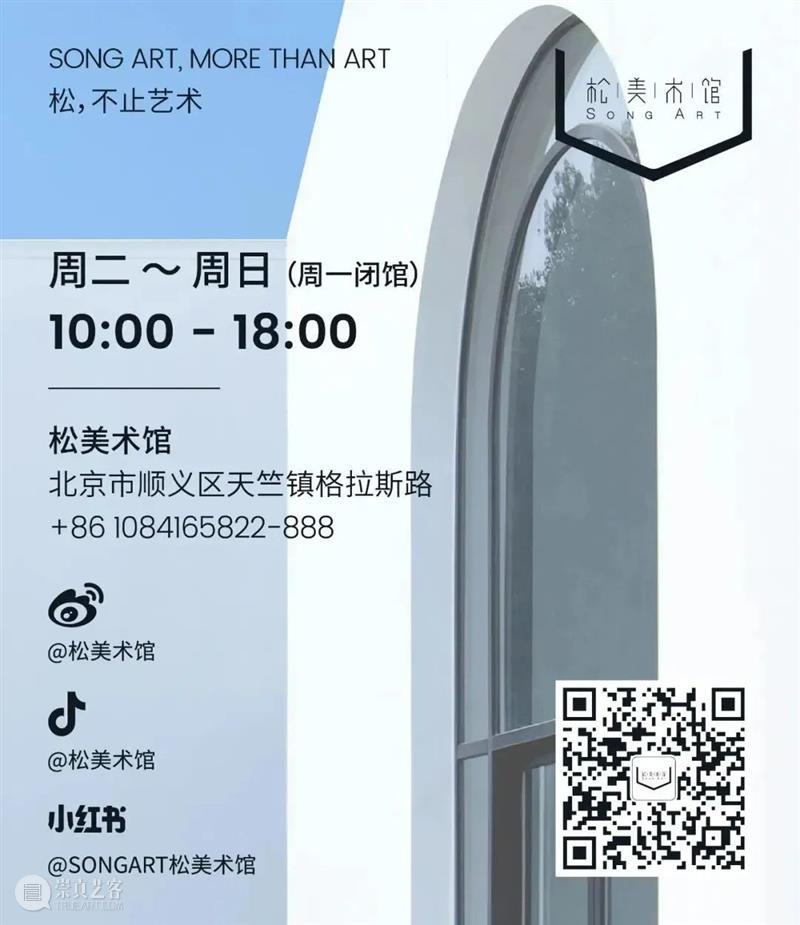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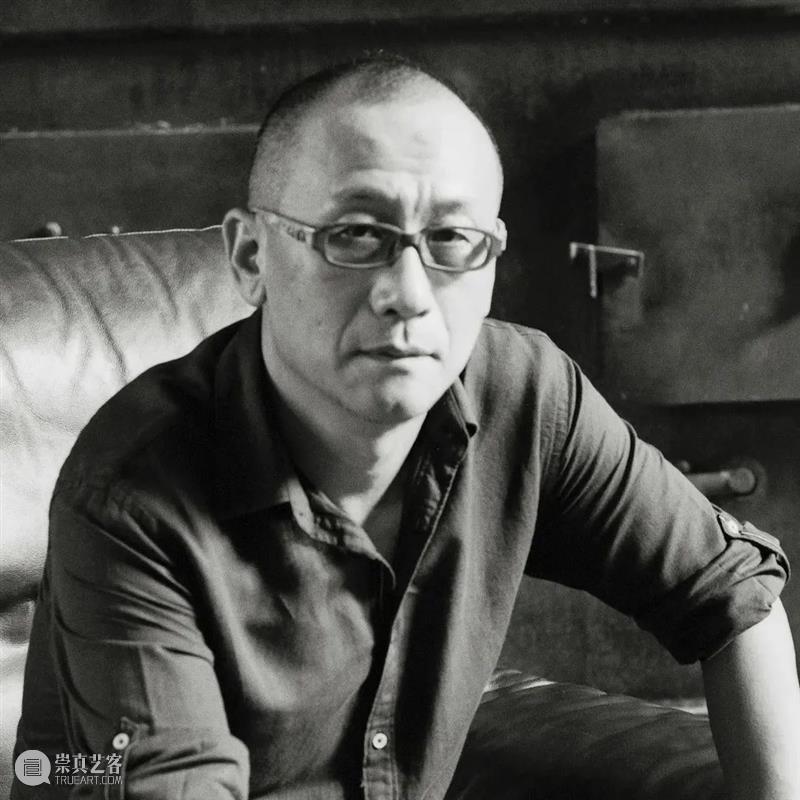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