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女、家庭主义与家务外包
[日]斋藤环 著,高璐璐 译
节选自《危险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标题为小编所拟
母女问题的时代背景
水无田:话说回来,我们对男性“何为父亲”的执念,大概是战后重新塑造的简单易懂的概念吧?
斋藤:不,我觉得所谓何为父性,在日本从来没有存在过。大家经常说“父性的衰败”,可其实本来就没有啊。我读过一本书叫《虐待和亲子的文学史》(平田厚著,论创社,2011年),里面提到所谓严父的形象,其实是明治三十年之后人为创造出来的。
水无田:这倒是能理解。
斋藤:《逝去的世界的模样》(渡边京二著,苇书房,1998年)这本书里写过,之前的日本社会对女性没有任何压制和束缚,可以说是理想的育儿环境,连欧美人都表示羡慕,但这种环境随着快速的现代化而消失了,所以称之为“逝去的世界”。这本书里还提到,现代化的宪法被引入后,家庭制度得以定型,父权制这种东西也被人为创造出来,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虐待儿童的情况,文艺作品也出现了这类题材。
水无田:真是影响深远啊。
斋藤:虽然有战前的黑暗期这个说法,但战前也有很多不同的时代。如果说是明治三十年之后的时代产物,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才出现的传统罢了。
水无田:说起明治三十年代之后,还真是标志性的时代。那时候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令,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未婚女性成为一个醒目的社会阶层。当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最为盛行的年代,作品中出现了大量身着褐红色褶裙,还有穿着类似制服的女性,也许是男性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再加上国家的现代化,男性对于之后如何体现自己的父权感到了压力,于是出现 了所谓萝莉控趣味的倾向。也正是这一时期,田山花袋创作了《少女病》这样的作品。之后,贤妻良母的说法也出现了,还成了女子学校教育思想的基础。
斋藤:就是这样。
水无田:其实也可以说,贤妻良母、萝莉控的说法和少女趣味,以及随后出现的父权制的强化和虐待儿童的现象,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斋藤:还真的是里外呼应啊,恋母和萝莉控尤其如此,两者在特别深层的地方其实是相通的。用精神分析的说法就是,“想去保护”萝莉的心理和“想被保护”的恋母心理可以简单粗暴地相互替换。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基础正是明治三十年代之后的快速变化带来的。所以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感觉,妈妈和女儿之间有点别扭的关系实际上是这种变化的副产物,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婴儿潮一代的母亲和她们现在三四十岁的女儿,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如果是之后的几代人,我反倒一下子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水无田:可能真的是这样,欧美的情况如何呢?
斋藤:说起欧美的话,我读过几本剖析这个问题的书,但大多数都把妈妈和女儿的关系当作普通的亲子关系来看待,没有做特别区分。卡洛琳和娜塔莉写的《所以妈妈和女儿难以相处》(夏目幸子译,白水社,2005年)在法国成了畅销书,但精神分析的书都没有时间概念,这种框架写出来的书,也不会明确写出何时出现了我们说的母女问题。
水无田:是这样啊。我印象中,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做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比例比较高。
斋藤:我印象中也差不多。
水无田:日本的情况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吧,随着婴儿潮一代经历结婚生孩子等一系列家庭活动,女性做家庭主妇的比例也达到了最高。那一代人和她们的孩子,也就是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之间的关系的确相当别扭,这也是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
而且,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是失去的一代。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在同年龄段的男性中找到像自己父亲那样有一定经济实力、能买得起房子、可以完全负担得起育儿成本的丈夫,可选择的范围实在太小了。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差距,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差距最大的两代人,可能就是婴儿潮一代的母亲和第二次婴儿潮一代的女儿之间吧。
斋藤:是啊。我的实际感受是这个代际差的“下限”还可以往前倒推二十到三十年,她们也是最容易有母女问题的两代人。
水无田:如果是儿子的话,就不得不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毕竟“经济情况变得拮据了,双薪家庭也力有不逮”。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就是现在不到三十五岁的人,正好是男女双方都必修过家庭教育的一代,他们一定程度上对做家务这件事没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
刚好就是三十五岁往上的这代人,三十多岁,四十岁这代人的境况最为严峻。女性的家庭责任仍旧相对繁重,而同年龄段的男性还保留着“昭和男儿”的做派,可偏偏又是失去的一代,这一代男性没办法像自己的父亲那样赚大钱。雪上加霜的是,母亲们还有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希望自己的人生得到肯定,于是希望女儿能理解自己的价值观,并对这样的价值观进行再生产。三十岁后半到四十多岁的这代女性,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而更加辛苦吧。
斋藤:我也有一样的感受。比婴儿潮一代年长的母亲们,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过战后民主主义教育,表面上男女平等,但实质上还保留着男尊女卑的行为模式,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别悬殊。之后发生的变化就像我们刚刚指出的,家庭的构造不再以夫妻为单位,而是以母子关系为主,父亲被疏离在关系之外,夫妻之间也很疏远,那么母亲要从哪里获得认可呢,只能和孩子相互依存。于是她们在育儿的过程中渴望得到自我认可,渐渐就和孩子难舍难分了。
日本十八岁至三十四岁这个年龄段的单身男女和父母同居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左右,和韩国不分上下,在国际上属于相当高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寄生虫问题。能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一个因素就在于母亲难以离开孩子,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于是孩子难以从家里独立出去。如果和父母同居的关系长期维持下去,那彼此会不会亲密过头,就像锅里的水煮干了一样。
失去的一代是就业特别困难的一代人,更容易出现和父母住在一起,甚至依赖父母的倾向。如果能从这种依赖里跨出一步,或许能稍微客观地看待亲子关系,但跨出这一步似乎非常困难,同居的状态也就一直无奈地保持着。这一点正是蛰居族现象存在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是母女关系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朝着一卵性母女关系发展的原因吧。和父母同住的比例如此之高,今后会如何演变呢?我对此十分关注。欧美的话,新教文化圈国家里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年轻人和父母同住,但天主教文化圈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个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十,蛰居族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水无田:是啊,现在在意大利也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还有少子化的问题。
斋藤:是的,也是寄生虫问题引起的。
水无田:意大利语中的妈宝男吧?
斋藤:对,还有母亲崇拜。
水无田:我听了一些案例后,感觉比日本的情况还要严重。
斋藤: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意大利的恋母是十分尊敬母亲,而日本的恋母是对母亲施加暴力。
水无田:就像斋藤医生您指出的,男性的人生往往要求与社会产生联系,但我在想,今后女性的人生也会被要求这一点啊。
斋藤: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对女性社交技巧的要求比男性更高啊,有时候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小孩子中间不是就有类似“女子会”这样的活动吗?
水无田:这一点确实如此,同时男性对双薪家庭的需求也变得强烈了,找同类人结婚的需求也相应提高了。他们希望找到学历和职业地位与自己差不多的对象,女性同时也在捕猎好的结婚对象,这样一来,当前的时代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斋藤:在同一个阶层找对象。
水无田: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是,阶层差距比性别差距更大。
斋藤:先不说好坏,我现在模糊地感觉欧美的阶层意识还没有在日本定型,今后会朝着这个方向变化吗?
水无田:是的。不仅仅是社会学学者,只要是研究涉及家庭、性别问题的人,都必须考虑更多阶层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正面剖析阶层的书往往会触碰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很难写出来,只能以贫富差距问题的形式来处理。
斋藤:山田昌弘老师的书就很畅销,有段时间还出现了一系列围绕差距展开的讨论,比如幸福差距和教育差距等。
水无田:社会对差距的敏感都到这一步了呢。然而,读这些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一点也不想接触和自己不同阶层的人,甚至彼此讨论这个话题本身都是禁忌。另一方面,我觉得社区的社会资本还是由家有学生的母亲们在承担。考虑到社区里接地气的生活实感,还有大家共生共存的社区形态,就会明白把孩子送到公立中小学的母亲们的部分认知很先进,这很让人意外,但也有一部分难以变通,深深扎根在脑海中。
母子之间的问题就是如此,因为日本社会的基础里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在被语言描述出来前就作为“常识”固定下来了,我觉得只有先消解这些东西,改变才会相应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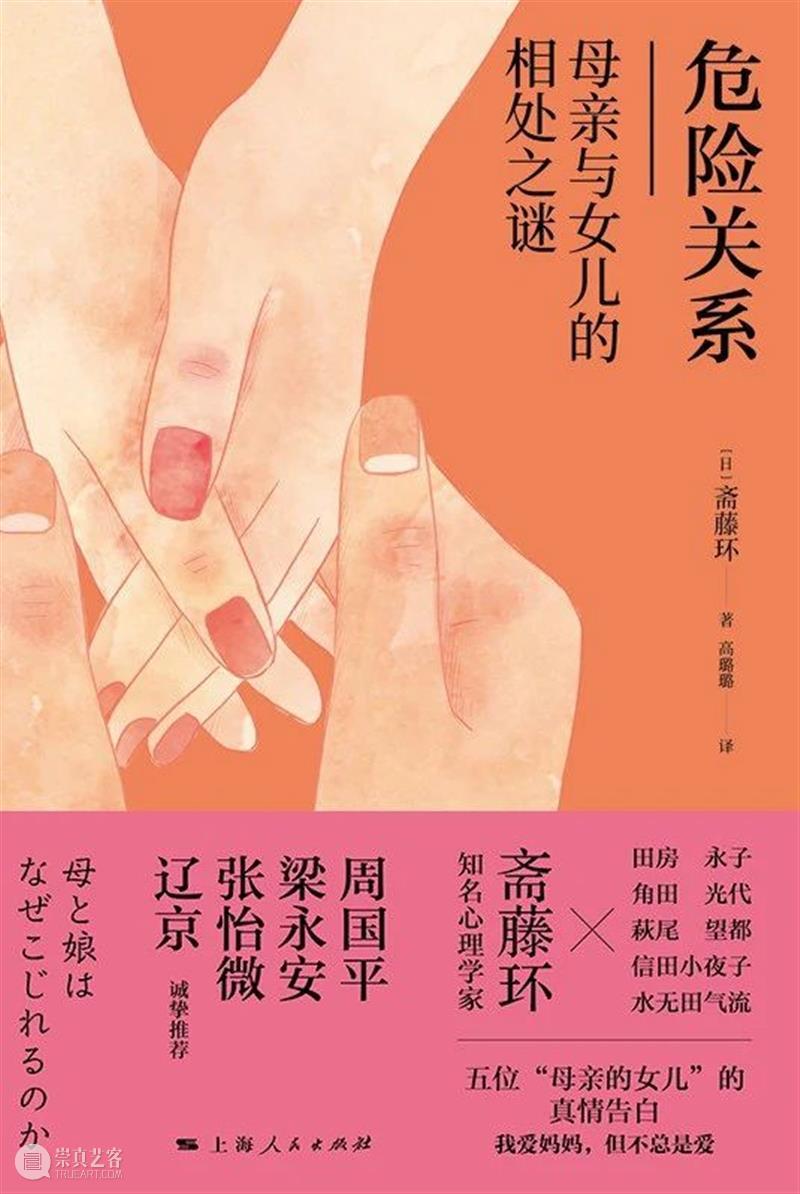
顽固的日本家庭主义
斋藤:说到家庭的形态,好像也给人顽固不化的感觉。
水无田:是这样的,我感觉还是在延续三十年前那套标准化的东西。我在很多场合就家庭问题做过发言,但收到了很多强烈批判和反对的声音。
斋藤:是吗?这么保守倒是出乎意料。
水无田:我和其他专业的年轻社会学学者讨论信息社会学或者媒体论的时候,经常被他们说,“水无田老师,有关IT的知识啊,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尤其是大叔根本不懂,他们最多敷衍一句,还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水无田老师说的有关家庭和女性问题的言论,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不利嘛。因为他们会感觉自己平时生活里接触的,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被批判了。”
斋藤: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吗?
水无田:从专业分类来说,大家对家庭似懂非懂,或者说这个问题太庞大了很难分析……尤其是我在后来一次次认识到,大家对女性社会学学者说的话有很大的抵触感。
斋藤:这倒是有点让我意外,会被抵触吗?
水无田:到现在都有很多。我觉得抵触也是回应,还算是好事。可能他们自身有不安的感觉吧,才会对我批判和抵触。或者不如说,有一些阶层的人希望眼前的生活不要发生任何变化,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会有恐惧感,因为他们的观念顽固不化。所以说家庭真的很难去直面,更不用说日本的母子关系是那么坚固。
斋藤:没想到母子一体化从而疏离父亲的家庭结构现在还是这么顽固,但我觉得有一点发生了变化,从临床现场的观察来看,母亲对孩子似乎没有抓得那么紧了。
尤其是治疗青春期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婴儿潮一代之前,也就是六十岁以上的那一代母亲还会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去守护孩子,先不说好坏,她们的这种观念只是顽固而已,但到了往下的一代人,抓住孩子的执念就淡化了很多,她们会对孩子说“之后全部靠你自己了”。如果孩子住院了,年龄大的那一代父母会担心得每天都来探望,直到孩子烦得说“你们不用来了”,但父母越年轻,就越倾向于把事情外包给专业的人做。还有家庭内部暴力的问题,上一代的母亲哪怕被孩子施暴,被打被踢也还是会照顾孩子,但往下一代的母亲就不这么想,她们会直接离家出走,或者不管孩子,有这样的行为趋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水无田:就是说,像《积木塌了》里那种孩子发疯了,对母亲又打又踢,母亲还忍受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上一代了?
斋藤: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不是到了某一代人,很难有这样的觉悟,当然,不好听的说法是,这样的父母渐渐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但我觉得这和欧美的个人主义又很难挂钩。
水无田:是这样。大概是2000年之后吧,舆论突然开始宣扬个人主义的自我责任和自我决定论,新自由主义的倾向也越发明显,但个体作为最关键的核心还是没有得到尊重。
斋藤:完全没有尊重呢。自民党一直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但宪法的提案里又出现了奇怪的解释,说“权利和义务是一套组合”,赤裸裸地否定了天赋人权的说法。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还是回到了农村社会的理论,逻辑有点像“只要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可以在社区里预存恩惠”。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是自我责任论。
水无田:但另一方面,比如接受生活补助的话,又要先确认三等亲的亲戚不能提供援助,在奇怪的地方又出现了家庭主义。
斋藤:家庭主义难道不是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吗?我觉得日本的政策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以贯之的家庭主义。
水无田:日本型福利社会是这样。
斋藤:对弱者的保护也经历过一直推脱给家庭的阶段,比如精神障碍患者直到战后的一段时间,都还一直被关在自己家里一也可以说是禁闭室。直到昭和三十年代·,大医院多了起来,这样的情况才慢慢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高龄老人的问题。照顾老年人也推向了家庭责任,之后有看护保险才勉强好一点。现在又轮到了年轻人,给人感觉蛰居族的问题也应该由家人自己处理。
水无田:而且,一旦家里有蛰居族,大家很容易去责备父母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尤其会责怪母亲的不是。
斋藤:是啊,现在还会这样说。闭蛰居族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三十二岁,完全是成年人了。日本这个群体的数量几乎相当于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不过数据还有待证实。据说英国的青少年流浪汉大约有二十五万,而美国有一百万人以上,日本的青少年流浪汉还不到一万人。至少数据上是这样的。
水无田:网吧难民这一类人呢?
斋藤:据说大概只有五千人。如果是露宿街头的年轻流浪汉,数量对比起来更是少得多。那些不适应社会,或者反过来说,被社会淘汰的年轻人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家里。
水无田:但是,父母的状况会越来越差吧。
斋藤:您说得太对了,而且日本现在无家可归的不良少年好像越来越多了。从某种不好的意义上说,我预测日本以后在这方面也会朝欧美的方向发展,大概十年内蛰居族人口就会达到顶峰,其中大多数都是无家可归的不良少年吧,但其实现在多多少少就能看出这样的前兆。
水无田:我明白。还有一点,蛰居族的男性数量更多,但说到无家可归的问题,近些年的网吧难民里,年轻女性增加了不少。听说涩谷那一带的网吧里,年轻人尤其多,几乎占到了一半。其实全年有收人的女性中,到手不足三百万日元的有七成,雪上加霜的是一半女性都处于非正式雇佣状态。如果没办法像过去那样通过结婚被家庭保护,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瞬间跌入无家可归的处境。
斋藤:是这样。即便还没有沦为街头露宿者,但从网吧难民的意义上说,也有可能引发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流浪汉问题。
水无田: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有年轻女性离家出走后,在论坛里发帖子,“今晚请让我住你家”。
斋藤:会的。找一个“保护”自己的男性,要多少有多少。
水无田:所以很多时候也很难认定她们算不算无家可归的人。那些从家里跑出来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家暴,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在精神方面有问题,这样的情况都有。包括刚刚提到的大阪丢弃二孩事件,是家庭会议决定了不给亲生母亲提供任何援助,作为当事人的被告当时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处于不能好好保护孩子的状态。可即便如此,她还是要履行妈妈的责任,这已经是多问题家庭,或者说综合问题家庭的话题了。只要细看家庭问题,会引出很多交织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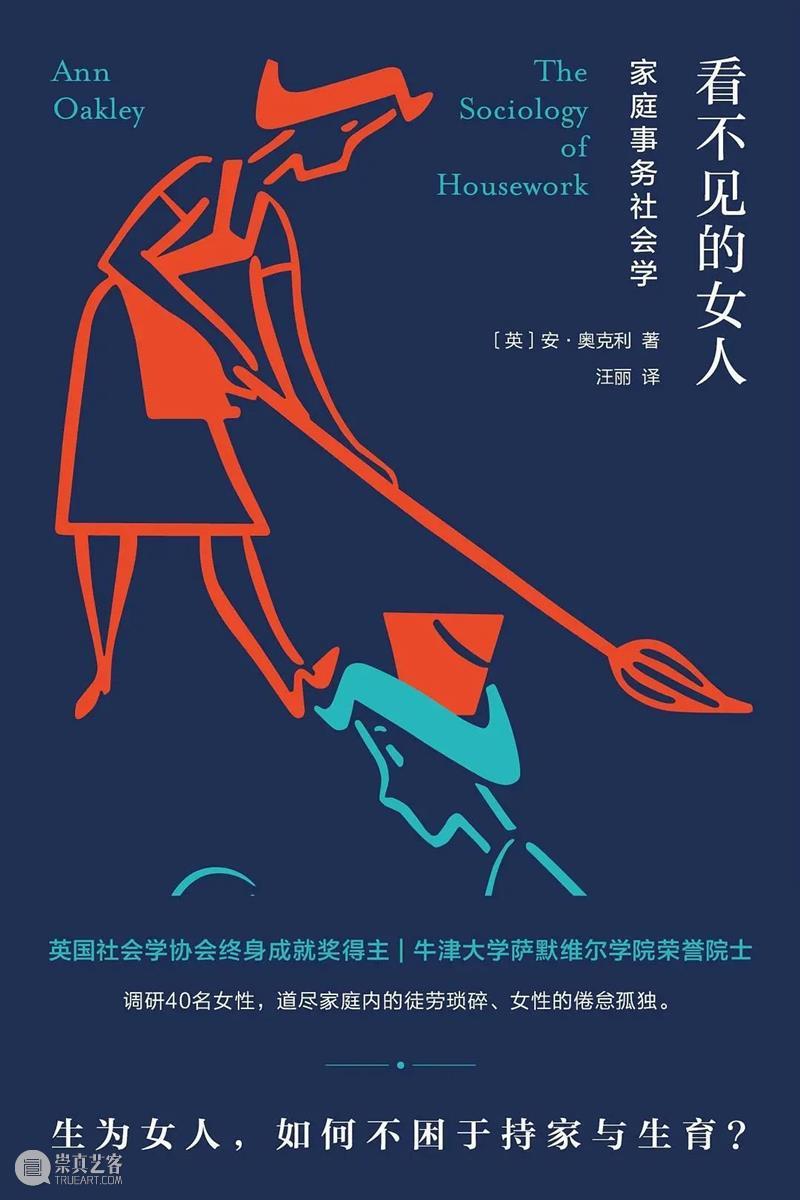
家务的外包化
斋藤:最后想请教您的是关于具身性的问题。在养育男孩和女孩的过程中,我会想象在具身性的教育上两者是不是有不同之处,了解到水无田老师母亲的育儿方式后,感觉您受到的是偏向男孩的养育,但这种教育似乎并没有在您身上留下什么问题,您自己的感受呢?
水无田:母亲毕竟拿过家庭科的教师资格证,她教了我做饭、裁缝这些技能。
斋藤:是作为生活技能教的吧。
水无田:是技能吧。而且,某些情况下还是按照体育训练那种风格进行的…比如我的手不小心被针扎了,或者被剪刀割伤了,她会说“这点小伤不用管也会好,但你剪坏的布就没办法修复了”(笑)。她教我做饭也像做科学实验,比如告诉我食物和渗透压的关系,从分子结构告诉我应该按什么顺序加调料,还从蛋白质的特性教我如何调整温度,完全就是技术训练。
斋藤:原来是这样。或许用这种方法彻底教会您技能,反倒不容易产生矛盾吧。您和母亲之间会不会相互借对方的衣服穿呢?
水无田:我读初中之前,穿的衣服大多是妈妈手工缝制的。我们基本没去逛街买过衣服,而是去布料店买布料。她会一次性买很多便宜的布料,想好“理惠子的衣服用这一块,妹妹的衣服用这一块,我的用这个”再开始做衣服。
斋藤:这样不是很好吗,和换衣服穿的感觉会不一样。
水无田:不一样。当时有很多布料店,妈妈一边买一边教我们如何搭配布料的种类和用途,如何挑选。那时候是昭和四十几年吧,母亲还自己做衣服。
斋藤:也自己打板?
水无田:是的。妈妈定期购买《DressMaking的可爱童装》,在目录里选自己想穿的款式,再按照原样做出来。布料也好食物也好,妈妈是那种能立即计算出成本的人,她一直说成品的童装比自己用布料做贵太多了。她偶尔也给我买成品的衣服,但把里子翻过来一看,说“哎呀,这个里子的做工不行啊”,又退回去了。然后说,“一样的款式,我做的比卖的更好”,结果她做出来的真的比成品还漂亮。
斋藤:我发自内心觉得,您母亲在各方面都技能精湛。
水无田:从作为母亲需要的技能来说,我的确比不上她。也正因为如此,坦白说,我从没想过要成为她那样的母亲,我也做不到。
斋藤:我觉得技能方面如此能干的话,某种程度会不会是压抑的产物,您觉得呢?
水无田:技能水平真的太高了,几乎是专业级别。
斋藤:某种意义上,她也给人感觉做到了母亲的专业级别。
水无田:说句极端的,就好像父母是厨师的话,自己绝不想在家里做一样的饭菜。
斋藤:意思是水平过于高超了。这些技能其实也不全是从外婆那里继承的吧。
水无田:有一些不是外婆那里学的。妈妈上过西式缝纫学校,日式缝纫好像和外婆学过一些,但我听说她的技能基本上还是在短期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的。
斋藤:等于是外部习得的技术。
水无田:当时那个年代,刚好也是新娘培训课程商业化开始的时期吧。
斋藤:已经商业化了啊,其实商业化挺好的。如果是代代相传的模式,外婆传给妈妈,妈妈再传给女儿,越依赖这种方式,这个过程中就越容易产生冲突。
水无田:妈妈那一代人恰好比婴儿潮一代年长一些,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家务和新娘培训课程开始朝商业方向转移,妇女杂志和料理教室里经常能看到这类信息。也是那个时候,大家不再局限于传统食物,开始自己做洋食,《生活的手帖》(生活的手帖社)也会刊登法式酱汁的配方。感觉战后有一段时间,家庭料理的概念被颠覆了似的。所以那时候妈妈在料理教室学的东西比外婆教给她的传统味道更丰富。
斋藤:当时是不是很常见呢?
水无田:是吧。
斋藤:大家都这样吗?
水无田:回想起来,妈妈在短期大学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样但我老家一带的母亲们似乎不是。妈妈之所以被家里兴致勃勃地送去学校学习新娘培训课程,可能还是因为她算是大家闺秀吧。
斋藤:是啊。我听了您的分享后想到,性别教育还是需要通过技能学习的商业化,用公开的形式来实现,而不是母女相传的模式,这或许也是避免冲突的秘诀吧。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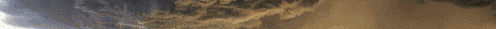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