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能
姚云帆 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在西方思想史之中,潜能这个概念可以用多种词语来表达:例如,潜在、潜能、能力、或然性,和可能性等等。但是,无论何种表达,人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概念:第一条思想路径从属于数学和逻辑学意义上的“可能性(Probability)”问题,第二条思想路径从属于物理学上的“潜能(Potentiality)”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更关心可能性问题。柏拉图区分了“真理(Aletheia/Truth)”和“意见(Doxa)”;前者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而后者是看似真正的存在。在《智者篇》中,他把这种看起来真实的存在理解为可能的存在(Sophists. 370d, 371a; Clt. 407e, 408e, 410d;248a, 249+, 254a, 261e+)。这就是可能性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中第一次被系统表达。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能性问题被转化为潜能问题。他指出,特定事物真正的存在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质料,第二个层次是形式。质料蕴含着产生事物真实形态的潜能(Energia),而形式则将这一潜能转化为动能(Dynamis),造成了事物为我们所看见的样子(Physics. 201a30-35) 。例如,青铜矿作为一种质料,其硬度和质地有制作青铜雕像的潜能;当这个潜能转化为真正动力之后,青铜雕像就完成了。在柏拉图看来,看似真的存在是真存在本质属性的分有,是真实存在数量和性质上的偏离和扭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偶然存在,一切偶然存在,都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潜能存在,只要这一潜能存转化为现实,事物就会呈现为现实上的存在。
但是,亚里士多德通过物理学手段处理逻辑学问题造成了一个矛盾。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看出了这个矛盾。阿甘本发现,如果潜能也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和实现的存在具有同样的地位。因此,如果潜能通过实现自身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这个现实存在应该是潜能自身;可是,潜能变成现实,它就不可能成为现实(Metaphy. 1046a32)。这时,现实既不是潜能,又是潜能,在逻辑上,这是矛盾的。

亚里士多德潜能学说造成的逻辑矛盾,在古希腊哲学中虽然很重要,但真正的影响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试图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解释万物的存在基础,他的潜能-实现学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在解释“上帝”的存在时,这一学说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上帝是世界万物的来源,因此,他应该是让万物存在的潜能;但是,没有上帝,万物无法存在,那他应该是最真实、最现实的存在。经院哲学家们由此发现,亚里士多德所造成的矛盾引发了上帝存在的逻辑矛盾:他既存在,又不存在。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就是阿拉伯哲学家阿维罗伊(Ibn Rushd)。他在论述伊斯兰真神“安拉”存在的哲学依据时,他将这一造物主的实质看作纯粹的潜能,通过潜能的无限实现,造物主创造了世界万物。当这一学说引入基督教世界之后,让人们知道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阿威罗伊已经早于阿甘本发现了这一逻辑矛盾,他的思想虽然被基督教世界看作异端,却对斯宾诺莎以后的现代潜能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宾诺莎是现代潜能学说的开启者。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试图改造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学说。他第一次将潜能看作驱动世界整体运动变化的能力(Potentia),而不是特定静止的目的和形式。由此,只要世界不断变化运动,潜能的实现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这样潜能和现实的矛盾似乎得到了解决。
斯宾诺莎的看法启发了尼采和德勒兹。通过引入“永恒轮回”这一概念,尼采强化了斯宾诺莎“能力”概念的内在性。尼采认为,潜能实现自身的方式不是对事物位移和形态的驱动和改造,而是一种对运动自身的重复。斯宾诺莎将世界整体看成“神”,从而为潜能的实现保留了最后的稳定形式。尼采认为,这个形式本身也在不断重复运动中走向差异。德勒兹受到斯宾诺莎和尼采的启发,他发现:在空间上,潜能的实现在空间上外在于潜能,它通过“逃逸线”和“解地域化”的方式,让潜能从规范的社会空间中逃离出来,从而证明潜能“尚未被穷尽”;在质地上,这一实现必须不同于耗尽潜能所造就的现实。这就好像卡夫卡的小说《耗子歌手约瑟芬》中女耗子的歌唱,声音怪异,无法被人听到,不像人们心目的文艺形式,却又在歌声之外成为歌声,在艺术之外成为了反艺术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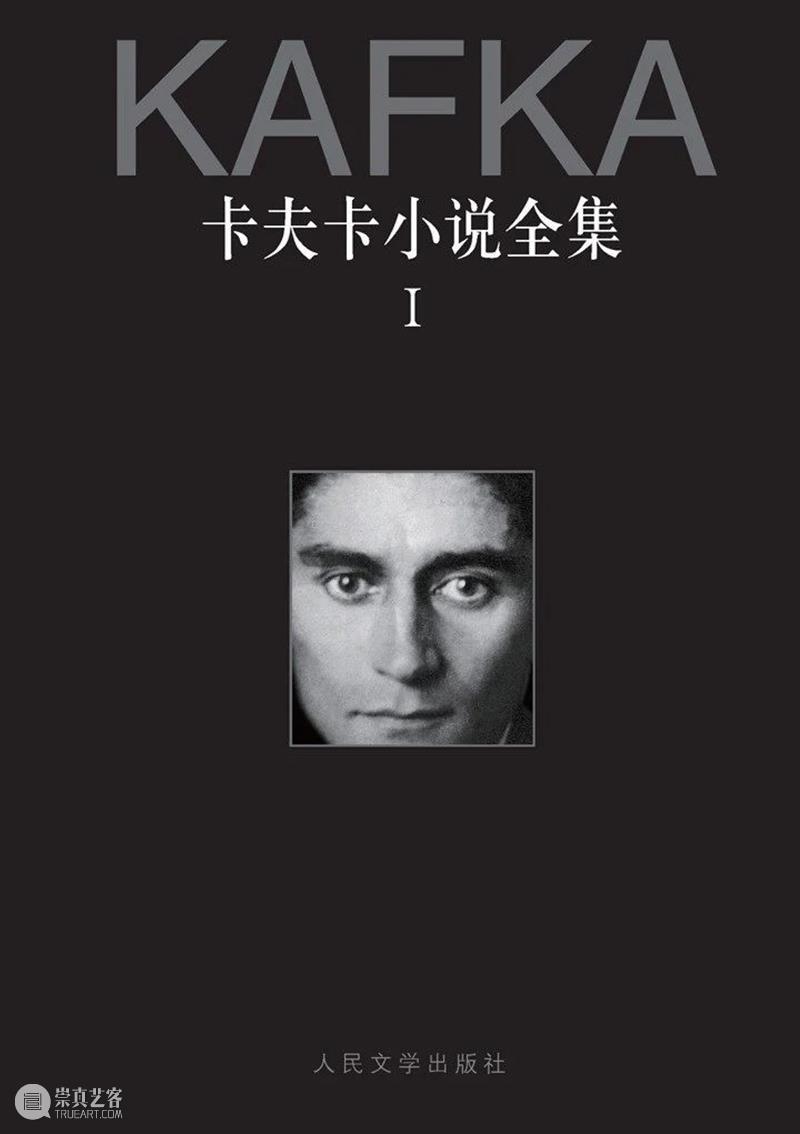
阿甘本则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潜能和实现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斯宾诺莎、尼采还是德勒兹,都将潜能“大于”或“多于”现实看作潜能得以实现的表征;但是,他却认为,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并非一种“大于”或“多于”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由此,阿甘本再一次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悖论本身。他指出,如果潜能真正要在现实中实现,就必须维持其潜能状态;这也就是说,潜能必须通过一种“非现实”的,不为我们所见的方式保存在现实之中,而不是以一种不断运动的“超出现实”的方式为我们所见。他以俄罗斯诗人阿赫马托娃对自己著名诗集《安魂曲》诞生过程的描述来论证这一点。阿赫马托娃回忆道,当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等待因为“政治问题”而杳无音信的儿子的下落时,一个同样等待亲人的妇女突然问她:“你能说出这种感觉吗?”阿赫马托娃长时间地保持沉默,然后说了一句:“是的,我可以。”
诗人的这句回答包含着奇妙的矛盾:一方面,她用言语和诗歌来表达等待儿子时的复杂感情:焦灼、盼望、悲伤和压抑等等;另一方面,她的沉默标记了这种情绪的不可表达性。只有当这种处于潜能状态的不可表达之物,内在于她的诗歌表达之中,她才能真正表达她想说的东西。因此,阿甘本发现,真正的潜能并非试图超越现实形式和规范的改变性力量,而是内在于现实的沉默和否定。他进而把这一看法应用于政治哲学领域,并用它来解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主权权力”。
从语源学看,英语“权力”这一概念来源于拉丁语“力量(Potesta)”,后者正是希腊词“动能”的拉丁语翻译。因此,在阿甘本看来,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都是特定政治潜能的实现。主权权力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国家中一切政治潜能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主权权力的完全实现,恰恰来源于对现存政治权力形态的否定和悬置。这和潜能的实现必须是它的“不实现”基于同样的原理。这种对既定政治权力结构的悬置产生了两种可能性。在第一种可能性中,一种更具实体性的主权权力,替代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控制,形成了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说的例外状态。在阿甘本看来,这只是用一种潜能的实现方式对其它实现方式的否定,尽管,这也间接阻碍了一部分潜能的实现,让其转换为某种“非潜能”。在第二种可能性中,潜能成为了彻底的“非潜能”,它永不试图化身为稳定的权力形式,反对任何稳固的政治秩序,却反而成为本雅明所谓的“纯粹律法(Pure Law)” ,不断维持自身创造全新政治运动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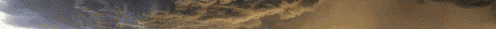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