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托与精神分析和哲学的相遇
——拉康对阿尔托的(非)阅读
雅克布·罗格辛斯基 文,赵天舒译,卓悦校
原文载于《上海文化》,2023年第7期
感谢译者授权
摘要:“疯癫诗人”阿尔托,曾陷入谵妄中无法自拔,并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根据拉康的诊断,这种精神病让阿尔托弃绝了父名,抹除了自我的身份认同。由于该过程不可逆,因此精神医师断言诗人无法再次提笔写作。然而,阿尔托走出病院、重新进行诗歌创作并以姓氏署名,却揭示了拉康精神病理论的缺陷,即谵妄之人的一种反弃绝、通过写作战胜精神病的可能性。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了诗人晚期使用妄语所作的诗歌之中,体现在那些神秘得近似咒语、却又不断将自我之名锤炼成音节的诗句上。
雅克布·罗格辛斯基(Jacob Rogozinski),法国著名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曾任巴黎国际哲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科研项目主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于200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接替让-吕克·南希的职位,并在此执教二十年。
本文为雅克布·罗格辛斯基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所做的关于阿尔托的线上系列讲座第一讲,讲座题目即为本文标题,讲座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 译者赵天舒,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卓悦,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法国作家之一。身为诗人、演员与导演,他尤以戏剧理论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其著作《戏剧及其重影》(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 1936)深刻革新了戏剧艺术。他同时也对当代法国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莫里斯·布朗肖、茱莉亚·克里斯特娃、雅克·德里达都分析过他的写作与画作,吉尔·德勒兹则将之视为“诗人们的基督,就像斯宾诺莎是哲人们的基督一样”。他之所以会如此具有魅力,也是因为他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形象(figure),即“疯癫诗人”(poète fou)的形象。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自阿尔托以来”,疯癫(folie)已成为“文学语言所趋近的场域”。事实上在1937到1946年间,这位诗人曾被关进不同的精神病院中。在罗德兹(Rodez)的病院关押期间,他终于从自己的谵妄(délire)中走了出来,重新开始写作并署自己的姓名,这让他得以离开病院,重回巴黎近郊生活。在荷尔德林、奈瓦尔和其他作家与艺术家之后,他的经历再次让人审视疯癫与审美创作之间的关系。正如一条始于柏拉图、在浪漫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身上重现的传统所认为的那样,疯癫是否是艺术作品、尤其是诗歌的终极源泉?德勒兹便坚持这样的立场,他断言阿尔托的“精神分裂”(schizophrénie)是后者写作极端激进特质的基础。又或者恰恰相反,疯癫就像福柯所断言的那样,是“作品的缺席”,是其崩塌之点,是其不可能的状态?
我想在这两场讲座上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以便向贵国的知识界听众介绍阿尔托。在这第一讲中,我讨论的内容将涉及精神分析(psychanalyse),尤其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后继者之一雅克·拉康的理论。我将尝试说明阿尔托的生涯轨迹、他历经并走出谵妄以及他对写作的回归,也许证明了拉康精神病(psychose)理论的某种缺陷,但也想说明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得以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艺术与疯癫之间的关系。在第二讲中,我将讨论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Logique du sens, 1969)中对阿尔托进行的所谓“精神分裂”的分析,也是在这本书中德勒兹第一次提出了“无器官的身体”(corps sans organes)这个将在他的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概念。我会谈到德勒兹在他后来的作品,譬如《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和《千高原》(Mille Plateaux)中对这个概念的重塑,也会说明哪怕他的理论看似与拉康的思路方法截然相反,却也同样曲解了阿尔托作品的意义与影响。

阿尔托
自孩提时代起,阿尔托就患有各种疾病,表现为剧烈的头痛与其他类型的躯体疼痛,并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出现抑郁状态。我们不清楚这些症状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未经治疗的婴儿脑膜炎?遗传性梅毒?伴有躯体症状的精神紊乱?……——然而这些并不重要。我们要避免做出某种医学或精神病学诊断,因为这种诊断有可能将阿尔托的症状限制在疾病分类学范畴当中。反之,我们应当尝试去辨别这种“病症”对他的存在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他的病症使他很早就多次入住诊所,接受不同的精神治疗,并服用会进一步影响他健康的药物。这些病症还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精神紊乱,阿尔托自己将之形容为不能以连贯的方式组织他的思想。他将之称为一种“中枢崩溃”,一种让他的思想被撕裂的“痉挛”,一种“肢解”、一场“受难”、一个“分肢与解体的可怕温床”。这种“思维要素的异常分离”阻碍着思维“在成型过程中获得实体”,进而导致了阿尔托体会到一种剥夺之感,仿佛“某种鬼鬼祟祟的东西”偷走了他的思想和话语。由于在他的语言与身体、在他的思维与生命之间造成了某种分裂,这种疾病让他觉得他的生命正在弃他而去,从而让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一个幽灵、一尊“木乃伊”,让他的诗歌变得好似“幼虫”、好似夭折的废物一般。他在他早期的书作中,尤其在他《给雅克·里维埃尔的信》(Lettres à Jacques Rivière,1924)中描述了这些。这部书是阿尔托与文人里维埃尔之间的通信集,后者是《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主编,彼时刚刚拒绝了发表阿尔托的诗歌。就像随后发生的情况一样,诗人通过向里维埃尔讲述自己写作的困境,设法将这次失败转变为了某种“成功”。他后来在论及自己早期作品时写道:“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是通过写一些书来表达我根本写不出任何东西,每当我有什么想说或想写的内容时,我的思维却完全将我拒之门外……在当时的我看来,我的书充斥着裂痕、缺陷与陈词滥调……但是20年过去后,它们却让我感到目瞪口呆,其成就与我无关,而是关乎那无法被表达的东西。”[i]
将使阿尔托免于绝望——也许同时免于自杀倾向——的,是他与诗人安德烈·布列东、以及同参与后者所创立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其他成员的相遇。他尤其欣赏这些作家那种名为“自动写作”(écriture automatique)的书写方式。布列东在首篇《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 1924)中将之形容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通过这种活动……来表现思维的真实运作方式。(这是一种)在排除了一切美学或道德顾虑、在没有任何理性控制的情况下,对思维的呈现”。这种取消一切逻辑与句法限制的做法,让阿尔托接受了他自己在清晰表达思想方面的困难。正如他后来所写,“超现实主义无法让我找回某种已经遗失的东西,但是它教会我不再去在思维活动中寻求一种对我而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连续性”(I-2, p. 67)。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者的相遇也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了他。布列东及其友人们那套充满革命性的修辞,他们对挑衅与谩骂的使用都将向他展示出,如何才能把这啃噬着他的痛苦通过投射到外部对象之上而弃置于自身之外。从此时起,那些曾经用来形容他生命中所遭受的劫难的词汇(碾碎、阉割、幼虫、木乃伊、挫败……),开始出现在他以“超现实主义研究局”(Bureau de recherches surréalistes)的名义所发起的种种激烈的攻击当中,其攻击对象包括权威的所有代言人、教皇与大学校长们、文学评论家们与疯人院的主治医师们。他还在《超现实主义革命》(La Révolution surréalist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宣言,肯定了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彻底解放精神的方式”,“是精神发出的呐喊,因为它要回归自身、决心不顾一切地粉碎自己枷锁/必要时会抡起物质的巨锤”(I-2, p. 30)。
阿尔托于1927年突然不再参与超现实主义团体,因为当时布列东、艾吕雅和阿拉贡开始和法国共产党过从甚密,并将他们杂志的标题改为了《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可阿尔托拒绝让艺术创作屈从于一个政党的指令,并批评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对某些人造偶像的崇拜与对共产主义的奴颜婢膝”。因此,他仍然忠于他所谓的“艺术的社会无政府状态”(anarchie sociale de l’art)。这个表述需要从它的词源上去理解:“an-archie”,也就是无arkhè,无那种企图将自己强加于艺术之上的指导原则或外部权威。实际上,阿尔托认为社会转型不足以解放全人类。相对于超现实主义者们通过法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与政治介入,他则提出了一种属于“高级革命者”的观点,拒绝将革命约简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单纯的权力转移”,反之则认为“痛苦与恶的真正根源更加深远”(II, p. 25),源自于一种生命本身所患的病症。这就是为何他呼吁一场“全面革命”,一场如阿蒂尔·兰波所愿的、能够“改变生命”、彻底颠覆我们生活与思考方式的革命。几年之后,他还宣称“社会革命只是全面革命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因为“若没有文化革命,即如果我们不对理解生命的方式、不对质疑生命的方式进行革新,那就没有革命”(Œ, p. 733)。因此他与其他异见者,譬如作家乔治·巴塔耶一道,被驱逐出了超现实主义团体。
自此,阿尔托开始孤独地继续他的旅程,力图在艺术中寻觅能够“治愈生命”的良药。当他在其1936年宣言般的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断言“没有比戏剧更佳的革命工具”时,他赋予戏剧的任务是创造一个集体治愈的场所,创造一种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共同体(communauté),或更确切地说在二者之间创造一种共融(communion),一种将会使观众转变为“激动不安的信徒”的神圣的感染(contagion sacrée)。这一切仿佛意味着,阿尔托将他个人疾病的主要症状搬移到了集体的层面,他现在开始将其个人病症视作整个西方文明的病症,将之呈现为“一个从未与生命接轨的文化”的崩塌。这就可以解释他对于东方戏剧、尤其是巴厘岛戏剧的浓厚兴趣,他专门为此撰写了数篇文章。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自身存在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分裂:因此,他想要创造的新形式的戏剧——他称之为“残酷戏剧”(théâtre de la cruauté)——将以接合戏剧中通常来说相互分离的部分(舞台与剧场、语言与动作、情感与思想)为己任。他的疾病导致了“他的思维脱离肉体”:而与之相反,戏剧则力图让思维重新道成肉身,将语言、图像与思想重新纳入身体之中。既然这种疾病阻碍思想“获得实体”,那就需要重塑身体,发明一种“情感田径运动”(athlétisme affectif),让演员以节奏与呼吸为中心重建他的身体。因此,阿尔托希望利用戏剧的资源来克服生命与我们分离的问题,他以为这种分离不仅是他自己所遭受的折磨、也是西方世界的极端痛苦与罪恶之根源。
这让他赋予艺术家——尤其是赋予新戏剧的演员——以救世的使命。事实上,他授予艺术家、授予演员的是一种悲剧英雄的角色,其作用是主导一种集体净化(catharsis)。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悲剧特有的功能定义为一种摹仿(mimèsis)(一种“模仿”?一种“再现”?这些术语在此都不足以将这个概念翻译出来),它“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来完成对这类情感的宣泄净化”[ii]。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呢?在古希腊,净化最初指的是一种仪式性的净礼,即暴力驱逐或者杀死牺牲者。阿尔托所强调的正是这种释义,所以他会不无道理地将这个意义上的净化视作是回归古希腊文化、回归古代悲剧的真理,而在当下这种真理已经被扭曲和遗忘了。彼时的布莱希特正在呼吁人们与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戏剧艺术理论决裂,让观众不要像这种艺术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去将自己代入(identification)到角色当中。然而,阿尔托却自视为这一戏剧传统最忠实的捍卫者。根据戏剧净化的传统观念,观众和演员是分离的。如果观众代入到角色当中,这种代入也是充满距离感的,发生于舞台呈现所创造的间距之中,且此类净化只会在观众的意识这一“第二舞台”中完成。反之,阿尔托宣扬一种直接即时的代入,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感染,它能够取消舞台与剧场之间的一切距离:因而他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净化,并因此与戏剧摹仿的一切传统形式决裂。尽管如此,这种净化的极端化却忠实于其原始含义。作为这种净化疗法的载体,演员——以及事实上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牺牲者,一个“代罪羔羊”,其工作是“磁化、吸引从而让游荡于时代之中的种种怒火落在他的肩上,以此祛除时代的不幸”(Œ, p. 731)。艺术家的这一职责让他成为了被社会共同体排斥之人,或用阿尔托后来形容梵·高的话来说,成为了“被社会自杀的人”(suicidé de la société)。正是这种原生的排斥构成了被阿尔托所抨击的一种“针对一切诗歌的宗教式的仇恨精神/它宗教式地、虔诚地、仿佛仪式性地碾碎和翻转,在我们诗人的舌头后面/经我们的整个舌头向口中张开呼吸,翻转/碾碎并翻转了这个火焰点,这个错位的眼睛幽灵/这个古老潮汐依旧燃烧着的浪峰,上面漂滚着埃德加·坡、波德莱尔、梵·高、热拉尔·德·奈瓦尔的巨大头颅”(Œ, p. 1624)
这种排斥与阿尔托即将遭遇的肉体上的排斥是一样的,在随后的八年中,他陆续被关押在了几间精神病院里,有时还会被束缚在紧身衣中,经受诸如电击等暴力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导致他被监禁?日常生活的波折——失败、丧亲之痛、爱情破碎……——从来不足以使人发疯,但正是在这类事情中,一条无形的裂痕显露了出来。阿尔托那可以被称为崩溃或陷入疯癫的事件发生于1937年,彼时他正在爱尔兰旅行,在此他被拘捕并被强行遣返法国,随即入院。他的旅行总是与幻想或神话交织在一起,是后者赋予了他旅行的目的和意义。他离开法国是为了逃离一种绝境,逃离一种将要困住他的陷阱。他排演的一出剧目失败了,他创办的剧团也破产了,于是在1936年他去了墨西哥。根据他自己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仪式与圣药的体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塔拉乌玛拉之国行记》(D’un voyage au pays des Tarahumaras)。为何要去墨西哥?他说是为了去发掘那种“神奇的文化”,发掘那种文化与生命之间紧密的纽带,而这种纽带是西方文明之中极度缺乏的。他希望在墨西哥找到一种原始知识,一种治愈集体的仪式,能够通过将神话的狂野之力与之调和在一起来滋养已经干涸的西方文化。由于思维和生命之间的这种断裂也是阿尔托一直以来所遭受的痛苦,所以通过参与塔拉乌玛拉印第安人的仪式,他同时寻求治愈自己。这便是他在屡屡怀揣激动之情、又屡屡感到失望的过程中不断追寻的。实际上在墨西哥,他开始意识到神话的枯竭,意识到我们不可能返归失落的源起。印第安祭司教导他的,是“上帝已经退隐”,是世界正在黑暗之中越陷越深。而使用乌羽玉这种无刺仙人掌——印第安人的圣药——进行的仪式,正是要祛除这种灾祸,即太阳神在日落之地的无情衰落。但净化仪式总是失败。阿尔托在塔拉乌玛拉人的圣舞中所期待的,是在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假、真理与幻想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因为“乌羽玉会将自我带回到他真正的源头”,让他知道他“在不陷入虚幻之中便无法抵达”的地方是什么(IX, p. 27)。然而很快,诗人就任由自己被某种东西所侵袭,某种“可怕的东西……它并非来自于我,而是源自我身上的黑暗,在这黑暗之中人的灵魂不知道自我生于何处、终于何处”。因此阿尔托至少明白了,这种仪式的终极意义正在不断消逝。他感到“在这一切的背后,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在这之外,还隐藏着另外的东西:那至关重要的东西(le Principal)”(IX, p. 49)。是否是这个从未完全弄清楚的谜团,被他在后来称为“印第安文化最大的秘密”,即那个让“世界归零”和重生成为可能的秘密?正因为它保持了一个谜团的开放性,让诗人得以参与仪式却不被它蛊惑住,所以这次在塔拉乌玛拉国度的旅行并没有以死局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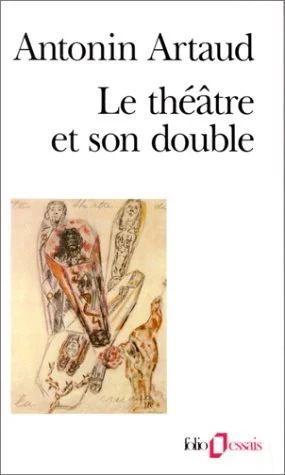
《戏剧及其重影》法文版
回到巴黎后,阿尔托重新开始写作,开始修改《戏剧及其重影》的校样,同时也在准备与一位叫做塞西尔·施拉姆(Cécile Schramme)的年轻女子结婚。正如他在信中对她所写,“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VII, p. 196):而结婚则是最终成功为自己命名,愿意通过让自己变成父亲以将其姓氏传承下去。然而在几周之后,出于不太为人所知的原因,他突然解除了婚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签署自己的姓名”,并命令出版社“把一切会让人联想到(他)姓名的内容删去”。自此之后,“阿尔托”对他而言将只是“虚无的词源名”(XXVI, p. 10)。面对空虚,面对无名的萦绕,他将在随后尝试用其他方式为自我重新命名。和奈瓦尔与塞利纳一样,他将从他的母系脉络中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姓名:从今以后,他将用他母亲的娘家姓氏纳尔帕(Nalpas)为自己署名。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因为这个姓氏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没有(它)(n’a [l] pas)、即对自己不再有姓名这一事实的供认不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决定在1937年夏天前往爱尔兰,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这一次,他所寻求的不是某种具有启示性的知识,而是去物归原主。实际上他想要把一根他的友人赠予他的手杖归还给爱尔兰人民,因为他将其视作圣帕特里克这位爱尔兰的主保圣人的手杖。他会在夜晚将这条手杖——他也称其为孔子的手杖……——放在他和他的情妇们之间,以防止任何肌肤之亲。事实上他将之看做是一种护身灵符,一种驱魔的工具:对他来说手杖的作用是“让那些恶灵保持静默”(XI, p. 143),也许还可以防止他被女性高潮的深渊所吞没。他在爱尔兰遗失了他的手杖,于是便陷入到了以为自己受到迫害的谵妄之中,在多年之后他才会恢复正常。正如一位医生在他的拘禁证明中所写的,他“说别人给他吃有毒的食物,在他的单人囚室中释放毒气,他看到他附近有黑人,以为警察在追捕他,会威胁他周围的人”(转引自Œ, p. 847)……
让我们试着综合这些不同的迹象,并大胆给出一种解读。正是在阿尔托放弃结婚、放弃成为父亲时,他要求将他的署名从他的书中抹除,仿佛他发觉他父亲的姓氏无法保证他的“声名”——即他的文学荣耀与自我命名的可能性——且他能做的只剩去承认与面对这种无能为力。他的爱尔兰之行完全围绕着那所谓的“圣帕特里克手杖”,这并非偶然,因为“帕特里克”(Patrick)这一人名源自于拉丁词语pater,父亲,而正是丢失了这充满阳具意味的护身符才让他陷入疯癫。什么是疯癫?阿尔托给出了如下回答:它“是一种向本质之外的迁移,让人落入到内外的深渊之中”(XI, p. 189)。他具体解释说,发疯就是一个人从他永远是身体性的本质当中被连根拔起:即一个人被放逐出他的自身、他的身体、他独异的自我。是让自己被一个大他者奴役直至失却自己的身份认同,迷失在内与外、我与非我混淆不分的深渊之中。使这种剥夺之感成为可能的是对无名状态的肯定,是同意去抹除自己的姓名、亦即抹除其父亲的姓氏这一绝对被动的、被大他者支配的、然而却是决绝的决定。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神经症(névrose)的原理是某个被压抑(refoulement)在无意识中的心理因素以症状(强迫症、恐惧症、癔症等等)的形式回归。因此它不同于精神病——即以谵妄、幻觉(hallucination)、见诸行动(passage à l’acte)为病症的那类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后者基于的是一种有时被他命名为Verwerfung或“拒绝”、“拒斥”的特定过程。雅克·拉康建议将这一术语翻译成弃绝(forclusion)。在他看来,这一心理过程所针对的是一个根本的、被他称为父名(Nom-du-Père)的能指。正是对父名的弃绝禁止了一个主体去“回应父亲职能的召唤”(例如像诗人在动身前往爱尔兰之前试图做的那样,通过结婚成为父亲)。这导致了构成他自我主体基础的象征结构的崩塌。诚然,某一位父亲的姓氏不能与父名这个无意识的、谜一般的、难以言说的能指相混淆,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何对父姓的一种病态的篡改总是标志着对父名的一种彻底的扭曲,譬如当一个主体不再能够签署自己的姓名,却像荷尔德林一样签下“斯卡达内利”(Scardanelli)、像尼采一样签下“狄俄尼索斯”(Dionysos)、亦或签下“纳尔帕”之时……
阿尔托崩溃的种种情况,他抹除一切有关自己姓名的痕迹的决定,构成他谵妄的种种因素,即他被一个迫害“神”、被一个幻想出来的重影所困扰,用对其残酷的享乐代替父系权威的失灵,所有这些都可以完美地用拉康的精神病理论来解释。然而,拉康其实参与过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并认识阿尔托,且当这位诗人被转运到巴黎的圣安娜(Sainte-Anne)病院时,他曾有过机会亲自给后者诊疗。“他已经固化了。哪怕他活到八十岁,他也永远不会再写作了。文学已经不再适合他了”:据说这可能是拉康对阿尔托的一位朋友讲的话,而为此诗人永远无法原谅他。当多年后阿尔托从谵妄之中康复后,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努力否认这个诊断判决:不停地写作,不让自己固化,尝试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是疯癫让他的思维完全瘫痪,给他下了死刑判决。阿尔托若想痊愈就不可能不去撤销这一“判决”,而这意味着调动一切写作和思维的资源来推翻精神医师们无情的诊断。刚离开罗德兹病院,诗人便写了《梵·高或曰被社会自杀的人》(Van Gogh ou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1946),在这部作品中他猛烈抨击了那些精神医师们,抨击了梵·高的友人加歇医生(docteur Gachet),因为他认为后者对梵·高的死负有责任,还抨击了这位他仅用其姓氏首字母指代的“极不公正的炽天使”:“没有哪个精神医师不是个臭名昭著的钟情妄想狂(érotomane)……/我就认识一个,几年前,当看到我如此一股脑地指责所有那群上流混蛋和有执照的骗子们时,他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员。/他对我说,阿尔托先生,我呢,我可不是钟情妄想狂……/L姓医生,我只需让你自己看看,……/你脸上可是带着钟情妄想狂的烙印呢,/无耻的混蛋……/你将正常运转的意识宣称为精神错乱,可另一方面呢,你却用你那卑鄙下流的性将它扼杀。”(XIII, p. 15-16)那么这位L姓医生是谁呢?
在他去世前不久,阿尔托向一位女性友人透露了这位医生的真实身份:他的那些谩骂针对的确实就是拉康。这仅仅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小秘密而已吗?毕竟这一切只是个单纯的误诊,犯下错误的医师还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且许多年后他才撰写了自己的理论著作……但是,如果说这个“错误”无论如何还是有着某种象征意义呢?如果说它预先就已经指出了拉康精神病理论的某种局限呢?将L姓医生当做那些无法理解诗意疯癫的精神医师的典型代表,阿尔托这样做是否是有道理的呢?他所指责这些医师的,正是他们曲解了疯癫的真相。在病院里,他“看到在疯子们的谵妄中,有着比那声称要治愈他们的医生的色情阳具中还要多的真理”(XXII, p. 304)。精神医师们的错误知识所没有认识到的,正是这更多的真理。因为精神病学也属于这种“驱魔”,热衷于将真理从疯癫、从诗歌中排除出去。拘禁、紧身衣、人工昏迷、电击:这么多的“慢性死亡疗法”,且“为了慢慢孵化死亡,为了将死者们关在孵化器中,没什么比精神病院更合适的地方了”(XIII, p. 57)。诸如加歇或拉康之辈的盲目无知,便在于他们无法理解特殊的、例外的个体,即只能在疯癫中才能设法找到“出路”的艺术家:“不成为……一切天才的某种天生的敌人,就他妈的不可能成为精神医师。”因为“在每个疯子身上都有某种不被理解的天才……他只有在谵妄之中才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应对生活准备对他进行的种种扼杀”(XIII, p. 31-32)。对拉康(即作为精神分析的再创者而非圣安娜的年轻精神医师的拉康)而言,这一判断也许会显得不太公正。他后来所强调的反而是精神病当中所蕴藏的真理。由于被弃绝的能指所遭遇的并不是普通的压抑,它在幻觉和谵妄中重新出现时是“不戴着面具”的,这也让精神病患者成为了“无意识的殉道者”,成为了它真实的见证人。然而作为精神病的主要特征,“对父名的弃绝”是不可逆的:“在此异化是彻底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对能指的原始剥夺”,意味着“主体没有被整合进能指的系统中”[iii]。弃绝之所以区别于单纯的压抑——也是因为这点阿尔托并不是一个与其症状斗争的普通的神经症患者——是因为被弃绝的元素从未属于象征秩序,因为它从未到来过。与被压抑的元素不同,它无法返归,无法重新出现在能指链(chaîne signifiante)中,而只能突然出现在别处,譬如在幻觉与见诸行动的实在界(réel)里。因此在精神病中,被弃绝的东西和重现的东西是分属于两个相互异质的层面的,一方属于象征界(symbolique)——或更确切地说:属于象征界的裂缝——而另一方属于实在界。无论谵妄多么有创造性,多么真实,它永远无法修复名的灾难;而如果一种写作多少能够与精神病共存(譬如拉康将在70年代研究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这是因为它能够避免让作家陷入疯癫之中。这就是为何在圣安娜被束缚在紧身衣中的、被拉康诊疗过的诗人阿尔托必然是“固化”的,注定永远无法再写作,除非是以可笑的、纯粹是病理学的形式,就像他那些魔怔的咒骂。但是令L姓医生无法想象的,是那种通过在作品中升华谵妄来战胜精神病的可能性:那种通过绘画、戏剧或诗歌来跨越名的空洞的可能性;因为“一直以来任何人写作、绘画、雕刻、形塑、建造或发明,事实上都只是为了逃离地狱”(XIII, p.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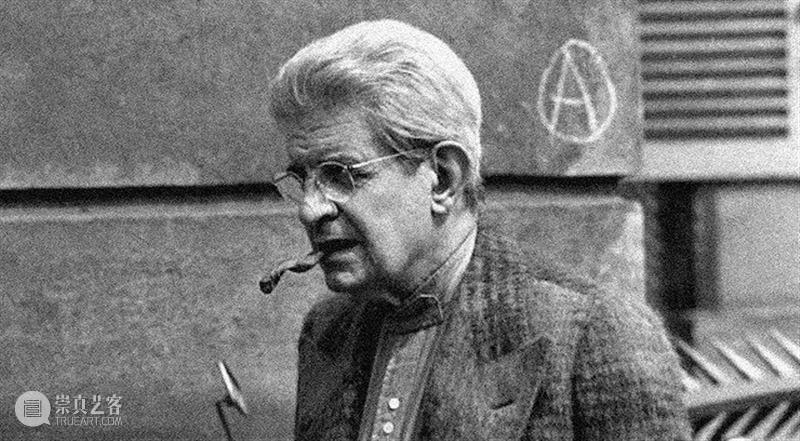
拉康
阿尔托和拉康之间的分歧不仅于此。阿尔托说,圣安娜的那位精神医师——以及他的所有同僚们——让他反感的地方,是这位医师的“钟情妄想症”(érotomanie):即他“把自己的性猎物引入舌下”的方式,与他因享乐而产生的“全身震颤”。这是疯话,还是对某个幻想的讽刺模仿?阿尔托所谴责的钟情妄想症在词源义上是指一种色情意味的疯癫:这一术语在此则指的是一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愚蠢偏见,即对无意识中性欲望(désir)首要地位的肯定。阿尔托对拉康的怒火,与他自己想要“让性归其位”的愿望密不可分,而其方式是将性的舞台布景与另一个场景区分开来:“在比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libido)更远的地方/还存在着一种肮脏的混沌”,一个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要原始的维度。他希望成为这片混沌的探索者,为它画出地图全貌,而他的每一首诗都见证着一种为这个不可名状的深渊命名的企图。在此,我们可能会又一次觉得这针对拉康的攻击不太公平,因为他恰恰是通过与弗洛伊德学派的“钟情妄想症”理论保持距离,来将精神分析重新导向象征界的人。当他尝试用死亡驱力(pulsion de mort)来解释享乐(jouissance)时,他其实和阿尔托非常相似(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点?),因为后者将“存在的享乐”和其“享乐的科学”视为恶、痛苦和死亡的根源[iv]。关于这点,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应该没什么要补充的。但二者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拉康区分了主体的享乐,亦即引导他欲望的享乐,和大他者的享乐,亦即僭越乱伦禁忌的致命幻想。而对诗人阿尔托来说,一切享乐都是大他者的享乐,是一个将他的自我剥夺的邪恶大他者的享乐。为此他才诅咒无意识,因为这是大他者的领地,是后者享乐的领地,在此主体会化为乌有——“所有人的可疑的无意识的狂欢对立于一个人的错愕的意识。”(XIV-1, p. 36)因此,一切性欲、一切与另一个身体的接触都被这种享乐的恐怖所牵连;而救赎只存在于一种“绝对贞洁”当中,在此身体封闭于自身以致成为了一具“无器官的身体”。如此看来,阿尔托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无意识欲望的主张者同想要比弗洛伊德力比多走得更远的人之间的对立;前者区分了欲望与享乐,后者则抗拒享乐贱斥出来的一切欲望与性。
因此,阿尔托的生涯轨迹向我们揭示了拉康精神病理论的主要缺陷:它没能看到一种反弃绝(dé-forclusion)、一种历经并走出精神病的可能性。后者实际上意味着被排斥的元素可以(重新)出现在它失灵的地方:并非出现在幻觉的实在界当中,而是出现在语言、出现在由它的缺失造成的无词空洞当中。这需要一种对象征界的强力促成,让被弃绝的名得以粗暴地闯入到这个一直以来将之排斥在外的语言当中。治愈的代价便是:它要求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如何发明?在语言中,代替这个难以言说的父名的通常是某一位父亲的姓氏,譬如“阿尔托”这一姓氏,将之抹除便宣告了疯癫即将到来。假如对名的反弃绝是可能的,那么它的表现方式应当是(a)阿尔托这个姓氏重新出现,(b)但要以一种前所未见的爆炸形式,进而导致对象征秩序的全面重塑;而且(c)这种回归必须发生在阿尔托这个姓氏被排斥在外的地方,发生在父系能指被弃绝的那个点上。第一个条件于1943年秋天被满足,彼时在罗德兹的病院里,阿尔托放弃了笔名“纳尔帕”,重新开始用他自己的姓氏署名:这是走出没有(n’y-a-pas)语词的绝境,因为他同时决定重新开始写作。几天后他给他的朋友包兰(Paulhan)寄了一篇长文,在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他那套特有的语词发明,即那套在他的晚期作品中突然出现、且成为了他风格特征之一的语汇。他将之称为“身体词”(vocable corporel)、“被造出的音节”(syllabe inventée),而我们则通常将之称为“妄语”(glossolalie)。在精神病学的术语中,这个词用来形容某些精神病患者难以理解的语言。矛盾的是,阿尔托是在他开始从谵妄中恢复时才开始使用它的。让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寄给包兰的文章题为kabhar enis – kathar esti。这些谜一般的词是什么意思?后两个像是一个古希腊语表达方式,意为“他是纯洁的”,而且我们还能从其发音听辨出阿尔托那个“戏剧革命”计划的核心词汇,净化(catharsis)。可能对ar这个音节的重复还是一个秘密的署名,指阿尔托(Ar[taud])和艺术家(ar[tiste])这两个加密的名词。这种重新命名的行为,即以粗暴的方式重新占有被疯癫所窃取的署名,在一篇1947年的文章《我唾弃与生俱来的基督》(« Je crache sur le christ inné »)中更为显著。在断言耶稣基督姓“纳尔帕”之后,阿尔托宣称真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人并不是这位耶稣-纳尔帕,而是一个“不信神的喜剧演员”,“一个从未有人知其名的无名之辈”:“教士们似乎将他当做/那绝对不可见的气息发出的声音/那没有记忆、不可能返归的绝对虚无的状态。”(Œ, p. 1559)这句话表明了对名的弃绝是不可逆的——但这种“没有记忆、不可能返归”的抹除却恰恰并非不可逆,而我们的“喜剧演员”也立刻打破了那个他自己刚刚才指出的禁忌。这含糊不清的气息,这不可名状者被遗忘的名字实际上是在一句妄语的嘶哑呼喊中被大声喊出的:“arhmong amag tamau”,而于这句话中我们一次又一次辨认出了ar/tau这两个音节仿佛持续捶打般的声音。这篇文章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尾所揭示的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在教士们的指令下于各各他被处决的无名之辈就是我,我不是基督,我谁也不是。”从1946年起,他开始提及“傻子(mômo)阿尔托的回归”。在普罗旺斯俚语中,“mômo”一词是“傻子”的意思。这个词听起来也像是“孩子”(môme)、“木乃伊”(momie)或词语(mot):回归是“词语”一词的回归,即那被他的疯癫所剥夺的诗意写作的回归;而这诗歌的重现也伴随着“阿尔托”这个姓氏的复调回归。
看待阿尔托的妄语有好几种方式。它是否如德勒兹所坚持的那样,是一种直接源自一个“无器官的身体”深处的“精神分裂”的语言?我的第二讲将讨论这个问题,而在此之前,我建议将之理解为一种无尽的署名(signature infinie),即不知疲倦地不断重新铭写他的姓名:这是当他拒绝再让自己的姓名被他的“死者之名”掩盖时,当他不再管自己叫做“纳尔帕”时,让他的姓名重新进入语言的方式。因为妄语的出现,是与他对那个曾萦绕在他谵妄之中的、迫害他的大他者的废除密不可分的。因此这妄语与那类在某些精神病当中自发出现的疯话是毫无关系的。他的妄语嵌在诗歌的进程中,经过精雕细琢,缀满文字游戏,所以并非他疯癫的残余痕迹,而是诗意的发明创造。荷尔德林对诗句的关联与并置,人们在他晚期赞歌中发现的那种时态错乱与句法断裂,阿多诺强调说这些并不能被简化为一种临床症状的表现形式,说“诗歌把它们从疯癫的地盘里夺了出来” [v]。阿尔托的妄语也是如此。他创造妄语并非因为自己是“精神分裂”,而是因为自己正在努力康复:他把它们从疯癫的地盘里夺了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妄语发明意在扭曲、颠倒、散播他姓氏的爆裂音,将他的文本转化成一个无止境的署名。他在梦境(德语是Traum)与创伤(traumatisme)的交织中援引的正是这无尽的署名,即“在tau-trauma-ratau-traum中实现的成就”(XVII, p. 219)。这所涉及到的完全是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意义上的近音书写(paragramme):依凭一个不变内核(ar-tau)而展开的一系列语音变体,而这一内核则是一个隐去的姓氏留下的痕迹。于是便有了这由ar和ra、art和tra、to和ot构成的游戏:“ratara ratara ratara/atara tatara rana/otara otara katara/otara ratara kana”(IX, p. 172),此中我们能够同时听出艺术(art)、挫败(ratage)、瑕疵(tare)、古希腊语诅咒(katara)、净化(catharsis)和手杖(canne)这些词的回响。还有这些加密的名字所构成的“artedra/bula tatra/tratra”(XIII, p. 176),这句话向阿尔托宣布了“艺术会助佑你”(l’art t’aidera)这个好消息……他将不断地把这些神奇的音节一个一个读出来,而他的姓名则似乎无休止地消散于此,又像一个秘密的署名一样返归并萦绕在语言当中。
不仅他的妄语,自罗德兹以来他的全部写作所做的都是将阿尔托这个姓氏置于各种近音词(paronyme)之中,即置于各种重复、模仿他姓氏的准同音异义词之中:阿伯拉尔(Abélard)、“贝托王”(Roi Pétaud)、“塔罗”(tarot,他有时会提到这种用于占卜的纸牌游戏)或“圣塔尔托”(Saint Tarto)……相比于近音书写,它们没那么晦涩与零散,还会将这种关于署名的无尽游戏重新引入到他的母语中。在这个有关名的新戏剧的残酷舞台上,这些近音词中每一个都可能变成一个重影,即变成一个对手,一个潜在的篡位者,一个“耶稣-纳尔帕”。通过找回他被剥夺的署名,通过将它念出来、朝各个方向揉搓它,阿尔托便遭遇到了这些曾夺走他署名的或神圣、或恶魔般的形象:“那两个托(Tau)和黑月的托(tau)。/锤头敲击对众生的耶稣基督,托(tau)对十字架。/那两个托(tau)对地狱。”(XVI, p. 146‑147)当他给自己改名为施拉姆托(Schramm-tau)或基托(Kristau)时,他在所有迫害他的人——从塞西尔·施拉姆到耶稣基督——身上刻下了他的印记,留下了他锤头(marteau)的敲击。但他不满足于拒斥与诅咒这些曾经拒绝过他的人的姓名:通过将它们击碎并打散,他也解放了它们那重命名的“无限力量”。通过无数的变体,他将这些姓名化作了诗歌的母体。在所有这些加密的名字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之一是以托(Itau),它是对阿尔托(Artaud)和古法语itou(“同样”,“也”)两个词的缩合,后者则源自拉丁语iter:它就指的是词语的近音,指语言单词的可重复性(itérabilité),指其无限自我复制、不停地在自我变化中自我重复的能力。此外,贯穿他全部作品的那个最顽固的近音词,可能也是最隐而不现的。无论是“子宫括约肌”、“折磨”还是“痉挛”,这些最顽固的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对扼杀、对某种致命收缩、对某个身体腔口的收紧无法摆脱的恐惧。大概这种恐惧源自于躯体的一些基础活动;但它也根植于语言之中,根植于这些让其姓氏不断重现的神奇音节之中,因为阿尔托肯定知道,arto在拉丁语中意为“我扼紧”、“我碾压”、“我掐死”(或“我将自己勒住”)。那些被我们有些操之过急地当做是幻想或诗意隐喻的内容,事实上指的是语言的繁多性当中能指的串连。关于近音词的那种显然是随机的游戏便以此为基础,也以此作为其隐含的必然性。正如词源学告诉我们的,构成拉丁语动词artare的词根ar(“连接”,“收紧”),同样也是“艺术”(art)一词的词源。艺术家(artiste)首先是让相互分离的元素得以聚合、相互增补的人。因此,阿尔托的全部作品便似乎是AR在起着无穷无尽的作用。妄语、近音书写和近音词便显示出一种对父名的反弃绝,而父名粗野的、可笑的死而复生则扰乱了整个能指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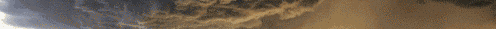
注 释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