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里达的幽灵学——影像与拟像
董树宝 著,
选自《影像的叛逆:法国当代哲学的艺术之思》,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通观德里达的哲学世界,“幽灵”(spectre)始终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徘徊,时隐时现,“几十年来,我的著作到处涌现了众多幽灵”[1],“声音”、“书写”、“他者”、“精神”、“朋友”等概念似乎成了“幽灵”的变体,持续游荡在德里达的文本之间。与此同时,“幽灵”与死亡、“像”/“影像”、“拟像”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德里达幽灵学的重要内容。及至《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1993),德里达从《哈姆雷特》的“鬼魂”显形入手,阐述了幽灵的特点、呈现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集中论述他所谓的“幽灵学”或“幽灵诗学”,进而明确“幽灵”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当代技术等领域的多维关系。“至于幽灵性的逻辑——与(作为可重复性的效果的理想性的理性化的)理念之理念、动机本身密不可分,让我们不要谈解构的‘理念’,这种逻辑以最常见的、清楚的方式在我过去二十余年出版的论著中,尤其在《论精神》(De l’esprit)一书中发挥着作用。‘归魂’(revenant)也是《论精神》的第一个名词(我将谈论归魂……)。”[2]因而,从时间节点上看,《播撒》应该是德里达探讨幽灵学的真正起点,而且《播撒》的内容也充分证明幽灵与死亡、幻像、拟像的密切关系。“毕竟有关鬼魂、鬼影和幽灵的思想始终在德里达的全部著作(从《播撒》[1972年]到《绘画中的真理》[1978年]、从《为了保罗·德曼的回忆》[1988年]到《每次都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2003年]中起作用。”[3]从《柏拉图的药》[4]和《双重场景》开始,德里达就对“幽灵”问题进行深刻的研究,最终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幽灵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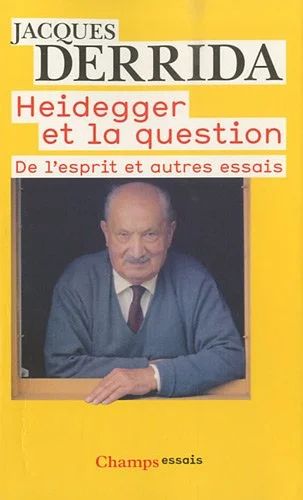
如若从词源上探讨“幽灵”问题,我们的目光将不得不投向古希腊世界,不得不探讨“幽灵”与“像”(eidolon)、“幻像”(phantasma)、“鬼魂”(phasma)和“灵魂”(psuche)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词汇经常出现在《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柏拉图对话录等作品中,关联着影子、水中影、镜中像、梦境等词汇,意味着某种可见的或视觉性的东西,模模糊糊,极不真实。例如,奥德修斯游冥府看到了众多希腊英雄的“幽灵”,他们音容相貌与生前相似,不过他们飘忽不定,难以捉住,“幽灵”或“亡魂”由此成为“像”的呈现形式之一,徘徊在生与死、实在与非实在之间,变成了生者的重影。法国古典学家皮埃尔·韦尔南曾以石像(colossos)为例来探讨“像”与幽灵、亡魂、偶像、梦境、影子等现象的关系,尽管这些词汇之间的词义差异较大,但它们都涉及到“重影”:“在墓底代替尸首的是石像,目的不在于重现死者的相貌,不在于展现死者的肉体面目。化身并固定在石头上的不是死者的外形,而是他在彼岸世界的生命,这个生命与尘世的生命相对立,就像黑暗的世界与光明的世界相对立一样。石像不是一个外形,它是一个重影,正如死者本身是生者的重影一样。”[5] 因而,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幽灵”或“鬼魂”经常作为生者的“重影”与这些词汇交织在一起,“值得认真研究的是这些意义有所不同的词汇如何用西方哲学语言来翻译——如figura、forma、simulacrum、effigy与imago(此后的image)——柏拉图主义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中所主导的翻译以及由之进行的解释”[6]。
在《双重场景》中,德里达将马拉美(Mallarmé)的评论《摹拟》(Mimique)与柏拉图的《斐莱布》进行对照性解读,将西方传统的摹仿论置于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中进行考量。他的这一研究启发着我们重新思考一种充满“幽灵性”的摹仿理论,重新激活那些居于生与死、在场与缺席、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拟像、幻像、重影和鬼魂,促使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游戏。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的摹仿论必然关系着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必然涉及到柏拉图的理念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摹仿(mimesis)被要求遵从真理:或者摹仿以摹本或重影替代存在者的方式妨碍物本身的‘去蔽’,或者摹仿通过重影的相似来为真理效劳。尽管本身被书写所摹仿,但逻各斯只有作为真理才具有价值;也正是在这一名义下,逻各斯才被柏拉图提出质询。”(LD,213)在第一种情况下,摹仿通过摹本替代原型的方式进行,例如书写之于言语的摹仿,远离真理;在第二种情况下,摹仿根据相似性的原则来为真理效劳,正如言说之于逻各斯,直接呈现真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床喻”谴责荷马和悲剧诗人,认为他们是摹仿者,他们制造幻像,与真理隔了两层,由此远离真理与实在。(《理想国》,599a)[7]“床喻”具有层次鲜明的等级关系,被德里达称之为摹仿的“临床范式”(paradigme clinique)[8]:“理念的床”居于最高层,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现实的床”次之,是对“理念”的摹仿,是理念的摹本;“艺术的床”处于最底层,是对现实的摹仿,是“摹本的摹本”,因而作为“摹本的摹本”的“拟像”在这个等级关系中是最低级的,理念与实在先于它而显现,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权和主导权。进而言之,被摹仿者处于更加实在的、更具本体性的等级,由所指、单纯物所构建;而摹仿者处于次级的、远离真理与实在的等级,由能指、重影所构建。因而,好的摹仿应该遵循着真理的过程,忠实地、似真地摹仿被摹仿者,真理的规则、秩序、法则就是在场者的在场(la presence du présent)。在德里达看来,被摹仿者与摹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幽灵显现的关系,像写作和绘画等摹仿性艺术远离真理与实在,只是后者的显现而已。德里达通过《斐莱布》的对话佐证这一点,阐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灵魂、书写与绘画的隐秘关系。柏拉图以书比喻灵魂的方式阐释书写与绘画,他认为书写是对活生生的逻各斯的摹仿,逻各斯决定它的价值与意义,而绘画则是对书写的摹仿,摹仿的摹仿,远离逻各斯和真理。“逻各斯确实以理念(eidos)的原型为摹本,书再生产了逻各斯,而且一切都根据这种有关重复、相似、再重影、复制的关系来组织,经由这种镜子的光芒和反射的过程,其中事物、言语与书写相互映照。”(LD,214)书写与绘画只有在彼此被解释为活物、活生生的言语的影像、再生、再现、重复和动物性的形态时才是彼此的影像。因而,柏拉图始终拒绝书写与绘画在“本来的”意义上对事物本身产生直觉,因为它们只不过与摹本、摹本的摹本有关。“我们在得出意见和论断的时候要把视觉或其他感觉去掉,在此之后这位画家又在我们心中绘画,也就是在我们先前对之发表过意见和论断的那些对象的图画或影像。”(《斐莱布》,39b-c)
不过,在德里达看来,绘画与逻各斯之间出现一种奇怪的关系,一方始终是另一方的替补,绘画逐渐摆脱逻各斯的束缚,在隐喻的意义上与书写相互指涉,而且在柏拉图主义的内部出现“反柏拉图主义”。由此,德里达通过解读马拉美的《摹拟》使幽灵、拟像或幻像进入相互游戏,开启了与德勒兹“颠倒柏拉图主义”不同的“没有颠倒柏拉图主义及其传统的移位”(LD,240)。德里达没有像德勒兹那样致力于摹本与拟像的区分,而是基于摹仿的维度将书写与拟像联系起来,由之书写开启“重影、摹本、摹仿、拟像的可能性”(LD,181),进而改变柏拉图基于“临床范式”对拟像的界定。拟像不再是摹本的摹本,而是徘徊在“像”与原型之间,因此拟像是没有原型的“像”,既不是“像”,也不是原型,而是居于两者之间。马拉美在《摹拟》中分析了充满死亡氛围的哑剧剧本《皮埃罗杀妻》(Pierrot assassin de sa femme),这个剧本讲述了皮埃罗(Pierrot)发现妻子高隆比娜(Colombine)不忠,把她捆绑在床上,挠她的脚心,令她狂笑而亡。
马拉美就这样保留摹拟或摹仿的差分结构,但摈弃了柏拉图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后者意味着在某个地方存在者的存在被摹仿。马拉美甚至坚持(置身于)一种如同柏拉图那样定义的的幻像结构:作为摹本之摹本的拟像。除了不再有原型,也就是不再有摹本,而且这一结构(也包含了柏拉图的文本,包括他试图对文本的逃避)不再被用于指涉形而上学乃至辩证法。”(LD,234-235)

马拉美式的移位导致没有指涉对象的摹仿,在摹仿与摹仿的差异游戏中对摹仿进行摹仿,就像对柏拉图的拟像进行拟仿一样,因此拟像不再是理念的派生物,而是像空洞的幽灵一样的“重影”。德里达指出马拉美的这种“没有颠倒柏拉图主义及其传统的移位”,认为马拉美在摹拟与摹仿之间或摹仿与摹仿之间让剧中人物皮埃罗像没有肉身的鬼魂一样到处游荡。皮埃罗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犹如僵尸的面孔一般,致使柏拉图的“临床范式”遭遇危机。此外,德里达在《双重场景》中还玩弄着一个文字游戏:aparaître与l’apparition,后者是前者的名词形式,两个词既指一般意义上的显现或出场,同时又可以指神或鬼魂的显灵,德里达如同阐释pharmakon(药)一样巧妙地利用apparence(表象)的含混性来获得一种幽灵性效果。“语词apparence的历史性含混(既是现在的存在者[l’étant-présent]的显现或显灵,也是现在的存在者在它的表象后面的掩饰)提供了它在这一既非综合的也非冗余的序列上的未定褶皱:‘在现在的虚假表象之下’(sous une apparence fausse de présent)。”(LD,239-240)在《皮埃罗杀妻》的哑剧表演中,表演者保罗·马格利特“在现在的虚假表象之下”摹仿过去发生的杀妻过程,也就是以现在时的方式摹仿一个过去的事件,表演者马格利特轮番扮演着皮埃罗与高隆比娜,也就是谋杀者与被谋杀者,最终在痉挛和狂笑中达到戏剧高潮。
马拉美极其重视摹拟与拟像,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摹仿任何东西的摹拟,是每种使任何东西再重影的重影。在这种充满镜像的游戏中,皮埃罗就像一个面目狰狞的鬼魂一样游荡,“没有任何肉身,飘荡不定,没有过去,没有死亡,没有出生,也没有在场”(LD,234)。德里达在《双重场景》中不断重复着《摹拟》的一个句子:“无声的独白,那苍白的鬼魂从头到尾以表情与手势依恋着他的灵魂,就像一张如同尚未被书写的白纸一样”(soliloque muet que, tout à long à son âme tient et du visage et des gestes le fantôme blanc comme une page pas encore écrite),一个拟像式的幽灵游荡在《皮埃罗杀妻》、《摹拟》与《双重场景》之间,不再有原本与摹本,哑剧演员没有再现任何东西,也没有摹仿任何东西,不再遵从任何外在的指涉对象。“《摹拟》的皮埃罗与《受罚的小丑》(Pitre châtié)的‘不详的哈姆雷特’(mauvais Hamlet)可以这样被彼此解读……皮埃罗就是那萦绕着马拉美文本的哈姆雷特的全部兄弟。”(LD,222)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这里引用了马拉美的诗《受罚的小丑》,其中“不祥的哈姆雷特”与皮埃罗成为“难兄难弟”,不仅萦绕着马拉美的文本,而且还暗示了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与《哈姆雷特》的隐秘关系,为“哈姆雷特的鬼魂”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哈姆雷特的鬼魂”最终在德里达“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Whither marxism ? / Où va le marxisme ?)的追问中骤然登场[9],它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灵感来源,“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德里达恍然之间洞察到两者的内在秘密,他开始像哈姆雷特一样“与鬼魂交谈”,希望最终在生与死之间学会生活:
学会生活,如果此事有待于去做,也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既不仅仅在生中,也不仅仅在死中。那是在两者之间发生的事,而且是在某人所乐意的所有“两者”之间(如生与死之间)发生的事,只有与某个鬼魂一起才能维护自身,只能与某个鬼魂交谈且只能谈论某个鬼魂。因此必须对灵魂有所认识。尤其是,如果这东西或者幽灵并不存在,如果那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本身永远也不会到场……并且这种与幽灵共存也是,或者不仅仅是,而且也是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SM,14-15)
德里达重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个人该如何生活?”[10],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正义的名义下探讨我们所处的世界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对“那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本身”进行招魂、祛魅与重生。
在幽灵学的探索中,德里达从西方文化世界的众多鬼魂中选取“哈姆雷特的鬼魂”作为幽灵学构建的起点。他用解构主义策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与莎士比亚、瓦莱里、布朗肖、海德格尔和福山等人的文本相互交织,进而揭示马克思所开创的幽灵政治学对新国际神话的解构意义。在这一解读中,《哈姆雷特》的“鬼魂”是一条核心主线,构建了文本阅读的基本框架。《马克思的幽灵》第一章以“哈姆雷特的鬼魂”开篇,又以《哈姆雷特》宫廷侍卫马西勒斯对霍拉旭说的一句话结束:“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说话,霍拉旭”。全书围绕着《哈姆雷特》拟仿着不断复现的幽灵或“哈姆雷特的鬼魂”,形成了一种类似“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回环往复结构。除此之外,“哈姆雷特的鬼魂”具有超越时空的典型症候,意味着 “哈姆雷特的鬼魂”、“共产主义的幽灵”与“马克主义的幽灵们”具有某种共通性,暗示了丹麦王国、19世纪的欧洲、当代世界都面对着“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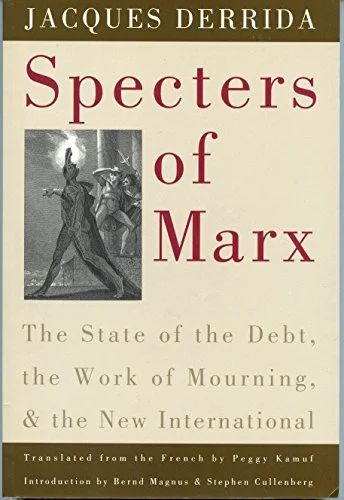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针对鬼魂、幽灵和拟像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哲理性疑问:“鬼魂是什么?幽灵——那似乎仍然与拟像一样无效的、潜在的或不坚实的东西——的效果性(effectivité)和在场(présence)是什么?在那里,在那东西本身与它的拟像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对立吗?”(SM,31)面对着这些疑问,“哈姆雷特的鬼魂”[11]开始登场:
哈姆雷特:……宣誓吧。
鬼魂:(在下)宣誓。
(二人宣誓)
哈姆雷特:“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魂!好,朋友们,我以满怀的热情,信赖着你们两位;要是在哈姆莱特的微弱的能力以内,能够有可以向你们表示他的友情之处,上帝在上,我一定不会有负你们。让我们一同进去;请你们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守口如瓶。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儿去吧。”[12]
马克思极其喜欢莎士比亚,而且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毋庸置疑,以“幽灵”开场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显然受启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召唤着沉默不语的“哈姆雷特的鬼魂”重返旧欧洲的舞台。德里达从中洞察到新近出现的同一谱系,在一群又一群的鬼魂喧嚣中,瓦莱里悄然登场,他在《精神的危机》中写道:
欧洲的哈姆雷特注视着成千上万的幽灵。但他是一个知识的哈姆雷特。他思索着真理的生与死。他将我们争论的全部对象视为鬼魂;他的懊悔是我们的荣耀的全部头衔,如果他抓住了一个头颅,那就是一个卓越的头颅——这是列奥纳多……另一个是梦想着世界和平的莱布尼兹的头颅。还有这个是康德的头颅,他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哈姆雷特并不知道如何处理所有这些头颅。但如果他放弃了他们……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吗?(SM,23-24)
德里达的这段引文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幽灵》的重要切入口之一。瓦莱里勾勒了一段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精神发展史,描述了这一发展史从达·芬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演变过程。通常“头颅”(crâne)象征精神,瓦莱里的文章标题《精神的危机》显然强化了头颅与精神的这种内在关系,德里达在这段引文的注释中指出,这一论题旨在将欧洲的问题再次定义为精神的问题,也就是幽灵的问题。擅长解读的德里达发现“一个奇特笔误”,一个省略号,“还有这个是康德的头颅,他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德里达认为这是幽灵意象与马克思一起的退场,或许会在其他地方重现。
更重要的问题是,注视着成千上万幽灵的哈姆雷特与这一系列“头颅”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德里达指出了一个新系列,“莎士比亚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瓦莱里(以及某些其他人)”(SM,23),于是两个差异性的系列开始运作,或者说精神系列与幽灵系列相互交织,马克思成为这两个系列的交汇点,两者开始变得难以区分,创造了那正如瓦莱里所说的“精神之精神”(esprit de l’esprit)的东西。“一旦幽灵与精神不再被区分,它就获得了形体,作为精神,它就会在幽灵中具体化……幽灵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是生成-形体(devenir-corps),是精神的某种现象的和肉身的形式。确切地说,它生成了某个仍难以被命名的‘东西’:既非灵魂,也非肉体,而且又亦此亦彼……精神、幽灵,并不是相同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突出这种差异”(SM,25)。幽灵是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已经溢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幽灵可以使精神显形,但又与精神有所不同。幽灵显现而又消失,似乎可见,但又不可见,它注视着我们,但我们却看不见它,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但它又会显形。“马西勒斯: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吗?勃那多:我还没有瞧见什么。”[13]幽灵产生了德里达所谓的“面甲效果”(effet de visière):我们看不见谁在盯着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某个不可见的东西,其中隐藏着不可见物的可见性或可见物的不可见性。哈姆雷特父王的鬼魂“自头至踵全身甲胄”,甲胄令人根本看不见鬼魂的形体,也令人难以识别,但鬼魂可以看见别人而又不被别人看见。哈姆雷特焦急想知道谁看到他的父亲,看到他的眼睛。不管怎样,总是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却看不见那双眼睛与目光,其中存在着一种不对称性和不可逆性。“这某种幽灵性的其他人注视着我们,我们感觉到被它注视着,在任何同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上,按照一种时间先前性(它可能属于世代的秩序,且不止一个世代的秩序)和绝对的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比例失调。时间错位在此成为法(loi)。感觉自己被一种永远不可能相遇的目光注视着,这就是我们从法中继承来的面具效果。”(SM,27)德里达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幽灵与圣像和偶像、影像的影像、柏拉图的幻像区分开来,还可以与某个东西的简单拟像区分开,尽管它与拟像很相近,在某些方面还共享了很多特点。综上所论,德里达试图解释“鬼魂是什么?”或“鬼魂不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着对幽灵的效果性进行描述,为我们认识幽灵与拟像的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鬼魂”在《哈姆雷特》中占据着国王的位置和父亲的位置,“我是你父亲的灵魂”。鬼魂一再出场,萦绕着城堡的上空,制造了一种“阴魂不散”的氛围,这关涉着鬼魂与拟像之间的重复问题。“重复与第一次重复也是重复与最后一次重复,因为任何第一次的奇异性(singularité)也就成了最后一次重复。每一次都是事件本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是另一回事。历史的终结即将登场。我们不妨称之为幽灵学(hantologie)。”(SM,31)幽灵的这种重复性逻辑启发着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本体论追问,植入一种末世论和终结论的维度。历史终结之后,精神以归魂的方式到来,它既可以赋形于归来的死者,又可以赋形于一次次被期待归来的鬼魂。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归来就呈现了这种特点,“精神的危机”在哈姆雷特的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回归,循环往复,鬼魂出场,鬼魂退场,鬼魂再出场……如此往复,由之鬼魂与它的拟像构成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对立关系,每次归来的都是一种幽灵性的重现,是鬼魂的重复性归来,是归魂(revenant)的拟象性重生形态。这已然不是某个东西的简单拟像,柏拉图基于摹仿论的拟像不再发挥作用,因为鬼魂是非真实的、非实在的、非生命的非存在,它的本身不是某个东西,飘忽不定,若隐若现。“重复的问题,就是幽灵永远是归魂。”(SM,32) “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以颇具戏剧性的显形登上19世纪欧洲的舞台,这难道不就是一个重复性的归魂,不就是一场“精神的危机”的重新归来吗?“幽灵”就是一个类似老哈姆雷特的父亲般角色,比活生生的在场更具有潜在的效能,它质疑“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最后一个人的终结”等末世学论题。“幽灵”促使德里达深入思考哈姆雷特的“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The Time is out of joint)论题——马克思和德里达承继的论题。

在对“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的四种法译本分析中,德里达指出原作与各种译本的翻译如同鬼魂与归魂一样运行,鬼魂到处游荡,居无定所,具有一种幽灵性的效果。译本的混乱、脱节、无序进一步凸显“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的隐秘意义,促使着哈姆雷特匡扶正义,重整乾坤,“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一点恰恰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的“开场白”中所探讨的正义问题相呼应,鬼魂、幽灵和归魂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学会生活最终要“学会与鬼魂谈话”,或许这是德里达并置《共产党宣言》系列与《哈姆雷特》系列的根本原因。借此,他希望解决“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的论题,呼唤马克思的幽灵们还魂。归魂超越时空的限制,终将复返,隐含着一个多样性的、异质性的未来,意味着一种“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14]。就此,德里达在一个关于本雅明的注释中给出清晰的阐释:“我们试图在此谈论某种贫乏的弥赛亚,在一种继承与生成的幽灵性逻辑中谈论,不过是一种在异质的和脱节的时间中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逻辑。”(SM,95-96)这种幽灵性逻辑正是德里达批评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观念论逻辑(logique idéaliste)和经验主义逻辑的重要依据,也是马克思幽灵政治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其鬼魂、幽灵、归魂云集的著作中充分调动这种幽灵性逻辑,无论是金钱还是意识形态要素,全部观念化的运动都是“各种鬼魂、错觉、拟像、表象或显灵的产物”(SM,81),仿佛金钱既是精神的起源,也是贪婪的起源,商品的变形也经受了幽灵诗学(spectropoetique)的变样的观念化过程。这种观念化的过程或精神化的过程既使幽灵化变成资本(本金),又使主体“变成绝对的鬼魂,实际上是精神—幽灵的鬼魂的鬼魂,是永无终结的拟像的拟像”(SM,203-204)。
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柏拉图主义的继承者。正如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贬斥、诱捕、围剿或驱逐智者们一样,马克思也对他同时代的“智者”施蒂纳(Stirner)进行诱捕或围剿。其实德里达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马克思为面具,也继承柏拉图主义的这一传统,对福山等当代“智者们”也展开诱捕与围剿:
在他们的共同揭露中,在这一揭露同时更具批判性和本体论的部分中,马克思与圣麦克斯(saint Max)也承继了柏拉图主义传统,更准确地说是承继了这一严格地在其活死者(mort-vivant)的鬼魂式的或游荡的维度上把‘像’与幽灵、偶像(idole)与幻像(phantasmata)联系起来的传统。《斐多》(81d)或《蒂迈欧》(71a)没有与‘拟像’(eidôla)区分开的‘幻像’,是一些死魂灵的形象,是死者的灵魂:它们不是在墓碑和墓地附近闲逛(《斐多》),就是日夜纠缠着某些活人的灵魂(《蒂迈欧》)。这种结合不仅十分紧密,而且重复出现,不会被拆开。它促使人思考活死者的幸存,回归那属于偶像的本质。当然也属于偶像的非本质的本质。属于那赋于思想以形体的东西,不过这形体只有较低级的本体论内容,或者它与其说是实在的,倒不如说是观念本身。只有在死亡的背景下,偶像才出现,或者才被规定。这大概是一个毫无原创性的假设,不管其结果可以通过一个巨大传统的稳定性加以衡量,必须谈及哲学的遗产,就像这笔遗产通过最具弑父性质的转变来从柏拉图传给圣麦克斯,传给马克思及其他人。(SM,235)
德里达批评柏拉图在《斐多》和《蒂迈欧》中关于幽灵与“像”“幻像”、拟像的思想是一个毫无原创性的假设,是较低级的本体论探讨,它没有触及这一问题的实质,但是作为一笔哲学遗产,柏拉图主义的这一传统还是传给马克思及其他人。柏拉图曾用拟像、摹仿术(mimème)和幻像诱捕和围剿智者们,马克思也继承这种反诡辩术,不得不使用拟像、摹仿术和幻像来诱捕和围剿他的对手施蒂纳,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般围绕着幽灵展开一场毫无休止的角逐,最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绘出一张关于幽灵的十诫表(Table)[15]。
这张十诫表的周围,成群结队的幽灵蜂拥而至,它们游荡着,吵闹着,不停地繁殖着。“结果、联系、一连串的嘈杂声、没有终结络绎不绝的现象形式的过程,在深夜里,一切都是白色的和透明的。显形的形式就是精神的现象形体,这就是幽灵的定义。鬼魂是精神的现象。”(SM,216)幽灵来自精神,它分有着精神,它从属于精神,它就好像鬼魂的重影一样追随着精神。不过,精神也是自身的精神,也是一个鬼魂,一个始终是通过重新返回来作为另一种精神的腹语而让人惊异的鬼魂[16]。鬼魂在精神的火焰[17]上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它们在幽灵般的图表上舞蹈。Table在法语中不仅指“图表”、“表格”,而且指“桌子”。德里达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汇的奥妙。“这种诸精神的图表将以圆桌会议的影像变动。它开始在我们的眼前跳舞,就像《资本论》中的某张‘桌子’一样,当它生成商品的过程敞开隐秘的、神秘的和拜物教的维度时,我们马上就看到它在移动。”(SM,226)桌子登上舞台,当市场的帷幕拉开时,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一张木制的桌子变成商品,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一种可感的而又非可感的、可感的而又超可感的东西,本来是一件物品,却在幽灵的效果下变成一件商品。桌子有腿,有面,有形体,它站立着,上升、起立,它抬起头(一个木制的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显形,是物品、动物、对象、商品,总之它就是幽灵。桌子开始疯狂、执拗、难以固定,从木质的头颅中提炼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从木制品向非木制品转变,从质料向非质料转变[18],由此木头获得生命,获得精神,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变成一张会舞蹈的桌子,变成一个“幽灵性拟像”(simulacre spectral)。“咳,幽灵在你的头脑中游荡……”[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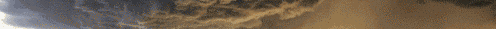
注 释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