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登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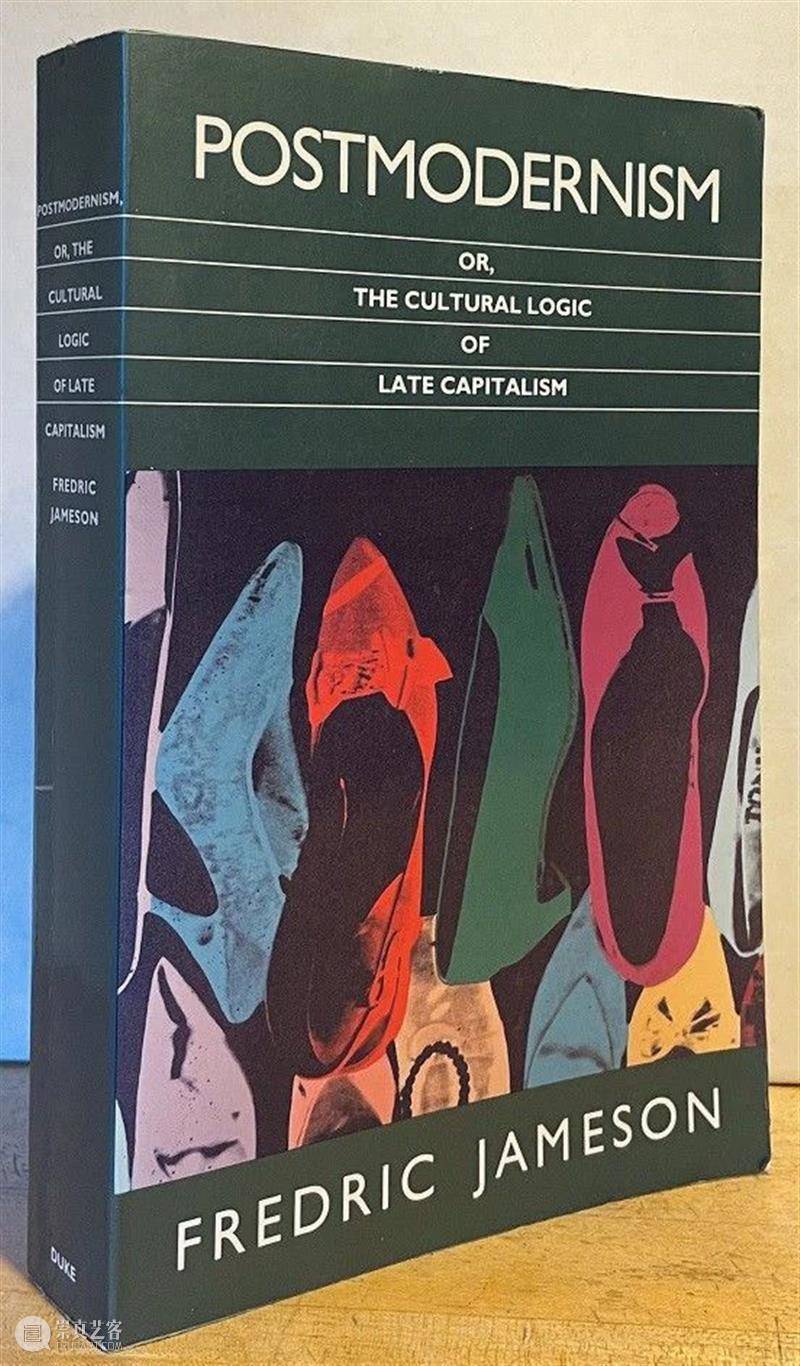
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 “反美学”的再审视:基于《十月》学派的研究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发自美国的新左派“反美学”思潮,常被误读为反对审美、人性或情感。但“反美学”针对的不是绘画、美或感性本身,而是反对将学科内部的评价体系当成唯一合法的评价体系,反对将跨学科的艺术与启蒙成就化约为供人赏玩的消费品、固化阶层地位的工具。作为“祛魅”或“解构”的当代艺术也远非艺术圈内部的游戏或娱乐,而是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就像“现代性——未完成的事业”一样,后现代的“反美学”也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关键词:反美学,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哈尔·福斯特,解构
在当代关于“美”的种种讨论中,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美学”批评思想,常常被简化为反对审美、人性或情感等等,仿佛过去丰富细腻的传统艺术批评方法,都一概被左派的政治诉求取代了。从那时至今,绘画、美或感性,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每一种“回归”都不免声明 “反美学”已成为过去。但“反美学”究竟是为了反对什么?在1983年划时代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导论中,编者哈尔·福斯特给出了一种明确的定义:从狭义上说,“反美学”是对于自律美学(在那个时代以阿多诺、格林伯格为代表)的质疑,但从更深意义上说,是主张跨学科的实践——拓宽艺术的评价体系,不再限于艺术本身的学科权威。他这样归纳文集中几位作者①的共识:
对于西方种种再现模式和现代的“超级叙事”的批评;以关注差异性的概念思考(没有对立的他者,没有等级的异质性)的需求;对于文化自主的“空间”或是专家区隔“领域”的怀疑;对超越形式上的继承关系(从文本到文本)和追踪社会联系(在生活世界中体制性的文本“浓度”)的呼吁;简言之,一种意愿,去捕捉文化和政治中现时的连接,确立一种既针对学院派现代主义,也针对反动政治的抵抗实践。 [1] xv
所谓“既针对学院派现代主义,也针对反动政治”,这前一个重点,是针对法典化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它真正反对的并不是绘画、美或感性本身,而是反对将学科内部的评价体系当成唯一合法的评价体系,将学科权威性作为唯一的“正道”,当成打压激进革命实践的旗帜,将跨学科的艺术与启蒙成就化约为供人赏玩的消费品,或是固化阶层地位的工具。但这一阶段性的任务,几乎已经在前二十年间的许多艺术与批评实践中完成了。如果还继续从各个方面提出反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已经全面主流化的那个时代,已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反美学”在当年的历史任务其实重在其二:主张继续拓宽激进艺术的路线,作为针对所谓“反动”的保守文化的抵抗。对当时的新左派批评家来说,反动(reactionary)一词,批判的是当年在里根与撒切尔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经体系之下,对新秩序作出全面肯定的主流文化。
本文将重在从这一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出发,细述当年的批评圈关于“后现代”“反美学”这些术语的核心分歧,以破除我们过去对“后现代艺术”的误解和简化。以下第一部分将解释“反美学”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 “反美学”的代表批评家们当年的艺术批评观点——它反对当年对种种新式绘画的无限吹捧,也质疑作为“艺术风格史”的传统艺术史建构;第三部分结合文学、文化领域的发展,理解“解构”的历史意义;第四部分讨论这一“后结构主义”“反美学”的左派艺术潮流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一、抵抗的后现代主义:
从“否定”到“介入”
在1983年的美国艺术圈,《反美学》一出版就成为人手一册的重要参考物。在那之前,虽然在文化领域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保罗·德曼的著述不断,在艺术领域有《十月》的克劳斯、克林普等先行者提出的各种“后现代”批评方法,但到这部文集才首度让两个领域紧密交织起来。福斯特在导论中解释,现代性发展所重视的学术自律,使得人文学科和政治各具一方,互不干涉,让人文学科不得不在有限的领域之中钻牛角尖,而大片需要人文关怀的地带却都被边缘化了。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在生活世界中结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各种宗教的后援会。而(阿多诺式的)现代主义所高举的“否定”的旗帜,对高高在上的“解放效应”的指望,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企图返回曾经存在过的那么一种超越表征的理想空间, “但本书的批评家认定:我们从未置身于表征之外,或者说,从未置身于表征的政治之外”。 [1] x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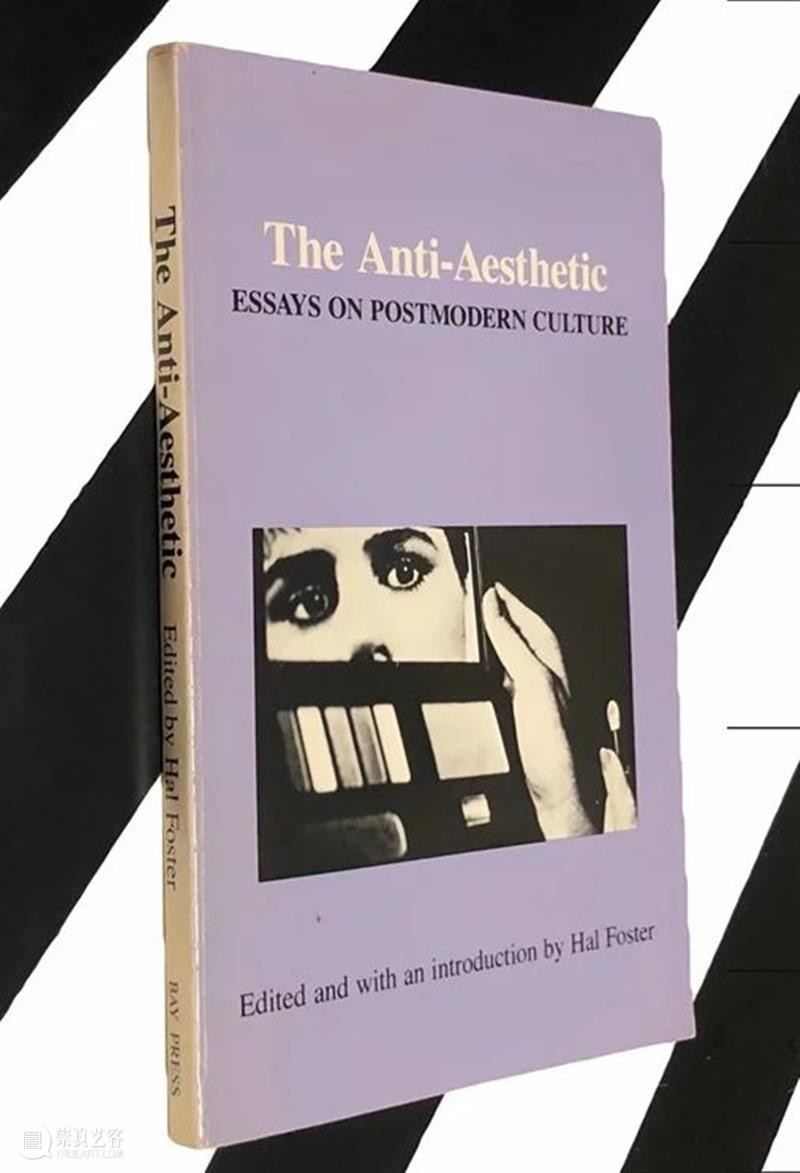
图一:哈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
“宗教的后援会”“乌托邦”和“理想空间”,这批评的不只是美国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代言人格林伯格和弗雷德,更是针对阿多诺的《审美理论》——“艺术自律”最坚实的理论壁垒。从马尔库塞的“肯定的文化”到阿多诺的“管理世界”,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不但深刻影响了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如詹姆逊,也重塑了艺术批评家的世界观,构成了十月学派的社会观的基石。然而,无论是对于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十月》的克劳斯和麦克尔森,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热烈投入的布赫洛、福斯特等等,都是以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的社会学的成果,结合当时的艺术批评现状,反对由阿多诺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左派美学,简言之,站在阿多诺的肩膀上反对阿多诺。当福斯特于2010年回顾时,他简明扼要地概括道:“我所编辑的第一本书是1983年的《反美学》,那明显是反阿多诺的。此书关注的是提出一个‘抵抗的后现代主义’,它关于文化政治的见解主要是葛兰西主义的。”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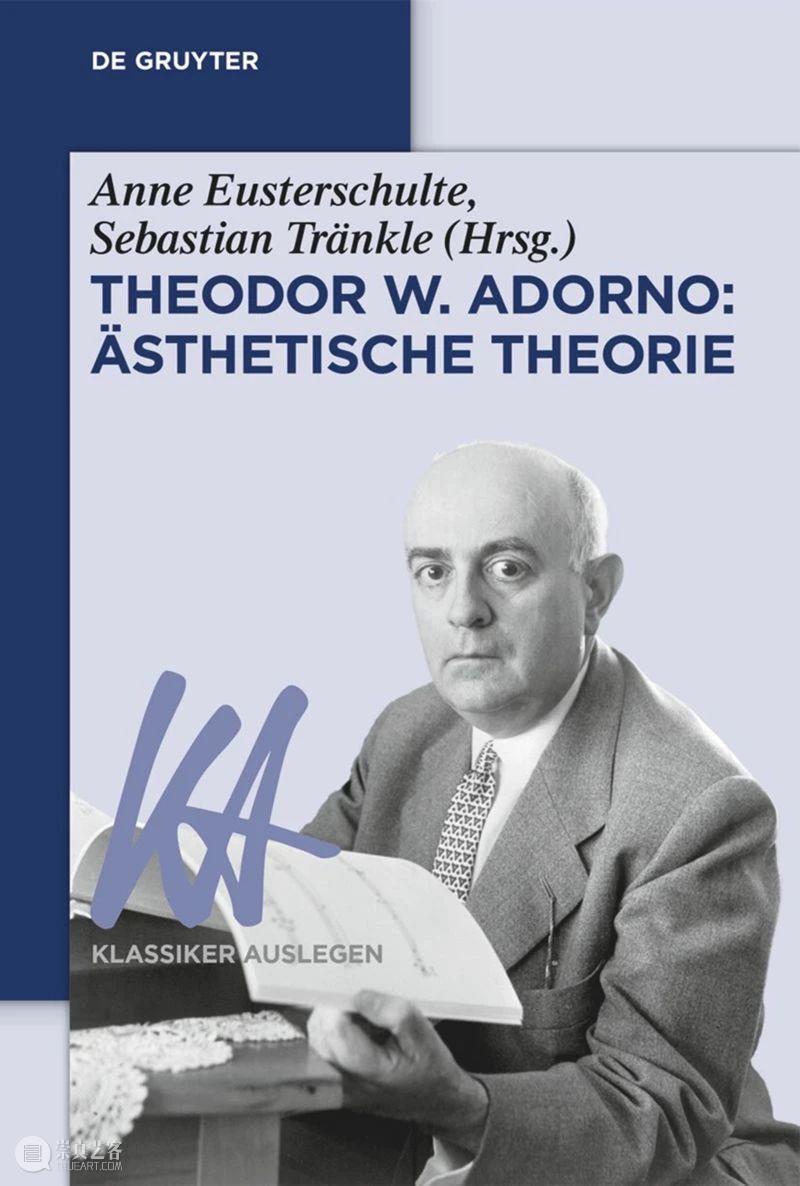
图二:阿多诺 《审美理论》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的一面旗帜。《狱中札记》英文版的出版,引发了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于70年代的“葛兰西转向”,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后来的“文化革命”理念,也正是这一理念,加上德勒兹提出的“少数文学”,居伊·德波的情境主义等等,共同定义了批评家的政治介入。就像格林伯格和弗雷德二人的早期批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托洛茨基一样,《十月》学派的诸多论述也常常提及半个世纪之前的葛兰西。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否定相比,甚至与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相比,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领导权)的理论在当时看来似乎更有实践性。他主张,工人阶级可以试图通过文化上的努力,逐步取得“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权”,也就是通过文化领导权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表示,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他们打开了基于具体社会实践的工作方式,不再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单纯地被强加的文化,被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的合谋所强加于大众头上的文化,而是将文化理解为由底层力量和上层力量的不断互动、彼此妥协所调配成的复杂耦合体,强调意义与阐释、生产与消费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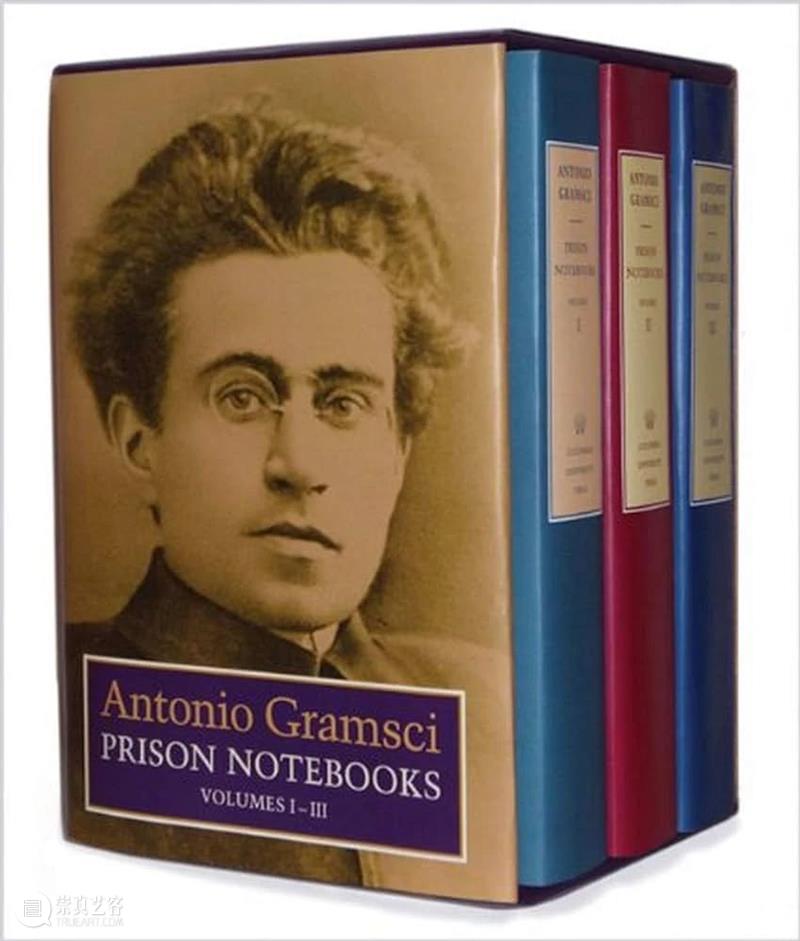
图三:葛兰西《狱中札记》
简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路线,是企图通过与文化工业的疏离,以对抗文化工业背后的国家机器或资本主义,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介入”的路线,是要求通过与文化工业的合作,“打入敌人内部”,以逐步改变那背后的——不再是国家机器或资本主义了,而是被全面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严密的综合体。在后来于2004年出版的《1900以来的艺术》中,《十月》学派的另一位新前卫批评家本雅明·布赫洛解释了新的文化研究路径在那时对于他们的意义:
斯图尔特·霍尔提出一种在分析大众文化时无限分层的方法……在从革命与解放到倒退与反动之间所产生的风格演变中的那种辩证运动,同样也可以在大众文化生产中察觉到,在这里,在工业化的文化适应过程中,从最初的反对与背离,到最终的确认,一种永恒的摆动总是发生着……要克服欧洲中心的文化霸权论,第一步就应该知道,不同的观众,是以不同的传统结构、语言习俗和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来交流的。因此,根据新的文化研究路径,观众身份和体验的特殊性,应该凌驾于所有神圣又独裁的审美等级制评价准则之上——这种法典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保留白种男性资产阶级文化至高无上的优势的确证。[4]366
“审美等级制”和“白人男性资产阶级文化优势”,是当时的艺术自律路线难以摆脱的原罪。此种嫌疑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中,凡是属于经典艺术范畴的鉴赏和演练,的确在极大程度上属于精英/有闲阶层。在阿多诺和格林伯格式的艺术自律的圈子中,最优秀也最稀缺的高级艺术,无论其观感是优雅还是粗俗的,最终都成了权贵地位的象征。从立体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所有曾经被灌注过愤怒和嘶喊的作品,都难逃高级奢侈品的命运。这些被寄予“解放”式期待的现代主义艺术,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在1960年代之后不再有活力可言,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②
与其将这一衰落归罪于后现代主义,倒不如归因于现代主义大厦本身的局限。阿多诺对文化工业运作机制的批判鞭辟入里,但他为视觉艺术提出的期望并不切实际。从《审美理论》中的实例看,他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划定了一种过于狭窄的路线——既保持艺术自律,又能实现某种政治抗争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一路线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总体化,是不得已而为之。与同时代出版《先锋派理论》的比格尔相比,他们虽然对“先锋派”意义的看法一贬一褒,截然相反,但对于新先锋派的否定倒是一致的:“抵抗”式的革命前卫艺术,到了1960年代已经没法继续进行了。
在《反美学》的首篇《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中,哈贝马斯秉持和阿多诺相似的观点,一举抨击了胡乱实验的前卫艺术和一切都不在乎的新保守派。但在两年后的论文集《重新编码:艺术、景观、文化政治》(Recoding: Art, Spectacle, Cultural Politics)中,福斯特明确反驳了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代表人物。同样从社会批判理论出发,福斯特论证,哈贝马斯关于文化的堕落是责怪错了对象:真正侵蚀了启蒙事业的,并不是那些新艺术的越界或是解构批评(常常只是学院里的操演),而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为在经济、官僚、技术和科学领域中,大部分的活动都使得人被进一步工具化了,对价值或道德判断的重视是远远不足的。他回顾格林伯格的时代,旧式的资产阶级出于对于专业艺术的尊重,还支持着批评的写作空间,支持着整个的代表资产阶级趣味、启蒙理性和言论自由理想的共同体。而到七八十年代,这一共同体已经彻底被投机资本所侵蚀或者转换了。“在这一管理世界中,艺术和批评都被边缘化了;这就是它们的功能,‘表现人的边缘性’。于是它们被当成既重要却又奢侈的,就像供人沉醉的奢侈品,或是让人急于摆脱的麻烦。”[5]3-4这正是在克劳斯、布赫洛和福斯特等人那时的写作中一再出现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在艺术世界的内部争执什么形式自律,而是探索新的途径,积极抵抗艺术世界的“被殖民”。因为正在被殖民的不仅是自律的艺术,也包括各种“一切皆可”的艺术,整个艺术圈被卷入了一种新型的体制:被强迫的多元主义。③
布赫洛在一篇1988年的艺评中也讨论了艺术和学术自律的动因,针对阿多诺在《论介入/担当》(“Commitment”)和《论顺从》(“Resignation”)这些名文中表达的观点,他强调,阿多诺所立足的现代主义模式,那种资产阶级艺术自律的概念及其产生条件,早在20世纪初已经被改变了,而已经发生的那些新的艺术形式,也已经被彻底地吸纳进了阿多诺所谓“全面管理的世界”。于是,作为美学创作的视觉艺术,“其主导性范畴的霸权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社会和政治解放的现实体现。”[6]156这种解放的现实,我们不妨联系起本雅明一度对于“机械复制时代”的期望。在电影、摄影等视觉艺术领域中,艺术更加贴近大众,思想也能更有效地传播,那么,怎能要求高雅艺术继续闭门造车,将最有力的传播手段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比起“1984”的预言,“美丽新世界”的威胁反而更为迫近,势不可挡,就像工业革命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改造了所有行业的传统生态,激进的艺术除了“介入”已别无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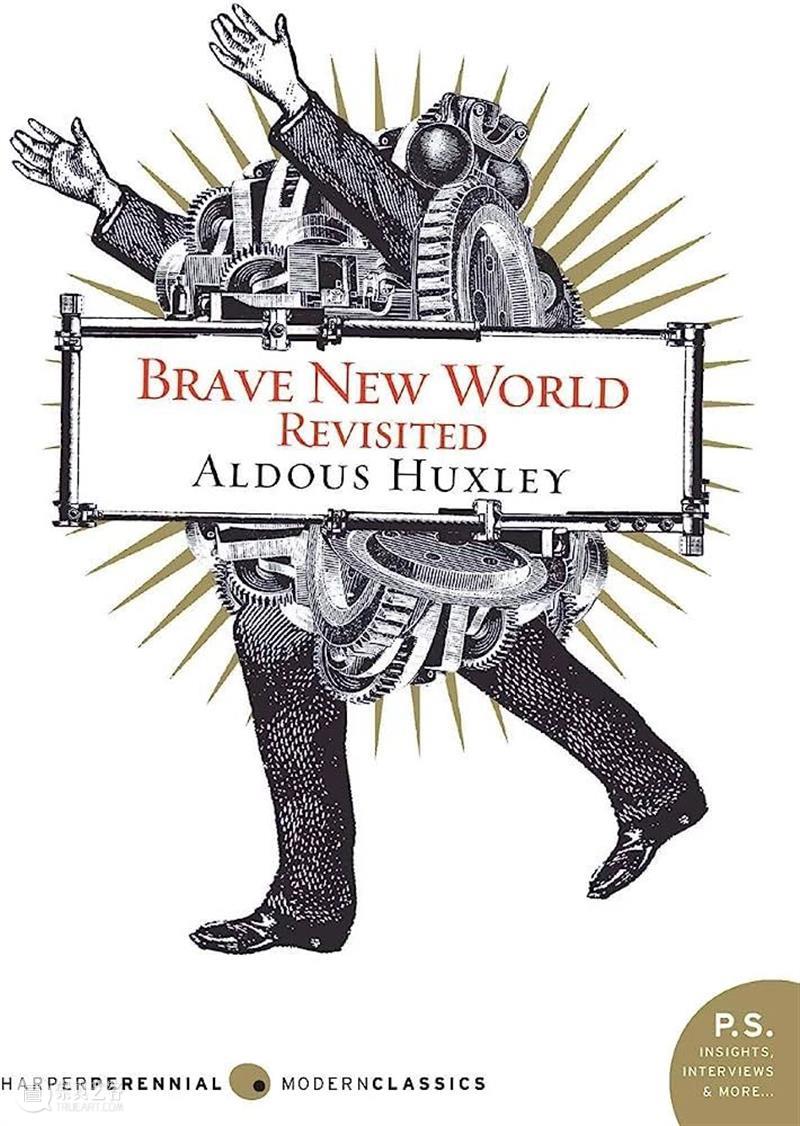
图四: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
从“风格”到“表象”
由上可知,在艺术批评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转向,从“否定”到“介入”的这种转向,是一种在当时情境下别无他选、势在必行之事,这是“反美学”的历史背景。在方法论的层面,批评家们利用的主要是一系列被笼统称为后现代哲学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在当时统称“后结构主义”。《十月》创始人罗莎琳·克劳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法国理论,当作抵抗主流后现代的武器,也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必要补充。在文集《重新编码》中,福斯特特地更新了他那赫赫有名的关于两种后现代主义的二分法④,抵抗的后现代”相对于“反动的后现代”之分,改为“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相对于“新保守派的后现代”之分,从目的论的黑白对立,转向从方法论上予以甄别,自此“后结构主义者”也就成了《十月》批评家的代称,这一代称几乎沿用至今。
这十几年间的哲学式艺术批评成了艺术批评史上最难以理解的文本,单篇论文就可能涉及巴特、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和拉康等数种理论模型,读者公认:理论家(theorist)比恐怖分子(terrorist)还要可怕。同时代的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这样自辩:“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寓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寓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寓言的办法。”[7]5 这些理论之间有许多具体的分歧,甚至其理论家大部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们最终在左派批评家们这里汇聚了起来,主要因其共同的历史语境。福斯特总结道,那个时代《十月》批评家群体的许多论文,都是在当时情境的压力之下撰写的,其伦理判断多于其分析性,诸多 “反中心”“后结构”“反宏大叙事”的法国理论,都是用来在理论层面上支持一种去学科/学院化。正如詹姆逊说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7]5,艺术批评理论也是如此,它们是工具,是历史性的,被用以进行“为了重新铭写表征的秩序而不惜将之解构的一种批判”。福斯特的文集也正是以德勒兹所提出的对现代性的“规范重建(recoding)”作为标题。
但同样作为新左派、后结构主义者,当时的文学、文化批评圈对整个后现代主义艺术圈的判断极为笼统模糊。回顾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批评家们提及艺术领域的片段,不难发现,他们和1960年代的比格尔有着差不多的盲区,不太了解同时代的艺术和批评话语。如詹姆逊在70年代的描述:
当代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标志着现代主义范式的解体,这些范式有关于神话和象征、时间性、有机形式和实在、普遍之物的限定,关于主体的认同,还有语言表达的持续性。这也预示了一些新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现身,或者说关于手工艺品的精神分裂观念的现身,那些手工艺品现在策略性地重组成了“文本”或者说“书写”,并且强调不连续性、寓言、机械之物、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裂缝,意义之中的差错,还有主体经验中的晕厥感。 [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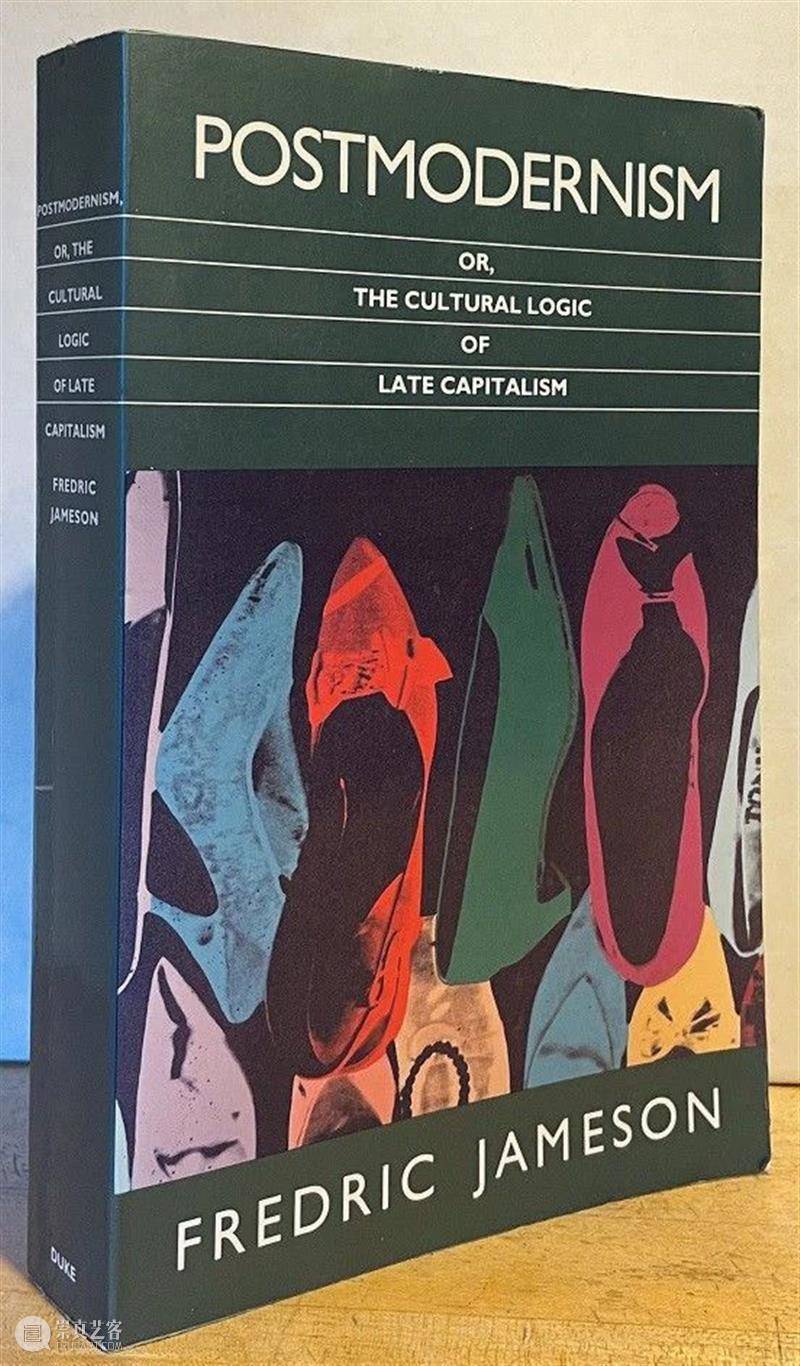
图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从那个时代至今,诸如此类的描述在学术论文和画册文本中比比皆是,但不了解其背景的读者怎么可能辨识出,这类文字的立场,是在赞美、接受后现代的美学,还是在批判?即便对于同时代的观众,要做出区分也是困难的,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也常常被误以为是褒奖。这也正是今天的艺术界对“后现代”一词的矛盾印象的来源,一方面,它似乎曾经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它的代表性作品又凌乱无聊,令人难以接受。
关于上文中“手工艺品”的重组,从现代主义的“作品”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的转向,福斯特解释道:原本“作品”暗示着一种审美的、象征性的整体,由源头(比如作者)和结果(比如一种被再现的现实或先验的意义)两方面予以定性,是个对外相对独立的闭环;而“文本”是暗示一种反审美的、“多维度的空间,让各式各样的写作混合并互相碰撞,其中没有哪一种是原初的”(如巴特《写作的零度》那样)。但他立刻表示,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样的二分法常常走入岔路,(后)结构主义的工作常常被指责为一种对文本的审美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文本”也的确如此。[5]129
“抵抗”被审美化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主流后现代中的“拟像”。在1971年由巴特所宣布的一种“对能指的拜物教”,在1972年被鲍德里亚诊断成了“符号的拜物教”。鲍德里亚分析,将指称物和所指都放入括号的做法,正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将使用价值放入括号的同样逻辑。符号的差异结构,是随着商品的差异结构来的,对符号的解放也就是它的碎片化。于是,在那时的许多艺术和建筑中都非常明显的这种碎片化,或许是附和着资本的逻辑,也就是暗示着资本已经彻底地穿透了符号。[5]129然而这些哲学、社会学思想很快就被艺术圈用来联系上了种种碎片化的艺术风格,通向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阵营:一边是后结构主义者对“碎片化”的洞察、分析与批评,另一边是新保守派对“碎片式艺术”的审美鉴赏。但后者这样打着鲍德里亚旗号的,欣赏碎片与拟像的各种潮流,却主要是对鲍德里亚的误用,鲍德里亚本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才明白了这一点:他自己的批评模型已被美国的艺术圈滥用到了各种空洞装饰物的头上,其实质是对符码的热情追捧,而不是对它的批评。 [9] 43-45于是两派批评家有可能会以相反的话语去肯定同一类作品,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可能同时充当两派批评论文的图示,如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都是常见的例子,而詹姆逊、鲍德里亚等文化批评家的许多笼统讨论,在艺术圈也能被论战双方都用以引证。这让后代的读者尤其感到扑朔迷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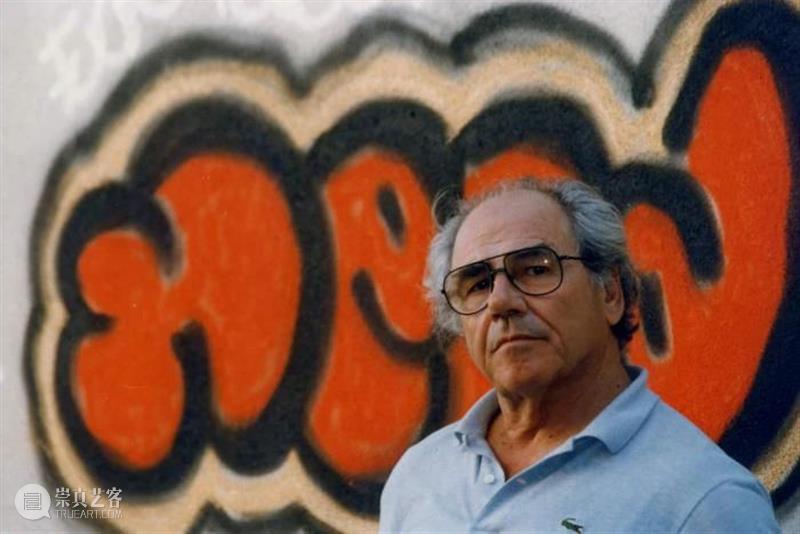
图六:让·鲍德里亚
在20世纪80年代初,声望如日中天的新表现主义绘画提供了另外一种案例,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眼中,它们不但是对解构、碎片、文本的审美主义,从更深层面上说,是对历史传统的审美主义。在那时甚嚣尘上的关于“表现/再现”的回归之下,真正在回归的是一些保守的意识形态,如专制权威性、被动心理、性别等级等等。⑤这类回归的作品也同时被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从两种后现代的二分法看,这正是代表“主流”“新保守派”的后现代主义。
如《十月》学派另一位主力道格拉斯·克林普所说,在人们眼中,总的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就是“反革命、多元化、对艺术自由的幻想”,但他认为,这是随着现代主义的终结而出现的一些“退化的症候”:“与其将这些症候描述为后现代主义,我认为不如把它们视为现代主义在形式上的收缩、僵化及还原。我认为,它们是现代主义终结的病态症候。”[10]60
在一些批评家眼中是“现代主义在形式上的收缩、僵化及还原”,但对于另外一些批评家,却可能意味着“多元、自由和解放”,因此,从道德立场上讨论艺术作品的风格,已经很难有什么实际意义。为突破这种僵局,哈尔·福斯特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而非道德立场上,分析了两种批评话语的根本区别: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后现代主义之间彼此对立之处,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新保守派处理历史风格的方式是犯了双重错误:风格,不是从自由表现中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文化符码所述的;历史(就像现实一样)不是他们所暗示的那样一个已给定的、待捕捉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待建构的叙事,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待生产出来的观念。简言之,从后结构主义者的立场,历史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本体论的基准。 [5]128
这是从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念中生发出来的分歧,因此这两种后现代的代表艺术和批评路线最鲜明的对立,就体现在对再现/表象⑥的理解上。在福斯特看来,最确切地说,是这种对于表象的批评,促成了他们这种左派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哲学不分彼此的紧密结盟。新保守派回归再现/表象,它对其图像的指涉状态和意义的解读,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这也正是煽情修辞的回归,它背后暗含的价值也就是“天才”“风格”等神话形式,是可以由金融资本任意拔高的价值(今人所谓的“品牌附加值”)。而后结构主义者重视的是对表象的批评,质疑视觉表象(无论是写实主义、象征还是抽象)的所谓“内容”的真实性,揭示不同类型的编码所支持的种种关于意义和秩序的体制(regimes)。
总的来说,围绕“风格”或“表象”这些术语的论争,其基底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新教伦理之战。在那个 “解构”一词人人皆知的年代,表象只是表象还是现实,历史是一个认识论还是本体论的问题,风格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还是来自天才、个性——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了十几年的论争,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中,后结构主义者所愤怒的,是部分写作者的选择性失明:对由新表现主义所代表的绘画回归的高调赞美,其下的话语背景正是作为主流的“好玩的后现代”,而从那时至今的所谓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只是“声称前卫已完成了使命,在充满各种意义和审美的多元主义假面舞会上,有了一个体面的位子。”[11]41
(未完待续)
[1] Foster, Hal. ed.,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C], Seattle: Bay Press, 1983.
[2] Foster, Hal. "An Interview with Hal Foster: Is the Funeral for the Wrong Corpse?." [J] Platypus Review 22, 2010.
[3]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 沈语冰、张晓剑主编:《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
[5] Foster, Hal. Recodings: Art, spectacle, cultural politics[M]. Bay Press, 1985.
[6] 本雅明·布赫洛,《新前卫与文化工业1955年到1975年间欧美艺术评论集》[M],何卫华,史岩林,桂宏军,钱纪芳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4.
[7]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桥、严锋等译,三联书店,1997.
[8] Fredric Jameson, Fables of Aggression: Wyndham Lewis, the Modernist as Fascis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9] Baudrillard, Jean. The Conspiracy of Art: Manifestos, Interviews, Essays. [M] Semiotext, 2005.
[10] 道格拉斯·克林普:《在博物馆的废墟上》[M], 汤益明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
[11] Buchloh, Benjamin HD. "Figures of authority, ciphers of regression: notes on the return of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an painting." [J] October, 1981.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