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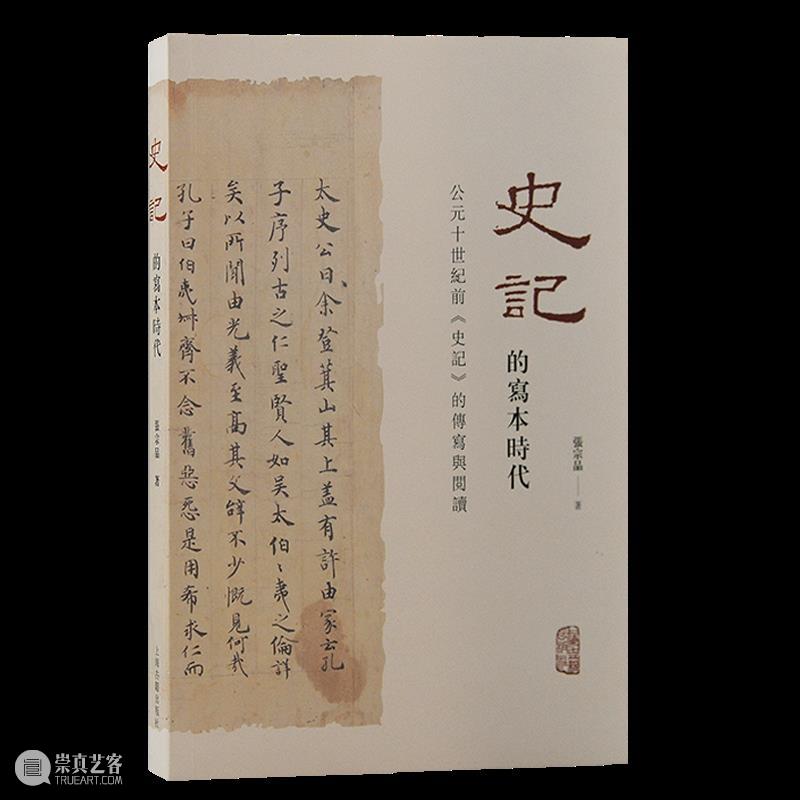
《史记》的写本时代
——公元十世纪前《史记》的传写与阅读
张宗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10月
98.00元
978-7-5732-0780-7

作者简介
张宗品,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写本文献、秦汉文献。近年来在《敦煌研究》《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汉学研究》(台湾)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校书与修史:东观与东汉帝制文化整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
《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历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从公元前一世纪问世到公元十世纪,《史记》的文本内容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删削与续补,晋唐之际注本的形成乃至唐代定型的三家注都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段。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史记》的经典化问题。全书以《史记》的多种古写本为重要文献来源,将写本内部及写、刻本间的文本变化作为切入点,详细梳理了汉代以来《史记》的传写、阅读史。同时,本书还对《史记》日藏古写本及敦煌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衍及日本《史记》学的变迁。本书持论严谨,资料详实,探研深入,心得独具,从书籍史、阅读史角度,为学界的《史记》研究提供新的着眼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意义/1
第二节 材料与方法/8
第三节 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13
第一章 道势背景下的《史记》文本问题/29
引言/29
第一节 道统与治统/30
第二节 太史公之意/35
第三节 汉武治统与《史记》的文本问题/41
第四节 史书续改与史家道统的易位/48
第五节 作为权力象征的《史记》及其史书化/54
余论/58
第二章 汉晋士人的抄读与《史记》文本之变迁/60
引言/60
第一节 内廷本及其抄读/61
第二节 家藏本及其抄读/68
第三节 《史记》文本的层累与变迁/75
第四节 经典化与《史记》经典文本的形成/93
第三章 从古写本看汉唐之际《史记》的抄写与阅读/101
第一节 《音隐》与写本时代《史记》的抄读特质/101
第二节 吐鲁番《史记》写本残片与《史》《汉》对读的风习/108
第三节 从《春秋后语》残卷看晋唐史家的《史记》阅读——兼论《史记》的文本衍生现象/128
第四章 裴注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目考/144
引言 裴氏八十卷本之旧不可复见/144
第一节 《二中历•经史历》所载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目录》/146
第二节 论《史记目录》为《集解》篇目之旧/159
第三节 《史记目录》与古书篇卷的再认识/164
余论/166
第五章 从写本到刻本——唐宋之际《史记》传本的变迁/169
第一节 刻本时代与《史记》的文本规范/169
第二节 写本与刻本的兴替——刻本时代《史记》的形态转变与文本校订/176
第三节 从《史记目录》看写刻演变与《史记》篇名篇序之改易/190
余论 刻本时代与《史记》写本的淡出/204
第六章 《订正史记真本》与《史记》真本问题/206
第一节 《订正史记真本》与宋代《史记》删本/206
第二节 洪氏“真本”之形貌/210
第三节 《史记》“真本”之遗音/216
余论/218
第七章 长安、西域与东瀛——大江家国写本与日本平安时期的《史记》阅读/219
第一节 《史记》文本的传入及其在平安时期的传写阅读/219
第二节 大江家族与博士家的《史记》学/226
第三节 大江家国写本的传写特征及其致误规律/232
第四节 批注、师说与背隐义/241
余论 长安、西域与东瀛:日藏古写本的再思考/250
附录 日藏大江家国写本《史记》所见中古佚注八种考述/252
第八章 余论:《史记》阅读的四个向度/268
引言/268
第一节 政治性阅读/269
第二节 应用性阅读/271
第三节 文献性阅读/275
第四节 审美性阅读/277
结语/279
附录 现存《史记》古写本叙录/283
征引文献/316
后记/331
后 记
小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回首求学经历,小书的撰作颇感偶然。
二〇〇五年秋,我从皖西的偏远乡村来到南京,第一次知道古典文献学这个专业。在徐师有富先生及程章灿、武秀成、徐雁平、张宗友等诸位老师的关心和鼓励下,我才略识门径,并鼓起勇气继续求学。
二〇〇八年秋,我有幸进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安师平秋先生的指导下,我最终以《〈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前〈史记〉的传写与阅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此期间,安先生对本文从材料搜集到写作方法都倾注了很多心力。记忆中的谈话里,先生经常鼓励我大胆尝试。二〇一〇年夏天,安先生与曹亦冰、吴国武两位老师到日本开会,还专程到足利学校为我复制日藏《史记》古写本,令我感愧非常。在论文写作和答辩过程中,杨忠、曹亦冰、贾二强、廖可斌、刘玉才、顾永新、杨海峥等诸位先生也多有批评指正,使我获益匪浅。
《史记》写本材料的搜集,受惠于诸多师友。早稻田大学博士生原田信君,时在日本京都大学交流的吴海,金泽大学的陈小远,台湾大学的徐奉先、付佳等诸位学友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苏芃先生、江苏社科院的李由女史在文献资料上多有襄助,谨此并申谢忱。
我和学术结缘较晚,当初的博士论文从立意到用语,今天看来难免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或许这就是“学术青春期”的通病吧。从二〇一二年博士毕业至今,写本研究乃至文献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递有推进,新成果不断涌现。《史记》新校本的出现,出土资料的更新,以及近十年来专家学者的创见也极为丰富,小书的思考有些已经过时。为尽量保持原貌,除内容疏误之外,不多作补充更定。除删减内容之外,对于之后撰写的部分章节,这里略作说明。
二〇一二年夏,我来到《史记》的诞生地——司马迁的故乡陕西,跟随贾二强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贾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先生建议我继续完善《史记》写本文献的相关研究。长安十年,逐渐发现愚钝如我,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文献学都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解。不禁怀疑自己的研究能否与这部伟大著作展开有价值的对话。时易世变,沧海桑田。先天禀赋、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天差地别,彼此理解何以可能?我声称的理解或许只能是理解自认为理解的内容,与太史公以及文献本身并无太多关涉。作为一个遥远而渺小的眺望者,遂简单梳理了《史记》阅读史,总结了《史记》读者的几种类型,草成《〈史记〉阅读的四个向度》一章。
二〇一七年至二〇一八年秋,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系访学。访学期间,我需要定期与倪豪仕(William H. Nienhauser,Jr.)先生学习讨论《史记》文本英译的工作。研讨之余,我也常去学校的纪念图书馆(Memorial Library)翻看一些国内不常见的图书。有一次我借到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著的《日本书目大成》,其中的《二中历·经史历》竟然载有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目录。经与写本文献和传世注家文本核对,我认为其正是六朝裴注的基本样貌,遂将相关思考补录书中。后又结合大江家国写本,初步完成了平安时期日本学者《史记》阅读的初步探讨。
完美的理论构想在付诸实践之际难免会有各种走样和变形,甚至远离初心。小书与导论的设计也颇有距离。自己也一如既往地愚钝而惶惑。岁月蹉跎,深怀愧竦。
十余年来,南北西东,不遑宁居,感谢家人一直以来的理解与支持。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小书列入出版计划。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小书进行了细致编校,让拙著避免了更多的讹误。在此并致谢忱。
是为记。
责编:毛承慈、秦娴;排版:王曦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