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理论的贫瘠未来
玛莎·努斯鲍姆 著, 李怡霖 于世哲 译,范昀 审校,
节选自《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第六章“感知的平衡:文学理论与伦理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2023年
纽瑟姆夫人穿的衣服从来都不是“低开式”的,而且她也从不在颈项上围一条宽阔的红丝带。假如她也这样穿着,可不可能达到这样令他心醉神迷的效果?1
——亨利·詹姆斯《使节》
斯特瑞塞在向小比尔汉姆讲述有关查德·纽瑟姆令人惊讶的进展时,讲述了他自己的观念和他的兴趣:
在谈论他的为人、他的举止与品行、他的性格和生活时,我是把他和她联系在一起的。我所谈到的他,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交谈并一起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我是把他当作一种社会动物来谈的。(I.283)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别是近年来,并不经常有跟斯特瑞塞一样的关切与联系。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关切和联系,它会有一个贫瘠的未来。相反,我想象在未来,我们关于文学的讨论将越来越多地回到对实践的关注上——回到让文学在我们生活中具有高度重要性的伦理和社会问题上。在未来,这些兴趣,就如这里的斯特瑞塞那样,将发现自己与德·维奥内夫人的利益联系一起,也就是说,在伦理判断领域内,那些情感和欲望是无法和谐共处的。在那里,文学-哲学性探究将以类似于斯特瑞塞的“耽于幻想”(I.61)以及“诚心诚意地好奇”(I.49),询问文学作品对这些问题表达了什么——通过它们的“内容”表达,但也不可分割地通过它们的形式和结构表达,因为这些方式“在任何时侯”(就如斯特瑞塞“哲学分析”那样)都是“感知的条件,思想的指辞”(Ⅱ.49)。简而言之,在未来,文学理论(同时也不要忘记它的许多其他追求)也将参与伦理理论,一同寻求对“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回答。
“参与”,我的意思不是作为说教式的道德主义者那样去参与,而是作为迂回的盟友和反叛性的批评家那样去参与。因为我们注意到,斯特瑞塞的回答将他自己对查德的更全面的感知与马萨诸塞州乌勒特的狭隘道德观念进行了对比。在斯特瑞塞密集的感知受到攻击之前,我们这些被系统的伦理理论所吸引的人可能会像他一样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光亮之潮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种也许可以说是更为古怪的知识之中”(Ⅱ.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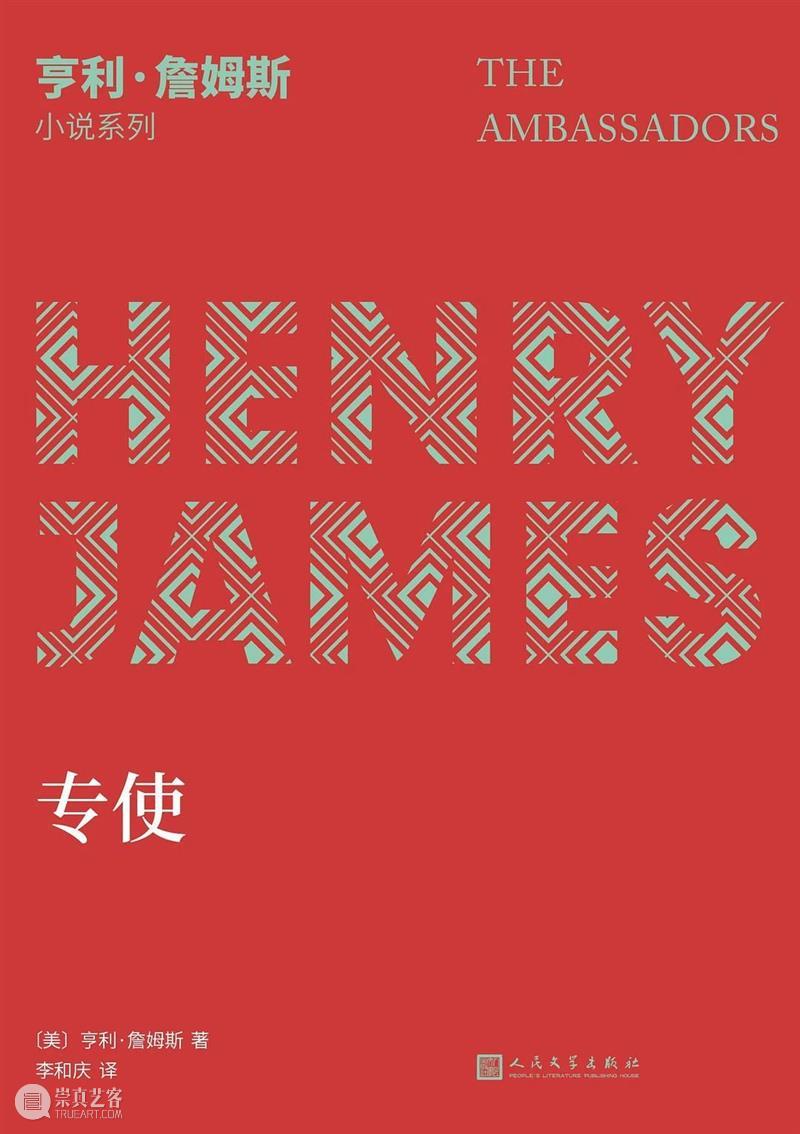
最近的文学理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无论是从它提出的问题的性质还是从它寻求启迪所涉及的名字来看,都很难将它与哲学区分开来。有关现实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有关怀疑论与辩护的问题;有关语言本质的问题——这些现在都是这两个专业的共同兴趣。在追求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文学理论不仅讨论和教授那些直接探讨文学问题的哲学家的作品(如尼采、海德格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斯坦利·卡维尔、纳尔逊·古德曼、希拉里·普特南),而且也会探讨和教授诸多并不直接关注文学问题的哲学家的著作(如W.V.0.蒯因、保罗·费耶阿本德、S.A.克里普克、托马斯·库恩、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些有意筛选的清单也显示了影响当前文学领域的哲学风格和方法的多样性。)事实上,对于当代几位杰出的人物——尤其是雅克·德里达和理查德·罗蒂——他们属于哪个专业?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其实本身便让人提不起兴致,因为不同专业领域共同分享了如此多的问题,而且方法论上的差异存在于每个专业内部,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学科界限划分。
但当我们从认识论转向伦理学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个道德哲学丰富且精彩的时代。2人们无法在时代的年轮中找到一个时代——如果不算更早时代的话,就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时代开始——有如此多杰出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各种各样的著作,探讨人类生活的核心伦理和政治问题。关于正义,关于幸福和社会分配,关于道德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关于理性的本质,关于人的观念,关于情感和欲望,关于人类生活中的运气所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些和其他问题都从许多方面得到了相当激烈甚至紧迫的辩论。这些哲学辩论经常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涉及的人类问题是多个研究领域的核心。比如,关于情感,道德哲学家与心理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关于道德相对主义,则与文化人类学者展开对话;关于幸福生活和理性,他们又同经济学家积极交流。人们当然会期待文学和文学理论在这些辩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洞察,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文学形式密不可分。因此,人们会期待那些以对文学进行一般性思考为职业的人,会讨论这些问题并参与这些公共辩论。
我们知道,这些并未发生。文学批评处理特定的文本与作者,当然,也会继续谈论对于那些作者而言至关重要的伦理与社会关切。然而,即便是这种关切亦受到当前思想压力的制约,这种思想认为讨论一个文本的伦理和社会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本性”,即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之相关的——尽管更极端——观点认为文本根本不涉及人类生活,只涉及其他文本与它们自身。3假如人们从文学批评转向关于文学的更为一般性与理论性的写作,那么伦理思想或多或少就会完全消失。我们理解这一点是借助对哲学文献的考察。哲学家的名字经常出现。然而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的名字——约翰·罗尔斯、伯纳德·威廉斯、托马斯·内格尔、德里克·帕菲特、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以及其他人,还有昔日伟大道德哲学家的名字——比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边沁、亨利·西季威克4、卢梭,以及伦理方面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和康德,根本没有出现。(即使是那些最近的道德哲学家,比如伯纳德·威廉斯、希拉里·普特南、艾丽丝·默多克5,也是如此,他们对体系化伦理理论的批判让他们自己成了文学的同盟。)文学理论领域并不研究这些作者的伦理学,就如他们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领域的同行那样。(在过去和今天)他们之中既探讨伦理学也探讨认识论的学者,也只被片面地研究过。简而言之,这些对人类社会经验的多样而出色的分析,通常不被认为会对理论家的活动产生任何有趣的影响。
文学理论可以忽略道德哲学,但仍保持了对伦理热切的兴趣——尽管之后我会尝试指出一些原因,说明为什么转向哲学可以在这里提供有价值的启迪。然而,在人们忙于关注其他类型的哲学时,道德哲学的缺失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事实上,它标志着一种更为惊人的缺失:文学理论中缺失道德哲学的组织问题,以及道德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紧迫感。我们是社会性存在,在面对巨大道德困境时,会苦苦思考对我们而言什么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对此的感受——这种实践重要性的感受,激发了当代伦理理论,也一直激励着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我们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家的著作中是缺失的。没有比读过尼采后,再阅读雅克·德里达的《马刺:尼采的风格》6更清晰地衡量这种缺失的办法了。一旦人们完成并恰当地(我认为)被德里达对尼采风格敏锐而机智的分析所折服,他就会在所有文雅的尽头感到一种相当于饥饿的空洞渴望,一种对艰难、风险和实践紧迫感的渴望,这些都与查拉图斯特拉的舞蹈不可分割。渴望对尼采看到了欧洲与整个人类的危机有所了解,他以为,无论一个人是以基督徒还是以其他尚未明确的方式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献给了这种想象。显然,尼采的作品是对现存伦理理论的深刻批判,然而,除其他以外,这也是对最初苏格拉底式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回应。德里达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查拉图斯特拉说:“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一个人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东西。”7在阅读德里达而且不仅仅是德里达之后,我感到对血有一种特定的渴望,也就是说,渴求那些谈论人类生活和选择的文学作品的写作,就好像它们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一样。8
毕竟,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本着这种精神曾经并且正在被书写与阅读的。我们接触文学的确是为了消遣和娱乐,为了那种跟随形式的舞蹈和解开文本联系的网络所带来的兴奋。(即使在这里,我也不会很快承认,有关从我们人类实际的利益和欲望中抽象出来的审美愉悦的描述存在着任何一致性)。但是能使文学对我们来说比一场复杂的游戏——比如国际象棋和网球,这种因其复杂之美使我们惊叹不已的游戏——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像斯特瑞塞那样言说。它讲述的是关于我们,关于我们的生活、选择和情感,关于我们的社会存在和我们关系的全部。9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观察到的,它是深刻的,有助于我们探究应当如何生活,因为它不仅仅(像历史那样)简单记录了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它寻求的是可能性的模式——选择和环境,以及选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在人类生活中以如此持续的方式出现,以至于它们必须被视为我们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对文学的兴趣就变成了(就像斯特瑞塞对查德的兴趣)认知性的:一种——寻找(通过观察和感受其他方式的感知)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可能性(以及悲剧性的不可能性),以及它为我们支持与颠覆了怎样的希望与恐惧——的兴趣。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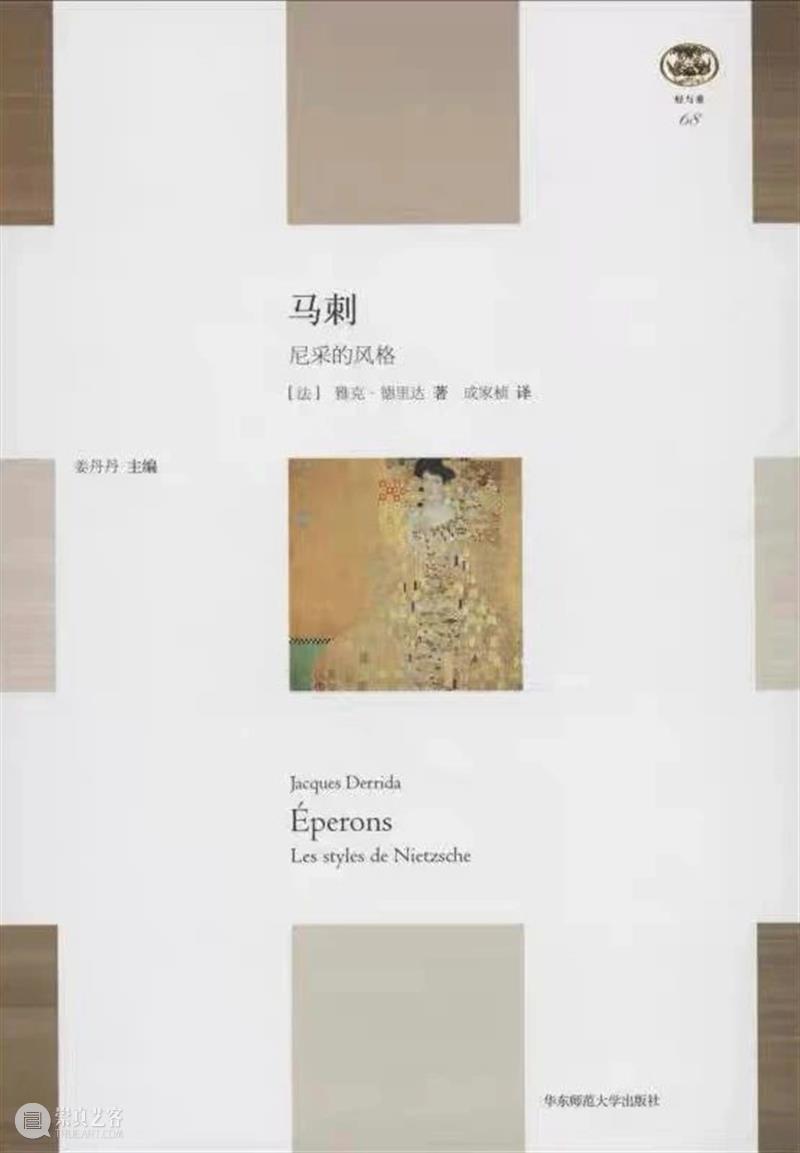
要解释文学理论是如何失去这种实践维度的,那会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将包括康德美学的影响、二十世纪早期的形式主义以及新批评。它将包括伦理理论中几种盛行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些伦理学观点,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在对待与想象性文学任何可能的关系上如此不友好,以至于伦理学一方也把对话切断了。11它也将包含对一些文学写作的批判性审视,这些写作长久以来一直将伦理关切纳入考虑。因为不少这种写作由于忽略了文学形式和简化的道德说教,给有关文学的伦理写作带来不好的名声。人们很容易感到,伦理写作必然会对文学施以暴力。当然,很明显,关注形式而忽略作品的生活意义与选择并不是一种解决方式,只是一种变相的暴力。人们本应意识到,这两种暴力都是不需要的;只有当我们仔细研究文学文本体现和表达的形式时,才能掌握它的实践内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探究詹姆斯小说所表达的生活意义,我们就无法正确地描述文学形式。然而,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12这些总的来说并没有得到承认;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历史原因。
在我看来,未来的文学理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详细地写出这段历史。我不打算在这里承担这样的任务。不过我会从我所设想的这项事业的另一个部分开始。通过详细地举一个例子,我将试着去说明文学理论可以与伦理理论协同工作,勾勒出这种理论可能关切的一些问题;并且我将提出一些方法,通过与道德哲学家的对话来协助我们发展它们。在这一点上,我将讨论詹姆斯的《使节》,我把它当作一部道德哲学的重要作品——它谈的是道德哲学如何受到一种感知的质询,谈的是纽瑟姆夫人礼服特征如何指出了在伦理理性的某些解释中的缺陷,这些解释甚至在今天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在我们开始谈斯特瑞塞之前,无论多么粗略和不完整,我们都需要讲述一下我的关于将文学理论和伦理理论结合的提议。13对于一些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某些描述而言,会将其中一方或另一方降格为合伙人身份。找到一种对伦理探询任务无偏见描述的困难本身就会阐明我们的问题;一些关于这一任务的当代著名的哲学性描述中隐藏的偏见将开始向我们表明,由于缺乏与文学思想的对话,道德哲学已经失去了什么。
我已经说过,我的文学-伦理探询开始于“人应该如何生活”14这一问题。这个出发点的选择是有其意义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像康德式的问题“我的道德义务是什么”那样)假设存在一个“道德”价值的领域,这个领域可以从人类生活中所有其他实践价值中分离出来。它也不像功利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我如何实现功效的最大化”那样,假定所有选择和行动的价值都由它们倾向于促进的结果来评估;它同样也没有假定否认这些主张。到目前为止它是中立的,只不过把这些主张留在探询中去进行审视。重点是要以一种一般性与包容的方式来陈述开头的问题,在一开始就不排除任何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主要故事。
那么,这项研究问的是,一个人如何才能过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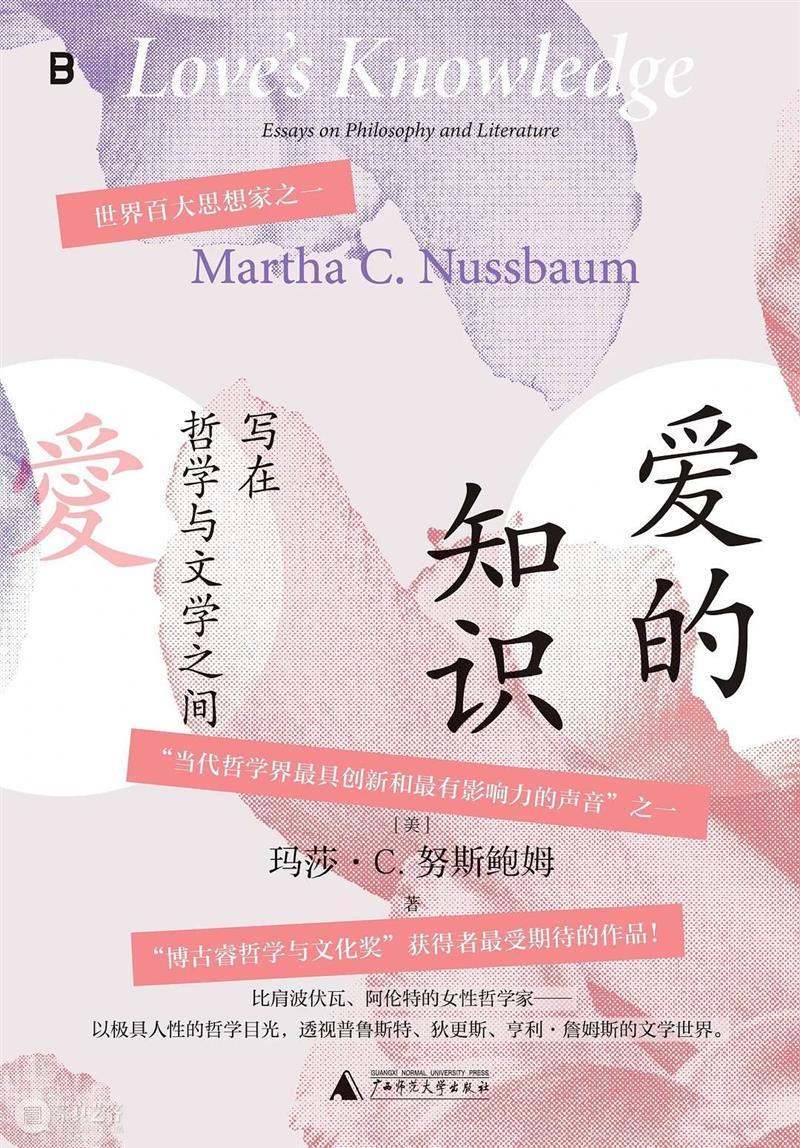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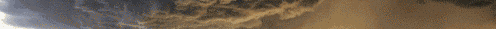
注 释
相关文章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