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疼痛是一种文化现象”?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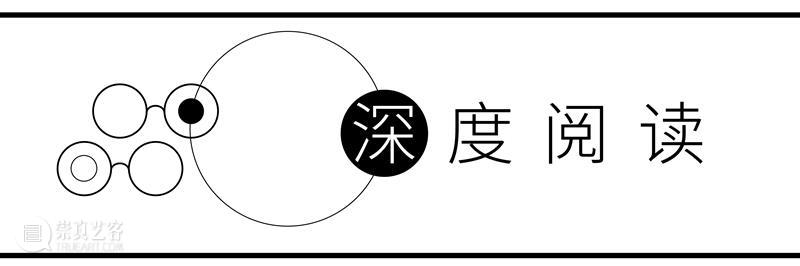

“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38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读文化、艺文志、薄荷实验、后浪、重庆大学出版社、万有引力、东方出版中心、世纪文景、新行思、明室、大学问、新经典、雅众、假杂志、七楼书店、好·奇、大风文化、华章同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微言、乐府、纸上造物、长江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十分欢迎更多出版机构一起来玩,详情请加微信lonzr25咨询(添加时请务必注明“书摊+出版机构名”)。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142期:光启书局新书《疼痛的故事》(乔安娜·伯克 著;王宸 译)。
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疼痛?如何应对疼痛?
一部跨越三百年的疼痛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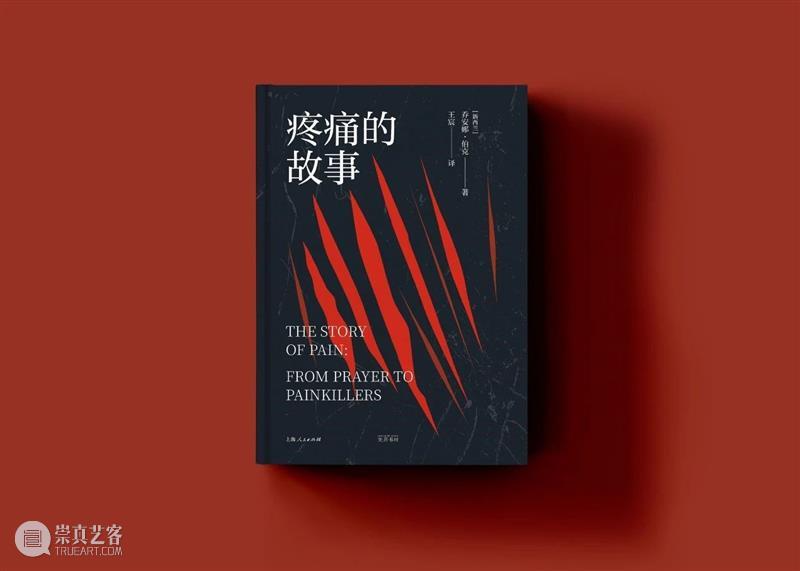
从牙痛、头痛、痛经、肌肉痛,到精神痛苦,每个人都为疼痛所扰,都试图用各种形象的隐喻来描述它。从“积极的情感体验”到需要战胜的“邪恶”,人们对于疼痛的认知和讲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有些人借此展现英雄气概,有些人则无权喊疼;有些人被认为对疼痛天生敏感,有些人则似乎特别耐疼……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人们在痛苦时如何自处?本书讲述了18世纪以来关于疼痛的故事,横跨医学、文学、宗教、生物等各领域,考察人们对疼痛的讲述发生了哪些变化,信仰、性别、种族、阶级等意识形态因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展现了身体、意识、文化、语言之间的动态联系,为我们理解疼痛提供了新方法。
○●○●
疼痛叙述的困扰
语言努力试图超越悲惨肉体的要求,以和他人交流,这部分程度上也是由于经历疼痛的人会变成自己苦楚的见证者。传达不舒服的状态有种离奇能力,会反弹到原本的受害者身上。疼痛叙述可能激起羞耻感和自我憎恨:它们都提醒疼痛者他有多落魄,加强他的绝望。
至关重要的是,叙述痛苦可能让它复苏。在《同情论,由两部分组成》(1781年)里,医师塞金 · 亨利 · 杰克逊(Seguin Henry Jackson)描述了这种效应。“回忆不愉快的客体,或让人悲伤的事件,”他指出,“会重新唤起对它们的最初印象。”因为他相信,身体器官和心理印象都会“共鸣”(我将在第8章里探讨这种理论),身体某一部分的任何运动或变化都会影响其他所有部分。因此,当“某种印象[例如疼痛]的力量持续了一段时间,心灵也相应地注意到了上述印象,由此产生的共鸣还会在印象出现之后持续很久”。思考或谈论疼痛会触发身体的“共鸣”反应,或者好像疼痛会继续回弹。
对疼痛记忆的这种特征,苦于严重疼痛的人们经常发表评论。例如在1812年,作家范妮 · 伯尼(Fanny
Burney)试图向姐妹解释,为什么自己做了乳房切除术(没有任何麻醉),却不告诉她。她的理由是,表述身体的煎熬,必然会带来痛楚。她写道:
我最亲爱的埃丝特(Esther),不是几天,不是几周,而是几个月,说起这件可怕的事,简直相当于再经历一遍!我就连想到它都感觉在经受苦难!我生病了,让一个问题搞得心烦意乱——哪怕现在,过去几个月以后,继续处理这件事都让我头疼!
哈丽雅特 · 马蒂诺也暗示了类似的现象,她观察到,虽然“没有感觉时,就无法想象它们”,对她来说,回忆疼痛感觉的“伴随物”却没有困难。事实上,与原先疼痛有关的感觉和事件“可能被记住并以那样生动的方式想象,以便在将来激发情感”。疼痛的“伴随物”异常生动地复活了跟她原先剧痛相联系的情感。大约和马蒂诺写下这篇文章同时,一位无名医师详细阐述了疼痛的这个奇怪方面。跟伯尼一样,他被迫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动了大手术。他承认,虽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但围绕着手术的全部记忆在脑海里都是清晰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痛苦体验。他回忆道,手术期间,感官都“异常敏锐”。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外科医师所做的一切。我照样可以回想起器械的伸展、止血带的缠绕、第一个切口、手指触及锯断的骨头、按在皮瓣上的海绵、扎紧的血管、缝合的皮肤、血淋淋的断肢躺在地板上,生动鲜活到难以接受。他承认,这些都是“不愉快的回忆”,而且困扰了他很长时间。“哪怕现在,”他如实表示,“它们也很容易复苏。”至关重要的是,他接着说:[尽管这些记忆]不能把跟事件相伴的痛苦(这在我的记忆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带回来,却会自行引起痛苦,变成忧虑的根源——对身心健康都不利。他那种同自己身体剧痛保持一定距离的“异常敏锐”的感觉,至少传达了原本感觉的一部分。玛丽 · 兰金(Mary Rankin)的截肢激起了类似的情感。1842年时,没有乙醚也没有氯仿,而且兰金拒绝了递给她的酒。“我现在要给这让人厌烦的场景拉上幕布,”她写道,“我的思绪一回来,就会体验到最深切的情感。哪怕这么多天过去,我一想到它,就会触碰到一根纤维,似乎让我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在震颤。”如果说疼痛叙述会让原本受苦受难者心中的痛楚复活,那么它同样会让听众感到苦恼。疼痛中的人往往选择对自己的苦楚保持沉默,以保护所爱之人,让他们免遭见证痛苦的折磨。政治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Adam Smith)承认了疼痛故事的这种影响。1759年,他观察到,“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体验”,除非通过“想象我们自己在类似情况下的感受”。我们将自己置于他的处境,设想自己承受着同样的煎熬,仿佛进入他的身体,某种意义上和他变成了同一个人,因此形成了关于他感觉的某些概念,甚至感觉到了某种东西,虽然程度更弱,却和他的并无二致。结果,“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别人的“剧痛”。它们“终于开始影响我们,然后我们一想到他的感受,就害怕得颤抖”。另一位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杜格尔德 · 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斯密的学生)也提出了相近的观点,尽管晚了差不多70年。在《人类积极与道德力量的哲学》(1828年)里,斯图尔特暗示,表达身体痛苦是不礼貌甚至粗鲁的。他嘱咐疼痛者记住,对疼痛的“所有激烈表达”都“毫无疑问让人不快,良好的教养规定,它们应当受到约束”。有必要自我控制,原因在于见证痛苦的人发现,很容易“陷进主要挂念的那个人的境况”。事实上,“灾难”深深“引起了旁观者的兴趣”,激发了他们的“同情……那样敏锐且生机勃勃”。因此,他指出:在[疼痛]下的镇定冷静,虽然表明了自我克制的男子气概,可如果我们假定,它是出于对别人感受的体贴(不管程度如何),就会有些特别让人愉快的地方。在不打麻药动手术的情况下,斯图尔特相信,对疼痛的想象“超越了真实”,而且“毫无疑问,当患者是我们爱的对象时,他感受到的痛苦所需的勇气,没有我们那么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因疼痛而发声的受苦受难者会迫使见证者战栗、瑟瑟发抖。事实上,仅仅目睹另一个人的痛苦就可能造成疯狂或死亡。例如,医护人员面临因见证太多痛苦而不堪重负的风险,这就是导致护士爱玛 · 埃德蒙兹(Emma Edmonds)心理崩溃的原因。她在美国联邦军队的服役结束得并不光彩,当时她因发烧而虚弱,又让致命的爆炸吓坏了,精神恢复力忽然消失。“我所有的军人品质似乎都不见了”,她沮丧地观察到:我又成了个可怜、胆小、神经紧张、爱抱怨的女人;仿佛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发泄压抑了很久的情绪,除了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哭,我什么也做不了,直到脑袋好像真变成了眼泪的喷泉,心变成了沉重的悲伤的负担。过去两年里我目睹的一切可怕场景,此刻都清晰逼真地出现在面前,我什么别的都想不起来。相对而言,埃德蒙兹遭的罪还不算太严重。有人因目睹痛苦而心碎至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救护队工作的年轻护士观察到,一位上了年纪的随军牧师被他在前线见证的苦难压垮了。他不断呻吟:“啊,这些可怜的孩子。上帝,他们遭了什么罪。多么了不起的英勇……噢,恐怖的屠杀……它太可怕了。”人们没法安慰他,不久以后他就“死于心碎”。莱瑟姆承认,“疼痛会杀人”——它摧毁了目击者和受苦受难者。疼痛故事的这种离奇特征要怎么解释?说法有三种。第一,目睹别人的痛苦会唤起观察者自己的疼痛记忆。1842年有人对一次特别痛苦的拔牙的描述:“我可怜的小女仆贝蒂(Betty),听到对这次糟糕手术的描述就开始尖叫,物伤其类,她回忆起了曾经在牙医手底下吃的苦头。”作家简 · 卡莱尔(Jane Carlyle)试图解释为什么没提到一场让她陷入“前所未有的剧痛”的事故时,给出的也是这个理由。1863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里,她告诉姑母,在街上滑倒以后,她承受着“长达数月的痛苦”,而且说她担心“伊丽莎白、你和安,你们有过类似事故的可怕经历,所以可能为我感到震惊和忧虑,超出了(我希望的)必要程度”。因为她们有遭受类似伤害的第一手经验,卡莱尔试图保护她们免受自己事故的影响,害怕唤起她们痛苦的回忆。第二,仅仅凭着想象的力量,听说别人的痛苦就足以让见证者感到不安,无论他们是否能回想起经历过的类似苦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亚当 · 斯密的观点。诗人威廉 · 考珀也提到了疼痛故事的这种特征。1792年,他的密友玛丽 · 昂温(Mary
Unwin)中风了,考珀坦白道:“我在精神上遭受了几乎和她身体上一样的残疾。”他承认,“所有学习研究能力,所有关于荷马(Homer)跟弥尔顿(Milton)的想法都被远远赶开”,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看着我可怜的病人”。一位论派(Unitarian)传教士西奥多 · 克拉普(Theodore Clapp)更进一步。回顾在19世纪30年代黄热病流行期间救助新奥尔良垂死市民的努力时,他承认:“异常痛苦的”死亡的“恐怖画面很长时间里一直困扰着我,不管是睡是醒。”几十年以后,克拉普依然声称:“几乎每一夜,我在梦里都会或多或少为扭曲的面孔、尖叫、抽搐、呻吟、挣扎和恐惧所苦。”他饱受折磨的想象力可能异常敏锐,因为眼睁睁看着两个心爱的小女儿在疫病中痛苦万状地死去。作家爱丽丝 · 詹姆斯(Alice James)被诊断出乳腺癌,1891年她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担忧:“悲伤都是为了K.和H.,他们会看到一切,而我只会感觉到。”疼痛的这方面特征在贫困家庭中格外明显,患者更可能紧紧挨着亲朋好友。那些观察工人阶层家庭中疾病状况的人就持这种看法。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格拉斯哥癌症医院相关的管理者和慈善家一次又一次报告:看到所爱之人死于无痛的癌症,是件可怕的事—说它可怕,是因为无助感;然而当这种疾病伴随着极度疼痛—疼痛如此剧烈,凡人几乎无法忍受—时,就可怕多了。如果说这在富裕或殷实家庭中是糟糕的,那么丈夫或妻子跟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情形下,状况又要严重多少?贫困的患者更可能一直跟亲人距离非常近,这加重了后者的痛苦。第三,还有不同领域的其他观点,如21世纪时,神经学家猜测,目睹他人的疼痛会给观察者带来痛苦,因为共情可以调动神经过程。关于“镜像神经元”,科学上有很多争议,不过在第8章里,将讨论目睹疼痛会产生的影响这一方面。由于表达疼痛经常会伤害别人,疼痛中的人有强烈的动机去压抑呻吟,他们不想伤害别人。例如,1811年范妮 · 伯尼在接受乳房切除术之前,确保她丈夫被叫走。根据她的回忆,当看到告知她几小时后要切除乳房的便条时:我装出一副要花很久读那张便条的模样,好争取时间制定某些计划,我害怕将M. d’A.[伯尼的丈夫]牵扯进来,让他目睹我不得不经历的一切,徒劳而凄惨,它击败了其他所有人,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表现得如同在指挥另一个人。另一些人只是压抑自己的剧烈痛楚。这看上去是蕾切尔 · 贝茨做出的决定。在1834年的回忆录里,贝茨描述,自己承受着“极度疼痛”,之后她观察到姊妹在哭泣。贝茨感到羞愧,承认“我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痛苦多么巨大”,因为发泄出来“好像是种解脱”。然而,她补充道:“我不希望让你难过。”一小会儿以后,妈妈问她“有没有好点”,贝茨轻声喃喃道:“挺好的。”这是个在疼痛叙述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并不局限于贝茨这样的虔诚者。一名机械师在1856年11月的日记里承认,他“不敢给密友写信,因为疼痛实在太巨大了,我害怕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来,让她担心,这没必要”。护士德 · 特拉福德(De Trafford)在一名士兵身上也观察到了这种不让亲人“担心”的愿望。那人名叫泰特(Tait),肠子被射穿了。她报告说,泰特“非常凄惨地呻吟着,有时还会哭泣和抽噎”,然而他恳求他们,别叫他母亲来,“希望母亲不要来—看到他遭罪,她会难过的”。他们无视泰特的恳求,尽管他“害怕疼痛会开始……当她在那里的时候”,他保持着坚忍的模样,她离开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承受痛苦的男男女女经常试图向所爱之人“隐瞒”自己“处于巨大疼痛当中”的事实。一名丈夫跟护士解释为什么要让妻子出去办事:“[我]疼得厉害,然而我不想毁了伊丽莎(Eliza)的圣诞节。”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接近三分之二的转移性癌症患者承认,他们试图掩饰疼痛,免得让所爱之人“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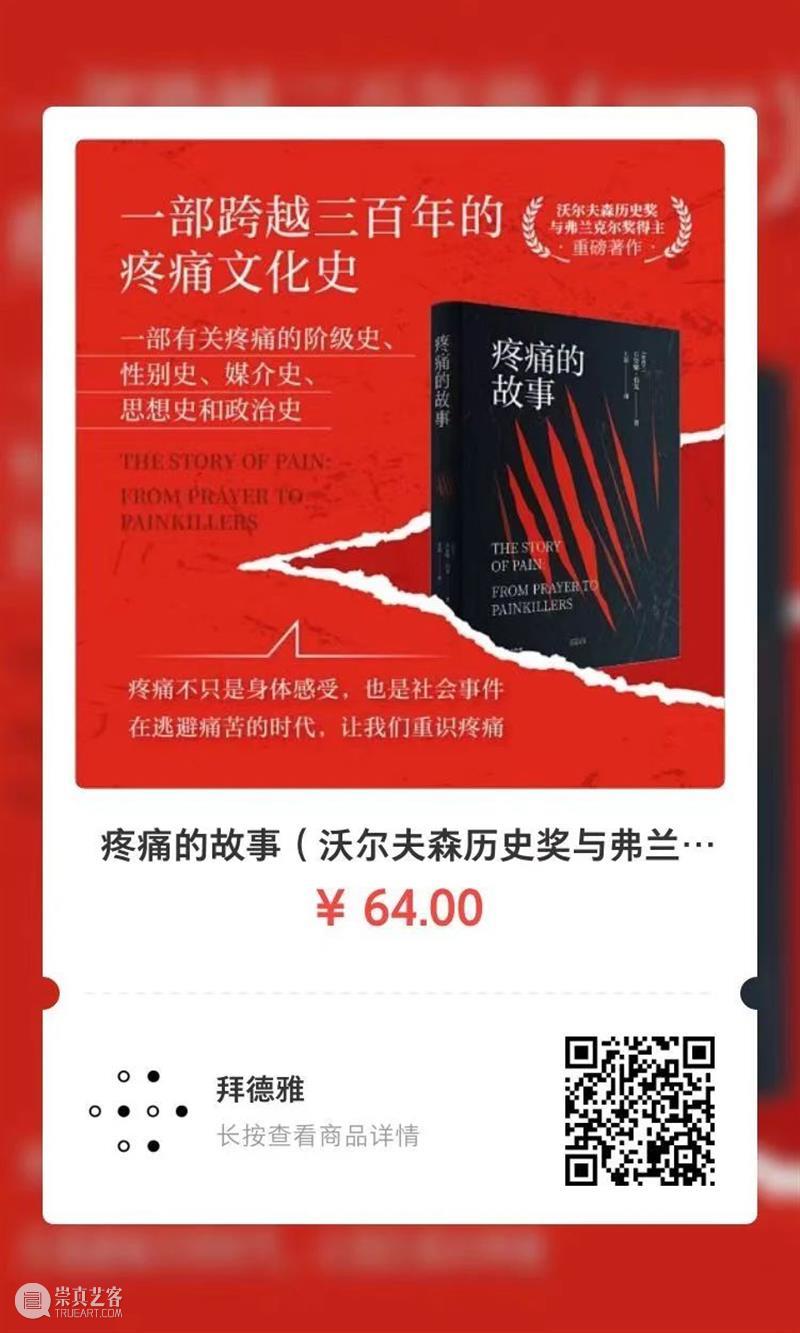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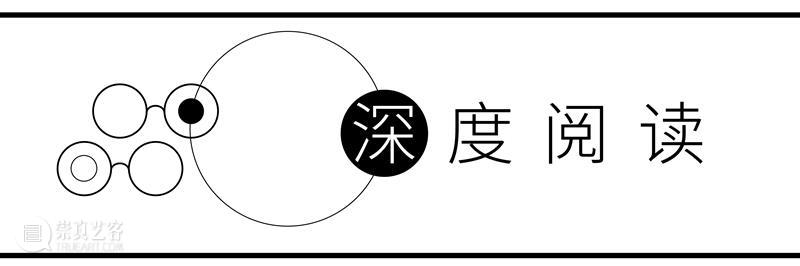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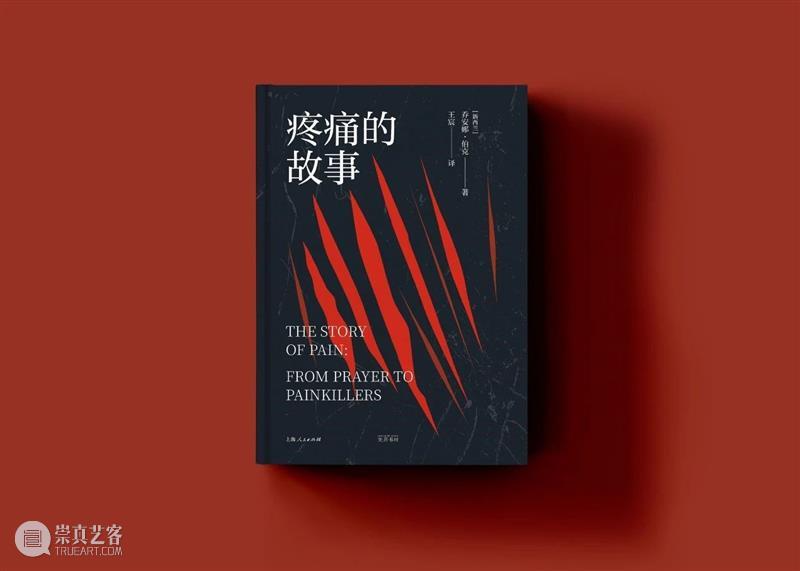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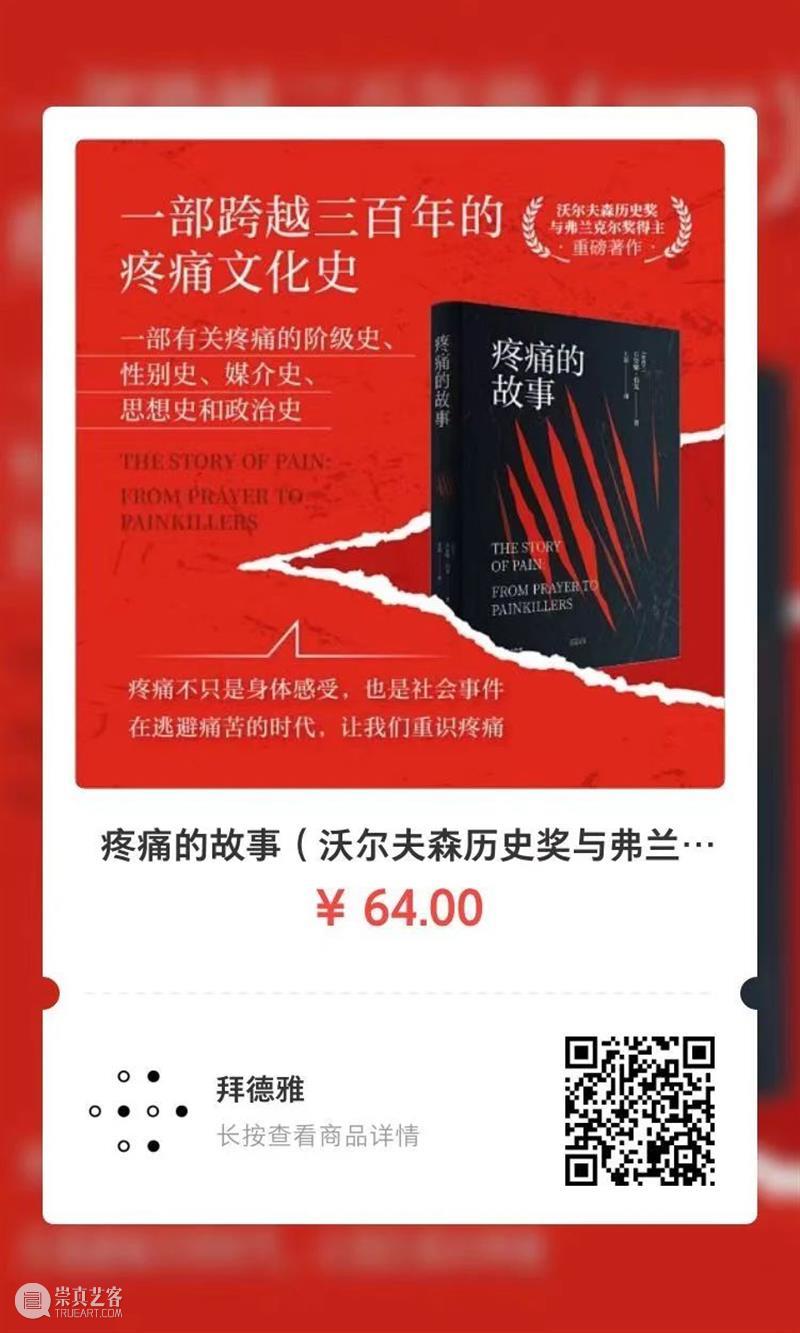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