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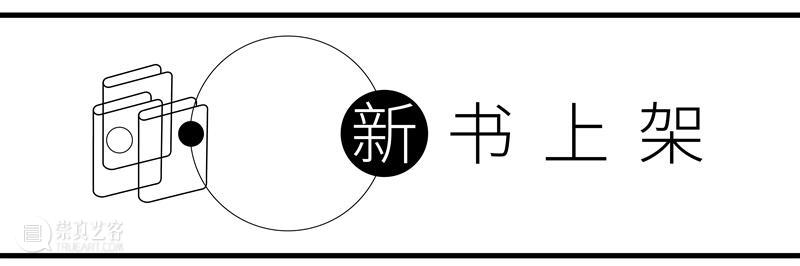
大家好,拜德雅图书工作室近日推出了2023年的第17-18种新书,从属于“拜德雅·人文丛书”:
《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布鲁诺·拉图尔 著,史晨 刘兆晖 刘鹏 译)
《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3版)》(亨利·列斐伏尔 著,米兰 译)
这两种新书均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
卡夫卡曾写到
一本好书应如冰斧般拥有强大的冲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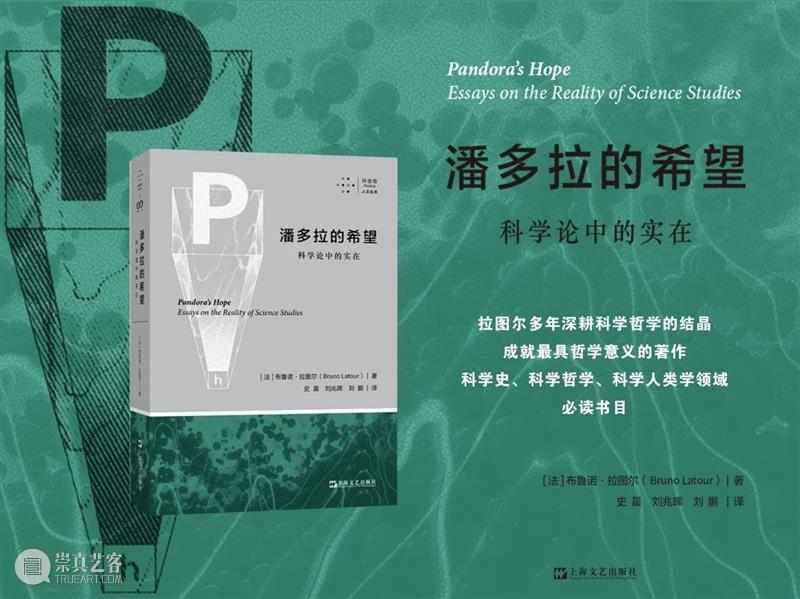
今天给大家推送《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书摘(节选自本书第7章)。
在《高尔吉亚篇》的三次对话中,强权和公理似乎从来没有可比性;稍后我们将看到原因。两类专家知识具有可通约的相对性质,而这种可通约性处于争议之中:一类专家知识掌握在苏格拉底手中,另一类掌握在修辞学家手中(“修辞学家”似乎是在《高尔吉亚篇》中被发明的)。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和稻草人智者认为,需要一些专家知识来使雅典人举止得体或使他们走投无路、闭嘴不言。尽管困扰着广场人们的问题仍出现在对话中,至少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但苏格拉底和稻草人智者不再显而易见地去解决它:鉴于政治在数量众多的人、总体性、紧迫性和优先性方面强加的限制,聚集起来的政治体就不能仅仅依赖专家知识而做出决策。我们将在第 8 章探讨这个问题。在不诉诸专家手中的客观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做出决策就需要像民众本身那般纷繁复杂的、广泛传播的知识。整体的知识需要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少数,但这对卡利克勒和苏格拉底来说是一个丑闻——一个有着一以贯之称谓的丑闻:民主。
因此,此时此地的两位同伴相比于彼此的分歧,更需要达成彻底的一致:这场较量事关如何更快、更严实地堵住人们的嘴。在这种情况下,卡利克勒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双方都认为专家需要像家长那般“照看社区及其公民”(513c),但就何为最好的知识展开了争论。修辞学家有一种专业知识,而苏格拉底有另一种专业知识。前一种辞藻华丽,而后一种属于绝对真理。前一种适用于广场的危险境地,而后一种是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在远程的、平静的一对一对话中所孜孜以求的。乍一看,似乎应该是苏格拉底在这场角逐中失利,因为他的方法本身就是广场恐惧症的,且只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运转,因而无法用来说服广场上的公民。“如果你能证明我论点的有效性,我就满足了,”苏格拉底天真地向波卢斯坦白,“而且我只想获得你的投票, 并不关心其他人的所思所想”(476a)。但政治恰恰是“关心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只拉一张票,犯了比犯罪更糟糕的政治错误。因此,当卡利克勒责备苏格拉底的这种孩子气行为时,他就应该获胜了:“避开了社区的核心处和广场的最深处,即使再天生有才也无法发展成真正的人,因为正如荷马所说,那些地方是‘崭露头角’之地。相反,他将自己的余生埋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在角落里与三四个年轻人窃窃私语而从不公开表达重要的、有意义的想法。”(485d-e)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对话只应该以这样一个场景结束:苏格拉底被送回校园的角落;哲学被限定为一种无用的专业痴迷,与“真正的人”如何以“重要的、有意义的想法”来“崭露头角”毫不相关。这应当是修辞的用武之地。但在一次次地重铸科学(大写的科学,即Science)权力时,我们并不会这么做。随着苏格拉底提出“真理语境”,卡利克勒就不再可能获得胜利。这种精妙的诡计足以扭转对话的逻辑进程,使苏格拉底反败为胜。
绝对真理性的推理多了些什么,使这种推理比智者援引的自然律好得多?智者援引的这种自然律用于反对“奴隶和各种人类废物”的习俗。这种绝对真理性的推理则是无可争议的:
苏格拉底:但是知识可以既真又假吗?
高尔吉亚: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显然, 信念 [pistis] 和知识 [episteme] 是不一样的。(454d)
智者的超越性在于超出习俗,但并未越过争议,因为不管投入多少种钟形曲线(Bell Curves),更优越、更自然、更天生、更有教养的问题还是引发了另一波讨论,这种讨论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卡利克勒设法降低人群的物理重量和数量,但并未完全逃离人山人海的广场。苏格拉底的解决方案则强多了。他掌握了数学证明的秘密,即步步为营地说服和迫使人们认同一切。然而,这种推理方式绝不适用于广场这种极其严苛的状况,用女权主义的老口号来说,这种不适用性就好比自行车之于鱼的无用性。因此,苏格拉底必须做得更多才能运用这一武器。他首先必须迫使其他人放下武器,或者至少让他们相信自身已彻底放下武器:“所以我们最好从两种说服角度进行思考:一种是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商讨信念 [to men pistin parchomenon aneu tou eidenai],另一种是商讨知识 [epistemel]。”(454e)
知识啊,多少罪行都是以你的名义犯下的!整个历史都指望知识。这种反对意见尤为可敬,使我们可能在这一点上失去勇气,看不出这种论点有多么离奇和不合逻辑,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受操纵的强权与公理之争。这两种说服的区别就在于两个无伤大雅的单词:“without understanding”(缺乏理解)。但理解什么呢?如果苏格拉底指的是理解政治性讨论中的特定适切条件,也就是数量众多的人、紧迫性和优先性,那么他肯定错了。恰恰是因果的绝对推理,即知识才是“缺乏理解”的,这没有考虑到实用状况,即决定那些在广场深处同时发言的万余人下一步行动的实用状况。苏格拉底自身的非情境化的证明知识,无法取代广场的实用知识。他的武器难以置信、缄默不语,但在广场情境中只是无谓的威慑。他需要帮助。谁来帮他一把?帮手就是柏拉图所发明的陪衬者(foils),他们通常就像理想中的稻草人一样容易掉进陷阱。
如果作为木偶的智者们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厌恶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所使用的技巧和花招,那么对话就无法奏效,也不能使苏格拉底克服重重困难而获胜。因此,当苏格拉底区分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时,稻草人智者们并不会对此有异议,因为他们对实践有着同款的贵族蔑视:“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烹饪绝不涉及任何专业知识;它既不考虑快乐的本质,也不考虑快乐发生的原因……有技术含量的厨师所能做的,就是记住一套由习惯和过去经验而来的、根深蒂固的例行程序,也正是它使我们拥有了快乐的经历。”(501a-b)
有趣的是,尽管这种纯实践技能受到了轻蔑,却符合今天的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和认知人类学家对“知识”的定义。但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知识和实践技能之间的区分本身只包含了苏格拉底对平民的鄙视。此时的苏格拉底如履薄冰。知识和实践技能之间的区分,不仅使苏格拉底能诉诸一种缄默不语的、优越的自然律,还通过堵住大量民众的嘴来强制执行这一区分,这些民众每天忙着自己的事情却不知道在做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识和实践技能之间的区分就会消失。因此,如果不是由纯力量来强制执行这种绝对的划界(这是历代认识论的真正任务),那么“真理语境”就无法左右公共争论中极其有害的氛围。历史上很少有运用“纯力量”的案例。我们有什么可以用来强化这种区分呢?我们有的只是苏格拉底对此的言论,以及高尔吉亚、波卢斯和卡利克勒做出妥协,温顺地接受了苏格拉底的定义,它们在柏拉图的戏剧机器中小心翼翼地演出。对无条件诉诸非建构的“客观法则”而言,这些条件是相当多的。
正如利奥塔不久前揭示的、芭芭拉·卡森最近有力证明的那样(Cassin 1995),需要一场政变才能实现对两种知识的区分,并确立力量和理性之间的绝对差异。这是一场从哲学中驱逐智者、从严格知识中驱逐平民的政变。如果没有这场政变,那么专家的证明知识就无法取代政治体成员们精确的、微妙的、必要的、广为流传的、不可或缺的知识。这些政治体的成员决定着广场的下一步行动。知识无法取代信念。当然,绝对真理性推理仍很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但与如何最好地约束众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如同所有政体的诞生一样,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最初也是由血腥政变而来。在这场政变中,流的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血,而这就是戏剧之美。苏格拉底的牺牲使他的行为更加不可抗拒,其合法性也更加不容置疑。到最后,剧院里的人都泪流满面了……
智者无力匹敌这一戏剧性的行为:首先,他们承认有必要用专家知识取代贫穷无知的民众所拥有的知识;其次,他们承认证明知识与平民用的技巧、花招是完全不同的,而不是相对不同的,并且还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的是空洞的专业知识。现在听起来,高尔吉亚的吹嘘是多么愚不可及:“难道不能简单一点吗,苏格拉底?修辞学是你唯一需要学习的专业领域。你可以忽略其他方面,但仍然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459c)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一明显愤世嫉俗的回答实际上精确定义了政治行动的非专业性质。不过,如果我们都忽略这一点,并开始接受较量,使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与修辞学家的相互竞争,那么诡辩术就会立马变成一种有壳无实的操纵之术。这就好比把赛车引入马拉松;新机器让慢速的跑步者看起来荒唐可笑。
苏格拉底:你所提到的这种现象,给人一种超自然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感觉。
高尔吉亚:你知道得太少了,苏格拉底!几乎每一项成就都立足于修辞学……在过去,我和我的兄弟或其他医生经常去找他们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拒绝吃药, 也不让医生给他做手术或烧灼伤口以止血消毒。医生无法说服病人接受他的治疗,但我做到了,尽管除了修辞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专业知识可用。(456a-b)
即使是这样的语句,我们也需要数百年巴甫洛夫式的训练才能把它们解读为愤世嫉俗的,因为真正的高尔吉亚在这里暗指的是,专家无法使全体人民共同做出艰难的决策。真正的高尔吉亚提出了一个异常精妙的技巧,苏格拉底不想理解这个技巧但又尤为灵巧地实践它;受人指使的木偶高尔吉亚声称,没有任何知识是必要的。舞台上的失利,使修辞学家们被送上了断头台。在接受修辞是一种专业知识,继而又发现它空洞无物后,修辞学家们现在被完全驱逐出知识的领域,他们的技巧也被贴上了“奉承”(502d)的标签。这种“奉承”是一种流行的、晦涩难解的技能,无法将这种技能与修辞区分开来。“嗯,在我看来,高尔吉亚,它并不涉及专业知识;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头脑、 一些勇气和一种与人打交道的天赋。我称之为‘奉承’。它还有许多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烹饪。我想说的是,烹饪看起来确实像一种专业知识,但它实际上不是:它是一种习惯化的本领 [ouk estintechne, all’empeiria kai tribe]”(463a-b)。
最动容的是,即使是在这场著名的政变中,苏格拉底仍在称赞修辞学,这一点值得我们多加关注。我们为何不将“精明的”“有勇气的”“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的”视为正面的品质呢?为何不将这些品质视为苏格拉底所缺乏的,哪怕苏格拉底主张的是其对立面?就此而言,有做厨师的天赋有何不好?相比于众多坏的领导者,我更喜欢主厨!但苏格拉底赢了。最弱的一方战胜了最强的一方。最不符合逻辑的“快乐的少数人”战胜了“所有人都同时关心作为整体的政治体”这一“普遍”逻辑。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最不适合统治人民,但又统治着他们,至少在咫尺天涯的祝福之岛(the Isles of the Blessed)是如此:“我认为,”他极其嘲讽地说,“我是雅典目前唯一真正的政治实践家, 是真正政治家的典范”(521d)。
事实是,已牺牲的死人对活人而言是最持久的、最不容置喙的统治,拥有最绝对的权力。
稻草人智者的失败无法与雅典平民的失败相提并论,这一点可以从对当前论证的总结中看出来。“人类废物和各种奴隶”是伟大的缺席者,他们甚至没有像经典悲剧那样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常识。当仔细阅读这段最著名的对话时,我们不仅发现了卡利克勒(强权)和苏格拉底(公理)之间的斗争,而且发现了两个重叠的争端,其中只有第一个争端被无数次地评论过。在这场木偶秀中,睿智的圣人与金发的野兽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表演如此出彩,以至于孩子们都惊恐地尖叫起来,担心强权会压倒公理。(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后来一个尼采式的编剧改写了剧情,使卡利克勒成为掌控者种族的领袖,出色又阳光;使苏格拉底成为牧师和怨恨者的后裔,堕落又邪恶,二者相互竞争,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这些孩子应该还是会尖叫,只不过这次尖叫是因为公理压倒强权,强权成为软弱而温顺的绵羊。)
但第二种斗争在台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对阵双方是雅典人民、成千上万的愚者 VS. 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这两个盟友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一致的,只是在让人群闭嘴的最快方法上存在分歧。我们如何最好地扭转力量平衡、让民众闭嘴,并终结这种杂乱无序的民主?是通过诉诸理性、几何、比例,还是通过贵族的美德和教养?苏格拉底和卡利克勒分别独自对抗人群,都想统治暴民以及获得这个或另一个世界的超额荣耀。
强权和公理之争像是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蕴含着卡利克勒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和解,双方都在充当对手的陪衬。稍早的版本是为了避免陷入强权,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理性的统治。稍后的版本也一样,只是颠倒了过来:为了避免陷入理性,我们无条件地投入强权的怀抱。但与此同时,站在台下的雅典人民沉默不语、困惑不解、目瞪口呆,他们仍然在等着掌控者找到颠覆他们“物理力量”的最好方法——如果他们的人数不是这么多,这种“物理力量”可能会被“彻底轻侮”。是的,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不会再有人受到有关强权与公理这一宇宙之争的幼稚故事的迷惑。现在,木偶师的手太明显,而苏格拉底和卡利克勒这对宿敌手挽手的丑闻,对小孩来说是一段富有启迪的经历,就好比看到《哈姆雷特》的演员们在幕布落下后在酒吧里一起开怀畅饮。
这样的经历应该会让我们变得更老练、更聪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三种不同的力量(或三种不同的理性;从现在开始,语词的不同选择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微妙差别)——苏格拉底的力量、卡利克勒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而不仅仅考虑力量和理性之间的戏剧性对立。我们必须处理的是这样的三部曲,而不再是一个对话。现在,两场更公开较量的拉锯战取代了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之间的绝对对立:一场是两位英雄之间的较量;另一场是哲学家尚未认识到的较量,对阵双方是站在同一边的两位英雄 VS. 站在另一边的万余名普通公民。在强权与公理之间的激烈选择中,排中律看起来尤为强大——“迅速选择你的阵营,否则一切都会失控”。但现在,作为第三政党而聚集起来的雅典人民打破了这一排中律, 他们正位于被排除的中间地带。这一点用法语可能更好理解:le tiers exclu c’est le Tiers Etat! (被排除的第三方就是第三国!)哲学家没有逃离洞穴,而是把所有民众都送入洞穴,并以阴影为食!
当听到暴民统治的危险时,我们现在可以平静地问:“你指的是卡利克勒的一元统治,还是‘人类废物和各种奴隶’聚集的沉默统治?”当听到“社会的”这一危险词时,我们能解剖出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卡利克勒强权的权力对抗苏格拉底的理性;另一种是在面对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试图施加的一元权力时,人群所进行的、从未被描述过的抵制。一方是两个体弱的、裸露的、傲慢的人;另一方是包含儿童、妇女和奴隶在内的雅典城。这种两个人对抗所有人的奇特战争使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这两个人,那将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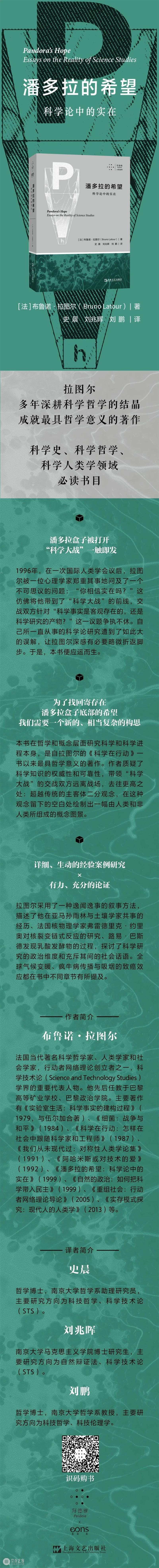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