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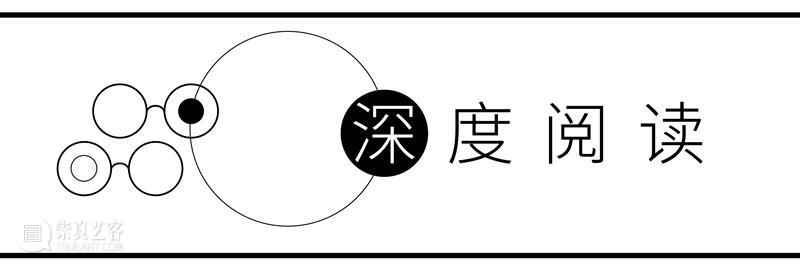

论一种新先锋派(1924)
我只想说:你一定既爱它又恨它——有多爱它就有多恨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电影是一门艺术,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个性。首要的困难在于选择其中正当可恨的地方。如果说这种选择是困难的,那是因为,它一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修正。
事实上,一门艺术最好的朋友,最终总会被他们的原则所迷惑。而由于艺术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超越其规则。这些昔日最好的朋友,就成为明天最大的敌人,成为忠实于陈腐方法的狂热者。对这种忠诚的不断颠覆,是所有艺术缓慢演进的特征。
因此,在今天终于——终于,但有些姗姗来迟——一年前还被认为是怪异与可疑的电影表达方法,变成了时尚(à la mode)。成为时髦总是意味着一种风格的终结。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抑制字幕的使用、快速剪辑、对布景的重视,以及布景的表现主义风格。
第一部没有字幕的电影几乎同时在美国和德国出现。在美国是查尔斯·雷的电影《乡间水塘》(The Old Swimmin’ Hole),虽晚了些时间,但它在这里发行并被加上字幕。发行商在本片的新颖性面前显得有些退缩,小心翼翼地在影片中加入了大约15条字幕。在德国是卢普·皮克的《碎片》(Scherben)。我在此并不是要为这种被称为“美国式”的字幕辩护——这种命名是不正确的,唉,因为法国往往也是这样。这种字幕事先向观众解释一遍他将要在下一个画面中看到的东西,之后又告诉他第二遍,以防他要么没看到,要么没理解。当然,抑制字幕使用作为一种新的方法有它的价值,并非完全在于它本身,却是各种方法中一种实用的方法。而卢普·皮克必须算是无字幕电影的大师,在上一季,他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完美的电影,那就是《圣西尔维斯特之夜》(The Night of St. Sylvester),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电影化的电影,在它的光影中,电影第一次传达了一种人类激情的极致。而无字幕电影的理论依据,显然是符合逻辑的:电影用影像而非文字来叙述。只是,人绝不应该走到理论的极端,理论的最远端,永远是导致其瓦解的弱点。因为你不能否认,出于心理学的原因,看一部完全没有字幕的电影是很压抑的。首先,字幕是眼睛休息的地方,是心灵得以喘息的点。一条字幕往往避免了长篇大论的视觉解释,这种视觉解释虽必要,但也有烦人或老套的缺点。而如果非要把自己局限于没有字幕的电影,那么多少原本美好的场景将变得无法实现。最后,我仍然认为,还有很多信息,用文字要比通过影像表达更审慎;如果你必须表明某个动作发生在晚上,也许简单地写出来,会比展示一个时针停在九点的钟面更好。
显然,在一部好电影中,字幕只是一种意外。但另一方面,将没有字幕作为一部电影的宣传要点,这不就像因为马拉美的诗没有标点符号而赞美它们吗?
在格里菲斯的巨作中,快速剪辑仍处于萌芽期。而将这一手法发展至完美的殊荣则归属于冈斯,他理应被认为是该方法的卓越发明者。《铁路的白蔷薇》(La Roue)仍然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电影丰碑,所有法国电影艺术都在它的阴影下存活和呼吸。各处的电影创作,都在试图摆脱它的控制和风格,但仍然很困难。如果说我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一会儿要说的内容决不能被理解为是对《铁路的白蔷薇》的批评。此外,它还包含着远比快速剪辑技术的发现更崇高、更纯粹、更有道德感的元素,这在我看来不过是影片中的一个意外。但如果在《铁路的白蔷薇》中,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意外,那么在许多其他的电影中,这个意外就会变得非常令人反感。如今,快速剪辑已被滥用,甚至在纪录片中也是如此,而每部剧情片都有一个甚至两三个场景是由多个小片段快速剪辑而成的。我向你们预言,1925 年将会有大量的电影涌入我们的视线,这些电影恰好符合 1923 年时,我们所怀有的电影理想中最肤浅的方面。1924 年已经开始,在一个月内,已经放映了四部使用极速剪辑的电影。已经太晚了,不再有趣了,反而有点可笑。如果我们的当代小说家还在用弗朗西斯·波埃特文的象征主义(Symbolist)风格来写作,像他一样,总是用“回忆”(resouvenance)取代“记忆”(souvenir),用“沮丧”(diséspérance)取代“绝望”(désespoir),岂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你非要说某部电影的布景很美,那我觉得最好什么都别说,这说明这部电影很糟糕。《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是电影中滥用布景的最好例子。《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代表了一种严重的电影痼疾:次要特征的过度增生,对“意外”的东西仍然给予极大的重视,而牺牲了本质。我不想主要谈论《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那“三十法郎的大路货”般粗劣的表现主义,而是想谈谈一部电影的原理,它绝不只是一组布景的照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中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布景:首先是场景的布置本身,其次是和布景一样被绘制和装饰的人物,最后是同样被绘制的灯光——一种电影中不可饶恕的亵渎——事先安排好的幻觉性阴影和幽光。因此,这部电影只不过是一幅静物画,所有生命的元素都被画笔的笔触抹杀了。与其他成百上千的元素一起,电影还从戏剧那里借来了布景。渐渐地,如果电影能独立生存,它就会偿还所欠的债,这笔债也会还。它不会让戏剧复兴,同样,画家的工作也不会成功让电影复兴。相反,画家的工作只会成功地阻碍电影趋向真诚而纯洁、同时具备戏剧性和诗意的正常发展。绘画是一回事,电影是另一回事。如果“戏剧艺术”在诞生之初就宣布,“文字创造了布景,也创造了其他的一切……”,然后现在诞生的“电影艺术”宣称,“姿势创造了布景,也创造了其他的一切”。在电影中,不应该也无法出现风格化的布景。在那寥寥数部几近可说是真正的电影的片段中,布景是解剖式的,在这个亲密的身体舞台上上演的戏剧是最为理想的。在特写中,可让你数清睫毛的眼睑,是每一个瞬间都被情感重塑的布景。眼皮下面出现的是目光,它成为戏剧的角色,它甚至超出了单纯的角色:它成为一个人。虹膜的圆圈以其无法察觉的动作,记录下了一个灵魂,还没有任何情感显微镜能够揭示其宗教般的秘密。在下巴的一绺胡须和眉毛的弧度之间,一整场悲剧得而复失,然后再得、再失。嘴唇仍贴在一起,微笑向银幕外震颤,在嘴唇构筑的舞台侧幕之间,是人的内心。当嘴巴终于张开时,欢乐便展翅飞翔。
如果说,我批评这三种尤其被现代电影误用的手法,这些在当下享有迟来的流行地位的手法,那是因为,这些手法是纯物质、纯机械的。电影的机械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电影必须被称为:对内心幻想的摄影。
我还记得我与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的初次见面。当时桑德拉尔在尼斯协助冈斯拍摄《铁路的白蔷薇》。我们聊起电影,桑德拉尔告诉我,“上镜头性是一个……很矫情,且有点傻的词;但它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渐渐地,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镜头性是个什么样的伟大奥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个人原因而拥有一些物品: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本书;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件非常平庸又有些丑陋的小饰品;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一件没有价值的家具。我们看不到它们的真实面目。说实话,我们无法将它们视为物体。我们从它们身上看到的,透过它们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些东西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倾注的、有时则是永远怀有的记忆和情感、计划或遗憾。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影的奥秘:像这样一个具有个人特质的物体;换言之,一个位于戏剧性动作之中、具有同样摄影特质的物体。当它以电影的方式被复制时,它的道德特质,它的人性与生命的表达会重新显现出来。
我想象一个银行家在家中等待来自证券交易所的坏消息。他正在等待一条空闲的电话线路。通话延迟。电话特写。如果电话的镜头表现得很清楚,呈现得很好,你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电话。你会解读出:毁灭、失败、痛苦、监狱、自杀。而在另一种氛围中,同一台电话会说:疾病、医生、帮助、死亡、孤独、悲伤。再换一种氛围,这台电话也会欢快地呼喊:快乐、爱、自由。这一切看似极为简单,它们可能被视为幼稚的符号。我承认,对我而言非常神秘的是,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为静态物体的简单反射注入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可以用自身的生命力将它激活。此外,我承认,在我看来,去关注这种电影心灵感应的现象,要比过分专注地培养两三种几乎纯机械性的方法重要得多。
《瑞士报》(La Suisse)的影评人让·舒先生曾为《忠实的心》(Cœur fidèle)写过一段话,我把这段话转述如下,但这段话并不只适用于这部电影。
特写镜头如何把人神化。哦,这些男人和女人的面孔,在银幕上显得如此严酷,像珐琅一样坚固,比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形象更具有强烈的雕塑感!看那一千颗不动的头颅,他们的凝视都瞄准了银幕上的一张巨大脸庞,目光被它垄断,为它魂牵梦绕,他们的视线都向着这张脸庞汇聚。多么令人痛苦的对话。一个偶像与诸众。就像印度的异教一样。但这里的偶像是活的,是个男人。这些特写镜头散发出非同寻常的能量。在它们之中,灵魂的分离就像人们分离出镭一样。它宣告了生活的恐怖,宣告其恐怖与神秘。这位可悲的玛丽,这位让,还有这位小保罗,它们除了呈现这位玛丽,这位让,还有这位小保罗,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吗?这不可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毫无疑问,确实还有别的东西。
电影是它的传令使者。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