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于话题
#格列柯#油画#艺术史#宗教
El Greco, Holy Family with Saint Anne
(c. 1590; oil on canvas, 127 x 106 cm; Toledo, Fundación Casa Ducal de Medinaceli, Hospital Tavera)
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圣家与圣安妮》与从斯福尔泽斯科城堡借出的科雷乔的《波洛尼尼圣母》之间的比较似乎不太合乎逻辑。但扎瓦塔和比吉-伊奥蒂(Zavatta and Bigi Iotti)在目录中写道,多梅尼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Doménikos Theotokópoulos 即格列柯)对科雷乔的艺术特别感兴趣。

Correggio, Madonna Bolognini (c. 1514-1519; oil on panel transported to canvas, 60 x 51 cm; Milan, Castello Sforzesco, Pinacoteca, inv. PIN 253)
这幅摹本的前提是能够直接看到科雷焦的原作,它还有助于令人信服地确定这位克里特画家在埃米利的旅居经历,迄今为止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许多评论家都提出了这一假设。科雷焦作品的摹本强化了埃尔-格列柯在帕尔马和雷焦艾米利亚之间旅居的观点,它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格列柯对科雷焦艺术着迷的观点,然而很难更进一步在他的画作中找到科雷焦式的元素,两幅作品之间的比较也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想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在这幅作品中,"埃尔-格列柯运用了一种深邃、细腻、亲密和温柔的语言,除了这幅场景如此亲密、如此充满爱意地表现母爱主题的作品代表了埃尔-格列柯创作的一个高峰。如果我们要从最早期的作品来看,这幅作品是在他离开意大利大约 15 年之后创作的、 这幅画距离他离开意大利的时间大约有 15 年之久,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的脑海中还能闪现出在帕尔马逗留的记忆,更何况科雷焦并不像丁托列托、提香、巴萨诺或维罗内塞那样是他创作的固定参照物。
El Greco, Spoliation of Christ (c. 1582; oil on canvas, 190 x 128.5 cm; Toledo, parish of Santa Leocadia and San Román, on deposit at the Santa Cruz Museum)
在希腊肖像画的主题之后最壮观的两个展厅,专门展出格列柯根据历史背景创作的宗教作品。托莱多是第一个执行遄达会议法令的城市,因此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比其他地方更早到达这座城市。这就是埃尔-格列柯富有远见、疯狂的神圣剧场,由戏剧性的、紧张的表演组成,目的是让信徒们最大程度地参与其中,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场景本身的一部分,这就是人们在观赏《耶稣受难图》时的感受,该画将观众投射到耶稣周围的人群中,使他们融入场景之中,耶稣神态庄严,全然不顾周围发生的一切,尽管压迫感占据了每一个空间,使人无法瞥见丝毫景观,只能看到远处闪烁的几片天空。人们几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被折磨者捆绑和拖拽着前进的基督面前,但又不会崩溃,尽管人物被拉长,尽管脸部被涂上了蜡色,尽管袍子上有金属褶皱,但这幅作品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然主义。

El Greco, Baptism of Christ (c. 1608 - 1621; oil on canvas, 330 x 211 cm; Toledo, Fundación Casa Ducal de Medinaceli, Hospital Tavera)而围绕着这幅画的其他作品却并非如此,首先是伟大的《基督洗礼》,这幅画于 1608 年左右开始创作,埃尔-格列柯未完成,后于 1621 年由其工作室的助手完成。埃尔-格列柯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完全人工化的世界,人物变成了无形的存在,天与地融为一体,物理定律不再受到尊重:我们在画布上看到的是纯粹的假象、纯粹的精神幻象、纯粹的狂喜。拜占庭圣像的庄严肃穆和恒星距离在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神圣剧场中得以延续:这或许就是格列柯艺术独创性的巅峰所在。
 El Greco, The Incarnation
El Greco, The Incarnation
(c. 1596-1600; oil on canvas, 114 x 67 cm; Madrid,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同样带有神秘顿悟色彩的还有从蒂森-博内米萨美术馆借来的《化身成圣》,这幅作品以一种压倒性的神秘幻想形式还原了这个神圣的主题,我们似乎被吸了进去,被云朵和基路伯的漩涡吞没,圣灵的鸽子俯冲而下,天使们胡乱嬉戏,空气和天空侵入空间。这样的视觉冲击力从何而来?
帕尔马-马丁内斯-布尔戈斯-加西亚(Palma Martínez-Burgos García)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埃尔-格列柯的艺术在反宗教改革和遄达大公会议后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背景下,被置于雄辩和虔诚的两极之中。埃尔-格列柯是西班牙领域第一位将情感公式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信仰服务的大师,他设计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物的姿态、模仿和姿势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它们是使格列柯的修辞有效的功能性因素。此外,埃尔-格列柯对他在威尼斯学到的知识进行了再加工,他对光影的处理令人惊叹,这种处理以最严谨的威尼斯和反瓦萨里亚传统为标志,他用不连贯的笔触涂抹色彩,增强了未完成的心理感觉,创造出强大的光影效果,强调并强化了宗教的意义。”

El Greco, Madonna and Child with Saints Martina and Agnes (1597-1599; oil on canvas, 193.5 x 103 cm; 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iedener Collection, inv. 1942.9.26)
El Greco,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c. 1603-1605; oil on canvas, 163 x 220 cm; Illescas, FUNCAVE - Fundación Hospital Ntra. Sra. de la Caridad)
展览继续进行,其中包括一些以玛利亚为主题的画作: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圣母与圣子玛蒂娜和艾格尼丝》(下面狮子头上多梅尼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名字缩写的细节令人好奇),以及精致的《圣伊丽莎白和圣约翰的圣家庭》(来自托莱多)。在这幅作品中,胡安-安东尼奥-加西亚-卡斯特罗写道:"埃尔-格列柯的绘画技巧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背景中暗示画布准备工作的云彩到最后的釉彩,经过对原始构思的修改--通过放射图像显示出来--以及美学技巧的使用,如浓密的浆状笔触或用有机黑色执行的轮廓,以赋予体积或创造一种分离感。这是一种受人追捧的效果,婴儿仿佛悬浮在母亲的膝上。”
 El Greco, Saint Sebastian (c. 1577; oil on canvas, 191 x 152 cm; Palencia, Cathedral)
El Greco, Saint Sebastian (c. 1577; oil on canvas, 191 x 152 cm; Palencia, Cathedral)

El Greco, Penitent Magdalene (c. 1585-1590; oil on canvas, 104.8 x 92.3 cm; Sitges, Museo del Cau Ferrat, Santiago Rusi?ol Collection, inv. 32.004)
El Greco, St. John the Evangelist and St. Francis of Assisi (c. 1600; oil on canvas, 110 x 86.5 cm; Florence, Uffizi Galleries, Gallery of Statues and Paintings, inv. 1890, no. 9493)隔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椭圆形圣母加冕图,最后是埃尔-格列柯的万神殿,从帕伦西亚大教堂不朽的《圣塞巴斯蒂安》(画家抵达西班牙后不久绘制,因此当时他脑海中仍有在罗马看到的古代雕像),到锡切斯《迷人的抹大拉》,再到乌菲齐的《圣约翰和圣弗朗西斯》。在倒数第二个房间里,则是埃尔-格列柯晚期成熟时期的圣人画作,在这一时期,画家恢复了他曾接受过的希腊圣像的等级性,呈现出正面姿势的圣人形象,庄严肃穆,没有额外的元素干扰与相对者的对话。人们在欣赏《使徒》系列或《奥洛特背十字架的基督》等作品时,会发现画家淡化了他的幻想天赋,转而创作更亲切、更有心理沉思、甚至可能更痛苦的图像,旨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动信徒的情感。

El Greco, Laocoon (c. 1610-1614; oil on canvas, 137.5 x 172.5 cm; 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Samuel H. Kress Collection, inv. 1946.18.1)
令人惊讶的结尾留给了《拉奥孔》:这是埃尔-格列柯绘制的唯一一幅神话题材的画作,也是画家在其职业生涯末期创作的作品。这幅画参考了1506 年发现的《拉奥孔》组画,埃尔-格列柯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这幅画,但画中的人物形象模棱两可,与神话相去甚远,难以解释,画面一如既往地以格列柯的家乡托莱多的风景为背景,在他的想象中,这座城市的形象反复出现。埃尔-格列柯的想象力让参观者目眩神迷,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在威尼斯和罗马之间学习绘画的艺术家,但他可能觉得对于一个以威尼斯人的风格作画并深深打上米开朗基罗艺术烙印的希腊人来说,在意大利工作太困难了。他的艺术生涯也许在西班牙度过得最好,但不是在菲利普二世的马德里,而是在文化气息浓厚但更加边缘化的托莱多,在那里他是孤独的,没有压力,没有与那些他也许觉得高不可攀的人相比的沉重感,没有束缚,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实验。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萌生出这样一位革命性的艺术家,正如 2015 年特雷维索展览所回顾的那样,这位艺术家在融合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天才,同时又不否认任何一种语言。因此,他的不拘一格并没有否定古典主义:他吸收它、重读它,甚至颠覆它,但从未否定它。在这里,我们钦佩这位如此现代的艺术家,他吸引了二十世纪如此多的伟大人物。看到埃尔-格列柯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塞尚或者毕加索。1911年,慕尼黑举办了匈牙利收藏家马尔泽尔-内梅斯(Marczell Nemes)的收藏展,其中有十几幅埃尔-格列柯的画作。一百年后,杜塞尔多夫举办了一次展览,在这次展览的基础上,探讨了 20 世纪早期艺术家与埃尔-格列柯的关系。康定斯基、马克、科科施卡,后来还有马克斯-恩斯特。二十世纪初,人们崇拜埃尔-格列柯,因为他有能力通过强大的情感力量来构建形式,崇拜他的反自然主义,他是一位将自己的构图建立在首先是内在的节奏和结构之上的艺术家。从本质上说,埃尔-格列柯开辟了一条道路,三百年后的人们将继续走这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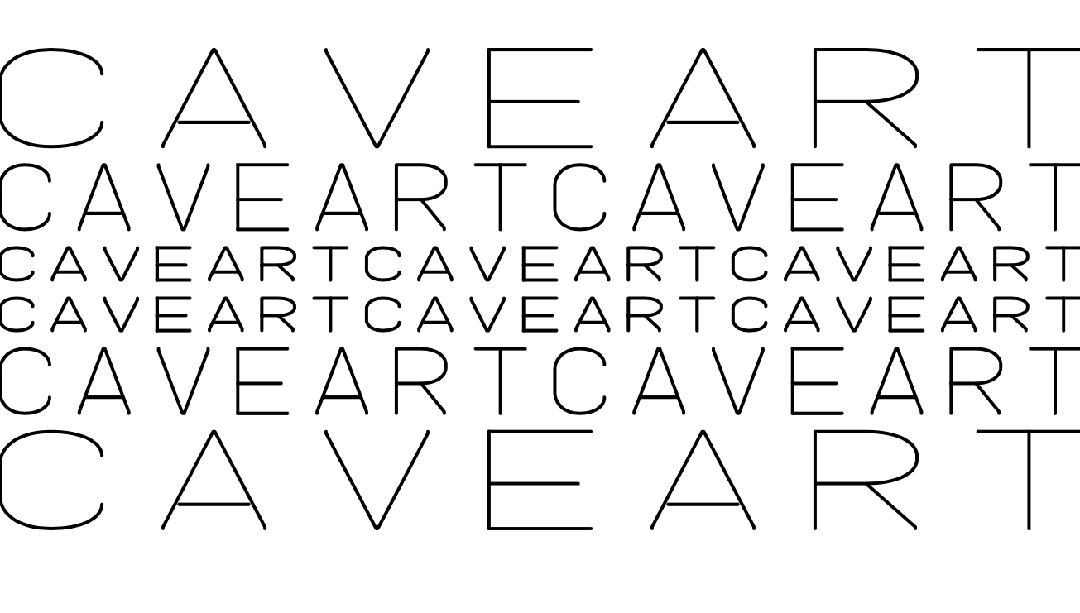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往期文章

岩洞CAVEART官方介绍 | Who we are?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的《阿波罗和达芙妮》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基督复活》

从起源到十七世纪艺术史上的眼镜

十七世纪艺术中的牙科





 El Greco, The Incarnation
El Greco, The Incarnation

 El Greco, Saint Sebastian (c. 1577; oil on canvas, 191 x 152 cm; Palencia, Cathedral)
El Greco, Saint Sebastian (c. 1577; oil on canvas, 191 x 152 cm; Palencia, Cathed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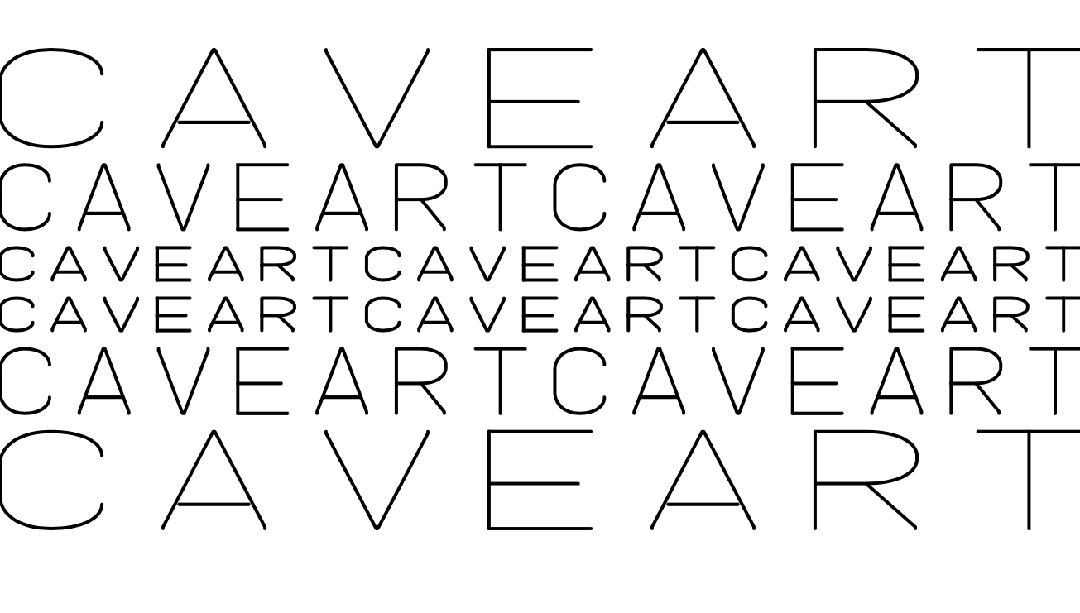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