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艺术史与艺术哲学集刊》第三辑
“世界3”:卡西尔与古德曼
孙宁
上期回顾
孙宁|“世界3”:卡西尔与古德曼(上)
二、世界的“样式”:古德曼的非实在论
古德曼在博士论文《性质的研究》(1941)(修订版以《表象的结构》为题于1951年出版,《性质的研究》直到1990年才出版)中实质性地推进了卡尔纳普在《构造》中提出的理论方案。和卡尔纳普一样,古德曼试图从基本对象和基本关系出发构造出世界中的诸对象,但他对卡尔纳普做出了两个关键修正。首先,卡尔纳普的主要构造方法是用类型论方法确定诸对象的层级序列,将一个层级上的对象定义为前一层级的逻辑类。而古德曼则认为,卡尔纳普的主要失误就在于使用了柏拉图式的逻辑类,因而没有如实展现出表象的真正结构。古德曼认为真正的构造方法不是建立在类型论之上的集合论(set theory),而是以“个体微积分”(calculus of individuals)为基础的整分论(mereology)。[1]集合论认为,虽然集合类的数量在原则上是无限的,但它们可以由相同的基本元素构成。而整分论则认为,相同的基本元素不能构成多于一个的实体,换言之,构成每个实体的基本元素都是独特的,它们不能在不同的构造进程中通用。古德曼试图阐明,真正的构造不应该探讨不同层级的逻辑类之间是如何“派生”(derivation)的,而应该探讨个体表象是如何“分延”(differentiation)的。这两种不同构造方法实际上导致了两种极为不同的构造体系。古德曼将卡尔纳普式的构造体系称为“殊相体系”(particularistic system),将自己的构造体系称为“现实体系”(realistic system),前者的基本单位是时空中的殊相,比如现象事件(phenomenal events),后者的基本单位是非具象的质性元素,比如感质(qualia)。 [2]古德曼指出,殊相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抽象问题”(the problem of abstraction),即从具体的殊相中抽象出可重复的普遍性质;现实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具象问题”(the problem of concretion),即从感质中建构出不可重复的具体殊相。[3]尽管古德曼认为这两条构造路径都是可行的,但他最终采用了以感质为基本单位的构造路径。这个选择有两个理论后果:其一,如古德曼所言,他的构造方案带有强烈的唯名论倾向,因为它的起点不是同质的属性,而是不可靠的甚至不可检验的感质;其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古德曼的构造方案是沿着和卡尔纳 普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因为感质是真正意义上的未经区分的原初整体。如果说卡尔纳普的构造是从基本元素开始的层级性构造,那么古德曼的构造则是从原初整体开始的逐步区分。因此,尽管卡尔纳普试图用“原初经验”取代感觉材料论者的“抽象所予”,但在古德曼看来,只要他没有用到从整体开始的“分延”方法, 就仍然处在和感觉材料论者相同的理论框架中。其次,虽然卡尔纳普在《构造》中选择现象论语汇(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 作为构造的出发点,但这个初始点的选择完全是理论实践中的约定。古德曼继承了这一点。他在《表象的结构》中指出,虽然该书的问题“在现象论的系统中得到处理”,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系统对物理主义的系统而言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因此,构造的基本单位“可以被理解为任何对象、主体、经验之流或系统中的其他实体。这些基本单位是中立的质料。比如,一个呈现可以是现象之流的一部分,也可以是物理对象的一部分,这取决于之后的系统构造”[4]。但与卡尔纳普不同的是,不同的构造系统在古德曼那里不仅仅是约定的语义学版本,而是各种可能对象构成的存在域本身。因此,古德曼的构造理论并不像卡尔纳普那样落脚于在约定主义视角下展开的逻辑句法研究,而是落脚于在可能世界视角下展开的多元实在论。尽管这两个落脚点都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但我们在讨论卡尔纳 普和古德曼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因素时要特别注意这个区分。在古德曼看来, 不同的构造语汇不仅体现了我们理解实在的各种“方式”(ways),还体现了实在本身的各种“样式”(versions)。他的这种多元实在论立场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标题中的“方式”是误导性的,因为在古德曼那里并不存在单纯心理性的“方式”,心灵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样式”。古德曼指出,“我们所谈论的是存在着多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对于一个唯一真实的世界我们可以有多种可能的选择”[5]。对传统意义上的实在论者或观念论者而言,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摇摆立场。古德曼自己也指出:“实在论者将会反对世界不存在这个结论;观念论者将会对所有相互抵触的样式都描述了不同的世界这个结论表示异议。对于我来说,这些观念既同样令人欣喜,也同样令人沮丧,因为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毕竟都是纯粹约定的。”[6]我们注意到,卡尔纳普也在《构造》中指出:“实在论、观念论和现象论这几种所谓认识论派别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一致的。构造理论表现出 了它们共同的中立的基础。它们只是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因而(如果它们可算是认识论派别的话)只是由于超越界限,才发生分歧的。”[7]但实际上,卡尔纳普在《构造》中悬置了本体论层面的探讨,而古德曼则试图用一种新的本体论来同时取代实在论和观念论的世界观。可以看到,就理论效应而言,古德曼对卡尔纳普的这两个修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果说卡尔纳普的构造方案以内容和形式的区分为前提(尽管他尝试通过基本关系来界定基本要素),那么古德曼的构造方案无论是在起点(作为原初整体的“感质”)还是在终点(世界的“样式”)都抛弃了这种区分。首先,就构造的起点而言,古德曼指出:“谈论未结构化的内容或一个未被概念化的所予之物或一个没有属性的实体都是一种自欺;……如果离开了形式,内容就会消失。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词或其他符号的世界。”[8]其次,就构造的终点而言,古德曼最终给出的方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纯形式化的构造,构造系统的逻辑句法同时也是被构造对象的内在结构。概而言之,我们无法在古德曼中明确区分“质料”和“方法”、“事实”和“理论”。正如古德曼所言,世界的构造只能“从一个样式开始,在另一个样式那里终结”[9]。古德曼最终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非实在论”(irrealism)。他在《论心灵及其他物质》(1984)中指出,自己既是“反实在论者”(anti-realist),又是“反观念论者”(anti-idealist),因而是一个“非实在论者”(irrealist)。[10]具体而言,非实在论“并不是认为每个事物甚至所有事物都是非实在的,而是认为世界消融为不同的样式,而正是这些样式构造了不同的世界”[11]。非实在论是一个极难澄清的立场,古德曼与普特南(Hilary Putnam)、舍夫勒(Israel Scheffler)和亨培尔(C. G. Hempel)就此展开了细致的辨析和争论。[12]比如,舍夫勒指出,古德曼一方面试图对世界做出“样式化解释”(versional interpretation),另一方面又试图对世界做出“客观化解释”(objectual interpretation),而这两种解释明显是对立的。因为前一种解释试图阐明世界是由我们构造的,而后一种解释则试图保留如下的可能性,即并不是每个事物甚至 所有事物都是非实在的。[13]较之于舍夫勒,普特南更倾向于对古德曼的非实在论做同情性理解。他一方面像古德曼一样拒绝承认一个预先存在的、不带“人面”(human face)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像古德曼那样承认世界就是由人构造的,他指出,“人的心灵并没有创造星星或山峦,但这个‘扁平的’(flat)说法并不足以解决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哲学问题”[14]。普特南认为,古德曼的立场有观念论的嫌疑,而他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则能够规避这种危险。他指出:“如果我们选择谈论世界,那么这些世界从何而来?古德曼的回答很明确:它们是我们制造的。……这样,一种像黑格尔或费希特那样极端的观念论形式就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完全成熟了。”[15]而古德曼对此的回应是:“普特南忘记了我的非实在论坚定地拒斥观念论和实在论。根据我的用法,‘实在论’回避所有观念论体系, ‘观念论’回避所有实在论体系,而‘非实在论’则不偏袒任何一方。”[16]我认为,理解非实在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古德曼意义上的“样式”。这里要特别指出四个要点。第一,如前所述,样式不仅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概念框架,还是世界本身的结构和肌理,有多少种样式就有多少个真实世界。古德曼指出:“我并不认为说不存在世界只存在样式就是观念论,因为我认为样式(不管是语言的还是图像的)不是心理性的,也不一般地指涉观念或理念,而是具有象征功能的对象。”[17]第二,样式的构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创造”(creation)。在古德曼的语境中,创造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ex nihilo),而是指“我们总是从一些在手的旧的样式或世界开始,我们一直这样坚持着它们,直到我们做出了新的决断,并获得了把它们重构成一个新的样式或世界的能力”[18]。第三,古德曼认为不同的世界样式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同于卡尔纳普或奎因的“一元论”(monism),即认为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样式原则上都可以被还原为同一个单一样式,古德曼认为不同的世界样式之间是无法对译的。他指出:“从一个体系向另一个体系的还原,确实有助于理解世界样式之间的关系;但严格合理意义上的还原却很少,它几乎总是不完整的,唯一的还原即使有,也极其罕见。”[19]第四,古德曼有时候会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受到严格限制的彻底相对主义”[20]。一方面,不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的“正确”样式,因为不存在一个脱离样式的世界供我们去对照符合;另一方面,世界的样式又必须是“契合实践”的,即必须考虑分类是否正确、归纳推理是否有效、举样是否合宜、样本是否自洽等。[21]古德曼认为,接受多元实在观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世界样式的批判性研究。他指出: “乐于接受所有的世界并没有构造出任何世界。仅仅承认许多可以利用的参照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天体运动图;仅仅承认不同的基础是适合的,并不能产生出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仅仅知晓各式各样的观看方式也不能绘制出图画。一个宽广的心灵并不能取代艰苦的工作。”[2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论心灵及其他物质》中指出:“我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我坚持认为必须对理论、解释和艺术品做出好坏的区分。”[23]古德曼的非实在论构想在他的艺术理论中得到了明确的示例。他指出,“现实主义”(realism)的标准是相对的,它“由特定时间下的特定文化或个人的表征系统标准所决定”,“如果表征取决于选择,而准确取决于信息,那么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习惯”。[24]如果我们对这个论断做极端的理解,那么原则上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现实主义。古德曼试图阐明,那些“纯粹抽象绘画”和“没有对象、不能字面地或隐喻地应用于任何事物甚至连那些最宽容的哲学家都不把它们视为任何世界的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虽然不能被“指谓”(denote),但可以被“例证”(exemplify)或“表达”(express)。[25]进一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艺术作品表征一个对象既不是“复制”它, 也不是“模仿”它,而是“实现”(achieve)它。[26]古德曼指出:“有效的表征和描述需要发明。……自然模仿艺术是一个过于胆小的断言。自然是艺术和话语的产物。”[27]我们应该在非实在论的语境中理解这些论断。它们想要阐明的是,心灵构造世界的形式就是世界本身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发明”(invention)也就意味着“发现”(discovery)。古德曼指出,“天真之眼(innocent eye)的神话和绝对所予(absolute given)的神话是邪恶的共犯”,而“接受(recep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运作,它们是完全相互依赖的。以一个康德式 的格言来说:天真之眼是盲的,纯洁的心灵是空的”。[28]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出艺术作品的“风格”(style)和“主题”(subject),我们只能说,“所言说的东西可以随着言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29]。三、心灵的构造与世界的肌理
如果我们将卡西尔和古德曼并置起来看,就会在两者的方案中看到一个明显的共性,即他们都开始对纯形式化的构造方案有所反思。卡西尔看到,每种象征形式的调性和诸象征形式之间的功能统一性无法在单纯的形式层面得到解决,我们需要通过在原因和形式之间展开的辩证法实现“世界与精神的综合”。而古德曼则试图阐明,完全停留在句法中的构造方案是无法成立的,我们在探讨心灵的构造时也在刻画世界的肌理,反过来,我们在勾勒世界的肌理时也在进行心灵的构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西尔和古德曼都试图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构造方案取代 康德式的构造方案,即从概念性(conceptual)的构造转向实体性(substantive) 的构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古德曼将构造理论从康德阶段推进到了黑格尔阶段。这个关于构造的黑格尔式洞见,用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话来说,就是拒斥在材料和框架之间做出二元区分的“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30]但是我们在探讨卡西尔和古德曼的共性时,除了看到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的理论效应,还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理论动因,即两者所处的象征主义语境。古德曼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提出了他和卡西尔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说存在着多个世界?真实的和虚构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它们是由什么构造的?它们是怎样被构造的?象征在世界的构造中起什么作用?构造世界和认识是如何发生联系的?”[31]这些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在象征活动中构造的世界是以何种存在模式存在的?促使卡西尔和古德曼提出黑格尔式方案的根本动因并不是观念论或分析哲学内部的理论推进,而是为了在象征主义的语境中解释围绕“世界3”展开的各种问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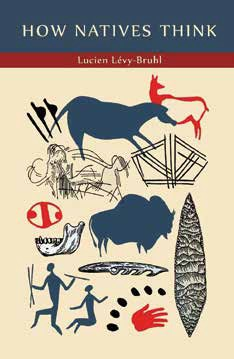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1926年版) 封面
因为卡西尔和古德曼采取的象征主义路径极大程度地拓展了康德所依据的精确科学框架,他们也就有了更丰富的理论资源来探讨构造的原因和形式问题。卡西尔在神化象征中看到心灵的构造与世界的肌理是如何统一的。在神化象征中,“我通过全能的意志把握所有事物,让它们服从我的目的;但正是这种尝试显示出我仍然完全被事物支配和主宰。所谓的做(doing)也意味着承受(undergoing)”。因此,在神话思维中只有一个未经区分的效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魔力(mana)被平等地归属于思维和人格、精神和物质、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32]。他还指出:“对神话而言,并不存在严格固定和分离的‘事物世界’,因为它尚缺少所有理论知识的第一目标:制造不变的联结。每个形式都可以转化为另一个形式,任何东西都可以来自任何东西。事物的形式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消失,因为这些形式并不是由固定的属性建构而来的。‘属性’和‘性质’是从经验性观察中得知的元素,它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反复出现的相同测定或关系。而神话却对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无所知,因为对它而言,世界可以在任何时候转换面孔,因为世界的面孔是由情感决定的。”[33]简言之,在神化象征中,“我”与“世界”的交缠是第一位的,而把“事物”从人类经验的整体中抽象出来,则需要经历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这让我们想到列维- 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对原始知觉的讨论。列维- 布留尔在《原始思维》(1922)中用“互渗”(participation)来界定原始的前逻辑思维。他指出:“与传统的万物有灵论相反,原始人的思维首先想象到的是神秘力量的连续、不间断的生命的本原,到处都有的灵性,而个体或者个人、灵魂、神灵则表现出只占次要地位。”[34]他还指出:“存在物的无处不在或者许多存在,一个与许多、一个与另一个、个体与种等等的同一——这一切会使服从于矛盾律的思维感到深 恶痛绝和陷入绝境的东西,确实是原逻辑思维所绝对能容忍的。此外,我们叫作经验的那种东西,亦即由观察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而得出的教训,对这种思维也是行不通的。它有自己的经验,这是彻头彻尾神秘的经验。”[35]古德曼在对艺术象征的讨论中得到了类似的洞见。他试图阐明,对艺术象征而言,区分外部对象的表征(representation)和内部情感的表达(expression)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象征中呈现的世界同时具有这两个面向。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了理解艺术象征,我们必须从二元的认知关系转向更为流动的审美关系, 从关注象征运作的认知效应(cognitive efficacy)转向关注象征运作的“审美征兆”(symptoms of the aesthetic)。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中指出,典型的认知效应包括“精细的区分,适当的暗指,把握、探索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分析、分类、排列和组织的方式,构造、操作、保留和改造知识的方式,对简单性和精妙性、力度和精确性、范围和选择性、熟悉度和新鲜度的考量”[36]。而审美征兆则包括句法密度(syntactic density)、语义密度(semantic density)、句法饱满性(syntactic repleteness)和例证(exemplification)。以句法饱满性为例,古德曼认为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的线条具有心电图所不具有的饱满性。[37]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他还试图阐明,从艺术象征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在分类和排列中确定世界,而是世界的“疯狂增殖”(mad proliferation)。[38]他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提出了构造世界的各种方式:组合(composition)和分解(decomposition)、加 权(weighting)或强调(emphasis)、排 序(ordering)、删减(deletion)和补充(supplementation)、变形(deformation)。在古德曼的 语境中,这些方式并不是构造世界的句法规则,而是世界本身的增殖形式。尽管卡西尔没有写出《象征形式哲学》的艺术卷,但他应该不会反对以下的论断,即 艺术象征和神化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源的。在艺术象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物交缠在一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心灵的构造就是世界的肌理。 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1831—1833年,木刻版画,25.7×37.9厘米
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1831—1833年,木刻版画,25.7×37.9厘米
卡西尔和古德曼从神话象征和艺术象征中得到的最终启示是:非人的世界(“世界1”)和属人的世界(“世界2”)是一个近代视域下的区分,“世界3”的本体论状态作为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框架下出现的。为了解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古代的世界,即一个非人的部分和属人的部分相互交缠的世界。对于不再天真的现代心灵而言,这个洞见是较难被领会的。卡西尔给出的提示是,在科学的象征形式下遇到的理解困难或许可以在另一种“调性”的象征形式(比如神话或艺术)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古德曼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是将“隐喻”引入构造语汇。在古德曼看来,隐喻的引入会给构造理论带来两个重要更新。首先,隐喻会打破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固态区分,由此在最大程度上打开构造的空间。他在《艺术的语言》中指出,“是否隐喻只是年轻的(juvenile)事实,事实不过是年老的(senile)隐喻?”[39]其次,隐喻通过在本域(native realm)和异域(foreign realm)之间有意制造赖尔意义上的“范畴谬误”,将已有的思维定式重新打散和再次激活,让我们在既有的构造之外看到新的可能性。古德曼指出:“隐喻性力量要求将新颖与适合、古怪与明显结合起来。好的隐喻既让人满足又使人惊讶。如果一个隐喻的转换产生了新的、显著的组织,而不是只是给旧的组织重新贴上标签,那么这个隐喻就是最有力的。”[40]当然,这些对隐喻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和空间。这些象征主义语境中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如果说古德曼对卡尔纳普的构造理 论有所推进,那么这种推进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是从构造的康德阶段推进到黑格尔 阶段,而是让我们看到,心灵与世界是在相互塑造的过程中不断展开的,一种好 的构造理论不仅应该关注已经成型的部分,更应该关注尚未成型的部分。更为重 要的是,卡西尔和古德曼的理论方案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探讨如何在“世界1”和“世界2”之间安置一个“世界3”,而应该将“世界3”作为理解“世界1”和“世界2”的基本前提和最终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世界3”不应该是被规定的对象,而是规定一切对象的基本场域。[1]最初的整分论构想由古德曼和莱纳德在研究生阶段提出。See Nelson Goodman and Henry Leonard, "The Calculus of Individuals and its Uses,"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5 (1940), 45-55.
[2]Nelson Goodman, 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6), 142.
[3] Ibid., 146.
[4]Goodman, 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 141-142.
[5]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2页。
[6]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123页。
[7]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
[8]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6—7页。
[9]同上书,第100—101页。
[10]Nelson Goodman, 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
[11]Goodman, 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29.
[12]See Peter McCormick, ed., Starmaking: Realism, Anti-Realism and Irre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13]Ibid., 133.
[14]Hilary Putnam,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
[15]McCormick, ed., Starmaking, 180.
[16]Ibid., 204.
[17]McCormick, ed., Starmaking.
[18]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100页。
[19]同上书,第5页。
[20]同上书,第2页。
[21]同上书,第143页。
[22]同上书,第22页。
[23]Goodman, 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i.
[24]Goodman, Languages of Art, 37-38.
[25]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109—110页。
[26]Goodman, Languages of Art, 9.
[27]Ibid., 33.
[28]Ibid., 8.
[29]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26页。
[30]戴维森将康德视为这一教条的典型代表。他指出:“我们从框架和实在的二分得到概念相对性,真是相对于框架而言的。抛弃了这个教条,这种相对性也随之消失。当然句子的真仍然是相对于语言而言,但这种真是客观的。我们并没有因为放弃了框架与世界的二分而放弃世界,而是无中介地触及了熟悉的对象,正是这些对象让我们的句子和信念为真或为假。”Donald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84), 198.[31]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1—2页。[32]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 2, 158-159.
[33]Cassirer,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 40.
[34]列维- 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1页。
[35]同上书,第493—494页。
[36]Goodman, Languages of Art, 258.
[37]Ibid., 252-253.
[38]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第21页。
[39]Goodman, Languages of Art, 68.
[40]Ibid., 79-80.
作者简介:孙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专长为古典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英美分析哲学和美国思想史研究。已出版专著3部(《匹兹堡学派研究: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古典实用主义的线索与视域》《分析视域中的康德与黑格尔》),译著8部(包括合译),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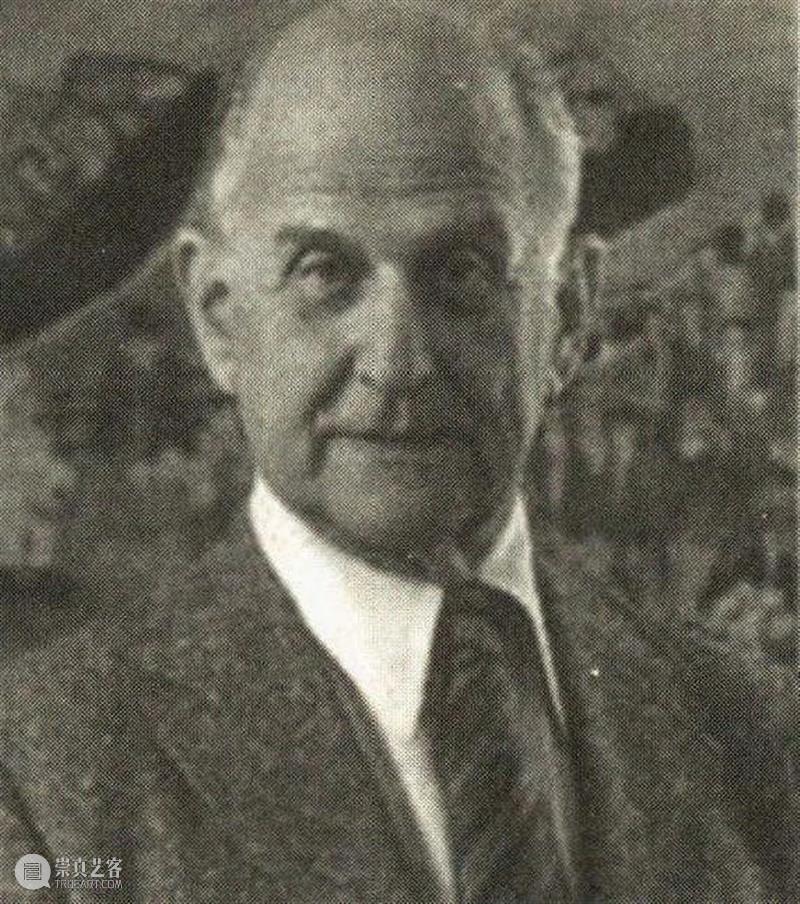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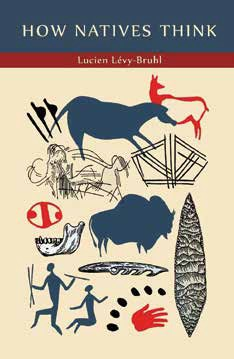
 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1831—1833年,木刻版画,25.7×37.9厘米
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1831—1833年,木刻版画,25.7×37.9厘米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