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录于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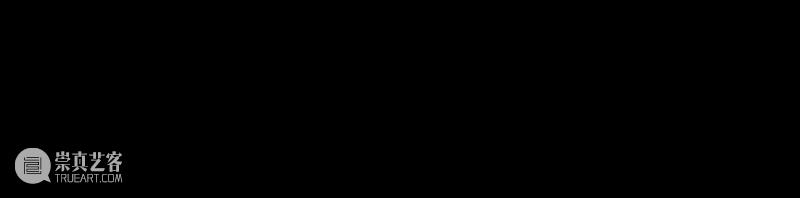

《尼奥·劳赫》(2019), 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Ltd 出版, ISBN: 978-I-84822-293-9

被允许进入艺术家的工作室是莫大的殊荣,也是一个不能轻易被提出或接受的请求。尼奥·劳赫(Neo Rauch)鲜少允许别?踏入他的创作洞穴、他的圣殿。他驻扎于这个位于莱比锡的老棉纺厂的空间已近二十五年。他也不太轻易谈论自己的作品,最多只是泛泛而谈。事实上,他不喜欢接受采访。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想要保护他的素材,也可以说是他的图像库。他不想把自己公之于众。他的绘画创作方法极其不寻常,有些?从写生模特开始,另一些则会在将颜料填涂到画布上之前准备大量的草图——特别是像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那种需要预先组织画面,以填充画面中空余部分的艺术家。倘若没有那些油画小稿,鲁本斯又会是什么样呢?
尼奥·劳赫的一些绘画几乎与鲁本斯的祭坛画一样大小,它们同样人物形象繁多,并且充满了骚动与复杂性。他的作品常常布满各种活动——正在形成的筑造结构;身处飞行或战斗中的人物形态;奇异的无定形区块,它们都处于如同自我生成般的半抽象的状态。所有这些都经过了精心安排,但并非事先部署而就,绝非如此。就像在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工作室里那样,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尼奥·劳赫会在创作之前提前做准备。工作室里也没有任何助手,所有绘画都由他只身一人构思创作,诞生于他灵巧的手腕。
他几乎不带预想或准备,直击空白的画布。一幅头脑中的图像、一份冒险的精神、也许还有一些涂画在废纸上的线条,这些便是全部的必需品了。画面上没有底稿,也没有严肃的草图。他并不知道究竟会从画面中浮现什么样的内容。只有在作画的过程中,他才会对即将出现的事物产生一些更清晰的认识。“画面不断地变得充盈丰富,直到某个时刻起,画作开始具备直接控制他的信心,而此时的劳赫则成了一个必须听命于画作本身的编舞者、剧场导演和管理者!”① 正如他曾对一位采访者所解释的那样,他意识到画作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便任其自由生长,直至现在画作掌控全局。“一幅画就像一个鲜活的有机体,它会紧抓自己的所需。从创作画的某个特定时刻开始,它就会控制我,通过我来描绘自己。”② 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中充满了各种角色(或者用他更喜欢的称呼,“生物”),它们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它们的创造者。画里画外,它们都是磨人的源泉。它们会在深夜和创作者搭话;令他夜不能寐;它们或可盛气凌人——尤其是在尚未找到最终形态的时候。
 尼奥·劳赫, 《血缘兄弟》, 2017, 布面油画, 300×250cm ? 尼奥·劳赫
尼奥·劳赫, 《血缘兄弟》, 2017, 布面油画, 300×250cm ? 尼奥·劳赫
画布本身即是某种能量场。它的脉冲点辐射出兴奋,指挥或引导着那只作画的顺从之手。劳赫认为绘画施加了魔法。它战胜世界的恐怖,它抵御——或者说是平衡了——善与恶的对立面,帮助世界本身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就好像艺术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庇护所或避风港那样。他曾说过,“如果你想并且能够把自己交给艺术,那它甚至可以让你与这个世界的暗面相互和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神秘——甚至有点魔幻?是不是有什么神明借由他在吐纳呼吸?“听起来似乎果真如此,但这本身又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尼奥·劳赫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无神论者,尽管他受泛神论影响的可能性更大。”③ 如此一来,一些不确定的、神明一般的冲动也许就会在某些地方发挥作用。或许,他同样认可这样的可能性。
正如劳赫所述那般,“他的绘画偶尔始于梦境,”④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许是在宣称自己与经典的超现实主义之间有着某种松散的亲缘关系。 而在许多作品中,你的确看得到德尔沃(Delvaux)、马格里特(Magritte)、布努埃尔(Bu?uel)、恩斯特(Ernst)、达利(Dalí)甚至德·基里科(De Chirico)的影子若隐若现——比如,他笔下的人物如何变得柔软、弯曲,甚至飘忽不定,让你会立即联想到达利。
例如,在他2010年的作品《骑士》中,桌腿和低音提琴都展现出异常可怖、令人不安的氛围。这些桌腿似乎在行走,而低音提琴的上半部分显然变形成了一棵树。在劳赫经常于画布之形式限制中构建起来的矛盾视角的方式里,可以看到有一半是来自德·基里科眩晕的、自我矛盾的视角——马格里特的双面人脸不时地潜伏在某处阴影,让人被其营造出的吊诡的空虚所萦绕——或者,那些充满激情、不合逻辑的冲动,那一幕幕情节支线里的冲突,都能在布努埃尔的电影《自由的幻影》(Phantom of Liberty)中找到蛛丝马迹。

简而言之,这些作品证明了他精神焕发地释放出非理性,但作为画家,他的创作实践还类似于一种对世界的放任,这些世界拥有各种从艺术史到历史、再到戏剧的全领域的明确参照。
比如,谁能否认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尼奥·劳赫浪漫而宏大作品中幽灵般的存在呢:在那种常被唤起的、徘徊于边缘的情绪中?或是乔托(Giotto)和丁托列托(Tintoretto)在他那些消散的、漂浮的?物形态中的存在?因而,这样的混杂是丰富而奇异的,所有的时代都融为一体。这些画事关众多时代,但又并不完全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它们具有一份古老的现代感——或者说是重新焕发出来的古老的新鲜感。它们是由奇特的层次构成的复写本。
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作室的日常世界里,其中放着木头文件柜、铝质的梯子、白墙、颜料斑驳的地面、一打又一打的书、转动的地球仪,还有,哦对了,墙上的时钟。时不时地,小哈巴狗斯米拉(Smylla)也会闯进来,满脸恳切地扒拉着食盆。总之,这里有人和狗所需的一切。
尼奥·劳赫本人,戴着巨大而笨拙的黑手套(一双笨拙的黑手套怎么能与正慢慢浮现而出的细腻的作品相匹配呢?),侧身站在画布旁,他左手攥着许多支粗细不一的画笔,同时右手涂抹着颜料。
他面容清瘦、壮实有力、谨慎专注、英俊潇洒,两鬓斑白,说话时轻声细语,从不仓促措辞,也从不做多余的表情动作。他不会提高嗓门,也不做手势。他并不是自己的表演者。当他说话时,他的脸几乎一动不动,仿佛他更像是自己的一个倾听者,而非诉说者。他说话精彩、细致、缓慢,他深思熟虑,但当这些话音落地之时,它们总是机敏地围绕起来,能被仔细地反思斟酌,甚至可谓一种场景设置——这有点让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回应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锲而不舍的提问方式。
你会感觉到,劳赫不希望他的画被面目全非地解释,以至于简化到只剩下躯壳。他也不太相信这种解释的重要性或相关性。他认为,画作的影响应该是立竿见影的,他希望不了解艺术或艺术史的观众也一样能轻松自如地欣赏作品——感受它们脉搏的跳动——就像他将整个艺术史图书馆的知识都运用到这些作品中?样。他并不希望或是邀请旁观者事先了解相关的知识。也许事实恰恰相反:带有一种全新的、近乎天真的、令?困惑的愉悦观看可能效果会更好。
出人意料的是,观看他作画的过程也不符合设想。他施加涂画颜料的形式并非完全是瓦格纳式的风格——尽管瓦格纳的《罗恩格林》(Lohengrin)是他的最爱。其中全无鼓点,也无任何华丽的装饰。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艺术家的罩衫工作服。相反,他身穿一件黑色T恤,搭配黑色的长裤。毕竟,他刚刚骑自行车到工作室不久——而现在,他刚刚扛着自己的空白画布艰难地走进工作室。
劳赫在创作作品的实际过程中相当认真,甚至是谦虚低调的,就好像他只是在一点一点地组装拼图,这幅拼图正是从他笔触的摩挲和急转之下浮现而出。而那些笔触本身——从快速且近乎疯狂的擦拭与填充,到一种繁琐讲究的细腻——往往看起来平凡,甚至时而犹豫不决,就好像他在重新教自己画画那样。
 尼奥·劳赫工作照 ? 尼奥·劳赫
尼奥·劳赫工作照 ? 尼奥·劳赫
这是否因为他总是在等待着什么事物的出现?他用画笔蘸着的颜料被放在颜料罐浅浅的塑料盖子里——也许没有什么会比一次性的塑料盖更实用,也更不受尊敬和被忽视的了。他拿着笔刷来来回回地创作,时而猛烈发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就好像他只是在用娴熟的速度、效率和专业的手法填补着空隙——就好像一个勤奋的工人正在专注于自己的日常工作那样。
诚然,他惯常的创作手法中具有一种日常性。创作是严肃的工作。有时,他会从绘画作品前的高台上爬下来,坐在管状钢质椅子上已经塌陷的黑色座位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多看几眼。暂停下来做总结,思考有关平衡、形式、色彩等相关的问题:画里的那个脚后跟,是不是需要更清晰地界定出来?
有时,他的妻子、画家罗萨·洛伊(Rosa Loy)也会站在画布旁提出自己的建议:那是头顶吗?还是个帽子?有时,他的老朋友、艾根画廊(EIGEN+ART)的格尔德·“朱迪”·莱布克(Gerd 'Judy' Lybke)也会加入讨论:某种特定颜色所具有的崭新强度如何?那会产生什么不同吗?任何有关作品的评价都不会受到限制。


① 摘自与冈瑟·奥伯伦泽的对话,《花园之后》,展览目录,埃塞尔美术馆,维也纳克洛斯特新堡,2011年,第215页
② 摘自与冈瑟·奥伯伦泽的对话,《花园之后》,展览目录,埃塞尔美术馆,维也纳克洛斯特新堡,2011年,第223页
③ 摘自《赫芬顿邮报》的采访,2016年8月12日
④ 摘自与迈克尔·格洛弗在莱比锡纺纱厂尼奥·劳赫工作室中的对话,2018年1月5日
⑤⑥ 尼古拉·格拉夫《尼奥·劳赫:同志们与同伴们》(电影),韦尔蒂诺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未完待续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