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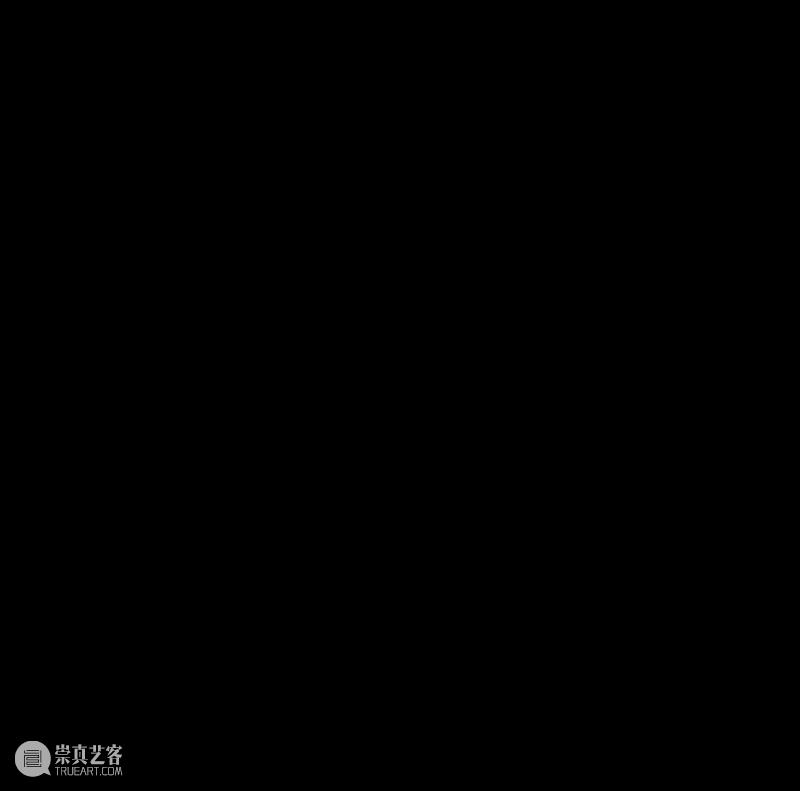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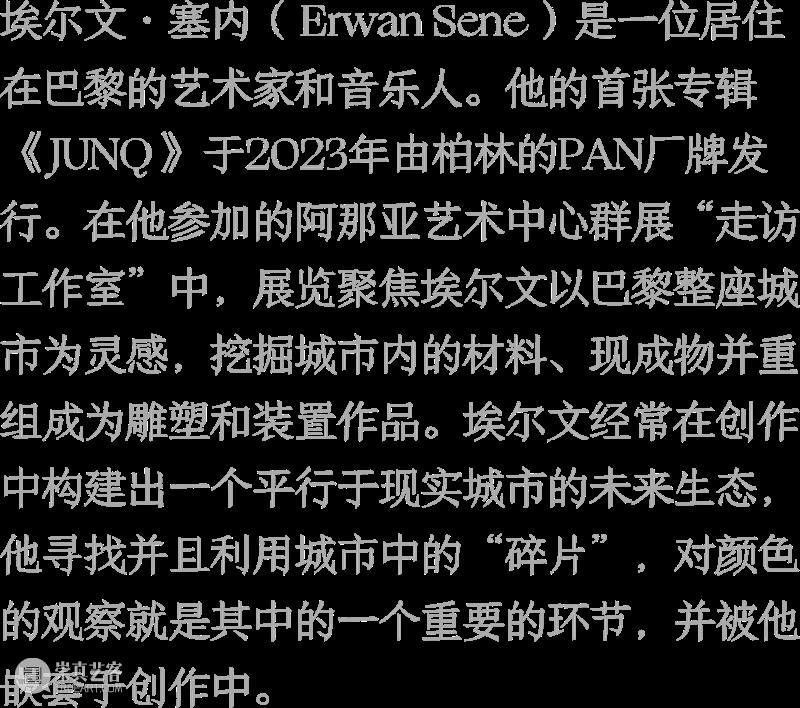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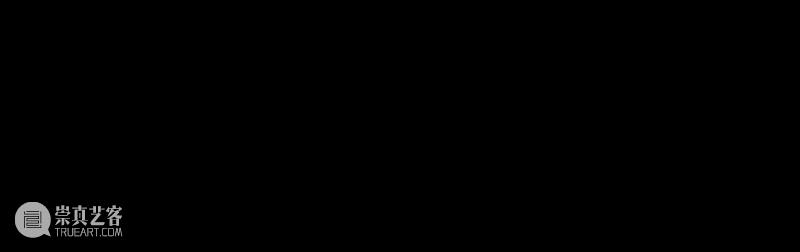
创作的时候,社会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我的兴趣,尤其是巴黎这座城市(我出生在这里,并且一直居住于此)试图维持(或不维持)的景观关系。Pigalle街区的霓虹灯在湿滑的柏油路面上反射发光——这个场景也因1981年的那部电影《雪》(Neige)而令人难忘——时至今日的塞纳河所呈现的略显淡淡的棕色。巴黎总是被不同的色域空间所统治,这些色彩几乎是从最工业到最近乎自然的跳跃与过渡。
多年间,巴黎的色调在不断变化。以前时常有发灰的污染,而如今为了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石头都被重新喷涂或更改成白色。在一块块崭新的奥斯曼风格的“白石头”之上,建筑师、房地产开发商、广告商和设计师们正在向公共空间中引入越来越多的色彩,通过色块的组合、建筑立面的包层、广告牌、街头家具和照明标志等形式,使得街道的颜色随着白天、夜晚和路灯光线的变化而改变。这是一座“光城”的新叙事所发生的地方,无论好坏。


向左滑动查看更多

公共空间中的物体,每一种颜色都标志着它与当下的关系,其象征也颇具社会学意味。
几百年来,色彩一直是魔法、宗教(比如巴黎圣母院的外立面曾是多色的)和政治权力的一部分,但今天,它被委托给了工业科学,并由后者来决定和设计我们城市的“色卡”。在巴黎,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如何长期规范建筑和街道色彩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的风潮吹响了色度理性主义,在数百种灰色调的笼罩下,构成了巴黎的氛围,并与建筑个体主义以及城市中标志物的扩散相互碰撞。
许多新建筑的诞生也被视为建筑师们所利用的一种识别手段,作为对抗通常被视作千篇一律的景观同质化的工具。

街头日益纷繁的色域规模(汽车、衣物、建筑等)与我们大脑对颜色的简单认知(天空是蓝色的、树是绿色的)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有时使我们难以完全视觉化城市的色彩景观。点缀着彩色斑点的灰色区域也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当你细细观察时,这些细微的差别里充满着色彩的层次、生活的结构和历史的痕迹,它们与颜色形成了独特的关系。
在城市中的闲逛让我能够定义对雕塑颜色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颜色并不总是与我使用的材料直接相关,而是作为意义和虚构的载体。
在朱丽叶·贝尓托(Juliette Berto)1981年执导的电影《雪》(Neige)中,我们发现穿过巴黎Pigalle红灯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昙花一现的建筑,以及各种或多或少非法活动的游乐场帐篷。脱衣舞俱乐部、赌场和巧克力甜甜圈对所有过路者触手可得,公共空间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游乐场。城市作为一个巨型游乐场的想法让我很感兴趣。网格状的街道和川流不息的人群创造了无限的邂逅、游离和体验新情绪的可能性。在装置作品(《六面粉红色工厂》)中,两个概念相互碰撞:机会和语言,两者都是为了体验城市(以我每日穿行而过的城市为灵感虚构)应际而生。小机库下方是一个粉色的矩形盒子,凸起部分则以投掷骰子为灵感。象征着随机性的偶发工厂控制着整个装置,通过驱动器中的电线与之相连(参考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感官游戏》中的游戏驱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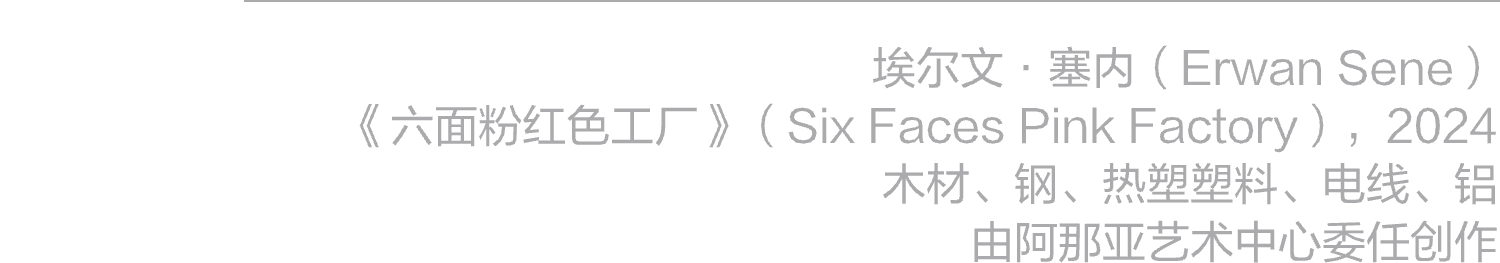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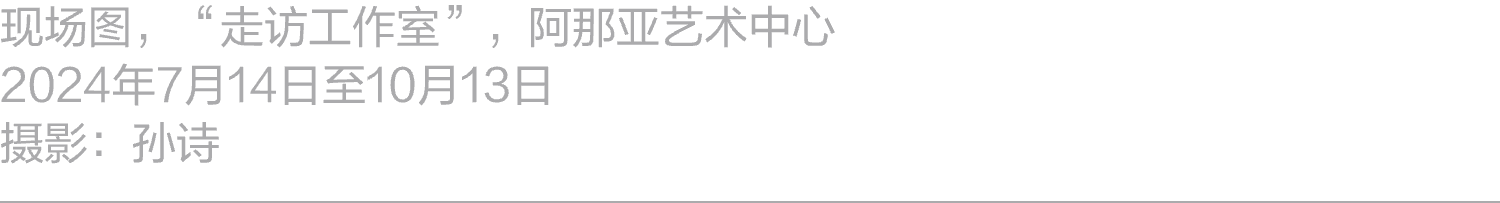
这次(在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展览)也展示了一个模型,它像一条狭长的走廊、一个堆积着垃圾桶和废物的地下游戏室的后巷。在这里,垃圾能够发出声音并互相交流。提到赌博时总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整座城市就像一台将一切都货币化的机器,每个人都想在这里碰碰运气,并被幻想所迷惑。当我们进入帐篷时,我们谈论的就是这台机器,它让人想起那些古老的旅游主题公园。大型的天线装置由回收的边缘物品制成,复原和改造后就像生锈的老旧自动机。它们诉说着地下语言、俚语和来自城市深处的摩斯密码。它们是否具有语言天赋,抑或只是在捕捉时空中消失的旧频率?在这里,一个临时的展览中,俚语等语言学实践和对运气的追求,为城市和世界增添了更多的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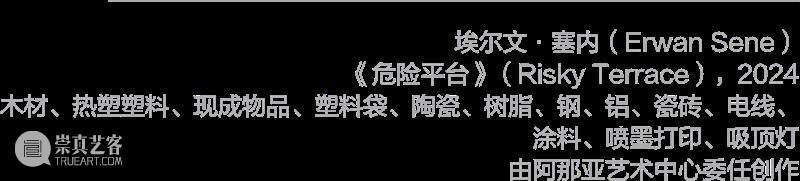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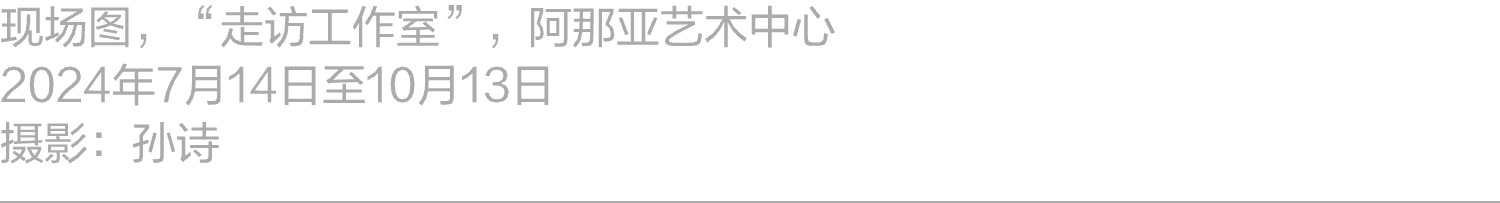
向左滑动查看更多
撰文:埃尔文·塞内(Erwan Sene)
翻译:高良娇
原文刊登于《V中文版》2024年8月刊“新五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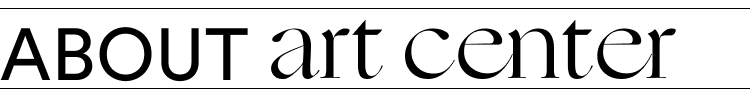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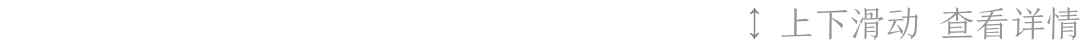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