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于《戏剧艺术》,2023年第1期 爱德华·马奈:《在花园温室里》 1879年,布面油画
爱德华·马奈:《在花园温室里》 1879年,布面油画
作为隐喻的剧场:
知觉主体与观演关系的嬗变
刘承臻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隐喻,剧场在不同的时代集合了知觉主体与观演关系的嬗变。在此,剧场指涉的是普遍的感知结构,而非狭义的戏剧/剧场艺术或其发生的场域,并导向总体的社会结构。参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剧场之隐喻所勾勒的知觉历史主要涉及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主体以去身体化的方式成为“再现”和幻觉的承担者;第二阶段为现代,伴随着知觉对象的物质化和对象化,主体恢复其主导权;第三阶段则指向数字虚拟化的时代,主体在其中蕴含着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解放的不同潜能。
关键词: 剧场 戏剧 再现 观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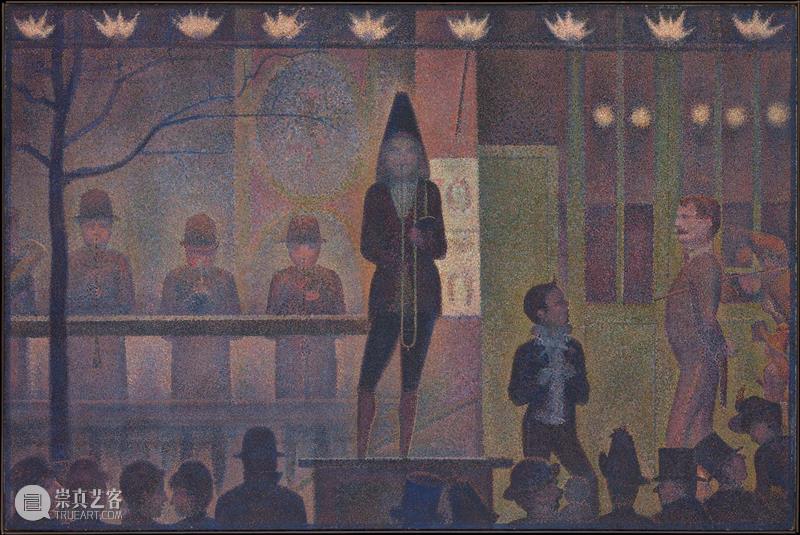
注释:
[1]高子文:《“戏剧”和“剧场”:概念考辨与文化探寻》,《戏剧艺术》,2021年第5期。
[2][美] 托马斯·波斯特威特、[加] 特蕾西·C.戴维斯:《“Theatricality”的历史维度和当代用法》,吴冠达、王慧敏译,《戏剧艺术》,2022年第2期。
[3]王志亮:《“翻转剧场”与“反场所的异托邦”——参与式艺术的两种空间特性》,《文艺研究》,2018年第10期。
[4][美] 克莱儿·毕莎普:《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林宏涛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2015年,第22页。
[5]张晓剑教授将其翻译为“观众”。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翻译习惯中,“audience”“spectator”“viewer”皆作“观众”,如此便会在特定语境中产生学理上的混淆。“beholder”在弗雷德的语境里有其特殊性,与“只有建立观者缺席或者不存在的虚构,才能确保他实际上置身画前并且沉迷其中”这一悖论相关。“外观者”的翻译强调了沉浸入画的观众本质上置身画外这一事实,本文将其囊括于“观者”这一统称和伞状概念之下。因此,为方便行文,弗雷德语境里的“外观者”后文皆用“观者”代替,只是在此强调其特殊性。
[6][美]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周宪译,《世界美术》,1992年第3期。
[7][美] 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张晓剑、沈语冰译,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8]Micheal Fried, Absorption and Theatricality:Painting and Beholder in the Age of Didero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7.
[9][美]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沈语冰、贺玉高译,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74页。
[10][美]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第198页。
[11][德]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北京:北京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作者简介:刘承臻,写作者、策展人、戏剧构作。生于山东,目前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ICAST)。他的写作可见于Artforum中文网、《戏剧》等各类平台与刊物,也从事当代剧场艺术的创作。现居杭州。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