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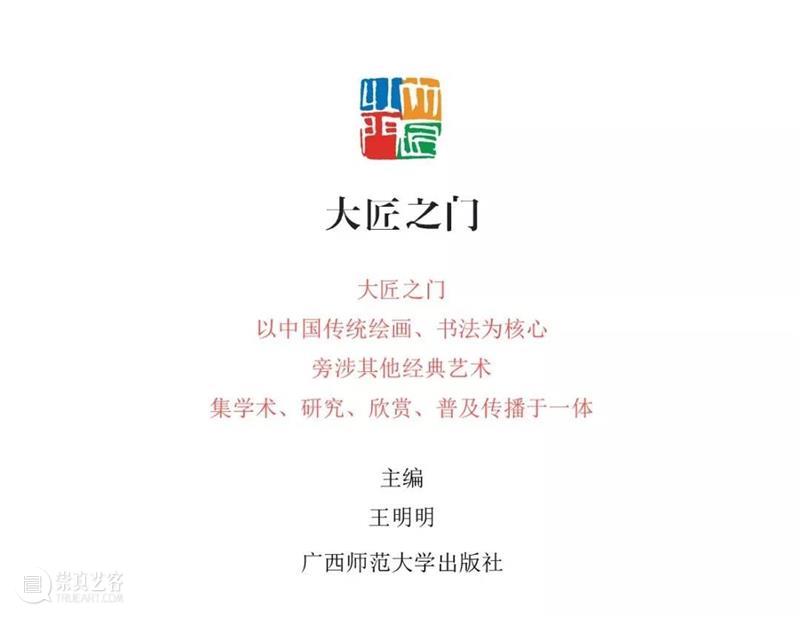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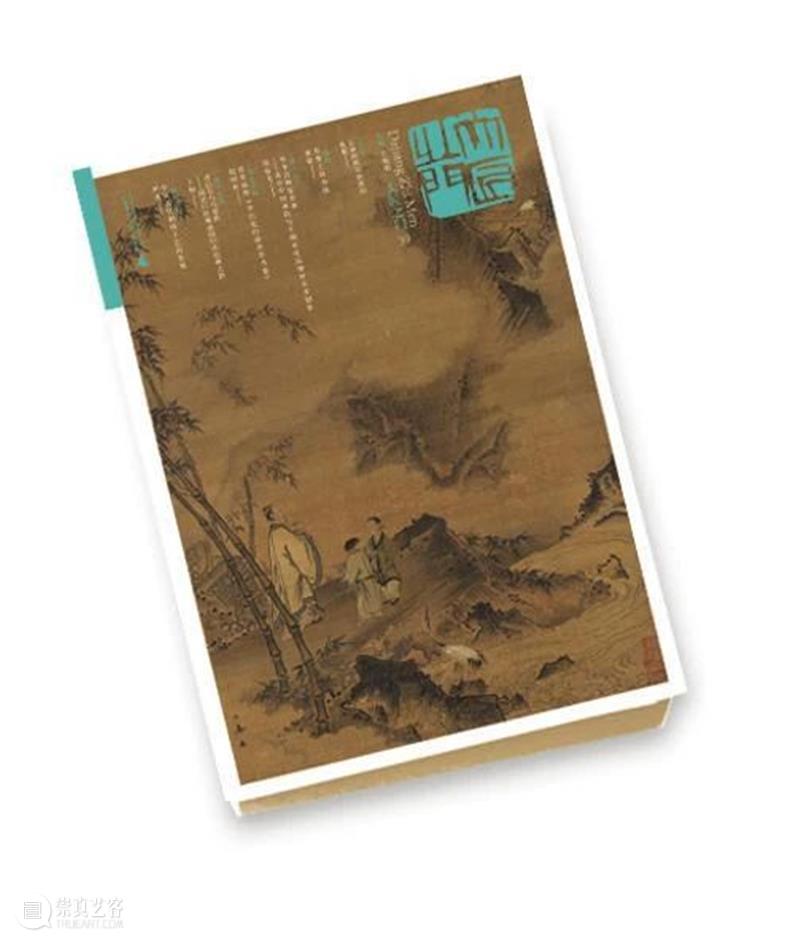
绣缋共职 黻黼韵生
——摭谈织绣与绘画的意蕴美
︱安夙︱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丝”的注解为:“蚕所吐也。从二糸。凡丝之属皆从丝。”通过考古可知,中国的纺织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殷商甲骨文中就不仅有桑、蚕、丝这样的记载,还有帛、绮等不同织造方式的文物出土。在纸张发明之前,丝织物作为绘画的绝好载体,与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彩)备谓之绣。”战国时期出土的帛画奠定了以线为造型的基础,历两汉至隋唐,宗教、花鸟、人物等题材的绘画大量涌现,五代、两宋间的山水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元、明、清追求水墨意境的文人画兴起,让绘画的形式、题材、风格和意境空前丰富。丝织物既可单纯作为绘画的载体,又可单独展示自身装饰性的纹样,同时在丝缕摹缂之间将绘画的色彩、线条、构图等刻画淋漓,直通画境。
《周礼·绘画注》曰:“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中国的织绣技艺历史悠久,以绘画为粉本的丝绣书画属于一个独特的门类。绣绘以丝为笔,以锦为地,着色晕染万物,其独有的肌理与柔美的质感,使作品呈现出细腻又深具变化的特点,故历来绣绘精品有“分翰墨之长,夺丹青之妙”的美誉。织绣技艺在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涵盖了织与绣等多种技法,下文中统称织绣或织绣绘画,旨在强调观赏性的丝绣作品,用以和传统绘画形成互文的关系。
在《尚书·益稷》中记有帝舜言:“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将织绣与绘画的关系上溯到了上古皋陶的时代。郑玄注:“会读为绘,谓画也。读为黹,黹 也,谓刺也。宗彝,虎 也,谓宗庙之郁鬯尊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龙也、华虫也,六者画以作绘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 以为绣施之于裳也。”《说文解字》云:“绘,会五采(彩)绣也。”清人段玉裁注:“会绘叠韵。今人分咎繇谟、绘绣为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统谓之设色之工而已。古者绘训画、绘训绣。”贾疏云:“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种种可见,古代绘与绣几乎同源同生,并具有相似的职能。
从《山海经》中所作嫘祖养蚕缫丝始,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记载的丝织品就有帛、缦、缟、纨、纱、绮、罗等;及至两汉,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蓬勃了织绣的发展,贾谊在《新书》中曾云:“匈奴之来者,家长以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并且出土的刺绣文物中多种绣法运用娴熟,纹样范式也日臻成熟。唐代的缂丝工艺始兴,但若论将绘画与丝绣结合而得大成者,当属宋代缂丝绘画。南宋缂丝涌现出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缂丝名家。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作:“宋时旧织者,白地或青地子,织诗词山水或古事人物、花木鸟兽,其配色如传彩,又谓之刻色,作此物甚难得。”织锦、刺绣、缂丝都属于织绣的范畴,三者之中直接受到绘画影响的当数缂丝。徽宗时期,画院的设立使得宫廷绘画尤为繁盛,缂丝书画也崭露头角,以院体画为粉本,由原本装饰性的纹样转变成一种纯供欣赏的艺术形式。清人姚际恒对南宋苏州缂丝名家沈子蕃的《榴花双鸟图》曾有“花叶浓淡,偐若渲染而成,树皮细皱,羽毛飞动,真奇制也”的评价。缂丝制作工艺繁缛复杂且造价甚高,从工艺实操上来看,与仅凭绢帛与绣线即可完成的刺绣工艺不同,缂丝必须依靠缂机等辅助才可完成,因其独有的特性历来受到皇权阶级的操控,故而并非女工专职,明人陆嘘云《世事通考》中有“只见刺绣而不见缂丝”之说。说的是元代蒙古族统一全国,织绣等技艺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停滞的状态。明人高濂曾曰:“元人之绣,便不及宋,以其用绒粗肥,落针不密,且人物禽鸟,用墨描画眉目,不若宋人以绒绣眉目,瞻跳生动,此宋元之别,以其眉目辨也。故宋绣山水,亦不多得,元人花鸟,尚可一二见耳。”明代以降,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宫廷恢复了画院制度,承袭南宋以来的院体画风,浙派、吴门、松江等众多画派繁兴,民间的绘画及版画兴起,均促成了织绣工艺的发展。禁内设立“绣作”,广招天下织绣妙手,南方以顾绣、苏绣,北方以鲁绣、京绣为代表,大量制作具有观赏性的织绣书画。清三代中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如同绘画的繁荣一样,织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皇宫造办处设有“织绣作”,集中了顾绣、苏绣、京绣、鲁绣、蜀绣、湘绣、粤绣等不同体系的织绣,以最精良的技艺织绣了大量形式多样、题材和技法丰富的传世作品。
南齐谢赫在《古画品论》中提出过“六法”理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虽然讲的是品鉴绘画,但是从实践来看,古代有“绘衣绣裳”之说,可知画与绣自古是等级的体现,是将五色绘于一处的艺术。另,绘画是笔与绢素的结合,而刺绣是针黹与丝线在绢素上的表现,二者有着天然共通之处。此外,画与绣皆是以二维的状物形式表现,同样遵循着“骨法用笔(线)”“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等规律,以求达到气韵生动的意境。清代《上海方志》中载:“苏绣之巧,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其法擘丝为之,针细如毫发。”又有清人评价顾绣为:“故世备称顾绣之巧,谓为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名之曰画绣。”画中之境,以绣摹之;绣工之妙,巧夺绘事;丹青之韵,绣之前导。在传统绘画风行的时代背景下,刺绣凭借着自身高超的技艺从一众工艺美术形式中异军突起,日益精进,形成了一种新潮流。

(宋) 梅竹鹦鹉图册 (局部)
刺绣 纵27.3厘米 横27.7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花鸟扶疏
明人高濂在其所著《遵生八笺》中有言:“宋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多精妙,设色开染,较画更佳。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备,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极言宋绣之妙。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花鸟题材一直是画师、工匠欣赏和表现的题材之一。宋画与宋绣中的花鸟作品,更有着精妙绝伦的表现力。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宋绣《梅竹鹦鹉图册》就是以宋代小品花鸟画为粉本刺绣而成。作品整体呈现标准的“对角线”式的构图,梅枝、竹叶、鹦鹉疏密有致地分布在左下角。作品主体的鹦鹉绣绘得极为精妙,采用长短针、套针等针法,以劈丝退晕等技法将鹦鹉翎毛的炫彩、尾羽的质感等表现得栩栩如生;再配合枝叶、花瓣等熟稔的表现技法,将画面的层次、色彩、质感、氛围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花鸟画《桃花山鸟图》的比对中,就展现出的视觉效果而言,两者往往难分伯仲。《梅竹鹦鹉图册》上有多方鉴赏收藏印,在收入清宫禁藏之前,曾有明人姜绍书,清人安岐、张镠等藏家收藏。此现象在传世的织绣作品中也为常见,宋代的刺绣对于文化史的贡献就在于,完全脱离了日常使用的功能,转变成专供欣赏的新艺术品类,并与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宋代刺绣同时在织绣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还属宋代缂丝,并且宋绣与宋缂是与绘画渊源最为深厚的两种技艺。清初收藏家安仪周在《墨缘汇观·名画》中评价朱克柔的缂丝作品:“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从创作宗旨来看,绘画是目的,织绣技艺是途径,但就其本身而言,宋缂展示出了笔墨情趣和惟妙惟肖的意蕴,同时依托其精湛的工艺令世人折服。元代赵孟 对宋缂的评价有“具足夺天孙之巧,极机杼之工”“镂织之精,无毫发遗憾”等。与宋缂追求精致的画面效果不同,明代的缂丝更强调一种线面结构的装饰性。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两件明代《缂丝五伦图》与《缂丝凤穿牡丹》都展现了此种图式的新风尚。作品以近乎平涂式的色彩块面来表现,色彩的晕染采用木梳戗和凤尾戗等缂法,装饰效果极强。明代以降,刺绣在表现绘画的质感和层次方面逐渐展现出更大的优势。清中晚期的顾绣承袭自我风格,并与绘画结合日益紧密,如露香园(朱文印)的《安居乐业图》就采用了大面积的绣绘结合的方式,与阚岚所画《玉堂富贵图》相较,在山石的处理上有着相似的创作思路,淡笔勾勒轮廓,石青多层罩染,体现了山石的质感与立体感,又不过于浓艳,晚清花鸟图式的审美倾向与表达由此可见一斑。

(清) 阚岚 玉堂富贵图
纸本设色 纵203厘米 横103厘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寄情山水
朱启钤在谈及宋绣《瑶台跨鹤图》时描述道:“界画楼台,以金夹线绣,人物寸许,眉目毕瞻,跨鹤凌空,仙袂飚举,俯瞰下方,云山竹树,气象万千,点染悉本六法,虽纤细之笔,丝毫不爽,女红之妙,神乎技矣!”劈丝、捻金、片金、双股线等精工绣法灵活运用,将仙山楼阁的金碧辉煌和仙人衣袂飘举的意境感拉满,并以白粉描染局部,在刺绣之中加入绘画。再与南宋《仙山楼阁图》相较,可以看到,两者虽门类不同,但就其表现效果和其中的意蕴而言,相同相合,气韵生动。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苏松地区巨贾云集,“汲古”“时玩”之风盛行,王绮在《寓圃杂记》中载:“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缂)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明代在绘画上不仅继宋代之后重设画院,浙派、吴门、松江等画派各领风骚,绘画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观赏性的丝绣绘画的发展。
明代以降,刺绣作品中加绘笔更为普遍,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此时的绣绘结合是商品化的简省之为,即将细微刻画之处和晕染的部分以绘代绣,但正是如此,绘画与丝绣技艺才巧妙融合,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另外,明代代表露香园“顾绣”也同样以绘绣结合的方式以期达到更完美的观赏效果。明清文人画兴起,一些职业画家和落魄士夫鬻画而生,与此同时,丝绣制品的商业属性也日趋增强。丝绣派别多样,题材日益丰富。织绣与书画既是两种拥有独特审美特色的艺术品类,又同是能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美学观念的载体,同样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色彩、线条与构图的运用,力求达到意境深远、意蕴丰富的效果。
古人云:“艺痴者技必良。”织绣与绘画两种艺术形式互为表里,丝绣以针代笔,绘画以笔传神。明代张应文所著《清秘藏》中云:“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具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 唼之态……”顾绣《米画山水图》,便是一件结合宋元绘画意匠与明代刺绣技艺的良作。绣法虽然简单,仅为套针和平针,却将米家的点染积墨所表现南宗山水的烟云迷蒙、恬淡空灵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配有诗云:“南宫颠笔,夜来神针。丝墨合影,山远云深。泊然幽赏,谁如其林。徘徊延伫,闻有啸音。”绣、画、诗熔于一炉,得妙境三昧。

(宋) 仙山楼阁图
刺绣 直径2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虔诚礼佛
传世的明清织锦刺绣题材的作品中有一类是宗教题材。明末战乱,大篇幅的织锦作品并不多见,清初康熙朝开始,由于国力日益鼎盛,织造巨幅织锦的工艺得以恢复,至乾隆朝达到顶峰,之后日渐式微。其中以清宫画师的画稿为粉本制成的织锦等堪称上品。较为著名的是以丁观鹏《极乐世界图》为底本创作的三幅织绣作品,《织锦极乐世界图》和《刺绣极乐世界图》“一稿三做”。丁观鹏的绘画以“西方三圣”为题材,画面正中是阿弥陀佛双手结禅定印,双脚结跏趺坐,左右分别为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主尊顶上有二重华盖,上饰垂缦和宝珠。上方左右有宝树、妙华宫殿、虚空宝阁、尊胜宝幢、多层佛塔和十道佛光,主尊周匝围绕着众菩萨、罗汉、天女、力士、伎乐等,均盛装华服,天衣曳地,璎珞玉佩,珠铛金翠,其手中各捧灯、花、果、涂、乐以为供养。下方为九品莲池,辅以宝珠、莲花、瑞鸟等。画面中心空白处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朱文)、“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八徵耄念之宝”(朱文)三枚乾隆皇帝的玺印。采用了工笔重彩的绘画方式,宏大叙事的手法,描绘西方极乐净土的佛国圣相,主尊及胁侍菩萨的开脸颇有明代波臣派的写实风格,并不仅以线绘;周围众仙等多以线为主体,画面结构严谨,敷色鲜艳,将《阿弥陀经》等净土变中所描述的极乐世界胜景,巨细靡遗地呈现给观者。《刺绣极乐世界图》为素绸地绣制而成,在遵循原粉本构图用色的基础上,采用了套针、缉针、盘金、打籽、戗针、和色线、施毛针等多种绣法,针法灵活,绣工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远视可追摹丁氏原作,近观可见局部的立体效果,以及丝织物特有的灿烂光华,独有情致。另一幅《石青地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以彩色纬线用控梭、长跑梭等工艺织成的重锦。此图为石青地显花重锦,织工细腻,人物形象多变,场面宏大。虽然与丁观鹏粉本的配色有别,但独有的装饰效果更为强烈。此三幅均著录于《秘殿珠林》中,可见当时亦是禁中珍品。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镇馆之宝《重锦无量寿尊佛(乾隆礼佛图)》相传也是据丁观鹏粉本所织,长695厘米,宽345厘米,幅面阔大,气势恢宏,施用色彩多至百种。此幅重锦创作时间亦是乾隆年间,画面主体为三世佛,正中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左右分别为阿閦佛和弥勒佛,周围有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个身着红袍头戴斗笠的“罗汉”,据考是为乾隆皇帝“cosplay(角色扮演)”的;上方可见金乌玉兔、天宫伎乐,下方有五色祥云拥簇。关于乾隆御容出镜在画中抑或在织绣中,此作并非孤例。丁观鹏的《弘历洗象图》和郎世宁的《弘历观画图》几乎都是丁观鹏和郎世宁两大宫廷画师通力合作的成果。与明代丁云鹏的《洗象图》不同,丁观鹏的《洗象图》不仅布局更为紧凑,坡石花草的笔触更有西洋味,而且将尊者(菩萨)的面容换成了乾隆御容。根据此画裱褙所题“嘉庆六年四月十九日静宜园来青轩北间墙上换下御容画一张”可知,御容画是有据可依的。比较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重锦中的乾隆面容与丁观鹏、郎世宁所绘乾隆之御容可知,所织、绘者皆是乾隆。
根据《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探源 — 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文可知,1947年社会学系吴泽霖教授委托京城振德兴行的掌柜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两幅,如今清华只存其一,另一幅在1949年后被调拨至当时处于筹建中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如此巨幅的重锦,存世量稀缺,是难得的时代样本,亦可从中比对画本与绣本各自的精妙之处,以及体会通过不同载体和工艺达到的妙趣。

(清) 丁观鹏 乾隆皇帝洗象图
纸本设色 纵132.3厘米 横6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博古清供
“博古”顾名思义,有博古通今、崇尚儒雅之寓意,古时用于达宦人家的宅第装饰,明代以降的汲古之风促生了人们对古物文玩的赏鉴之风。杜堇所绘的《玩古图》中就有一人闲坐于圈椅之上,侧身俯视案上的琳琅古物。上有题款:“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日无礼乐,人反块(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柽居杜堇,柬冕征玩古图并题。予则似求形外,意托言表,观者鉴之。”明人姚廷遴的《历年记》中曾云:“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可见“时玩”之风。而清供之意,原可解释为清雅之贡,如松、竹、梅、花果、清香等,亦指赏玩之供器。若按节庆来分有岁朝清供、端午清供、中秋清供,还有按礼俗区分的祝寿清供、婚嫁清供等。清供题材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发展,尤以清中后期发展至鼎盛。此种博古清供的题材也同样影响了绘画与织绣。
清晚期的博古清供图式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其追求吉祥寓意的属性,纵观绘画史自“扬州八怪”之后,文人画大行其道,被打开了“任督二脉”的艺术家们纷纷在追求笔墨性格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绘画的表现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不再囿于某一种艺术表达方式。织绣书画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所限,其相应变化在对比之下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米色地绣花卉博古图四条屏》在米色绫地上采用平针、滚针、套针、铺绒等绣法绣博古纹样,有鎏金凤首鸟笼、青铜器、花觚、投壶、香炉、吸杯、鼻烟壶、茶具、印盒、香橼及各类瓶花等。
这类清供题材的兴起,离不开明清之际推崇的王阳明所倡导的“格物致知”的主张,品藻格物以求知行合一。清供题材的绘画则高度体现了这一文化思潮的盛行。明代的“汲古之风”,催生了以品物为主题的雅集,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载:“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又有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时玩》中对时下品物之风盛行的描写:“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宫、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清代的清供图式承袭了明代的风格,同时又带着其独有的装饰趣味,常有“十全瓶花”配以香鼎、古瓷、宝剑、画轴、奇石等,反映出人们富足与风雅的追求。
汪曾祺曾说:“‘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于这几样:天竹果、蜡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橼’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蜡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清供为雅事,绘与绣仅为方式不同,但表达的意蕴并无二致,明代以降至清末,清供的绘画作品都是清雅与吉庆的象征。
中国传统织绣与绘画既是两个独立的门类,又是借由不同载体呈现的艺术形式,它们具有的审美特色共同体现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学观念。这种艺术形式强调形神兼备,注重画面的气韵生动和情感表达。在织绣书画艺术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密不可分,画面的主题和情感都要通过形式来表达。此外,中国传统织绣书画艺术注重色彩、线条和构图的运用,力求达到意境深远、意蕴丰富的效果。这两种艺术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属性,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传统织绣与绘画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技艺角度看,它们体现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艺术才华,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卓越成就;从审美角度看,织绣与绘画凝聚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理念和审美特点;从文化角度看,它们又传承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绣绘共职,衣画而裳绣”,绣因绘而成长,绘因绣而多样,以针梭代笔,十指春风之态,于绢素之中凝结巧思与技艺,将“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熔于一炉,同时绘画的意蕴也得到了新维度的延伸,将气韵之美诠释出新的内容。

(明) 杜堇 玩古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126.1厘米 横18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员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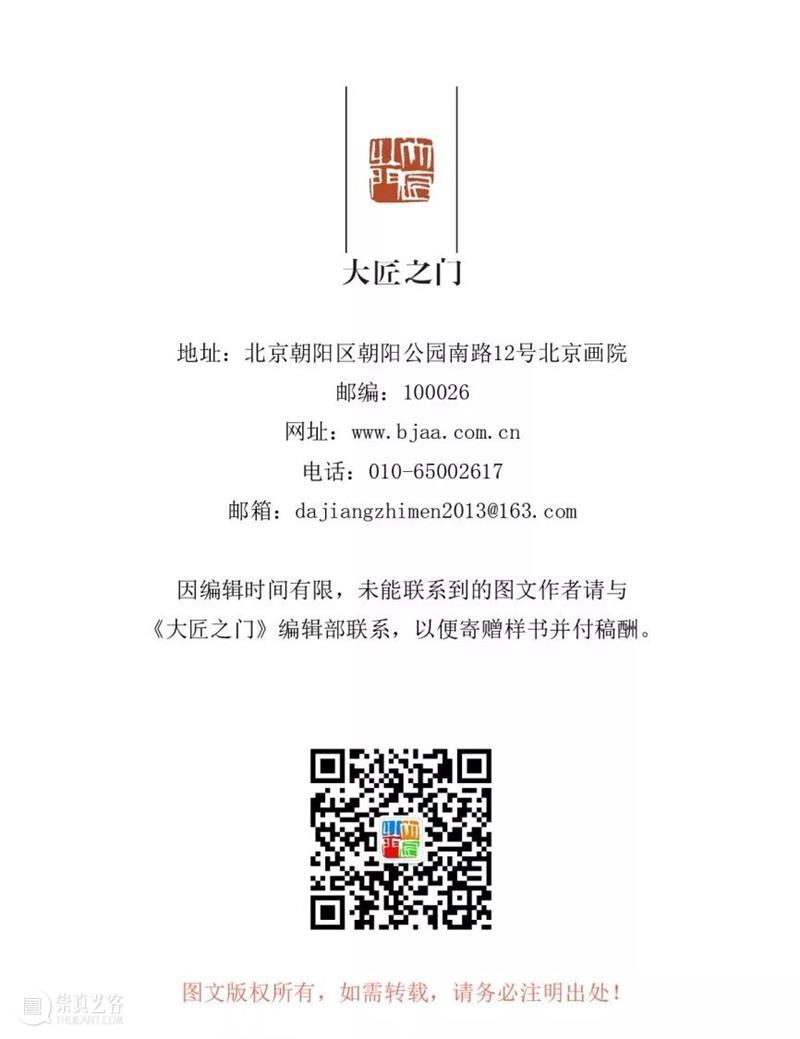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