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dex}}/{{bigImglist.length}}
转自公众号:artnet资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TkwMjYyNw==&mid=2247599434&idx=1&sn=5763c50f90dfc3a74f448dff9f7b7375
 岩村远肖像,2024年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肖像,2024年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肖像,2024年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肖像,2024年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绿色男孩》,2024年,陶瓷,92 x 83 x 60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绿色男孩》,2024年,陶瓷,92 x 83 x 60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绿色男孩》(细节),2024年,陶瓷,92 x 83 x 60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绿色男孩》(细节),2024年,陶瓷,92 x 83 x 60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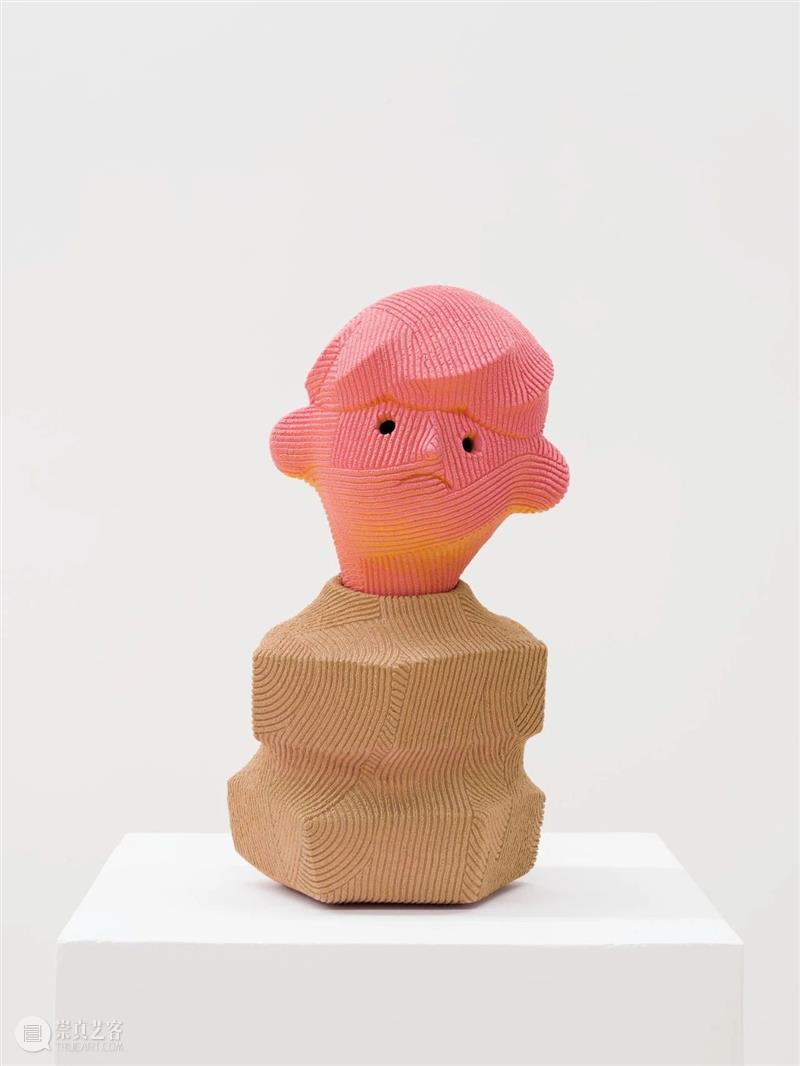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层叠毗邻》,2024年,陶瓷,40 x 20 x 19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层叠毗邻》,2024年,陶瓷,40 x 20 x 19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层叠毗邻》(细节),2024年,陶瓷,40 x 20 x 19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文时代:层叠毗邻》(细节),2024年,陶瓷,40 x 20 x 19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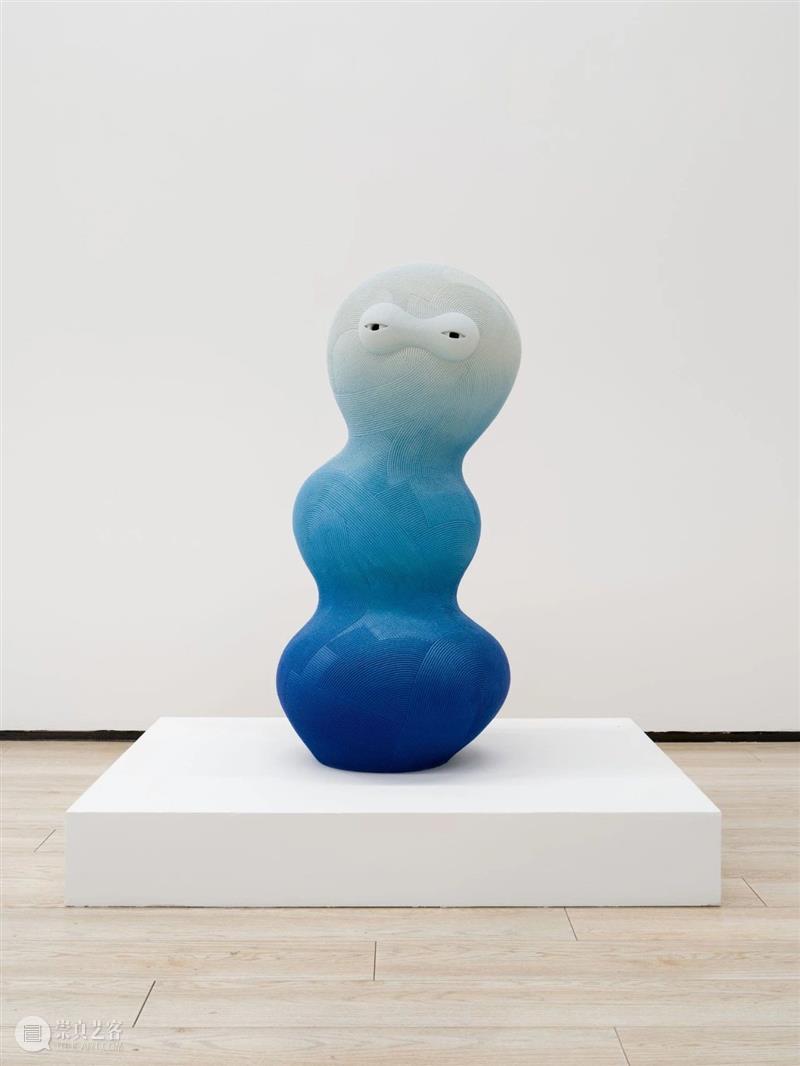 岩村远,《新绳纹时代:蓝色幽灵》,2024年,陶瓷,100 x 45 x 45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纹时代:蓝色幽灵》,2024年,陶瓷,100 x 45 x 45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纹时代:蓝色幽灵》(细节),2024年,陶瓷,100 x 45 x 45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新绳纹时代:蓝色幽灵》(细节),2024年,陶瓷,100 x 45 x 45 厘米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
岩村远,《回眸余音》,阿尔敏·莱希 - 上海,2024年10月25日 - 12月28日 ? 岩村远 - 致谢艺术家与阿尔敏·莱希,摄影:Alessandro Wang文丨大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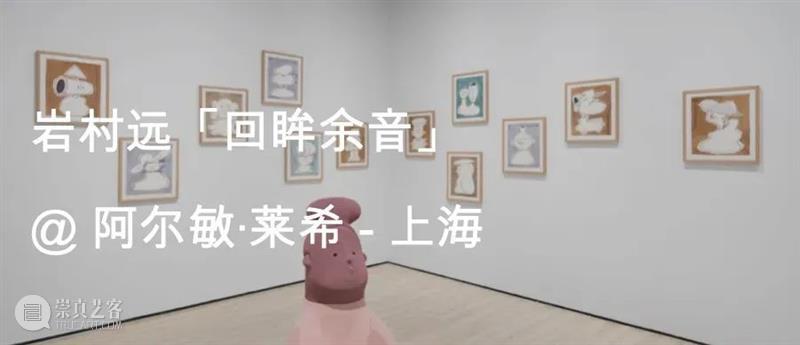
阿尔敏·莱希(巴黎 | 布鲁塞尔 | 伦敦 | 纽约 | 上海 | 摩纳哥)
于1997年创立,现代理众多国际上重要的著名和新晋艺术家,并致力于探索现代与当代艺术之间的联系。同时,阿尔敏·莱希也是阿尔敏与伯纳德·毕加索基金会(FABA)的两位创始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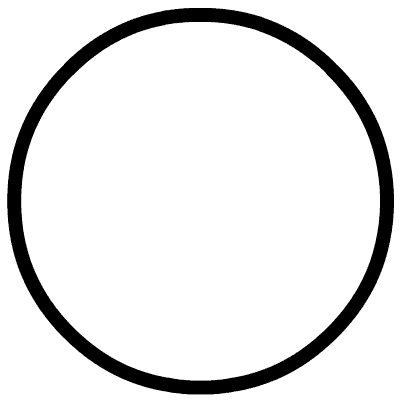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flexible[0].text}}


Find Your Art
{{pingfen1}}.{{pingfen2}}
吧唧吧唧
加载更多
已展示全部
{{layerTitle}}
使用微信扫一扫进入手机版留言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长按识别二维码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item}}
编辑
{{btntext}}
继续上滑切换下一篇文章
提示
是否置顶评论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取消置顶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删除评论
取消
确定
登录提示
还未登录崇真艺客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立即登录
跳过
注册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