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7日至2025年2月15日,上海当代艺术馆威尼斯双年展“镜中行旅”主题展览,继意大利威尼斯首站后,在上海以崭新姿态启幕中国之行。
本次展览中,作为中国较早涉足装置与影像媒介的代表艺术家,施勇带来了大型钢制装置《幸福250-A》,以及霓虹灯装置《三百个字》和《我的身体归你管。不!我的身体归你管》。
从霓虹灯到摩托车,从语言的碎片到物品的切割,施勇通过这些作品编织了一个共时性的艺术系统。在材料、语言与物品的交织与重构中,他深入探讨了现代城市、历史与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作为20世纪的产物,霓虹灯和摩托车看似象征着某种“旧时代”的符号,它们同时又具备一种鲜明的“城市性”。在施勇的创作中,霓虹灯与摩托车与“在地性”的语境路径建立链接。施勇选择霓虹灯作为创作媒介,是因为它“撩拔欲望的幻觉性”与“隐藏在幻觉性背后的脆弱性”。这种闪烁的光源,勾起了人们对欲望和虚幻的渴望,但其背后那种不稳定性和短暂性也让人感受到它的脆弱。霓虹灯象征了现代都市中对欲望的不断追逐与空洞的满足,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力与虚幻。
与此同时,施勇选择以“幸福250”摩托车作为创作的母题,将这件物品重置于全新语境:“选择一辆产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品牌的‘幸福250’摩托车,以历史的视角来对应今天的语境是作品的用意所在。”这辆摩托车承载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印记,它是那个时代都市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工业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幸福250-A》(局部)
施勇强调:“通过对其标准化的切割与一体化的排列,两种不同语境之间的现实张力就被瞬间促成了。”在作品中,施勇通过对霓虹灯和摩托车的切割与重新排列,巧妙地打破了时间的界限,使得历史的象征与现代的元素能够在同一空间中碰撞、交织。这种切割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重构,更是对时间和社会的间接干预。通过这种方式,施勇让观众在视觉上感受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以及这些历史符号如何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意义和层次:“我作品的出发点均源自周遭的现实。‘干扰’作为一个介入性的动词,它们是可以用来搅乱甚至瓦解一切既定权力语法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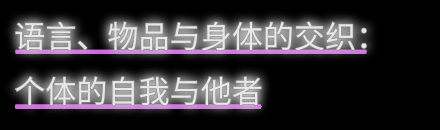
施勇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的切割与重组,它们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身体归你管。不!我的身体归你管》中,霓虹灯被用作表达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施勇通过霓虹灯的不断亮暗与变换,构建了一种循环否定与自我认同丧失的语法结构。他借此探讨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丧失自主性:“身体的自主性是如何在不断的否定中遗失掉了自我的判断与认同的。”通过这种编程与反复,施勇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持续的语言与思想上的冲击,使得观众在体验作品时,产生了对自我认同与社会规训的深刻反思。

《我的身体归你管。不!我的身体归你管》
而在《三百个字》这一作品中,施勇将整个叙事结构给完全打散了,使语言成为迷失的工具:“重要的不是300个字的文字谜底,它们早就以匮名的形式迷失在了城市之中。”这是施勇对语言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文字不再只是沟通的工具,而是一个充满迷失与失序的符号,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如何在信息过载中迷失自我。而同时,“创作者既是作为无法规避的被切割的一份子,但同时被切割的身体感知也暗藏着作为个体意识(被剔除的非标准化物件)用于逃逸与抵抗的那种潜在的能量。”

《三百个字》
这些作品中的各类元素,形成了一条隐性的传递链,从语言到物品,再到人的身体,最终汇聚成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和“他者”之间深刻关系的探讨。施勇通过对日常物品和语言的重构,打破了这些物品和符号的固定意义,让它们在观众眼中获得新的诠释空间。这些作品不仅是视觉上的干预,更是对社会结构、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思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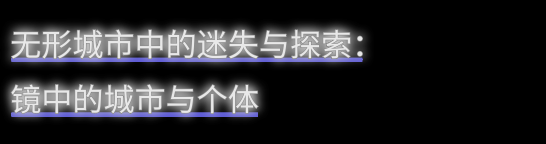
关于本次展览主题“镜中行旅”,施勇如此诠释:“卡尔维诺式空间叙事结构的本次‘镜中行旅’主题展,有意识地去预埋了从威尼斯到上海的这一‘无形之城’意象转换的可能性要件:借助旅者的视角与观者的自我编辑的想象来调度与激活城市的无形魅力。”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它的面貌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人眼中不断变化。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艺术家,施勇在作品中融入了对这座城市的深刻思考。他同时表示:“每个外来者对这座‘无形之城’没有相同的答案,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种“无形之城”的意象,正是施勇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这种流动与变幻的特性,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施勇作品中不断被“重构”的对象——“这座城市才让我们从自身出发,将其不断地置换与组装。”其代表作《今日上海新形象计划——请你选择最好的》与本次展出的霓虹灯文字作品,即展示了个体如何在这座不断变化、无固定形态的城市中迷失与探索。
于镜中行旅,城市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定位,它成为了个体心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镜像。在这座充满流动性和多重视角的“无形之城”中,个体的存在仿佛在镜中倒影,既是自我认同的探寻,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回应与反思。施勇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与符号,让观众在历史与现代的交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验在迷失与自我发现之间的复杂张力。每一块被切割的机械碎片,每一行闪烁的霓虹文字,都提醒着我们,城市不仅是一片空间,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反思的灵魂空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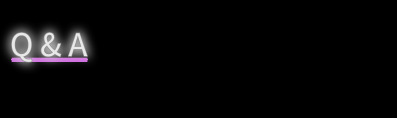
MoCA:在《幸福 250-A》中,摩托车被切割成标准化的6x6x6厘米模块。这个精确的模数设计背后是否象征着某种社会或心理上的“切割”行为?
施:我总是将表达的对象之物(想象之物与日常之物)视为另一种肉身。作为身体感知的一种隐喻,它们更像是社会归训化的产物。被标准化与被工具化是它们的不可挽回的归处。
MoCA:切割之后,模块排列成“候选之物”,而扭曲的基座则成为了支配者。这是有选择的排列方式吗?你是如何看待“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创作者在其中的身份是什么?
施:在这里,“选择”成为了“切割”语法中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主语。被切割的“候选之物”如同产品被区分出标准与非标准。非标准的被踢除,以用来确保标准化、一体化的产品被权力所支配。而创作者既是作为无法规避的被切割的一份子,但同时被切割的身体感知也暗藏着作为个体意识(被剔除的非标准化物件)用于逃逸与抵抗的那种潜在的能量。
MoCA:《三百个字》以倒置的霓虹灯文字组合形成了破碎的阅读体验,似乎想要冲破语言限制对个体内心的一种无形“规训”。谜底真的存在吗?
施:重要的不是300个字的文字谜底,它们早就以匱名的形式迷失在了城市之中而不知所踪。重要的是如迷宫般的城市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无止境的探寻与编织的可能性:时间、空间、事件、记忆、想象以及虚构在其中无休止地交替,反转,错置,填充与组装......
MoCA:在《我的身体 归你管。不!我的身体 归你管》中,霓虹灯的亮暗转换让观众的理解发生变化。这种视觉递进是否希望观众对“身体”和“主权”进行重新思考?
施:一种在循环中不断否定不断更改的语法句式。利用霓虹灯可编程及标语性的特质,将它们纳入到一个关于意识形态控制论的话语中去感受与探究:身体的自主性是如何在不断的否定中遗失掉了自我的判断与认同的。不断的重复与反转让人迷失,让人无所适从。
MoCA:你的作品有一种“干预”特质,比如对物体的切割、对语言的重构。这种特质是否来源于你对社会或现实环境的观察?
施:这是肯定的。我作品的出发点均源自周遭的现实。“干扰”作为一个介入性的动词,它们是可以用来搅乱甚至瓦解一切既定权力语法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它们却又可能是一股至暗的能量。因此,当不同面向的“干扰”介入到文字与装置的语法中去的那一刻,作品内在的那种不确定的能量便被埋下了被激活的可能性。
MoCA:本次展出的三件作品横跨了十年之久。从《三百个字》到《幸福 250-A》,作品似乎有一种从“语言控制”向“物理支配”过渡的过程,这些主题在不同时间点上是否反映了您对自我与城市关系的不同关注?
施:我从未有意从“语言控制”向“物理支配”过渡的方式来推进我的艺术创作。我更喜欢以共时性的方式来编织我的作品系统。换言之,只要它们更具语境的针对性,那么,“语言控制”也好,“物理支配”也罢,都是可以加以运用的。不过最近,我似乎特别感兴趣于在不同时间节点上来重新审视同样的作品在同样的城市空间中又会发生什么新的可能性。
MoCA:作为中国较早运用装置和影像媒介的代表艺术家,你如何理解城市在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带来的影响?
施:我作品的思考与推进,肯定与城市息息相关,它关联着我的一切:日常与非日常,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过往充满想象与虚构的历史与记忆,都影响着我作品的方方面面。
当作品跨越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展出时,我们应该重新去找寻已有的作品如何与“在地性”的语境路径相链接,从而重新激活出作品的新的上下文关系。
MoCA:作为艺术家,同时也是艺术从业者、收藏家,你对本次展览的观看感受?有什么特别留意的作品或展陈设计?
施:一次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秘密之旅。展陈空间与作品关系密度上的把控以及作品之间的情绪关联与组织值得肯定的。二楼展区中人形师组合“屏中市”的装置《屏中市第三精神卫生中心》,比较有印象。那是一组彼此分隔又彼此关联的屋形剧场:散落在不同房间的语焉不详的小人偶,他们被囚禁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之下,处处弥漫着大卫-林奇似的诡异气息,像是不小心你会被落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梦魇之中。另外还有在三楼展区末端的张赢的《异化星系运转系统》,几乎与我那件被放置于展厅入口处的《幸福250-A》有着异曲同工般的针对性表述。一种被操纵被归训下的无时无刻又无处不在的个体命运。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作品被按排在了起始与末尾,它们是故意被这样按排的吗?它们像是在暗示着什么……

- 关于艺术家 -

施勇作为中国较早从事装置与影像媒介的代表人物之一,自1993年起,他的作品就在国内外被广泛展出。早期创作致力于揭示现实内部的意识形态;九十年代开始关注改革开放神话下的当代上海的转型概念,继而引向更宏观的全球化,消费文化等层面。2006年,从作品“2007没有卡塞尔文献展”始,施勇将质疑的目光落实于艺术界本身,思考如何通过“搁置”创作来予以抵抗。2015年个展“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既是之前创作的延续,又传达了其未来意图在表面“抽象”之下展开对于“控制”的反思与实践。
-
Author: Kangxin
Designer: Tianqi
Mo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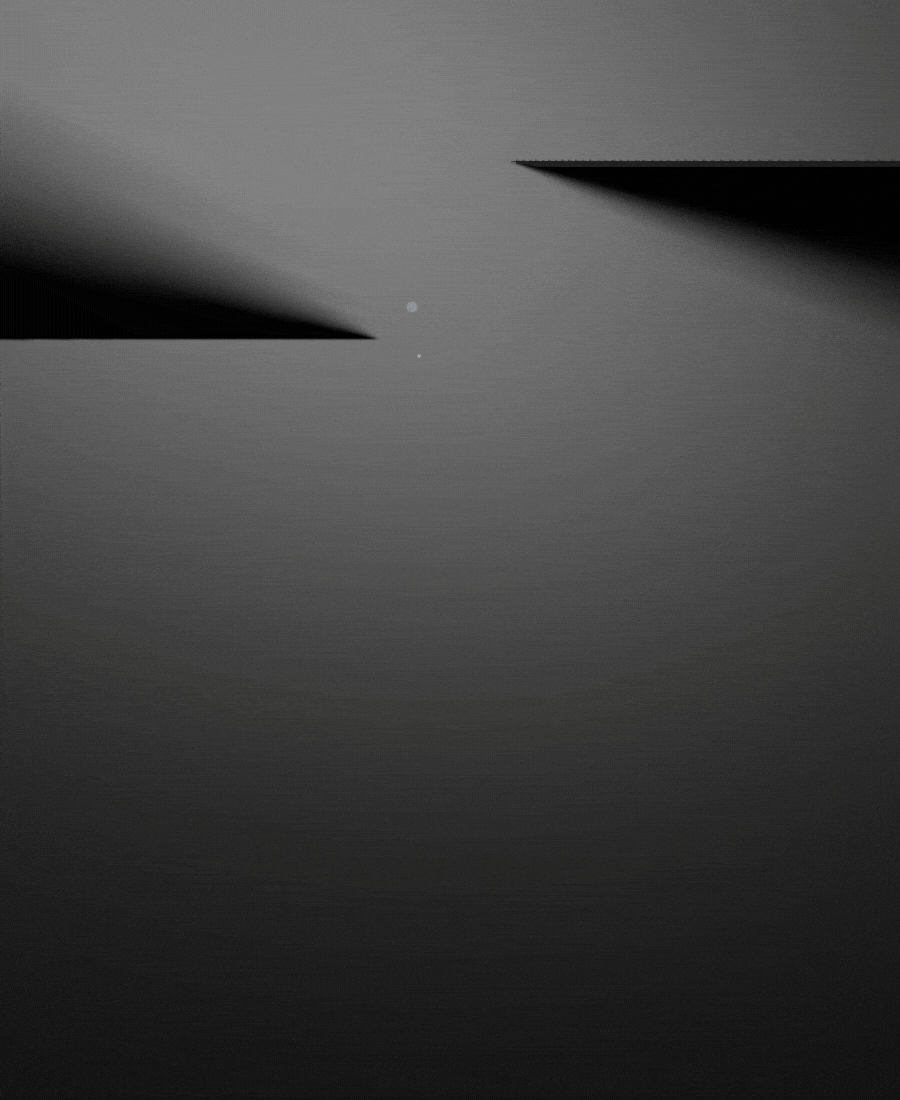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